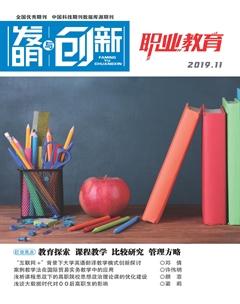文化詩學與歷史書寫
喻紅
摘 要: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的提出是新歷史主義的延伸,它把文學文本納入歷史視野里進行研究,通過社會、歷史的研究來對人性的完善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關鍵詞:文化詩學;詩學;歷史
文化詩學緣起于美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的新歷史主義“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研究,它徹底終結了持續半個多世紀不問社會歷史的文學“內部研究”,是一種關注社會文化語境、歷史語境與文學文本之間關系的實踐性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風潮盛行之時,在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影響擴大的時候,“文化詩學”理論由童慶炳教授提出,他反對“日常生活審美化”,指出“這只是欲望的宣泄”。他提出文學的最終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童慶炳先生還認為:“文化詩學”是要求把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與文化意義的揭示聯系起來,在文學研究和批評中通過對文本的細讀揭示出現實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終追求現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發展[1]。劉慶璋教授也指出:“‘文化詩學在‘詩學前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這一理論的人文內核,或者說,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詩學之魂。”[2]從提出之日開始,“文化詩學”與以往形式主義的“內部研究”不同,轉向了以文學“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式。正是由于文化與審美詩學的結合,才使得文學研究更具有人文情懷,才能發出在歷史語境中的文本意義的追問。
“文化詩學”將文化與詩意融合,注重在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學文本與社會文本、歷史文本的研究,從歷史的文獻中提煉出當前社會需要的人文精神,借古喻今。可以說,它是在學科邊界逐漸模糊、人文精神日漸缺失的語境下產生的,意在挖掘人性如何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得到發展和完善。所以文化詩學研究就是文學文本片段放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里的文學研究[3]。
對詩意的理解,仁者見仁。其實詩意并非僅是指詩情畫意;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從中提煉出超越的人類精神,追求人性的完善和人的發展。文化詩學是以詩意為核心,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早就提出了“人詩意地棲居在此大地之上”。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用“詩意地棲居”來表達他對人類技術性棲居的深度關懷。
“文化詩學”是對文學的另一種審美形式。它將文學文本與社會文本相結合,研究的是“文本中的文化”,并從文學作品中提煉出當前社會缺失的文化內涵,激活傳統,重構人文性;二是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其中具有鮮活文學性的文本,關注現實[4]。
從20世紀80年代最早被提出之時,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即與文學的政治功能論密切聯系,主要的學者認為文化詩學從文學的內部和外部共同發力,一是將文學放置于社會文化背景下進行文本分析,即文學作品中文本化的社會歷史背景,關注宏大歷史敘事中的歷史記憶,尤其是“個體視角和歷史經驗的主體意識”。二是把文學視為政治權力的博弈場地,用重構、抑制、顛覆等具有極強政治色彩的詞來進行話語研究[5]。
從格林布拉特教授提出新歷史主義之時,即投入到文學文本的歷史書寫研究中。他在自己對莎士比亞戲劇的研究中,就致力于將歷史與文學構成互涵互構的關系,搭建起文學審美與歷史之間的橋梁。在《回聲與驚嘆》中,他明確指出:“不參與的、 不作判斷的、 不將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的寫作是無任何價值的”。[6]也就是說,文學的敘述與歷史是不可分割,其敘述話語其實包含文學作者對于歷史和現在的態度和看法。
每一分每一秒形成的歷史都是人類活動軌跡和思想的組合。時間涵蓋了過去、現在和未來,而在已經過去的時間里形成的就是歷史。人類群體和個體的行為、思維軌跡都會成為影響未來的因素,構成人類群體或個體未來選擇和做出抉擇的前提。而所有這些活動軌跡和思想就形成了人所生存的環境,即風土人情、社會習俗、宗教信仰、哲學、文學等。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些環境因素亦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歷史與文學從來就是相互交融的兩個領域,歷史的敘事話語及敘事策略往往會影響文學寫作,而文學的寫作也會成為歷史敘事和策略的依托。歷史,無論是書寫的或是口頭的,作為人類的記憶,都會被引用從而進入文學的境域,關注歷史與當下語境的融合,和歷史對當前社會的影響。
對于這個在后現代主義之后出現的歷史記憶問題,主要分為體現群體意識的集體記憶和側重主體意志的個體記憶。無論集體記憶或個體記憶,都從后現代理論出發對歷史語境、歷史意義的建構。但是批評家們似乎開始不太執著于回溯歷史語境、建構歷史意義和探尋歷史真相的傳統,而是轉向以往的被遮蔽的個體視角和主體意識。而作為意義結構的歷史記憶是“我們的文化借此再現真實的形式”。[7]因此,具有重構意義的歷史記憶也逐漸在凸顯個體意識、在群體記憶中尋求個體視角中找到指向。
歷史記憶往往代表的是歷史主體的意識形態和闡釋話語,同時也將歷史主體對于歷史記憶的重塑過程進行呈現。隨著后現代主義的介入,在應對主流強勢文化的沖擊下,代表弱勢力量的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開始了各種“重寫歷史”的思潮。這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力量轉向了個體經驗和群體意識,建構一種文化認同的身份政治,以改變主流話語的統治地位[8]。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黑人女性文學就是在主流白人強勢話語沖擊下黑人女性發出的對自我身份、黑人歷史探尋的吶喊。其中的黑人女性歷史記憶是瓦解白人主流權力話語和男性父權主義的有力武器。黑人女作家們從白人主流文學和黑人男性文學的夾縫中,找到缺失的黑人女性敘事話語,從中剝離出其歷史以傳遞出作為弱勢群體的個體意愿。
對于歷史研究來說非常重要的文獻檔案無疑被視為研究歷史的權威;而在文學范圍里,這些最具有權威性的歷史檔案不一定具有真正文學審美價值,因為它們主要體現的是主流視角[9]。歷史記憶充滿了時間和空間的場域,其中不僅有符合大眾的歷史記憶,同時也有處于邊緣地位的個體視角。而文學文本的個體歷史視角為歷史記憶提供了闡釋模式和邊界。所以很多文學文本都會關注“江湖野史的邊緣視角”。這是在眾多文獻檔案中讀者無法找到的視角和闡釋方式。正如格林布拉特所指出的,“逸聞軼事能夠開放歷史,或者將其拋在一邊,因此文學文本總能夠找到切入的新基點”,也就是說,逸聞軼事能夠給讀者帶來新的解讀和闡釋[10]。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為文學視野打開了歷史意識和視角,同時歷史意識也給文學解讀帶來更新的闡釋形式和方式。
參考文獻
[1] 童慶炳.文化詩學:文學理論的新格局[J].東方叢刊,2006(1):30-37.
[2] 劉慶璋.文化詩學學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國第一次文化詩學學術研討會[J].文史哲,2001(3):60-62.
[3][4] 李圣傳.文化與詩學的互構:“文化詩學”與“文化研究”之辯[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12(1):73-79.
[5] 岑雪葦. 權利話語分析與文化詩學的政治[J].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371-376.
[6] 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7] Hans Kellner.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M].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8][9] 王進.文化詩學視域中的“歷史記憶”問題考辨[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52-56.
[10] Catherine Gallagher&Stephen Greenblatt.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