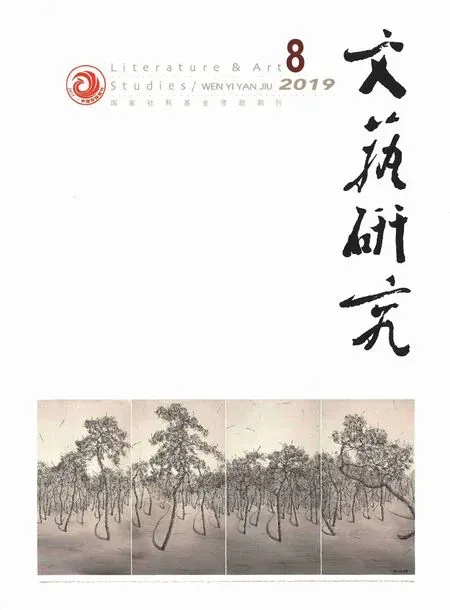革命文藝的“形式邏輯”
——論延安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問題
周維東
引 言
延安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是史學界與文學界共同關注的老話題,各自生產出系列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綜合兩個領域的研究結論,會發現學科差異造成了極為不同的歷史認知。簡單說來,史學研究借助“民族形式”論爭,更關注延安政治文化變遷的內在邏輯①;文學研究則側重考察新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②。同一研究對象因為學科差別呈現出不同的認知結果,既無可厚非,也有值得思考的空間。如楊奎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一文中,將“民族形式”論爭置于共產主義運動民族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整體背景下來理解,發現20世紀30年代末中國革命與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主義”的根本沖突③,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民族形式”話題的動機問題。此后,不少學者用更詳實的史料說明,在這一討論的背后,黨內出現過革命路線的討論和思想斗爭,強化了“民族形式”討論背后具有政治因素的結論。但限于研究范圍,這些研究沒有說明這一討論最終發展到文藝領域的根本原因。就文學研究而言,“民族形式”固然是新文學發展中的一般問題,但政治介入其中的原委也沒有澄清。文學界關于“民族形式”論爭的研究成果頗豐,汪暉曾將之概括為以下問題:“關于如何評價‘五四’文學運動,如何在民族戰爭的背景下重新審視‘五四’所確立的新/舊、現代/傳統、都市/鄉村的二元對立關系,如何處理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和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所確立起來的階級論的文藝觀,如何在語言和形式上具體理解地方、民族和世界的關系,等等。”④這些問題構成了“民族形式”論爭過程中的問題譜系,基本可以概括為“五四”之后新文化和新文學面臨的種種問題。雖然包括汪暉在內的很多作者也注意到這場論爭的背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關于這種政治背景與文藝問題結合的解釋依然顯得模糊,如汪暉給出的結論為“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中國的文化同一性問題”⑤,這只能說是在理論上找到了問題的根源,并沒有從史實角度找到二者結合的必然性,從而讓理論歷史化為具體問題。
實際上,如果完整審視歷史上的“民族形式”論爭,它應該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民族形式”討論的政治背景,這也是此前歷史學界深入討論的問題,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背景下“民族化”思想出現的原因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具體表現;第二,“民族形式”與新文化建設的相關問題,這也是此前文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即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現代性國家,如何解決現代化與民族化融合的問題;第三,作為政治話語的“民族形式”為何要滲透到文藝界的問題。關于這些問題,“民族形式”論爭進入文藝界的結果有較多討論,如賀桂梅的《“民族形式”問題與中國當代文學史(1940—70年代)的理論重構》便通過“民族形式”討論的結果,重新認識“中國”的政治文化內涵,進而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化提出自己的理論構想⑥。然而對于“民族形式”進入文藝界的動因問題,研究界往往一筆帶過,似乎是不必探討的常識,但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民族形式”從政治領域進入文藝領域,既包含一般理論問題,也包含更為具體的歷史淵源。這個問題的意義在于,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發起的“民族形式”討論,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文化領域,都不僅針對新文化建設中的一般問題,還有更具體的現實訴求。因此,討論“民族形式”論爭的結果,延安文藝的形式探索并不代表“民族形式”討論的完成,由延安文藝向當代文藝轉變的過程中,依然有許多理論問題值得探討。
本文進行討論的切入點,是革命文藝中的“形式”問題,焦點在于“形式”如何在革命文藝中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進而說明延安“民族形式”論爭進入文藝界的必然性。應該說,文藝形式常常不僅是文藝內部的問題,在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它往往成為爭論焦點,如詩歌的形式變革等。革命文藝關于形式的爭論的焦點不是“文藝”,而是“革命”,即如何通過文藝形式展示“革命”的內涵,為“革命”賦予一個全新的形象。這也是20世紀30年代“無產階級文學”興起過程中,創作方法、文學語言、形式選擇等問題被不斷拋向前臺的原因。然而,如果說早期革命文藝的形式討論,主要是為革命塑形,那么蘇區文藝及之后的延安文藝,則兼具為革命塑形和為具體革命工作服務的功能。因此,革命蘊含的變革性與實用性就發生了內在沖突。為了表現革命的引導性,革命文藝需要具有讓人耳目一新的形式,而為了凝聚更廣大的革命力量,革命文藝的形式又必須尊重傳統文藝的特點,如何解決這一沖突成為革命理論家必須突破的難題。由此視角審視,延安“民族形式”討論不僅針對新文學發展中的一般問題,更是革命的文藝和理論建構中必須克服的難題。探討“民族形式”背后的革命邏輯,有助于學界理清“五四”新文藝、延安文藝和當代文藝的內在關聯,更可以推動革命文藝的研究朝縱深發展。
一、蘇區時期的“新”“舊”問題
探討延安時期的“民族形式”論爭,需要溯源革命文藝中出現的舊形式利用問題。“民族形式”討論的根源,可以理解為如何徹底解決舊形式在新文學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在革命文藝中的合法性問題。如果回顧蘇區時期的文藝發展狀況,除“稚嫩”這一普遍特征外,“新”與“舊”的并呈也是十分明顯的特點,蘇區文藝最盛行的兩種形式——歌謠和戲劇,前者帶有“舊”的色彩,后者則完完全全是現代藝術形式。
蘇區文藝的發生,與同時期國統區的左翼文藝思潮并無太多關聯,反而與革命實踐有更加直接的聯系。學界普遍將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視為蘇區文藝發展中的重要會議,就可看出蘇區文藝的這種特點。該會決議案將“紅軍的宣傳工作”作為紅軍發展的“第一個重大工作”⑦,作為宣傳工作的補充,歌謠、戲劇等藝術形式得到重視,相應的文藝組織得以建立⑧,為蘇區文藝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為“宣傳”而發展起來的文藝,“新”與“舊”并舉并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在革命最艱苦的時期,“效果”一定是首要考慮的因素,相對于在上海的左翼文藝,蘇區文藝并不避“舊”。在蘇區《俱樂部綱要》中,要求音樂歌唱方面收集本地民歌,編制山歌或練習中國樂器(鑼鼓、“板笙笛”、胡琴等)編成音樂隊;表演方面可以采用說大鼓書,說故事或者配上簡單的音樂方式以至最簡單的化裝表演⑨。這樣的文藝發展邏輯,在蘇區的文藝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
革命工作必須務實,蘇維埃又是一個新生事物,它必須通過具體的形式為普通民眾樹立清晰形象,“紅色戲劇”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歷史上的蘇區多處于文化相對落后的偏僻鄉村,從務實的角度考慮,舊戲的傳播效果必然勝過現代話劇,但蘇區“紅色戲劇”多采用話劇形式。此外,蘇區很多文藝節目,如海軍舞、兒童舞、烏克蘭舞等,直接來自蘇聯,與蘇區群眾的接受習慣有相當距離。當然,如果回到蘇區文藝的具體語境,“紅色戲劇”并非沒有務實的考慮。首先,蘇區的“紅色戲劇”并沒有太高的藝術性,演出的形式極其簡單。如蘇區反映第三次“反圍剿”的戲劇《廬山之雪》,由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編劇,羅瑞卿擔任導演,采用“兵演兵,將演將”的方式,除敵方陣營由羅瑞卿演蔣介石、童小鵬演宋美齡、李卓然演德國顧問外,軍團政委聶榮臻演紅軍政委,軍團長林彪演紅軍司令員,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演紅軍政治部主任⑩。演出形式的自由可見一斑,相較于改編一個舊戲來說,成本也要低很多。其次,對于很多基層紅軍宣傳人員來說,“舊形式”利用所要求的技能遠高于話劇,如果沒有充足的文藝人才儲備,利用“舊形式”常常可望而不可即。引入蘇聯舞蹈也有同樣的考慮,相比創造一種新型的藝術形式,舶來無疑是一種成本最低的方式。實際上,革命文藝中舊戲改造較為成功的作品,到延安文藝后期才大量出現,那時邊區文藝人才儲備充足,物質條件也有相當大的改善。但即便如此,蘇區文藝并非沒有“形式”的考慮,無論是歌謠還是戲劇,蘇區文藝都嚴格遵循了革命文藝的生產邏輯。
蘇區時期《革命歌謠選集》的編選者在“編完之后”中道出了對“革命歌謠”的認識:
有一些同志,保持著文學上貴族主義的偏見,表示輕視大眾愛唱的歌謠。我們要說:我們用不著像酒鬼迷醉酒杯那樣,迷戀著玫瑰色的美麗詩詞,我們需要運用一切舊的技巧,那些為大眾所能通曉的一切技巧,作我們的階級斗爭的武器,它的形式就是舊的,它的內容卻是革命的,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偉大的藝術,應該為我們所歡迎所支持。?
從實踐的角度,蘇區革命歌謠的產生很多是出于無奈,然而一旦進入理論層面,左翼文藝理論就成了主導話語形式,其中的核心詞語,如“大眾”“階級斗爭”“革命”“貴族主義”等,在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中也大量出現。其實,純粹從宣傳的角度,革命歌謠依然可以獲得存在的合法性,但這樣的思維邏輯只能出現在革命文件當中,還不能成為革命文藝理論所包容的對象,這不能不說是蘇區文藝理論建設的缺陷。
蘇區戲劇發展中對舊戲的抵制和批判,也讓我們看到此時戲劇建設的一些細節。如因為一個舊戲班在瑞金演出舊戲,《紅色中華》曾刊登一則號召抵制舊戲演出的消息:
同志們,戲劇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在這勝利的革命戰爭交戰時期,一切利益要服從戰爭,不但不□□□□□□戲,□在赤化了的□□上面,反而□□□公開散布封建階級意識。我們應該大踏步向前開展蘇維埃文化運動,應該努力創造工農自己的藝術,動員群眾來徹底消滅封建殘余!這次上中鄉演封建戲,北郊的領導機關是要負責的,紅校政藝部正在通知瑞金縣委,要縣委去調查和制止這些封建殘余的活動!(方框為原文不清晰之處——引者注)?
如果僅僅說很多舊戲在內容上存在宣傳封建主義的弊端,并沒有太多問題,但將舊戲與“蘇維埃文化運動”對立,將其完全視為“封建殘余”并不太準確,如在延安文藝中,通過改造平劇、郿鄠、秦腔等舊劇種,很多作品都成為“工農自己的文藝”,舊戲與蘇維埃文化之間并不存在格格不入的矛盾。這種情況只能說明,在蘇區文藝運動中,理論創新是個“短板”,至少在“實踐”和“觀念”兩個層面,兩套話語無法很好兼容。如在實踐層面,舊形式常常被紅軍宣傳部門提倡,但真正進入文藝理論話語,似乎又無法對這些文藝形式進行恰當定位。
實際上,蘇區文藝的發展一直在兩個邏輯線條上展開:一個是來自實踐的創新原則,一個是左翼文藝理論建構的“觀念”原則。這種矛盾在蘇區文藝中尚未集中暴露,關鍵是蘇區文藝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相對于之后的延安文藝,更沒有將文藝的宣傳功能發揮到極致,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新”與“舊”在革命文藝中的內在矛盾。
二、延安文藝對舊形式利用的推進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舊形式態度的轉變,出現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之后,由于逐漸破除了“關門主義”的狹隘立場,文藝的傳播功能更受到重視。在這種語境下,人們開始關注舊形式,對其利用的范圍也變得更加廣泛,不僅包括各種民間形式,還包括“五四”時期受到批判的舊文藝。譬如延安戲劇理論家白苓對舊戲持如是看法:
但單就具有新形式新內容的話劇,也是不夠的,為著普遍的宣傳到民間,為著深入到民間起很大的效果,我們不得不盡量利用舊形式新內容的東西來一方面迎合民眾的水準情趣,一方面提高民眾抗敵的政治覺悟。因此我們對于舊形式,不但民歌小調都采用,連舊戲有時也宜選用。這正是目前所需要的手段。?
白苓在這段文字中,不再從“無產文藝”和“大眾文藝”的角度闡述使用舊形式的合理性,而是從“宣傳效果”出發說明采用舊形式的必要性。這在理論立場上較之于以前發生了很大改變,至少在觀念上,提倡者并不堅持教條主義的“無產文藝”標準,而是更注重實際效果和現實功用。其實,延安早期開始提倡舊形式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延安早期關于舊形式利用的討論,看似是抗戰爆發后文藝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開始從“關門主義”“教條主義”向立足實踐的創新、轉變。
不過,雖然在打破“關門主義”之后,務實的文藝觀開始抬頭,但礙于左翼文藝理論的巨大壓力,延安對舊形式的提倡依然顯得異常謹慎。從較早在延安提倡舊形式的理論家徐懋庸的文章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這一點:
我們已有這樣鞏固、這樣強大、這樣有力的工作內容(為著蘇維埃政權,為著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能夠而且應該表現于任何新的和舊的形式上;他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統轄、駕馭一切新的和舊的形式,其目的并不是在于和舊的形式調和,而是要使一切舊的形式,成為共產主義完全的、最后的、堅定的必然勝利之工具。?
徐懋庸在此處轉引了列寧的觀點,可見在他的觀念中,雖然認為舊形式的采用有現實依據,但上升到理論高度又缺少底氣,需要借助革命導師的觀點增加說服力;同時,將舊形式視為“工具”,可見他并沒有將立足實踐的文藝發展方向上升到理論高度。這說明,雖然因抗戰的實際需要,立足實踐需求的文藝觀更受到重視,但在延安還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并形成理論體系。
延安在“民族形式”概念提出之前對舊形式的提倡,都具有一定的自發性,提倡者多為參加過戰地服務和從事具體宣傳工作的文化人。雖然這種聲音還十分微弱,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建立的情況下,背后的力量和發展的潛力不容小視。提倡舊形式背后的實踐立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中一直存在,并且常常成為“制勝法寶”,只是缺乏理論建構的支持,無法在黨內廣泛傳播。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延安文藝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樣的文藝能夠直接而迅速地對政治、軍事斗爭產生最大效力。舊形式在早期延安文藝中受到廣泛重視,完全是邊區革命形勢決定的。1937年4月15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完全建立時,黨中央曾經發布“告全黨同志書”,在談到斗爭方式問題時提及舊形式的利用,認為在革命形勢“從革命戰爭轉到民主的與合法的運動,從同國民黨政府對立轉到同他們合作”的過程中,“還要懂得如何在舊形式中灌輸新內容,舊軀殼中注入新生命。這種新的斗爭方式與工作方式的研究學習與創造,今天成為展開黨的全部工作的需(重)要關鍵”?。這里的“舊形式”和“舊軀殼”,在內容上都超出了文藝的范疇,但道理是一樣的,即用革命的對象和基礎來決定工作的內容和方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利用舊形式,是因為革命的基礎擴大了,“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都成為革命團結的對象,因此革命方式理應更加靈活。而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取的策略來說,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必須發動廣大文化水平低下的農民,必須解決“藝術家底技巧與群眾底欣賞力之對立”?的問題,這也是舊形式的采用能夠形成潮流的重要基礎。
三、“土”“洋”問題的出現
1938年,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提出文藝隊伍的融合問題:“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其中,“亭子間的人”是指延安外來的文藝工作者,“山頂上的人”是指經歷過長征的原蘇區文藝工作者。毛澤東談到兩支隊伍的融合,也側面證明了兩支文藝隊伍之間存在隔閡。這種隔閡在文藝創作中表現為“土”與“洋”的沖突。若干年后,丁玲為《延安文藝叢書》作序,便用這種眼光看待當時的隔閡:
后來,延安又擁來了更多的進步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他們帶來了大后方、大城市的一些中外聞名的文學藝術作品,對推動和提高延安文學藝術工作的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與此同時,有些人就覺得延安原有的文藝太“土”了,有的人認為原來的都是宣傳品,沒有藝術性……?
與毛澤東從政治角度認識文藝問題相比,丁玲關于“土”和“洋”的回憶更具有直觀性和日常生活氣息,兩支文藝隊伍的隔閡在日常生活層面更多表現為文化偏見。如果把這些文化偏見細分一下,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文藝觀念的沖突,表現為“文藝主導”和“革命主導”的矛盾。在革命文學興起的過程中,魯迅曾表達這樣的看法:“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其中反映的問題,正是兩種不同立場的文藝觀的差異。魯迅的立場顯然是尊重文藝自身規律,反對以“革命”的名義隨意棒殺文藝家。不過,對早期倡導革命文藝的文藝家而言,所謂“革命立場”大多具有虛假性,只有部分文藝家直接參與了革命,更多作家并無具體的革命活動,所以魯迅譏諷他們:“只在吹噓同伙的文章,而對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
但在延安時期就不同了,蘇區時期的“革命文藝觀”是在戰爭和斗爭中形成的,有著堅實的現實基礎。譬如朱德在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演講時,就曾提出很多要求,如“一個馬列主義的藝術家應當是一個好的宣傳家”,“我們的藝術作品不是給少數人看的,而是給中國廣大民眾和軍隊看的”等?,都是從革命需要出發的。再如賀龍對話劇《中秋》的批評。《中秋》是魯藝教員劉因學習蘇聯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論體系創作的四幕話劇,描寫淪陷區農民的悲慘生活和戰爭的悲劇,當120師戰斗劇團將其帶回晉西北進行演出時,賀龍在觀看時大怒:“怎么宣傳起失敗主義呀!人都死了,還抗什么戰喲!”?朱德和賀龍雖然不能算是蘇區文藝工作者的代表,但在嚴峻的“反圍剿”語境下成長起來的蘇區文藝,要為軍事斗爭服務是文藝基本理念之一,而這種理念的最佳代言人便是革命將領。朱德和賀龍的觀點不是從“文藝理論”出發,但在戰爭語境下卻也是文藝發展需要關注的維度,可以代表“革命主導”文藝觀的立場。
外來文藝工作者帶來的“洋”,部分原因出自他們對作品藝術性的追求。外來知識分子初到延安時的作品,如丁玲的《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入伍》,周立波的《麻雀》《阿金的病》,何其芳的《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等,從中都能感受到他們的藝術追求。對這部分作家而言,追求藝術并非刻意為之,而是保持文藝創作的慣性,這在文化相對貧瘠的邊區,就演變為一種“洋”。
第二個方面是文化生活習慣的差別,可直觀概括為“都市”與“鄉村”文化習慣的不同。在很多回憶錄中,外來知識分子帶來的“洋”常表現在日常生活層面,是都市文化中產生的文化消費習慣。它們在革命敘事中常常被表述為“小資產階級”習氣,譬如茅盾筆下的魯藝:
月明之下,樹影婆娑,三人五人一小堆一小堆的青年,席地而坐。有靠著一株樹的,也有在游廊的石級上的;有人在低語談心,有人在月光下看書,有人琮琮地彈著曼陀琳,有人在低聲合唱,其聲如微風穿幽篁,悠然而又灑然。漸漸地合唱者多了,從宿舍里也傳出了歌曲的旋律,于是突然,男中音、女高音,一齊迸發,曼陀琳以外又加進了小提琴和簫管,錯落回旋。?
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除興趣愛好與眾不同外,很多外來知識分子在行為上也特立獨行,這是新文化深入人心后出現的積極效果,但在彌漫著軍事氣息的邊區就顯得格格不入。此外,這些外來知識分子喜歡西洋美術、音樂,與樸實的邊區工農兵就產生了距離,構成了所謂的“洋”。
第三個方面為文化發展方式的不同,表現為“學院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差別。外來文化人大多接受過一定程度的現代學校教育,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創新,注重專業人才的技能培養,但政治性和實用性并非考慮問題的首要出發點。從根本上說,邊區并不排斥現代學院教育,魯藝及其一系列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成立都說明了這個問題,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迫于現實常常更注重實踐。譬如在魯藝建立之初,毛澤東就號召魯藝師生走出“小觀園”到“大觀園”里去,他在演講中說:“現在你們的‘大觀園’是全中國,你們這些青年藝術工作者個個都是大觀園中的賈寶玉或林黛玉,要切實地在這個大觀園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們的作品,‘大綱’是全中國,‘小綱’是五臺山。”?可見,在毛澤東心目中,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并非青年學子安身立命的地方,走出校園并投身革命實踐才是最終的目的。但隨著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設立,學院派文化也開始發揮自身的影響力。譬如周立波在魯藝講授的《名著選讀》,僅依據留存下來的講稿,便可知他重點講述了蒙田、司湯達、巴爾扎克以及托爾斯泰等作家,間接涉及賀拉斯、愛默生、弗洛伊德、伊壁鳩魯、霍布斯、柏格森、斯賓塞、哈代、安徒生以及維吉爾等作家和理論家,整個課程估計涉及作家、理論家超過百人,基本是外國文學史的架構,如此淵博的知識自然獲得魯藝學子的歡迎。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來說,外國經典文學在20世紀40年代依然是“學習”的重要對象,“洋”是學院派文化自然散發出來的氣質。
相對于前文所談的“新”“舊”問題,“土”“洋”的背后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偏見:“新”“舊”是新文化運動后形成的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隨著革命文學的興起,凝固為革命立場的差別;“土”“洋”則是近代國門打開后中西文化之間形成的差異結構,“洋”代表了文化的先進性,“土”則成為落后和保守的象征。如果從革命實踐的角度出發,無論是“新”“舊”或“土”“洋”,都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舊形式的利用和對外來知識分子的吸納,都說明邊區有吸納和利用這些文化資源的意圖。但文化等級卻成為整合這些資源的障礙,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調解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是消解這些文化等級。
四、“民族形式”討論的展開
其實,新文學(新文化)發展至抗戰時期也遭遇了瓶頸,表現為不能滿足抗戰對文學和文化的需求。在進行戰時動員的過程中,宣傳工作者必須依賴新文學(新文化)之外的舊文學和舊文化。周揚曾經反思:“中國的新文學創作差不多都是歐化的,近幾年來技術的水準的確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時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在技術上優秀的作品的基本讀者,還只限于狹小的知識分子學生的階層。歐化的文字技巧在作者和落后的讀者中間筑起一道障壁。”?宗玨則認為:“(新文學的)一些作家往往忽略了吸收舊文學的傳統中底優秀的描寫方式這些問題,因而有時候在他們所刻畫的人物底思想故事中,大抵缺乏一種深厚的中國人所特有的氣息,和活生生的現實。”?雖然這些反思與“民族形式”討論有若干聯系,但如果沒有新文學在抗戰時期暴露出來的問題,這類質疑很難進入公共視野。而從兩位質疑者討論的問題看,“逐洋”與“求新”恰恰成為問題的焦點。所以不能不說,新文學(新文化)在抗戰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為邊區解決革命文藝中的問題提供了契機。
從舊形式利用問題升華為“民族形式”大討論,表面上看是一種話語策略:與曾作為新文學革命對象的舊形式相比,“民族形式”沒有天然的“原罪”,且在民族戰爭的語境下,它還具有不言自明的合理性——這似乎是為舊形式辯護。實際上,不管在話語層面還是在之后的討論中,“民族形式”都不等同于“舊形式”,其靈活性在于:無論是舊文藝還是新文藝,都不是天然的“民族形式”,但也都可以成為“民族形式”的重要資源。這為“民族形式”的論爭埋下了伏筆,但同時也為建設新的革命文藝的實踐創造了機遇,更重要的是為本土創新的革命思想拓展了理論視野。
延安“民族形式”論爭的這種特點,可以在論爭展開的組織過程中發現端倪。這次論爭是一場有組織的論爭,這既表現在論爭展開的組織過程中,也表現在理論話語的形式上。早期關于“民族形式”討論的文章,不是零散地出現在報刊上形成自然交匯的格局,而是有組織的批量出現的。
在毛澤東提出“民族形式”概念的《論新階段》(1938)發表后,1939年4月16日的《文藝戰線》同時刊出艾思奇的《舊形式利用的基本原則》和陳伯達的《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雜記》兩篇文章。兩位作者都是黨的宣傳部門的領導人,從文章的題目和語氣明顯可知,其目的是釋放信息,在文藝界掀起一場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之后,1939年6月25日的延安《文藝突擊》雜志推出一組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的文章,包括艾思奇《舊形式新問題》、柯仲平《介紹查路條并論創造新的民族歌劇》、楊松《論新文化運動中的兩條路線》、羅思《論美術上的民族形式與抗日內容》以及蕭三《論詩歌的民族形式》等。這幾位作者都是延安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他們參與討論的方式是結合自己所從事的藝術門類,使得“民族形式”的討論開始從政治向學理層面拓展。從幾篇文章的觀點來看,它們都對“民族形式”持認同的立場。在此之后,1939年11月16日,《文藝戰線》開辟“藝術創作者論民族形式問題專輯”,文章包括冼星海《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羅思《論美術上的民族形式與抗日內容》、蕭三《論詩歌的民族形式》、柯仲平《論文藝上的中國民族形式》、何其芳《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以及沙汀的《民族形式問題》等。這組文章與《文藝突擊》上的文章有部分重合,三位新作者也是延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們并不完全贊同“民族形式”,使得這場討論開始有了論爭的味道。不過這種“論爭”被規約在專輯編者的設計中:
下面是一個民族形式問題特輯,專請藝術各部門的幾位創作者執筆的。因為是創作者,從事的部門又不盡同,所以都獻出了各自的心得與獨見。大家的意見,在對文藝上民族形式之建立的積極主張上,是一致的。新文藝過去還民族化、中國化、大眾化得不夠,正因為不夠,所以需要向這方面特別努力,這也是大家所共同承認的。自然,在個別具體問題上,在對新文藝過去成就的評價上,還不免有意見上的若干差異,如在民族化的具體做法上,在對舊形式及其可能利用的限度的估計上。這些問題是需要討論的,更仔細更深入的,這樣才能使民族形式問題的理論更為精密與堅實。?
到了1939年12月,香港舉行了關于“民族形式”討論的座談會,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連續發表了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文章,“民族形式”討論隨即在香港、桂林等地展開。1940年初,重慶《文學月報》同時刊載潘梓年、葛一虹和向林冰的文章,表明延安的“民族形式”論爭開始在重慶等地受到關注,這場討論已擴展到全國范圍。需要注意的是,《大公報》和《文學月報》上的文章,幾乎都提到延安“民族形式”討論的情況,對此的解釋只能是,延安方面有意識將“民族形式”問題推廣到全國進行討論。
如果我們仔細體會延安有組織推出的文章,就會發現這種安排的背后有著非常清晰的理論建構的思路。在毛澤東《論新階段》發表后,艾思奇和陳伯達是最早針對這個報告進行闡述的理論家。從理論建設的角度看待他們的文章,其共同特點之一是非常明確地強調了文藝的傳播功能。艾思奇認為:“舊形式,一般地說,正是民眾的形式,民眾的文藝生活一直到現在都是舊形式的東西,新文藝并沒有深入民間。”?陳伯達則在文中強調:“文藝是精神的力量,但應該并可能,如許多民族的革命歷史所證明了的,變成物質的力量,這就是說,必要文藝真正能感召起千百萬人民起來,必要文藝真正能把握大眾并能為大眾所把握。”?與之前關于舊形式的論述相比,兩人對抗戰中文藝傳播功能的強調更加自信,并從這個立場出發,對新文藝進行了或多或少的批評。此外,兩人都對舊形式與新文藝做出了辯證的解釋,認為強調舊形式并不是否定新文藝,而是對后者的發展。不過,兩文對這個問題的論述還顯得不夠充分,在某種程度上使舊形式、新文藝和“民族形式”的關系變得曖昧不清。
而《文藝突擊》上的一組文章,從不同的藝術門類闡明了舊形式、新文藝和“民族形式”的關系。其大致關系可以概括如下:舊形式并不等于“民族形式”,而是創造“民族形式”的重要基礎;新文藝只能通過“民族形式”才能真正成為民族的新文藝,因此創造“民族形式”是新文藝發展的必經階段。這個關系表面上看沒有太大漏洞,但實際卻認同了一個理論預設:新文藝要發展,必須創造“民族形式”,而創造“民族形式”,就必須研究和采用舊形式。在此處,舊形式的采用既不是抗戰時期的權宜之舉,也不是與新文藝并列發展的另一種藝術形式,而是新文藝向前發展的必然選擇。就這樣,舊形式的研究和采用,在理論上就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但在這組文章里,所有人都沒有討論什么是“民族形式”,而這本是“民族形式”理論是否成立的基礎。從文藝發展的經驗看,“民族形式”只能是歷史選擇的結果,任何藝術形式只要被廣泛接受都有可能成為“民族形式”,它并不在藝術家可以掌控的范圍之內。
在《文藝戰線》上刊出的“藝術創作者論民族形式”專輯中,冼星海、何其芳以及沙汀三人“在對新文藝過去成就的評價上,在對舊形式及其可能利用的限度的估計上”?有不同意見。譬如,冼星海認為“新內容配合舊形式是有點不調和”?;何其芳認為“歐洲的文學比較中國的舊文學和民間文學進步,因此新文學的繼續生長仍然主要地應該吸收這種比較健康,比較新鮮,比較豐富的養分”?;沙汀則“不贊成在文藝價值上把舊形式估價得過高,因為目前民眾的現實生活已經和舊形式當中所表現的有著相當的距離了”?。作為在“五四”運動后成長起來的藝術家,他們堅持新文藝傳統,對舊形式利用的限度給予了充分的估計。但他們的反對意見與認為“民族形式”并不等于舊形式的論爭參與者的觀點并無齟齬,沒有對“民族形式”理論的基礎產生沖擊,因而只是在“如何創造民族形式”上提出了不同意見。
從傳播的效果看,冼星海、何其芳和沙汀的文章其實強化了“民族形式”討論的導向性。雖然,《文藝突擊》上的文章已經開始引導“民族形式”論爭的方向,但由于沒有造成“論爭”的效果,因此無法真正形成旁觀者關注的“焦點”。冼星海、何其芳和沙汀的文章則代表了一大批站在“五四”新文藝傳統的立場上,對“民族形式”持疑慮態度的文藝工作者的意見,他們的參與使“民族形式”討論朝重新評價和認識“五四”新文學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民族形式”論爭發起者的重要目的之一。
“民族形式”論爭對“五四”新文藝的質疑,主要觀點在左翼文化發軔期就曾經出現過,涉及問題包括“歐化”和不夠“大眾化”等問題。不過,作為左翼文藝大眾化理論的一部分,其影響力局限在左翼文化陣營內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下,重新提及這一觀點,其影響就不僅限于某個陣營。與之相適應,舊形式的意義就不再是特定的戰爭背景下的權宜之舉,而是新文藝繼續發展過程中需要充分重視和汲取的源泉。事實也證明如此,隨著“民族形式”論爭從延安拓展到全國文藝界,論爭也朝縱深發展,討論的范圍超越了革命文藝的范疇,成為對新文藝若干年發展的回顧和總結。不過,雖然“民族形式”成為文藝界普遍關心的問題符合延安首倡者的初衷,但當它完全成為新文藝發展經驗的總結后,就成為另一個學術問題,延安“民族形式”論爭已經實現它的初衷并告一段落。
結 語
通過對延安“民族形式”論爭緣起的考察,可以明確,抗戰時期文藝界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至少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革命文藝建設的內部問題,一個是新文學發展中的一般問題。就其在抗戰時期發生的過程看,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沒有革命文藝建設的迫切性,“民族形式”論爭不會首先在延安提出,并成為文化界普遍關注的一個“事件”。
從革命文藝建設的內在邏輯出發,延安“民族形式”論爭并非純學理層面的討論,即如何建構新文藝的“民族形式”,進而對“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和傳統文藝進行重新評價,而是建構革命文藝本土化發展的話語空間,打破革命文藝形成的形式偏見,為革命文藝的民族化奠定基礎。革命文藝形式偏見的形成,始于革命文藝發生的初期,當等級化的革命邏輯進入文藝之后,新、舊文藝形式的等級結構在革命文藝中形成并逐漸固化,這是“民族形式”論爭首先在革命文藝內部發生的緣由。
“民族形式”論爭之后,特別是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成為革命文藝具有標識性的特征,延安文藝對“民族形式”的探索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延安文藝對“民族形式”的探索并不表明對新文藝改造的完成,或者說新文藝已經獲得了它的“民族形式”,因為延安文藝的探索依然只是革命文藝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很多在“整風”中受到批評的作家通過創作具有“民族形式”的作品表明自己的轉變,更說明“民族形式”兼具的革命內涵。革命文藝需要一種較為“激進”的形式,在革命文藝發展初期,各種新形式的倡導都帶有標新立異的特點,“民族形式”的提出表面改變了革命文藝的“激進”特征,實際上依然符合“革命”的邏輯,相對于新文藝已經取得的“正統”地位,“民族形式”具有“再革命”的特點。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抗戰時期國共轄區間的文學互動研究”(批準號:15BZW153)成果。
① 史學界對“民族形式”論爭的探討,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角,代表成果有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3頁)、李建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的視角,代表成果有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兩種視角分別從理論和史實說明,“民族形式”討論是中國共產黨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在理論上的嘗試。
② 文學界對“民族形式”論爭研究成果豐碩,主要集中在思想史和文學史兩個維度,將這場論爭置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發展的整體背景下來認識是較為普遍的視角。代表成果有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討論》(《汪暉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375頁)、石鳳珍《文藝“民族形式”論爭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李松睿《民族形式論爭中的地方性問題》(載《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等。
③ 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論文集》,第72頁。
④⑤ 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討論》,《汪暉自選集》,第342頁,第345頁。
⑥ 賀桂梅:《“民族形式問題”與中國當代文學史(1940—70年代)的理論重構》,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1期。
⑦⑧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65頁,第566頁。
⑨ 《俱樂部綱要》,汪木蘭、鄧家琪編《蘇區文藝運動資料》,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頁。
⑩ 田本相、宋寶珍:《中國百年話劇史述》,遼寧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5頁。
? 《〈革命歌謠選集〉編完以后》,《蘇區文藝運動資料》,第223頁。
?《開展文化戰線上的斗爭——反對瑞金演封建戲》,載《紅色中華》1933年9月27日。
?白苓:《關于戲劇的舊形式與新內容——問題的提起》,載《新中華報》1938年2月10日。
? 徐懋庸:《民間藝術形式的采用》,丁玲主編《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659頁。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斗爭》,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頁。
? 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頁。
? 張振亞:《讀〈邊區自衛軍〉》,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3號,1939年4月16日。
? 毛澤東:《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 丁玲:《〈延安文藝叢書〉總序》,王巨才主編《延安文藝檔案·延安文論·延安文論作品》第40冊,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頁。
?? 魯迅:《三閑集·文藝與革命(并冬芬來信)》,《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第85頁。
?朱德:《三年來華北宣傳戰中的藝術工作——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所作報告的提綱》,《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第1冊,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頁。
? 莫耶、楊子江:《武將率文兵》,《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抗日戰爭時期》第1冊,第327頁。
? 茅盾:《記“魯迅藝術文學院”》,黃鋼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報告文學編》二,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0頁。
?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
? 周揚:《抗戰時期的文學》,載《自由中國》創刊號,1938年4月1日。
?宗玨:《文藝之民族形式問題的展開》,載(香港)《大公報·文藝》1939年12月12日。
??《藝術創作者論民族形式》“編者按”,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
?艾思奇:《舊形式利用的基本原則》,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3號,1939年4月16日。
?陳伯達:《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雜記》,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3號,1939年4月16日。
?冼星海:《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
?何其芳:《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
?沙汀:《民族形式問題》,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