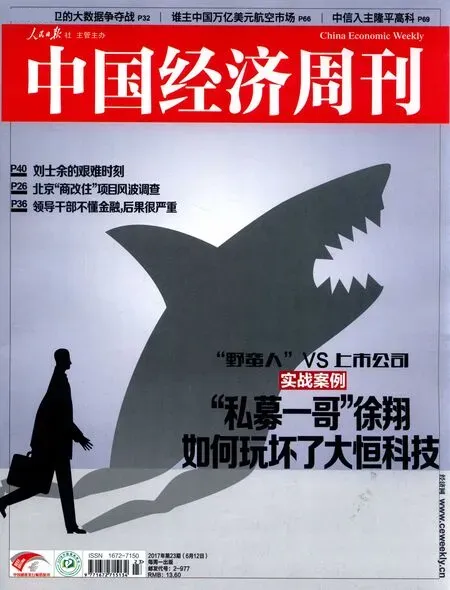社交電商黑馬淘集集之死


淘集集上海總部(資料圖)《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杰 攝
“向伙伴們說聲對不起,這可能是我們最后一條微博。”12月9日,社交電商平臺淘集集通過官方微博發布一則題為“已盡力未盡責”的致供應商、代理、團隊伙伴的公開信,信中提出由于資金未能如期到賬,正式進入破產清算或破產重整的程序。
10月25日,《中國經濟周刊》曾報道淘集集疑似資金鏈斷裂,等待新一輪投資人入場的消息。最終,負債總額預計16億元的淘集集沒有等來投資方“輸血”,迎來的是破產的結局。
員工:重組成功的海報用不上了
根據前述公開信中描述,淘集集曾有過A、B兩個潛在投資人,都是在今年國慶節前后就開始溝通。投資人A是某大型集團公司,B為某PreIPO公司牽頭的基金公司。投資人A一直積極跟進項目,在深入接觸后發現,來滬的供應商鬧得太兇,所以需要觀察一下情況,同時在業務層面展開深度合作幫助公司自救;投資人B已經簽署了投資協議,并接管了公司財務、法務工作(收走所有公章和銀行密鑰),但打款多次延期,超出了公司能承受的最后時限。
那么,在投資人B沒有明確不打款情況下,為什么淘集集忽然宣布并購重組失敗?
淘集集通過前述公開信對此也有回應:其一,在簽完投資協議后,投資人B多次拖延打款時間。其二,11月28日,投資人B實控企業某廣告代理公司申請訴前保全,司法凍結淘集集的支付寶賬戶,直接造成公司貨款退款無法正常支付,工資無法支付,對公司運營造成毀滅性影響。
淘集集創始人張正平在12月8日給員工的信中提到,由于11月28日支付寶賬戶被凍結,即公司所有賬戶已經被凍結,使得11月29日的工資沒有發出,11月社保也無法發出。接下來公司會成立員工善后處理小組。
張正平在信中表示:“遺憾加抱歉的是沒有帶著大家把淘集集做成。”
12月9日,有淘集集員工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工資沒有,各種報銷還欠著呢。前段時間慶祝重組成功的海報都做好了,就等官宣了,這下尷尬了。”
商家:被3份合同深套其中
淘集集破產的消息官宣,點燃了入駐商家的怒火。
“我所在的是六七線城市,通過淘集集賣茶葉是我的副業。10月16日,我赴上海見張正平,他親自接待了各省份代表,細節就不說了。我簽完合同就走了,回到家,上架產品,提報活動,正常發貨。一切仿佛沒發生過,一切又那么漫長。”商戶張先生10月底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說道。
當12月9日記者再一次與張先生聊起淘集集,他對記者說:“兩個月了,我以為我能坦然面對,真到事情敲定,最后一絲希望破滅,我發現我扛不住了,我可以接受上百萬元的虧損,我不是虧不起,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平臺的CEO和他的團隊為什么還能逍遙法外,還能在公開信里說讓我們再支持他們創業?”
張先生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復盤了近半年來與淘集集的“糾葛”。據張先生回顧,淘集集近半年曾出臺過3份合同挽回商家。
第一份合同:平臺真正出現問題應該在是7月份,6月份平臺要求必須簽署一份針對頭部商家的KA(重點客戶)合同,許諾會有更多的流量導向。當時我以為只有為數不多的商家可以簽,后來發現,大家都可以簽。
就這樣淘集集把我們這些入駐的商家變成了一個個“供貨商”,我們有店鋪的經營權、發貨權,但我們沒有店鋪的所有權,類似于自運營。當時是跟青島大漠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淘集集運營主體上海歡獸的分公司,現已改名為“青島鷹漠電子商貿有限公司”)簽訂的這個協議。
這份協議極不平等。如果不簽署,我們將被要求下架所有資源位和所有產品,我們的想法很簡單,覺得入駐平臺賣貨,沒那么復雜,無非就是貨款延遲一些,當時的打款周期是45天,所以就簽了這份協議。
據天眼查顯示,青島鷹漠電子商貿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為宋雅楠,最終受益人為張正平(持股比例達99%)。
第二份合同:一直到10月8日,平臺已經出現“爆雷”的征兆,這個時候已經有很多商家前往淘集集上海總部聚集了解情況。于是,在10月15日淘集集出臺了第二份合同,即兩個月之內完成并購重組,首先支付20%貨款,剩余80%的貨款等公司市值15億美金或者上市以后再償還。一些大的商家不希望平臺倒閉,希望平臺能繼續堅持,因為平臺倒了,那真的就全沒了,在眾多商家的支持下,平臺繼續運轉,打款周期變成了20天。
第三份合同:債轉股,按照淘集集平臺根據自身估值進行轉股,估值5.5億美金,將近40億元人民幣,進行80%的債務轉股。眾多商家也簽署了債轉股協議,轉股價為3.1元每股。
天眼查顯示,淘集集的運營主體為上海歡獸實業有限公司。天眼風險中,自身風險有4條信息,一條為合同糾紛,兩條為專利權糾紛,一條為凍結銀行存款人民幣218萬元或者查封或扣押同等價值的財產。關聯風險有6條,3條為投資企業股權被凍結,1條為子公司經營異常,2條投資企業進行簡易注銷。
此外,天眼查還顯示,淘集集有2位股東,分別為張正平和王蓓珺,有四家分支機構,對外投資6家公司,其中青島鷹漠電子商貿有 限公司、青島萬擊電子商貿有限公司和青島長留電子商貿有限公司即為上文提到的被凍結股權的三家對外投資公司,凍結金額為100萬元人民幣,凍結期限從2019年11月27日至2021年11月26日。
“燒”掉商戶的錢,讓“金主爸爸”滿意?
今年6月,淘集集曾收到過投資方的意向,融資2億美元,可是淘集集方面做好了迎接資方的準備,卻沒想到資方的錢遲遲沒有到賬。
進入7月,由于內外部影響,淘集集銷售業績突然下滑,為了讓“金主爸爸”不要真的“放鴿子”,張正平把時間繼續花在了融資上,策略上選擇繼續虧損獲取用戶。
但A輪融資差不多用完,接下來怎么自救?錢從哪里來?從前述3份合同來看,淘集集打起了商家貨款的主意。
“第一份合同,他將商家應付賬款的周期無限拉長,將本來打給商家的貨款投入營銷,滿減補貼、拉新增活,以換取投資人眼中的增長曲線,我們一夜變成了他們眼中的‘供貨商。第二份合同,為了讓我們繼續支持,合同上縮短了付款周期,但他們實際也沒做到如期支付!”商戶張先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張正平當時說,如果平臺倒了,錢更拿不回來了。我們的利益瞬間被捆綁,很多商戶都迫于無奈簽了,退一萬步而言,將這種做法‘合法化,是不是很缺德?”
一些商戶則控訴:淘集集挪用他們的十幾億貨款去打廣告買流量,將流量引流到已轉至淘集集分公司青島大漠名下的店鋪里,給他們的店鋪賺錢了。
有商戶揣測,張正平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下載量、活躍用戶數、客單價、回購數上去了,投資方的資金自然就會到賬,正好可以彌補所挪用的商家貨款。“我們是商家,不是什么供貨商,我們不是投資,我們這是在賣東西,淘集集只是起到中介周轉作用,為什么一句破產就可以不用負法律責任了?”
諸多商家追問的是:商家店鋪的保證金屬于什么資產?貨款究竟是屬于誰的資產?資金在淘集集賬戶停留的45天賬期內是否涉嫌挪用違規?淘集集平臺可以隨時挪用嗎?用我們的貨款去推廣獲取用戶是否合規呢?
資料顯示, 早于2017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于實施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有關事項的通知》,提出“非銀行支付機構不得挪用、占用客戶備付金,客戶備付金賬戶應開立在人民銀行或符合要求的商業銀行。人民銀行或商業銀行不向非銀行支付機構備付金賬戶計付利息”相關要求,人民銀行決定對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實施集中存管。
“這也就是說,為了保護廣大商戶的合法權益,像淘集集這種作為非銀行支付機構的平臺,凡是涉及到流經自身平臺的客戶的貨款或是備付金,都應當嚴格遵守資金管控的規定,集中存管在第三方監管機構賬戶中,以保障資金安全。如果出現為了支撐平臺自身經營、彌補財務漏洞而進行挪用的情況,確實嚴重違規了。”北京煒衡(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鞠秦儀律師這樣認為。
“跟共享單車的押金也是一樣的道理,只不過留存在共享單車企業內的押金可以持有的期限更長。”一家已經倒閉的共享單車企業管理層這樣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兩者的性質是很雷同的,都是寅吃卯糧,拿著其他人的錢來做噱頭,只不過一個是商家貨款,一個是社會大眾;一個資金額度大,一個資金額度小。小范圍地啟動資金,大范圍地吸納資金,危機之后以一招‘投資人即將進入進行緩解,最后跑路或者破產,留下一地雞毛。”
針對商戶和外界的上述質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聯系了淘集集的有關負責人,對方婉拒采訪,稱“一切以公告為準”。
但公告并沒有就相關問題進行回應。
有投資圈業內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投資人通常會給企業KPI,“比如必須要達到多少用戶量,所以企業一定會去做拉新的動作,不要說燒錢了,買用戶都是很正常的。如果完不成就死定了。”
據淘集集10月31日公告,截至10月23日,“供應商債權人”的簽約比例超51%,而這一比例也正是為了要令意向投資方滿意。
10月28日,淘集集發布公告稱:“收到資方書面TS,簽訂投資意向書。”
不過,所謂的“投資意向書”到底長啥樣,至今是個謎。
專家:供應商獲清償比例恐難樂觀
據網經社“電數寶”監測數據顯示,淘集集APP在蘋果應用商店下載排名曾經一度位列第一,而當下最新排名已在100名外。淘集集的最新版本發布日期停留在2019年12月2日下午2:24:29,這距離其2018年8月上線,過去不到兩年。

淘集集上海總部(資料圖)《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杰 攝
從黑馬到破產,不到兩年時間,淘集集經歷什么?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網絡零售部主任、高級分析師莫岱青指出,淘集集自身問題有三:其一,與競品重合度高,缺核心競爭力;其二,粗暴拉新、回款慢;其三,流量轉化成本高,經營手段“極端” 。
社交電商紅利期已過,進入洗牌期或許是根本原因。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認為,頭部平臺拼多多率先上市后可謂“一枝獨秀、遙遙領先”,加上“百億補貼”“天天領現金”等策略,快速拉高拼購類電商獲客成本。在這種激烈競爭的局面下,中小社交電商自然無以為繼,“叢林法則”導致優勝劣汰。
而從外部環境看,淘集集可謂生不逢時。曹磊分析:第一,經濟大環境下行風險加大市場“恐慌心理”,平臺型電商牽涉商家面廣、數量眾多、涉及金額大,這類創業公司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會“墻倒眾人推”,商家上門討債提現引發“擠兌危機”,加快平臺崩盤破產。第二,資本“寒冬”持續加劇,缺乏新的風險投資“接盤”跟進,加上洽談并購重組中的“大型機構”在簽訂投資意向書后不再做“接盤俠”,淘集集與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失之交臂。
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趙占領認為,一旦啟動破產清算程序,被欠款的供應商通常只是普通債權人,在淘集集支付完稅款、員工工資及補償金、清償完優先債權之后,與其他普通債權一起按照比例清償,具體獲得清償的比例現在難以確定,但肯定很不樂觀。
那么,公司創始人或股東將承擔哪些法律責任?
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延來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依據《公司法》的規定,公司屬于獨立承擔責任的法人組織,公司的債務應該由公司的資產承擔,因為經營不善等原因進入正常破產程序后的公司,債務由公司資產償還,股東僅以其認繳的注冊資本為限承擔有限責任,而無需以全部的身家性命承擔連帶責任。
“從目前的情況看,淘集集是因為正常的商業原因進入到破產程序,在公司股東和創始人沒有將個人財產和公司財產混同或者出現其他明確侵害他人權益等違法行為(例如欺詐)的情況下,股東和創始人是不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也更談不上承擔刑事責任了。”張延來說。
“但如果平臺在明知自身經營狀況已經出現嚴重問題或者已經資不抵債,仍然利用平臺的強勢地位、普通商戶對平臺的信任或者對平臺情況的信息不對稱,妄圖通過拉長賬期等手段來沉淀資金以支撐自身經營或者彌補漏洞,那可能就有詐騙之嫌了。”另一位律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
12月12日,在“淘集集破產追蹤群”中,記者看到,諸多商戶反映淘集集后臺系統已無法登錄,并表示已至公安機關報案。
相關閱讀

編輯:呂江濤 ?lvjiangtao@ceweekly.cn
編審:郭芳
美編:孟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