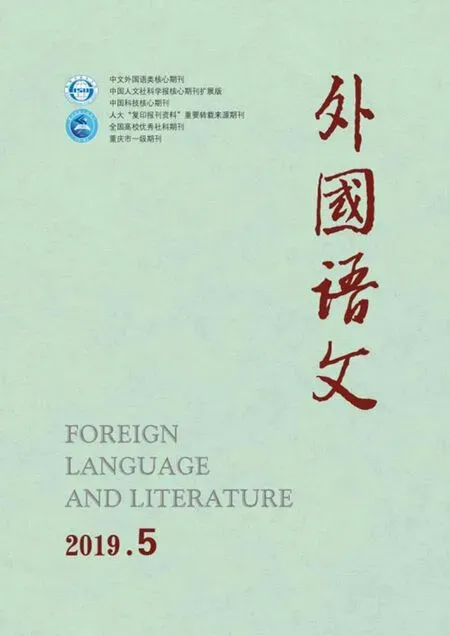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與“二戰”時期的美國
任虎軍
(四川外國語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重慶 400031)
0 引言
在人類歷史上,美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因為它的歷史是從反對歐洲大陸(特別是英國)的各種奴役、迫害和壓迫開始的。17世紀初,當首批英國人離開母國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的時候,他們覺得自己來到了一個“新世界”,一個上帝派他們來到的地方。興奮不已之余,在感謝上帝的同時,他們也痛恨英國政府對他們的統治與束縛。這種痛恨與日俱增,最終促使他們向世界發表了著名的《獨立宣言》,其中寫道:“我們認為這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來平等;上帝賦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追求。”(Baym, 1989: 640)基于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獨立宣言》還寫道:“這些聯合起來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權利成為自由而獨立的州……它們有充分的權力發動戰爭,宣布和平,締結聯盟,發展商業,以及其他獨立州有權做的事情。”(Baym, 1989: 643-644)《獨立宣言》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極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其反復強調的“獨立”“自由”“平等”與“和平”之主張,成為美利堅合眾國團結起來合力反抗英國統治走向獨立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成為美國人建國的理想與生活目標。在美國人看來,“自由”是“上帝賦予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這種“不可剝奪的權利”不僅屬于美國人,而且屬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美國人擺脫英國統治,追求自由,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所以,托馬斯·潘恩在其《常識》中說:“美國的事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類的事業。”(Baym, 1989: 618)
如果說《獨立宣言》為美國追求自由與平等提供了理論依據,圣約翰·德·克利夫科爾的《美國農夫的來信》為美國的自由與平等做了現實宣講:“這兒沒有占有一切的大地主,也沒有一無所有的平民。這兒沒有貴族家庭,沒有宮廷,沒有國王,沒有主教,沒有宗教統治,沒有可見的賦予極少數人的權力,沒有雇傭數千人的大雇主,沒有極其奢侈的享受。富人與窮人之差距沒有歐洲那么大……這兒,人是自由的,就像他應該自由一樣,這種令人歡喜的平等也不像許多其他平等那樣轉瞬即逝。”(Baym, 1989: 559)所以,歐洲人來到北美大陸之后,“一切都使他們再生了。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制度。這兒,他們是變化了的人。”(Baym, 1989: 560)他們不再是歐洲人,而是“一種新人”(Baym, 1989: 561)。在這個由“新人”組成的“新國家”,“很少有人犯罪……他不迫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迫害他”(Baym, 1989: 564)。這個“新國家”有著諸多歐洲無法相比的“誘人之處”,因為“如果你誠實、節儉、勤奮,你就有更大回報——自由與獨立”(Baym, 1989: 567-568)。
無論是《獨立宣言》的理論辯解,還是《美國農夫的來信》的現實宣講,都凸顯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是什么?在美國締造者看來,美國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因為它是“上帝選出來的國家”,是一個倡導自由與平等、反對奴役與暴政的國家;換言之,就身份而言,美國應該是反法西斯主義者,應該奉行《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人生來平等”的真理;然而,寫進《獨立宣言》的“人人生來平等”的這個“不言而喻的真理”,到了美國現實生活中卻成了令人費解的謬誤,因為美國社會從未實現“人人生來平等”的理想,美國絕非反法西斯主義者。正因如此,凡有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美國文人,都不失時機地將目光投向美國,通過書寫再現美國的各種言與行之間的矛盾與張力,竭力讓美國看清自己。諾曼·梅勒便是這樣一位文人,他的成名作《裸者與死者》(1948)通過再現美國國內的法西斯主義,向我們展現了“二戰”時期美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問題。
梅勒在《為我自己做廣告》中說,他寫作的目的是“在我們時代的意識中發起一場革命”(Mailer, 1959:17)。雖然梅勒從未明確表明他要革命的“我們時代的意識”是什么,但他革命“我們時代的意識”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社會”。梅勒在《詭秘的藝術:寫作漫談》中說:“我記得曾在1958年說過,‘我要在我們時代的意識中發起一場革命。’……那時候,我想我腦子里有幾部別人沒有的書,一旦把它們寫出來,社會就會發生變化。”(Mailer, 2003:62)從梅勒進行文學創作的歷史語境來看,他所說的“我們時代”正是“二戰”結束后美國與蘇聯進入冷戰的時代,這個時代美國社會意識除了帝國主義意識,還有性別歧視意識、種族主義意識和極權主義意識。梅勒在《存在主義差事》中說,美國“處于十分可怕的時代,患有十分嚴重的疾病。”(Mailer, 1972:341)他認為,“美國依靠生產破壞性資料獲得繁榮”,因此“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出美國人生活中健康的方面。”(Mailer, 1959: 189)他在《詭秘的藝術:寫作漫談》中說,美國作家的失敗在于沒有寫出一部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安娜·卡拉尼娜》和司湯達的《紅與黑》那樣“能使一個國家看清自己的偉大作品”(Mailer, 2003:300)。梅勒回憶說,每當失望之時,他都會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力圖通過自己的寫作挽救蘇聯(Mailer, 2003: 162-163)。由此可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梅勒力圖通過自己的寫作挽救“患有十分嚴重疾病”的美國。梅勒在《為我自己做廣告》中說,如果美國社會再次出現危機,那就不是“來自經濟中心,而是來自上層建筑”(Mailer, 1959: 215),因為美國社會的帝國主義意識、性別歧視意識、種族主義意識和極權主義意識的存在已經使美國社會“處于十分可怕的時代”,使“我們生活在滅絕威脅之下”(Mailer, 1959: 382)。梅勒認為,“偉大的藝術家總是跟他們的社會相對立”(Mailer, 1959: 190),他要以與美國社會相對立的姿態通過自己的寫作革命美國社會的這些意識,以阻止美國社會朝死亡方向前進。
雖然梅勒革命時代意識的寫作動機于1959年公之于眾,但他革命時代意識的意識在成名作《裸者與死者》中已經存在。《裸者與死者》是“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好小說”,它真實再現了“戰爭的殘酷性和普通士兵在整個戰爭中所受的身心傷害”。因此,它被視為反戰小說(Kinder, 2005: 190-191)。作為反戰小說,《裸者與死者》跟其之前的許多戰爭小說完全不同,因為它“沒有試圖賦予戰爭和那些參戰人任何浪漫色彩”(Kinder, 2005: 194);相反,它比較真實地再現了部隊內部的種族沖突、猖獗的反猶主義以及軍官與士兵之間的階級對立等美國社會的黑暗面。有評論家認為:“梅勒寫《裸者與死者》的部分目的是要提醒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讀者:什么東西正在從美國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中刪除。”(Kinder, 2005: 191)梅勒于1946年夏天開始創作《裸者與死者》,當時他剛從海外服役期滿回國,如果說他當時發現“什么東西正在從美國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中刪除”的話,那么,他要通過他的小說恢復這種“正在從美國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中刪除”的東西:“二戰”并不是正義對邪惡的戰爭,參與戰爭的美國并不是民主與自由的樂園,而是各種權力意識與反權力意識之間進行激烈爭斗的競技場。因此,《裸者與死者》努力恢復“二戰”之殘酷性的同時也“沒有試圖將制度種族主義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中消除”(Kinder, 2005: 194)。不僅如此,小說也沒有試圖將當時比較猖獗的性別歧視意識以及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極權主義意識從美國人對“二戰”的記憶中消除。事實上,《裸者與死者》的成功不僅在于它比較真實地再現了“二戰”的殘酷性及其對參戰士兵的身心傷害,而且在于它比較真實地再現了“二戰”期間美國社會各種權力意識與反權力意識之間的戰爭,比較真實地再現了戰爭期間美國的國內法西斯主義行為,從而使美國人看清了戰爭內外美國的法西斯主義真面目,這是這部“戰爭”小說書寫戰爭的真正用意所在。
1 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
《裸者與死者》是一部戰爭小說,也是一部再現“二戰”期間美國國內性別問題的小說。小說再現“二戰”的同時,也再現了戰爭期間美國社會的性別戰爭,這種戰爭通過小說中男性人物談論女性的話語、男性人物談論自己妻子的話語以及男性人物與妻子的對話得以充分展現。小說開始不久,布朗(Brown)和斯坦利(Stanley)就女人問題展開激烈的唇槍舌劍。布朗對斯坦利說:“你不能相信他們任何人,沒有女人你能夠相信。”斯坦利回應說:“我不知道,情況不完全那樣,我知道我信任我妻子。”布朗反駁說:“信任女人是不值得的。你占有我妻子吧,她很漂亮。”斯坦利回應說:“她的確是個美人。”布朗又說:“她是美人,你以為她會坐著等我嗎?不,不會。她正在外面鬼混瀟灑啦。”斯坦利則說:“我不那樣說。”(1)Norman Mailer, The Naked and the Dead.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8.下文中凡出自該版本的引文,均在引文后的括號內注明引文出現的頁碼。布朗和斯坦利談論女性的話語和口氣表明,他們對女性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之間的對話是性別歧視者與反性別歧視者之間的對話,他們的話語分別體現了性別歧視意識與反性別歧視意識。布朗的話語表明,他不僅是一個性別歧視者,而且是一個性別歧視意識的傳播者與推廣者;他不僅自己對女性抱有極大偏見,而且竭力使自己周圍的人也對女性產生偏見。在他看來,“干凈像樣的女人不再有”,“沒有一個男人一看就可以信任的女人”(120)。然而,不論他怎樣竭盡所能說服斯坦利,斯坦利都沒有跟他站在一起。斯坦利對布朗的對抗是反性別歧視對性別歧視的對抗。布朗和斯坦利對話中體現出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也體現在布朗、斯坦利、普拉克(Polack)和明尼塔(Minetta)等人談論女性的話語中。布朗認為:“沒有女人你能夠信任。”斯坦利回擊說:“我不知道,我信任我妻子,有各種各樣的女人。”布朗不認輸,仍然堅持說:“她們都一個樣。”明尼塔反駁說:“我信任我女友。”但普拉克卻站在布朗一邊說:“我一點都不信任那些婊子。”布朗覺得自己有了支持者,便說:“我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很不服氣地問明尼塔:“你信任你女友,哼?”明尼塔回答說:“那還用問,我當然信任她。”但他的回答使普拉克再次站到布朗一邊:“他就是信任那些婊子。”布朗再次很得意地說:“我告訴你,明尼塔,她們沒有一個你能夠信任的,她們都會欺騙你。”普拉克也隨即附和說:“該死的女人沒好的。”但他們沒有折服明尼塔:“我不會擔心。”斯坦利也從另一個角度反駁布朗說:“我可不一樣,我有孩子。”但布朗認為:“有孩子的女人最糟糕,她們最不容易滿足現狀,最需尋歡作樂。”普拉克再次支持布朗說:“我很高興,不用擔心那些婊子中有人會欺騙我。”但是,明尼塔還是沒有被他們折服,他回擊說:“去你的,你們以為你們好得不得了。”(184-186)這個眾聲喧嘩的對話中有兩種聲音:一種是性別歧視的聲音,另一種是反性別歧視的聲音。布朗和普拉克的聲音顯而易見是性別歧視的聲音,他們的話語體現了他們的性別歧視意識。斯坦利和明尼塔的聲音明顯是反性別歧視的聲音,他們的話語體現了他們的反性別歧視意識。斯坦利和明尼塔與布朗和普拉克的對抗是反性別歧視者與性別歧視者之間的對抗,體現了反性別歧視意識與性別歧視意識之間的對抗。布朗和普拉克的話語中體現出來的性別歧視意識也在卡明斯(Cummings)和羅斯(Roth)等人物談論女性的話語中體現出來。卡明斯認為:“一般的男人總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看自己的高低,其中沒有女人的角色,她們只是一個索引,一個[男人]用以衡量優越性的尺碼之一。”(322-323)羅斯認為,“女人應該關心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更為瑣細的東西”,因此,“很多事情是不能告訴女人的”(56)。
布朗、普拉克、卡明斯、羅斯以及斯坦利和明尼塔等男性談論女性的話語中體現出來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之間的沖突與斗爭也體現在卡明斯、布朗、羅斯和戈爾德斯坦因(Goldstein)等男性人物談論自己妻子的話語中。對卡明斯來說,妻子瑪格麗特(Margaret)不是他的情感與精神伴侶,而是他的生活助手與家庭保姆。“她忙于料理家務、處理愉悅和游玩賬單。”(416)不管她為家付出多少,在卡明斯眼中,她都不是什么賢妻。他毫無顧忌地對副手霍恩(Hearn)說,“我妻子就是一個婊子”,因為“她想盡一切辦法來羞辱我”(182)。與卡明斯不同,羅斯雖然認為“很多事情不能告訴女人”(56),但身在海外,他“努力想起他的妻兒,似乎在他看來,沒有比回到妻兒身邊更為美好的生活”(119)。跟羅斯一樣,“晚上,在帳篷里,戈爾德斯坦因總會……想自己兒子,或者努力想象他妻子此刻會在什么地方。有時候,如果他認為她可能在走親訪友,他會試圖想他們在說什么,想起家人的玩笑,他會帶著應有的高興搖搖頭”(205)。卡明斯、羅斯和戈爾德斯坦因對待妻子的不同態度體現了“二戰”期間美國社會對待女性的兩種不同態度和性別意識,這兩種不同態度和性別意識也體現在布朗和戈爾德斯坦因設想戰爭結束后他們回家對待妻子的態度中。小說末尾處,布朗和戰友想象著戰爭結束后回家跟妻子見面的情景:“我會跟某個娘們同居。我什么都不干,只玩女人,喝酒,整整玩兩周……然后,我會回家找我妻子,我會讓她知道我回來了,我會讓她感到驚訝,我會讓上帝見證。我會把她踢出家門,讓人們知道你如何對待一個婊子。”(710)布朗始終是一個性別歧視者,他對待妻子與其他女人一樣,因為在他眼中,她們只是性的玩物,只是男性滿足性欲的對象。但是,梅勒顯然要告訴我們,“二戰”期間,美國社會也有不同于布朗的男性,他們對女性比較友好,具有明顯的反性別歧視意識,戈爾德斯坦因就是他們的代表。與布朗不同,戈爾德斯坦因這樣想象戰爭結束后回家與妻子見面的情景:“我清早就回家,從格拉德(Grand)中心站搭乘出租車,一路直奔弗拉布什(Flatbush)公寓我們的家,然后上樓,按門鈴,娜塔莉(Natalie)會猜是誰,然后她會前來開門……”(710)戈爾德斯坦因與布朗迥然不同的想象,體現了他們迥然不同的性別意識。梅勒將戈爾德斯坦因的想象置于布朗的想象之后,目的是為了告訴讀者,性別歧視意識盡管想獨攬天下,但總是受到反性別歧視意識的對抗。梅勒在小說末尾處再現士兵想象回家的情形,旨在告訴讀者,美國即使結束了海外的軍事戰爭,卻無法結束國內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之間的戰爭。
小說還通過威爾遜(Wilson)與妻子艾麗斯(Alice)的對話再現“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之間的沖突與對抗。小說中出現過兩次威爾遜與艾麗斯的對話交流,一次是面對面的交流,另一次是書信交流。面對面的交流發生在艾麗斯在醫院生產后不久。一天,艾麗斯發現威爾遜在自己住院期間外出找了女人,而且花掉了她辛苦積攢下來的錢,她非常生氣地對他說:“伍德羅,我覺得你實在太卑鄙,沒有比一個男人對他妻子撒謊、在她和寶寶住院期間花掉他們的所有積蓄更為低劣的事了。”(378)但威爾遜卻反駁說,“我沒有什么可說的,艾麗斯,我們不說這個好吧,我多數時間都是你的好丈夫,你沒有必要那樣對我說話。我只想開心一下,我現在開心了,你最好不要把我的心情搞得一團糟。”(378)艾麗斯與威爾遜的爭吵是兩種性別意識之間的爭吵。威爾遜是性別歧視者,是男性至上主義者,他只知道自己享樂,卻不知道為妻兒承擔義務和責任。在他看來,男人不可以向女人(特別是妻子)袒露心聲,因為“你告訴女人的越少,你就越幸福”(259)。他很像卡明斯,卻沒有遇到像瑪格麗特那樣百依百順的妻子。他妻子艾麗斯具有強烈的反性別歧視意識,但遺憾的是,艾麗斯最終被威爾遜的糖衣炮彈所蒙騙,她的反性別歧視意識暫時被淡化,失去了最初的強度。威爾遜雖然暫時平息了艾麗斯的反抗,但他的性別歧視意識使他始終未改過去的做法,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欺騙妻子,因而引起了艾麗斯的再次反抗。威爾遜海外參戰期間,一天晚上,他收到妻子艾麗斯的抱怨信:“我不會再忍受了,我一直是你的好妻子,而你不是我的好丈夫……我已經煩做你的妻子了,因為你不理解……”(258)面對妻子的抱怨,威爾遜毫無愧疚之感,反而惱羞成怒,毫不客氣地回應道:“我告訴你,你最好有個像樣妻子的樣子,不要再嘮嘮叨叨;否則,我肯定不會回到你身邊……有很多女人愿意跟我在一起,你是知道的。”(258)艾麗斯對威爾遜的憤怒是反性別歧視意識對性別歧視意識的直接宣戰,但威爾遜對艾麗斯的強硬回應表明,“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的性別歧視意識十分猖獗。通過再現威爾遜與艾麗斯之間的劇烈沖突,梅勒再次表明,“二戰”期間,美國國內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之間的戰爭,就其劇烈程度而言,毫不亞于國外的軍事戰爭。
2 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
除了再現“二戰”期間美國社會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之間的戰爭,《裸者與死者》也再現了“二戰”期間美國國內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之間的戰爭,從而再次證明,《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人生來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到“二戰”時期已經完全成了令人費解的謬誤。小說中,除了男性人物談論女性的話語、男性人物談論自己妻子的話語以及男性人物與妻子的對話中體現出來的性別歧視意識與反性別歧視意識之間的沖突和對抗,種族主義意識與反種族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也比較明顯,這可以在少數族裔的生活經歷和感受以及白人談論少數族裔的話語中看出。
首先,小說通過明尼塔的生活經歷再現了“二戰”之前美國社會種族主義意識與反種族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明尼塔是墨西哥裔美國人,他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小時候就開始做歐裔白人的美國夢,但自始至終過著少數族裔的生活。小說這樣描述他的經歷:“墨西哥小男孩們也吸收了美國的寓言,也想成為英雄、飛行員、情人、金融家。”(63)“在圣安東(San Antone),一個墨西哥男孩能干什么?他能干廉價餐館的收銀員,能做敲鐘者,能在合適季節采摘棉花,能開雜貨店,但他就是做不了醫生、律師、大商人和領袖。”(65)“墨西哥小男孩們也吸收了美國的寓言,如果他們做不了飛行員,成不了金融家或軍官,他們仍然能成為英雄……只是這不能使你成為堅定而冷漠的白人新教徒。”(67)在描述明尼塔的生活經歷時,梅勒使用了“也”“但是”和“只是”等加強表達語氣和表達效果的詞語,旨在表明,像歐裔白人一樣,明尼塔也可以做自己的美國夢,但他不可能像歐裔白人那樣實現自己的美國夢。小說從第三人稱視角揭示了阻止明尼塔美國夢得以實現的種族主義意識,同時也通過溫和的“抱怨”揭示了明尼塔內心深處的反種族主義意識。
其次,小說還通過猶太人羅斯和戈爾德斯坦因的生活感受再現了“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羅斯是猶太人,大學畢業,受過良好教育,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但“他覺得凡事格格不入”(51)。羅斯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不是因為他與他們有年齡差距,而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是非猶太人歧視和排擠的對象。戈爾德斯坦因也是猶太人,他比羅斯年輕,但對非猶太人歧視猶太人的感受卻比羅斯更深。在海外服役期間,他親歷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幾個士兵跟一個卡車司機開玩笑,卡車司機給他們說哪個連好哪個連不好。他換擋準備離開時回頭喊了一句:“只希望你們不要到F連,那是安置猶太仔的地方。”他的話引起一陣哈哈大笑,有人甚至在他身后喊道:“如果他們把我安置在那兒,我就從部隊退出。”隨后又是一陣哈哈大笑(53)。這件事使戈爾德斯坦因頗受傷害,他“一想起來就氣紅了臉”,“他甚至在憤怒中感到一陣無望”,因為“他知道這于他無益”。他雖然“希望對那個回應卡車司機的男孩說點什么”,但“問題不在那男孩”,因為“他只是想耍點小聰明而已,問題在于那個卡車司機”(53)。戈爾德斯坦因知道,那個卡車司機之所以口出此言,并且能得到他人認可,是因為在他們身后,“所有一切都是反猶太人的”(53)。戈爾德斯坦因不明白為什么非猶太人要歧視猶太人,不明白為什么上帝允許反猶主義存在;所以,他反復責問上帝:“他們為什么這樣呢?”(53)“上帝為什么允許他們這樣?”(54)他對同胞羅斯說,“我就是不明白,上帝怎么能視而不見聽由他們這樣?我們應該是上帝的選民。選民啊!選出來受苦!”(54)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維護自己民族的尊嚴;因此,當羅斯說:“我覺得你對這些事憂慮過多,猶太人對自己憂慮太多,”他回答說:“如果我們不憂慮,沒有別人會憂慮”(54)。戈爾德斯坦因的話語表明,他不但具有強烈的反種族主義意識,而且具有很強的民族憂患意識;然而,他對這種猖獗的種族主義束手無策,不得不接受它的“合法”存在。因此,當羅斯抱怨自己受過高等教育卻找不到好工作時,戈爾德斯坦因說,“我的朋友啊,你就別跟我說了,我總是有工作,但有些工作不可一提啊,抱怨有何用?總體上看,我們還是相當不錯的,我們有老婆有孩子。”(55)
再次,小說通過白人談論少數民族的話語再現了“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種族主義意識與反種族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白人軍士克利夫特(Croft)認為,“有好的墨西哥人和不好的墨西哥人,你不能打擊好的墨西哥人”(62)。白人布朗認為,猶太人羅斯“懶惰,無精打采,凡事都無興趣”(119)。在白人看來,“你可以像殺死一頭大象那樣迅速從頭部殺死一個黑鬼”(159)。顯而易見,克拉夫特和布朗以及他們的白人同胞都是種族歧視者,他們談論墨西哥人、猶太人和黑人的話語體現了他們的種族主義意識,這種種族主義意識在威爾遜等人傷害戈爾德斯坦因的話語中體現得更為明顯。一天,威爾遜跟戰友聚在一起喝酒,戈爾德斯坦因在他們旁邊給妻子寫信。威爾遜邀請他一起喝酒,戈爾德斯坦因謝絕加入時,“他們都表示蔑視”,尤其是克拉夫特,他“吐了一口痰,不再看他”;加納格(Gallagher)毫不掩飾地說:“他們沒人喝酒”;威爾遜甚至罵道:“戈爾德斯坦因,你是個小屁孩,這就是你”;里德(Red)指責說,“人如果不能照顧自己,就一文不值”;威爾遜甚至說,“試圖對他好真是一種錯誤”(203-204)。威爾遜等人有意傷害戈爾德斯坦因的話語是其種族主義意識的體現,加納格的話——“他們沒人喝酒”——清楚地表明,非猶太人對猶太人的成見由來已久。面對威爾遜等人的侮辱,“戈爾德斯坦因突然轉身走開”,但他的行為并沒有對他們造成任何影響,因為“喝酒的那幫人湊得更近了,他們之間現在有一種幾乎可以摸得著的紐帶”(204)。戈爾德斯坦因不明白“他們為什么對我大發怒火?”不明白“他們為什么如此恨我?”(204)因為“他努力成為好士兵,從未溜走搭乘便車,跟他們任何人一樣強壯,比他們大多數人工作更賣力,站崗放哨時從未擦槍走火,不論這些多么誘惑他,但從未有人注意到這些,克拉夫特從未認識到他的價值”(204)。他思來想去,最后才明白,“他們是一群反猶主義者”(206)。他因此“討厭跟他們做朋友”,因為“他們不想跟他相處,他們恨他”(206)。遭受威爾遜等人侮辱之后,戈爾德斯坦因突然意識到,“他恨所有跟他一起生活和工作過的人,他不記得過去什么時候他有幾乎不喜歡的人。”(206)戈爾德斯坦因的生氣以及心理變化體現了他的反種族主義意識,表明了他與種族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這種沖突與對抗也在白人傷害羅斯的話語中得以體現。克拉夫特率領的偵察連準備攀登安納卡山(Mount Anaka),羅斯體力不支,數次跌倒被戰友扶起,最后實在無力堅持,任憑戰友怎樣催促,他都拒絕爬起,氣急之下,加納格對他說道,“起來吧,你這個猶太討厭鬼”。對羅斯來說,沒有什么比“你這個猶太討厭鬼”更能傷害他,也沒有什么比“你這個猶太討厭鬼”更能表達非猶太人對猶太人的憎恨。因此,一聽到加納格說他是“猶太討厭鬼”,羅斯頓時有一種觸電的感覺,一時間所有的疲勞都消失殆盡:“那種打擊、那句話本身,就像一股電流一樣激起了他,羅斯感覺自己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因為“這是第一次有人那樣罵他”。“他不吭不聲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努力接受這種震驚”,因為“有生以來他第一次真正很憤怒,憤怒刺激著他的身體,推動著他走了幾百碼,又一個幾百碼,再一個幾百碼”(658-662)。加納格的話語體現了他的種族主義意識,羅斯在加納格種族主義話語刺激下做出的非常態反應體現了他的反種族主義意識,也表明了他與種族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
最后,小說還通過戈爾德斯坦因的童年經歷和他對猶太人本質的理解再現了“二戰”之前美國社會種族主義意識與反種族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戈爾德斯坦因七歲那年,在放學回家路上,一群意大利小孩打了他,叫他“猶太人”。他哭著回家,向媽媽講述了自己被打的經歷,從爺爺那兒知道了他被打的原因:“他們打你,因為你是猶太人。”他還從爺爺那兒知道,猶太人受苦的原因:“我們是一個被折磨的民族,被壓迫者所困擾。我們必須從災難走向災難,這使我們比其他人更為強壯,也更為弱小,使我們比其他人更愛更恨另一個猶太人。我們受的苦那么多,我們知道了任何忍耐,我們總會忍耐的。”(483)年幼的戈爾德斯坦因雖然不太理解爺爺的高談闊論,但他從此知道了“受苦”這個詞的含義。爺爺將猶太人與“受苦”和“忍耐”緊密聯系,不是為了叫戈爾德斯坦因向種族主義低頭,而是叫他通過堅守自己民族的傳統去對抗種族主義,與種族主義進行斗爭。這個意義上講,爺爺的話語體現了他的反種族主義意識。像明尼塔一樣,年幼的戈爾德斯坦因“有抱負,他在讀中學時就有諸多關于上大學、成為工程師或科學家的不可能夢想,在僅有的閑暇時間,他閱讀技術書,夢想著離開糖果店,但當然了,他離開糖果店,便進入倉庫干起了裝船工的活,而他母親又雇了一個小孩做起了他以前做的事”(484)。此處的“但當然了”不僅表明戈爾德斯坦因的夢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表明戈爾德斯坦因難以實現夢想似乎理所當然,因為他生活在種族主義的控制之下,“但當然了”還表明了戈爾德斯坦因的反種族主義意識。
3 極權主義與反極權主義
除了再現“二戰”期間美國社會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裸者與死者》還再現了“二戰”期間美國社會極權主義與反極權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這種沖突與對抗體現了“二戰”期間美國社會階級之間的沖突與對抗,這可以在卡明斯將軍與其副手霍恩、美軍士兵與軍官以及克拉夫特軍士與其領導的偵察兵之間的沖突與對抗中看出。
卡明斯與霍恩是上下級關系,但非一般意義上的上下級關系,因為霍恩是卡明斯精心挑選出來的副手;然而,卡明斯從未視霍恩為具有完整個性的人,因此,他們之間不斷發生矛盾與沖突。在霍恩眼中,“將軍身上有很多矛盾,他本質上對自身舒服有一種完全冷漠,但生活中卻具有一個將軍至少所必需的奢侈”(77)。雖然“他事先就被廣告為營隊里最有同情心、最和藹的軍官,他的魅力眾所周知”,但霍恩發現,“他是個暴君,一個帶著鵝絨般柔軟聲音的暴君”(78)。卡明斯認為,霍恩的一切權利都是他給予的:“你作為一個人的所有權利完全取決于我一時的性質……沒有我,你只不過是個二等軍士。”(82)因此,跟卡明斯談話時,“霍恩一直處于防守狀態,掂量著他的話語,說話時毫無自由可言”(84)。雖然“他害怕過的人不多”,但“他害怕將軍”(170),因為他必須接受卡明斯的權力理論,成為其權力實施的對象;然而,他的本性使他走向反抗。卡明斯對霍恩說:“作為美國人,他們大多數都具有我們民主的特殊體現,他們腦子里不斷放大他們自己作為個人應該具有的權利而對他人作為個人應該具有的權利毫無概念。農民正好倒過來了,我告訴你,造就了士兵的是農民。”(175)因此,他要“鎮壓他們”,因為“每次士兵看到軍官得到一點特權,他都會受到一次打擊。”(175)但霍恩回應說,“我不明白這個,在我看來,他們會更加恨你。”(175)卡明斯回答說:“他們會恨我,但他們也會更怕我。我不管你給我什么人,只要他在我手下時間足夠長,我會讓他怕我……我要告訴你,羅伯特,要讓部隊工作運轉,你不得不讓每個人在懼怕之梯找到合適位置……當你懼怕上司而輕視下級的時候,部隊的作用就會發揮得最好”(175-176)。卡明斯認為:“二戰”是“權力集中營”,“政治跟歷史無關,就像道德規范跟具體個人的需要無關一樣。”(177)他認為,“在部隊,張揚個人個性的思想是一種障礙。”(181)卡明斯關心的不是善與惡的問題,也不是愛與恨的問題,而是上級與下級、有權與無權的問題。他關心的是權力的集中,而不是權力的分享。他是權力追求的偏執狂,甚至連眾人眼中至高無上的上帝也低他一等,他不認為他像上帝,而認為上帝像他(182)。如果沒人敢挑戰上帝的權威,卡明斯的意思顯而易見:他絕不容許任何人挑戰他的權威。因此,霍恩試圖挑戰他的權威時,他毫不猶豫地進行了懲罰,“擲煙頭”事件就是明證。霍恩本能地知道,“不能將火柴梗丟在將軍的地板上”(314),但卡明斯對他的壓制使他做出了違背自己本能的舉動。“他將火柴梗扔在將軍的腳柜旁,然后,隨著心臟的快速跳動,他小心翼翼地將煙頭扔到了將軍干凈地板的中間,狠狠地踩了幾下,帶著驚訝而受困的自豪,站著看著它。”(314)他這樣做,目的是“讓卡明斯看見,讓他看見”(314)。看到原本干干凈凈的地板上霍恩丟下的火柴梗和煙頭,卡明斯的第一反應是,“要是此刻他手中攥著一只動物,他會把它捏碎”(318),因為“霍恩所做的就等同于士兵的手伸到了他本人身上。對卡明斯來說,這是他部隊獨立的一個象征,是對他的反抗”(318)。卡明斯認為:“他的士兵對他的懼怕和尊敬,現在是理性的,是對他懲罰他們的權力的承認,這還不夠,還少了另一種懼怕,這種懼怕是不可推理的,它包含了他的極大權力,從效果來說,是挫敗他的種種瀆神的東西。地板上的煙頭是一種威脅,是對他的否認。”因此,“他不得不直接而無情地應對”,因為“你越滯留反抗,反抗就會越厲害,不得不毀了它”(318)。卡明斯對霍恩進行了嚴厲懲罰,但也受到霍恩強烈反抗。卡明斯與霍恩進行激烈的舌槍唇戰,體現了極權主義意識與反極權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卡明斯對霍恩陰險毒辣的懲罰以及霍恩的敗退表明,“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的極權主義意識極為猖獗。
卡明斯與霍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所體現出來的極權主義意識與反極權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也體現在美國士兵與軍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之中,這可以在比納上校(Major Binner)與卡明斯將軍對拉寧軍士(Sergeant Lanning)的恐嚇中看出。拉寧軍士巡邏作假被發現后,比納上校問他:“你巡邏期間有多少次這樣不負責任?”他回答說:“這是第一次,長官。”比納上校又問他:“你們連或營還有其他軍士也一直做虛假和錯誤巡邏報告嗎?”他回答說:“沒有,長官,從未聽說。”聽到這樣的回答,卡明斯將軍威脅說:“拉寧,你想回到美國還是想爛在這兒的罪犯集中營?”他回答說:“長官,我這身制服穿了三年,而且……”卡明斯將軍進而威脅說:“就是你跟我們一起二十年,我也不在意。還有其他軍士也一直做虛假巡邏報告嗎?”他回答說:“我不知道,長官。”卡明斯將軍換用另一種方式威脅說:“你有甜心[情人]嗎?”他回答說:“我結婚了,長官。”卡明斯將軍繼續威脅說,“你還想看到妻子嗎?”他回答說:“她一個月前離開了我,長官,我收到了絕交信。”(315)從這樣的對話中可以看出,盡管比納上校與卡明斯將軍竭盡全力對拉寧軍士實施權力,但拉寧軍士始終沒有就范。拉寧軍士的行為體現了他對壓抑性權力的反抗,也體現了他的反權力意識。拉寧軍士的行為中體現出來的反權力意識也體現在明尼塔的話語中。在明尼塔眼中,所有軍官都是“他媽的討厭軍官”,因為“他們是一幫狗雜種”(367)。霍恩從司令部調出之后,接替克拉夫特成為偵察連連長,對克拉夫特的“提升構成威脅”(李公昭 等,2003:68)因此成了克拉夫特的“敵人”。然而,霍恩跟卡明斯和克拉夫特完全不同,到了偵察連之后,他告誡自己“應該很快形成這樣的思想:他們[偵察連士兵]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人”(434)。他將手下士兵看成“不同個人”的思想顯示了他的反權力意識,使他成為讀者心目中卡明斯與克拉夫特的對立者。但是,當他強迫克拉夫特為殺死一只小鳥而向羅斯道歉時,他卻發現自己也成了卡明斯,因為“他服從命令撿起地上的煙頭時卡明斯可能也是這樣的感覺”,因此,他突然“很反感自己”(532)。霍恩的自我反感體現了他的反權力意識。
小說中極權主義意識與反極權主義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還體現在克拉夫特與加納格之間的沖突與對抗中。加納格與克拉夫特同在一個偵察小分隊,長時間偵察跋涉使他們身心疲憊。加納格希望克拉夫特放棄登山計劃,帶領小分隊踏上歸途;然而,克拉夫特卻沒有絲毫踏上歸途的念頭,他滿腦子想的是如何登上安納卡山(Mount Anaka),將它踩在腳下,從而征服它。但在加納格和明尼塔看來,登上安納卡山幾乎不可能,如果強行去登它,就等于白白送死。因此,加納格與克拉夫特之間發生激烈爭吵。加納格質問克拉夫特,“你究竟為什么不返回?難道你還沒有得到足夠獎章嗎?”克拉夫特以命令的口氣說:“加納格,閉上你的臭嘴。”但加納格毫不懼怕地說:“我不怕你,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克拉夫特再次命令加納格:“閉上你的嘴巴。”但加納格回擊說:“你最好別跟我們作對。”(691-692)加納格對克拉夫特的抗拒是他對權力的抗拒,他們之間的沖突是權力意識與反權力意識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表明,“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Foucault, 1978: 95)。
4 結語
通過再現“二戰”期間美國社會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以及極權主義與反極權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裸者與死者》再現了“二戰”期間美國國內在種族、性別及階級等方面的各種法西斯主義思想與行為,表明雖然美國打著反法西斯主義的旗號參與海外戰爭,卻無法遏制并消除國內十分猖獗的各種法西斯主義意識與行為。小說為什么要再現“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以及極權主義與反極權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梅勒在《為我自己做廣告》中說:“藝術的最終目的就是強化,甚至,如果必要的話,深化人們的道德意識。”(384)梅勒說:“我們感覺非常圣人般的時候,我們事實上也許是邪惡的。我們覺得最邪惡因而最終是腐化的時候,我們也許,借助上帝的驚訝判斷,被視為圣人般的。”(Mailer, 2003: 151)梅勒所言表明,他絕非生活在真空中進行純藝術探索的唯美主義作家,而是具有強烈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梅勒認為,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在于,他必須要有一種不安意識、一種冒險意識、一種善于洞察的意識(Mailer, 1959: 276)。1955年,梅勒接受《獨立報》(Independent,原名Exposé) 編輯利勒·斯圖爾特(Lyle Stuart)采訪時說:“我寫作是因為我想接觸人,通過接觸人,對我這個時代的歷史產生一點影響。”(Mailer, 1959: 269)1963年,他接受斯蒂芬·馬爾庫斯(Steven Marcus)采訪時再次重申了這一思想:作家如果做得很好的話,就能影響自己時代的意識,從而間接地影響后來時代的歷史(Mailer, 1978: 26)。梅勒傳記作家希拉里·米爾斯指出,梅勒的這一思想源于歐洲思想:“作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必須參與政治。”(Mills, 1982: 99)但評論家邁克爾K.格蘭迪(Michael K. Glendy)認為:“梅勒早已接受了更早的影響,即認為藝術根植于政治。”(Glendy, 1995: 7)尼格爾·雷(Nigel Leigh)指出:“至少在1948年選舉之前兩年,梅勒慎重地接受了華萊士(Wallace)的預言:美國已處于成為法西斯主義者的危險中。”(Leigh, 1990: 6-7)邁克爾K.格蘭迪認為:“《裸者與死者》的政治語境充滿的正是這種確信。”(Glendy, 1995: 8)可見,梅勒再現“二戰”期間美國社會的性別歧視與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以及極權主義與反極權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對抗,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梅勒熟知美國社會各種權力意識對人性的壓制和束縛,倡導自我與他人自由,倡導人人平等、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倡導通過理解、寬恕、懺悔和同情等人類美德消除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隔閡與沖突,從而達到和平共處、自由平等的理想狀態。梅勒在《為我自己做廣告》中說,他憎恨“擁有權力而無同情心的人,即那種連簡單人類理解都沒有的人”(271)。他還說,“我認為黑人與白人結成配偶是黑人的絕對人權。”(Mailer, 1959: 356)梅勒在《總統案卷》中說:“如果猶太人和黑人能獲得與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和愛爾蘭天主教徒一樣的平等,美國則會完全不一樣。不管它會成為什么,肯定跟我們能夠想象的任何情況完全不同;相反,如果黑人和猶太人被同化到現在美國人生活的那種毫無聲息、毫無想象的水平,美國則會跟現在完全一個樣,甚至更糟。”(Mailer, 1963:188)
梅勒認為,偉大的小說能夠對社會的自由發展做出貢獻。他說:“如果偉大的小說消失了……我們將會更加遠離自由社會。”(Mailer, 2003: 161)他還說:“一部偉大的小說具有一種對我們來說是新的意識”,但是,“我們在欣賞這部作品之前,必須被這種新的意識所鼓舞”(Mailer, 2003: 287)。《裸者與死者》無疑是一部意義深刻的小說,它能夠帶給“二戰”后讀者一種新的意識;然而,只有被這種新的意識感染之后,讀者才能真正欣賞它的深刻意義。作為一部“戰爭”小說,《裸者與死者》力圖再現的不是“二戰”本身,因為它只再現了戰爭的一個切面,它真正力圖再現的是“二戰”期間美國社會各種權力意識與反權力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通過再現這些權力意識與反意識之間的沖突與對抗,梅勒不僅表達了他對人類平等、自由與和平的倡導,而且告誡人們,真正威脅人類自由、平等與和平的不是軍事戰爭,而是各種權力意識。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深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