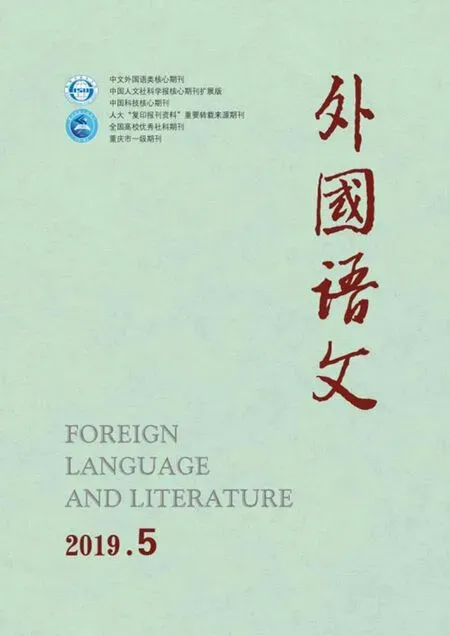從觀念形態到社會結構
——《郊區佛陀》中的階級表征及其文化意涵
李亞飛
(上海交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240)
0 引言
英國當代巴基斯坦裔作家哈尼夫·庫雷西(Hanif Kureishi)于1990年出版小說《郊區佛陀》,引發了不小轟動,不僅斬獲“惠特布雷德”最佳處女作獎,還在國外批評界產生了“無休止的評論”(Driscoll, 2009: 130)。小說書寫的歷史背景為20世紀70年代,其時恰逢英國社會文化的深刻裂變:流行文化、左翼思潮、青年亞文化等戰后社會運動和文化思潮彌漫英國社會。這些社會運動和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激進主義和反叛精神等觀念形態,它們充盈了整個英國社會,尤其受到廣大青年群體的青睞。由于觀念形態的轉變,社會階級結構也隨之發生顫動,階級之間的流動呈現出可能性,這是戰后英國社會變遷的一大動向。作為英國第二代少數族裔移民作家的庫雷西對此種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有深切的感知和敏銳的洞察,他以文學表征的形式,在《郊區佛陀》中書寫了南倫敦郊區底層中產階級的社會流動和階級跨越。小說在特殊歷史語境下探討英國社會的階級問題當然是具有特殊性的,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蘊,值得深入考察。然而,大多批評的觀點都只是關注作品中的族裔問題,對其中的階級問題鮮有涉及。為了進一步拓展對該小說的批評空間,有必要走出“純粹”的族裔身份分析模式,將階級問題納入考察的范疇。
本文嘗試以西方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為參照,重點關注作品中的少數族裔青年如何借助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觀念形態的結構性變化,憑借自身族裔經驗的特殊性來獲取階級的晉升。眾所周知,“階級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糜海波,2017: 16)。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觀實際上更多的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出發去進行闡發,認為階級矛盾的根源在于某一特定階層對生產方式的控制,而另一階級必須通過交易體力勞動來獲得基本生存資源(Day, 2001: 6)。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則將經典馬克思主義式的關注生產方式的分析方法轉向關注階級意識和階級文化,強調“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獨特的價值體系,認為它是歷史運動背后的推動力所在”(陸揚,2007:135)。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作為一種結構性存在,其實現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因素所決定(莫小麗, 2019: 20)。換言之,特定階級構型的生成并不單單只是受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制約,它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更為復雜,所涉及的相關方面也更為多元化。就小說《郊區佛陀》而言,70年代英國的特定歷史語境和彼時英國社會的族裔問題都構成形塑當時英國社會階級狀況的基本成分,它們為促成作品中的少數族裔青年群體實現階級跨越提供了重要助推力。本文將通過還原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考察小說對于70年代英國社會階級問題的表征,最終旨在揭示庫雷西通過對彼時英國階級政治的書寫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1 流行文化、反叛精神與70年代的社會觀念形態
庫雷西曾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他對流行文化“極其著迷”(Kumar et al., 2001: 124)。從第一部電影《我美麗的洗衣店》(MyBeautifulLaundrette)到《郊區佛陀》,再到后來的《黑色唱片》(TheBlackAlbum),都有對流行文化的大量書寫。1995年,庫雷西更是和音樂記者喬·薩維奇(Jon Savage)合編了一本關于流行音樂的書《費伯流行音樂讀物》(TheFaberBookofPop)。在書中他提到:“流行音樂是一種吶喊,不是一種書寫。它是關于個體的身體感受,不需要過多心智層面的理解,其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智的。”(Kureishi, 1995: xviii-xix)他認為:“從流行樂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關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種歷史,流行樂在表達歷史方面絕不亞于任何其他形式,因為它雜合了階級、種族和性別等各種問題,它已經成為戰后文化的核心。”(Kureishi, 1995: xix)就庫雷西來而言,流行文化是帶有重要社會文化內涵的符號,對于流行文化的探討也構成觀察特殊歷史語境中的階級、種族、性別等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
《郊區佛陀》展現了一幅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文化圖景,著重關注了諸如“解放運動,另類生活方式,以及流行文化(尤其是音樂文化)的興起”(Finney, 2006: 124)。小說中的青年,克里姆、查理、杰米拉都積極擁抱這一時期的流行文化,從思想觀念到行為習慣,無一不受其影響。他們對流行文化的狂熱和癡迷直接鑄就其思想觀念中充斥著激進主義和反叛精神。從某種程度上說,流行文化,或者說反主流文化滲透到來自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中,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體,對其所持有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性別認同等意識形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塑造和建構作用。然而青年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通常引領著整個社會的時尚,故流行文化對當時英國社會的整體社會觀念形態的重塑產生了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小說中的主人公克里姆在性取向上呈現出模棱狀態,有雙性戀的傾向。他不但對同性玩伴查理有愛慕之情,還與他的“青梅竹馬”杰米拉保持著性關系。克里姆到了倫敦從事劇院演藝事業之后,不但和來自上流社會的伊琳諾成為戀人,還傾心于其所在劇場的導演馬修·派克,并同時和其妻子瑪萊娜有過性經歷。克里姆混亂的性取向以及他個人的性實踐是當時大部分英國青年的一個縮影。克里姆極為反叛和另類的性觀念究竟源自哪里?和大多數的英國青年一樣,克里姆對搖滾音樂著迷,喜歡緋紅國王樂隊、軟機器樂隊、牛心上尉、弗蘭克·扎帕、野人漁夫等搖滾樂隊或歌手(庫雷西, 2016: 84-85)(1)下引此書只注明頁碼。。他的閱讀興趣也大多為較為激進的文學作品,如《北回歸線》《在路上》、田納西·威廉斯的戲劇集。無論是搖滾樂中對于個性的直接表達和對身體感官的頌揚,還是《北回歸線》《在路上》等文學作品對于性愛的大膽描寫,都無疑對于克里姆個人在性別、性等問題上的理解有直接的塑造作用,這種反叛精神沖擊著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念。
流行文化對于青年群體的價值觀念的塑造作用還體現在,它改變了青年一代對于性別認同的理解和實踐。同樣出生于南倫敦郊區的第二代印度移民杰米拉為克里姆的兒時玩伴,其思想觀念從一開始就受到一系列激進主義文化元素的塑造。小說中,她“從十三歲開始就讀個不停,讀波德萊爾、科萊特、拉迪蓋和她能找到的那些瘋狂作家的書”(71)。她在錢袋里放了張女性主義文化學者安吉拉·戴維斯的玉照,將其奉為偶像,克里姆就杰米拉的叛逆行為評論道:“她就想做波伏娃了。”(71)杰米拉的父親安瓦是一位保守的第一代移民,年輕時候從印度來到英國定居,但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仍然停留在印度社會的觀念系統當中,雖然身處英國,但仍然活在他自己想象中的印度。安瓦對其女兒杰米拉進行包辦婚姻,并用絕食的方法逼迫她嫁給來自印度孟買的錢格茲,杰米拉雖然屈服于父親對其婚姻的安排,并最終與錢格茲結為連理,但卻從未與錢格茲有任何實質性的夫妻行為。敘述者克里姆對杰米拉評價道:“不管怎么說,我們活在一個反叛時代非常時期,杰米拉對無政府主義者、情勢主義者、地下氣象員組織分子都很感興趣 ,他把所有與這些人相關的材料從報紙上剪下來給我看。在她心目中,嫁給錢格茲成為對反叛的再反叛,此舉是一種新穎的創造。”(110-111)在她父親去世后,她加入了公社生活,成為激進社區的一員,轉而成為一名雙性戀,同時和公社的西蒙和喬安娜相戀。杰米拉所持的激進的性別觀念,以及其操演的性別身份,都具有反傳統的意味,這同樣源自流行文化對青年日常生活的滲透。
流行文化對于青年群體的觀念形態和實踐行為的塑造是全國性的,不僅僅局限于倫敦郊區少數族裔青年。這種廣泛的影響也是跨階層的,來自不同階層的青年似乎在流行文化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當克里姆進入學校,第一次和女同學同班學習,班上的女同學叛逆之極,他“聽見她們在談論以前從不知曉的輕率的東西:打胎、海洛因、西爾維婭·普拉斯、賣淫。這些女的都是中產階級,但她們脫離了自己的家庭”(126)。這種風靡整個青年群體的激進主義和反叛精神似乎可以模糊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限,因為來自底層中產階級的克里姆和杰米拉與其他來自中產階級的同齡人都持有同樣的觀念形態。流行文化所倡導的反叛精神也成為底層中產階級和其他階層進行對話和交際的一個平臺,這將挑戰長期以來大多數英國人所持有的階級固化的觀念,無形之中影響社會階級結構發生變化。
2 從觀念形態到社會結構:文化轉型與階級流動
特定社會在特定歷史節點所出現的某些文化實踐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實際上是和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形態的演變聯系在一起的。丹尼爾·貝爾認為:“文化實踐和生活方式中的變化必然和社會結構相關,因為藝術品、飾物、唱片、電影和戲劇史在市場上買賣。文化中的變化作為一個整體,特別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現之所以成為可能,不僅是因為感覺方式發生了變化,也是因為社會結構本身有所改變。”(貝爾, 2012: 56)流行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興起和泛濫實際上也預示著社會結構方面的微妙變化。在小說《郊區佛陀》中,流行文化所傳播的激進和反叛思想對階層與階層之間固有的區隔形成一種消解和沖擊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來存在于不同階級之間的界限。從這個層面來看,《郊區佛陀》不僅捕捉了70年代英國社會出現的“文化轉型”(Head, 2002: 220),還洞察到了當時英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即原來存在于不同階層之間的區隔開始出現松動,階級之間的流動開始呈現出可能性。
作品中青年一代的整體觀念形態受到流行文化和左翼思潮的塑造,充斥著反叛精神和激進主義,而這打通了階層之間的交流渠道,使得來自不同階級背景的個體能夠開展社交,模糊了階層之間的明確界限。流行文化成為來自不同階級背景的青年可以共享的一個“空間”,成為他們之間相互交際和互動的虛擬場所。故事中的主人公克里姆來自南倫敦郊區的底層中產階級,他到達倫敦后從事左翼劇團表演工作。其同事伊琳諾出身顯赫,來自典型的上流社會背景,其“父親是美國人,擁有一家銀行;她母親是受人尊敬的英國肖像畫家;她有個哥哥是大學教授”(229-230)。然而,和當時眾多深受流行文化影響的青年一樣,伊琳諾思想激進,是不擇不扣的左翼戲劇演員。現實生活中,她接納“掃大街的,一個極肥極丑,穿防雨服,體重十六石的蘇格蘭人”希特(232),以實踐她所堅持的反叛思想和極端主義。與此同時,克里姆與伊琳諾同為倫敦左翼劇團的同事,二者都是左翼文化的實踐者,有共同的文化興趣。克里姆跨越階層的束縛,追求伊琳諾,和她成為戀人。流行文化中的激進因素對于階層之間原有的隔閡形成了一種沖擊力,來自不同階層的青年人在“激進”和“左翼”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能夠借此來進行社交互動。可以說,流行文化成為一種連接不同階層青年人的一個橋梁,這自然對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固有界限和區隔構成了一種挑戰。社會階級內在的規定性逐漸被外部條件所瓦解,即流行文化這種外部條件沖擊了原先的家庭門第、出身特權等自然決定因素,成為階級與階級之間流動的一個催化劑。
同樣來自郊區的查理在音樂上取得巨大成功,成為風靡全國的反主流斗士。查理通過玩弄流行音樂,迎合當時激進思想的潮流,實現階層的跨越同樣能夠說明流行文化對于階級流動的助推作用。和克里姆一樣,在郊區時的查理深受流行文化的影響,思想和行為都極為反叛,他“喜歡到處找地方睡覺,他一無所有,居無定所”,把每天都視為“一場冒險”(157)。小說中的查理發現,當時英國青年的音樂趣味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人們開始鐘情于表達憤怒和吶喊的流行音樂。如書中所言,“英國音樂風尚正在急轉,從豪華巴洛克轉向憤怒的車庫”(203)。查理由此加入朋克潮流中,并把自己的樂隊名改為“罪人”,稱自己為“查理英雄”(同上)。查理的音樂被當時的青年一代視為一種吶喊,受到廣泛的歡迎,為此他“被全國性的報紙、雜志、符號學家們沒完沒了地追逐,他的話被引用,成為新虛無主義、新絕望主義和新音樂的例證”(同上)。查理之所以能夠在音樂上取得成功,實現了從邊緣到中心的跨越,這和當時整個英國社會出現的流行文化的泛濫是分不開的,他的音樂形式迎合了當時青年一代對激進主義的向往,其個人也被作為英雄般的反主流文化斗士加以符號化。查理從郊區中產階級下層的背景出發,通過迎合大眾對于流行音樂文化的審美趣味,成為全國青年一代崇拜的對象,實現了階級的跨越。
如果說70年代流行文化中的激進主義和反叛精神為不同階層背景的青年群體提供了交際的空間,以此模糊了階層之間的界限的話,這一時期盛行的左翼思潮及其主張的對于英國族裔和階級問題的批判則為以克里姆為代表的郊區底層中產階級實現階層跨越提供了豐潤的滋養力。彼時英國社會所流行的左翼思潮強調對族裔問題和弱勢群體的關注,在文化實踐上對這類相關問題展開猛烈的社會批判。這為少數族裔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可以借用個人族裔身份的獨特性,迎合這一批判趣味,獲得與左翼批判群體為伍的機會和權力。在這一背景之下,小說中的少數族裔底層中產階級對個人獨特族裔經驗的挪用也成為促成其階級流動的另一個關鍵因素。來自郊區底層中產階級的克里姆通過利用其族裔經驗和移民社區文化,迎合當時社會對于族裔問題和階級問題的批判傾向,將其作為他實現階級晉升的一種策略。
克里姆為第二代印度移民,其父親是移民英國的印度人,母親是英國白人。雖然他自稱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但他對自己的混雜身份存在焦慮和不安,認為“人們常常覺得我這種英國人挺搞笑的,像是從兩個古老歷史里冒出來的新品種”(3)。獨特的族裔身份使得克里姆在學校受到種族歧視和欺凌。他在學校被人叫“大便臉”和“咖喱臉”,回家時滿身口水、鼻涕、粉筆印和木屑,“每天從學校回家身上沒有負重傷”(86)他就已經很幸運了。當他和來自上流社會的劇團同事伊琳諾交往時,克里姆試圖極力隱藏自己的南倫敦郊區口音,生怕暴露自己屬于郊區底層中產階級的階級背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于英國社會階級和族裔問題的批判成為一種流行,克里姆的族裔身份和獨特社區經驗因此成了他突破階層障礙躋身倫敦戲劇演藝界的一個關鍵籌碼。戲劇導演沙德維爾讓克里姆出演吉卜林《叢林之書》中的莫格利這一角色,因為在他看來,克里姆皮膚黝黑,“瘦小結實”“扮相可愛而健康”“不會顯得太色情”(186)。克里姆的表演非常成功,從而受到當紅左翼戲劇導演馬修·派克的賞識,派克因此要求克里姆加入他的下一部“圍繞英國所具有的唯一主題”(218)展開的戲劇,即有關“階級”的戲劇。克里姆想極力遮蔽和掩蓋的族裔和階級身份卻成為其個人演義事業上的一個資本,他不得不通過販賣和利用其獨特的族裔經驗和階級背景去贏取個人物質和社交關系上的成功。這也是為什么當克里姆拿下派克所導演戲劇的角色后,作為白人中產階級的鮑伊德對他說:“如果我不是白人和中產階級,現在我已經在演派克的戲了。明擺著眼下只靠才能什么事也成不了。眼下這七十年代的英格蘭,只有弱勢群體才能成功。”(219)
3 反思與批判:庫雷西階級書寫的文化意涵
20世紀末期,戴維·卡納戴恩指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階級’都是對英國社會結構最為準確的描述”(Day, 2001: 13)。卡納戴恩所說的“階級”實際上涵蓋了階級之間的流動。有學者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至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各個群體或社會階層在這樣的一種外部條件起主要作用的社會結構中,往往上下浮動,不斷地引發社會各群體在社會中的身份變動”(王曉路,2012: 168)。20世紀70年代,由于流行文化、左翼思潮等來自大眾的批判聲音籠罩英國社會,青年群體的觀念形態發生著持續的變化,這直接導致英國社會先前所形成的階級結構和基于這一階級結構的其他關聯模式開始出現顫動和流變,新的社會結構正在悄然形成。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庫雷西的《郊區佛陀》關注到了戰后英國的觀念形態和整體社會結構正在萌芽和生長的新內涵。
與奈保爾和魯西迪不同,庫雷西是一位出生并生長在英國的少數族裔作家,他并沒有殖民地地區的成長和教育經歷,然而他作為第二代巴基斯坦裔的族裔身份使其不可避免地攜帶有殖民地傳統的成分,這使得他在作品中對英國社會少數族裔階級問題的探討帶有獨特的視角。庫雷西于1954年出生于英國倫敦郊區,父親是來自巴基斯坦的第一代移民,而其母親是一位來自底層中產階級家庭的英國白人。庫雷西對英國少數族裔的階級問題的探討并不僅僅只是停留在后殖民主義的層面,即不止于分析殖民主義遺產如何影響少數族裔移民的價值觀念、文化身份以及意識形態。更為重要的是,他能夠從英國文化特性的角度對“后帝國”時代的英國文化做出整體性的思考,即他能夠從英國社會文化內部去反思英國文化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對英國整體文化在特定歷史時期所發生的斷裂與分崩有敏銳的感知。換言之,庫雷西的階級書寫具有移民和本土的雙重視角,對戰后英國社會和文化的探討具有一種反思的批判性。
庫雷西在《郊區佛陀》中所書寫的少數族裔階級政治實則是他本人對后帝國時代英國整體文化景觀的一種反思和批判。小說表達了70年代的英國呈現出階級流動的可能性,流行文化作為一種消解力,沖擊了原來存在于階層之間的隔閡。同時,彼時盛行的左翼思潮倡導對英國的社會文化發起批判,關注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等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境況,這為少數族裔挪用個人獨特族裔身份和階級身份搭建了平臺,他們借此加入到批判英國社會文化的群體中。這一方面說明,來自殖民地區域的少數族裔移民可以顛覆被“凝視”和被塑造的殖民系統,并在帝國中心開始他們的生活和實踐。他們之間的關系也開始從帝國時代英國對少數族裔的“凝視”到后帝國時代二者之間的“對視”。如小說敘述者克里姆所說:“我們追求‘英國玫瑰’就如同我們追求英國;通過得到這些獎品,得到這些親善和美麗,我們壯起了膽子與帝國及所有的傲氣臣民們對視——對視‘毛毛背’的眼睛,對視大丹犬的眼睛。我們變成了英國的一部分……”(301)
另一方面,這也同樣說明,這一時期的英國作為一個整體文化概念的內涵也在發生蛻變。少數族裔能夠在流行文化和左翼思潮等助推力量之下,獲得個人階層的跨越和晉升,從而取得加入左翼劇團表演的權力,實現個人在后帝國時代從郊區邊緣到城市中心的流動。這種從郊區邊緣到城市中心的流動,不僅僅意味著階級身份的一種變化,更暗示了英國文化內涵從早期單一而同質化的英國性到全新的多元化的英國性轉變。正如庫雷西曾經所指出:“是英國人,白種英國人,必須學習身為英國人之道不再是以往那一套方式。現在稱自己為英國人是一件更復雜的事,牽涉到新的因素。因此必須有一種嶄新看待不列顛的方式和必須面臨的選擇:經過這些時日后,必得有一種身為英國人的新方式。許多想法、討論和自我檢驗必須牽涉到考慮這種需求,也就是身為英國人的新方式和什么有關,以及取得這種條件有多困難。”(Kureishi, 2002: 55)克里姆加入左翼劇團,與當時的英國左翼文化知識分子一道,對英國的社會問題提出批判,在過程中將族裔多元性融入英國社會的整體文化圖景之中。通過在英國文化中摻雜來自不同族裔背景和不同階層背景的聲音,他們對英國文化的內涵加以“狂歡化”,挑戰傳統帝國時代英國文化的純潔性。從這一點來看,《郊區佛陀》也是庫雷西對英國文化內涵加以改寫和修正的一種嘗試。
4 結語
《郊區佛陀》以社會觀念形態的變化管窺社會結構的轉型,將70年代影響英國社會極為盛行的流行文化和頗有影響的左翼思潮與階級流動性關聯起來,書寫了流行文化如何影響英國社會的階級流動。流行文化作為一種消解階層之間區隔的沖擊力,為來自不同階層背景和族裔背景的個體提供一個普遍認同領域,進而模糊了階層之間的界限。與此同時,為迎合當時英國社會所流行的對族裔和階級問題的批判趣味,邊緣少數族裔通過挪用其獨特的族裔經驗和社區文化,出演戲劇表演中的少數族裔角色,取得和上層左翼知識分子共同開展文化批判活動的權力,進而從邊緣郊區走向中心城市,躋身上流文化知識分子圈。他們因此也開始在整個英國文化景觀當中融入少數族裔的聲音和觀點。庫雷西試圖由此說明,后帝國時代的英國整體文化內涵正在被族裔的多元性、階級的流動性及身份的混雜性重新界定,英國文化的整體內涵和所指也在發生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