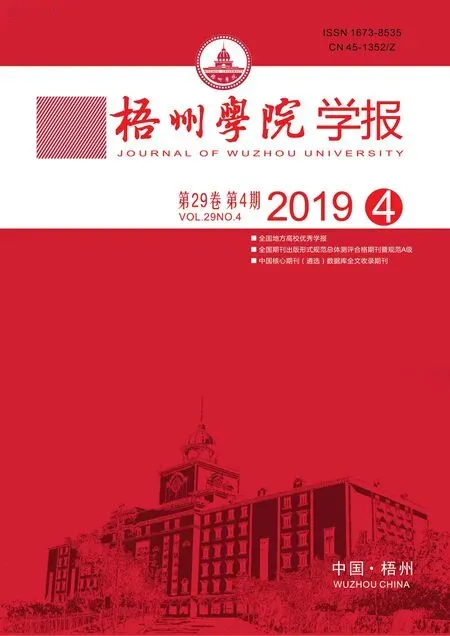清末民初寡妻的繼承權利研究
——以大理院民事判例為中心
阮致遠
(福州大學法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6)
寡妻,即無子孀婦。在研究民初女性繼承權利時,寡妻是很特殊的一個群體:夫在時,她附庸于夫的身份而存在,無獨立的法律地位;夫亡時,寡妻雖有“承夫分”的權利,但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往往受到限制。
民國初年,大理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其通過對“現行律”的司法解釋,賦予寡妻排他性的擇繼權利,但這種權利應當在遵從“家政統于一尊之義”的傳統倫理和服從尊長教令的前提下行使。與此同時,大理院賦予寡妻遺產“管理權”與必要時“處分權”,寡妻可通過“約定”獲得遺產完全處分權,但這種權利的行使受制于亡夫遺愿。大理院拓寬了寡妻權利的行使,然而也對寡妻的權利進行了限制。本文回顧傳統中國和清末民初法制中寡妻的權利,著眼于大理院的民事審判實踐,探究“寡妻”這一特殊群體在司法實踐中繼承權利的變化和限制。通過研究“寡妻”在大理院司法實踐中權利的行使,管窺女性整體權利的提升。
一、傳統中國法制中寡妻的繼承權利
傳統中國奉行以男系為中心的宗法制度,宗祧繼承為繼承制度之核心。而宗祧繼承的核心,“一為有子立嫡,一為無子立后。”[1]故對寡妻而言,立嗣是其參與宗祧繼承的方式。而傳統社會是否存在“財產繼承”,有學者認為,西方的繼承制度源自于羅馬法,即對已故者財產的承受,以“個人財產制”及“死后財產制”為基本內容,而傳統中國“同居共財”的生活模式,使得傳統中國不會出現西方意義上的財產“繼承”[2]。因此,探究傳統中國寡妻“繼承權利”,主要是探討寡妻的立嗣權利。
《唐律·戶婚》“立嫡違法”條稱:“諸立嫡違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以立嫡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3]259疏議曰:“立嫡子,本擬承襲。嫡妻之長子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違法’合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謂婦人年五十以上,不復乳育,故許立庶子為嫡。皆先立長,不立長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3]259該條規定嫡妻立庶子的前提條件(五十以上無子)以及立嫡條件(立庶子、先立長)。《唐律·戶婚》“養子”條,疏議曰:“依戶令:‘無子者,聽養同宗于昭穆相當者。’”[3]258疏議中采用“聽養”的說法,意味著立繼不是一個法律責任而是一種法律權利[4]49。《宋刑統·戶婚》“養子立嫡”條規定與唐律基本相同[5]。依據學者對宋代《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判例的研究,在宋代,寡妻在立繼中擁有極大的權利和自由[4]49-51。
至明代,出現了針對寡妻立嗣的規定,《大明令·戶令》“夫亡守志”條曰:“凡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6]該條規定了夫亡守志的寡妻,具有“承夫分”的擇嗣權利。其后,《大清律例》“立嫡子違法”條例第二承繼該規定[7]。事實上,明代以后,寡妻對于立嗣有明確的法律責任,寡妻擁有廢繼別立、擇立自己喜愛的嗣子之權[8]132-133。
二、清末民初立法中寡妻繼承權利的變化
清末的民事立法,《大清民律草案》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成果。但由于《親屬》《承繼》兩編涉及傳統禮教,“人事法緣于民情風俗而生,自不能強行規撫,致貽削趾就屢之誚。是編凡親屬、婚姻、繼承等事,除與立憲相悖酌量變通外,或取諸現行法制,或本諸經義,或參諸道德,務期整飭風紀,以維持數千年民彝于不敝。”[9]1855
對于寡妻的法律地位,《大清民律草案·承繼編》第8條規定:“繼承人若在繼承前死亡,或失繼承之權利者,其直系卑屬承其應繼之分為繼承人。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得承其夫應繼之分為繼承人。”[9]552該條文的立法理由稱:“謂繼承人死亡或喪失權利而又并無子孫,若其婦獨能守志,則其應繼之分應歸于其婦。所謂無子守志者,謂其并無親生之子,如承夫分為繼承,后族中茍有可繼之人,仍可立嗣,非謂終身絕后使得繼承也。”[9]552《大清民律草案》承繼《大清律例》的規定,認同寡妻具有“承夫分”的權利。《大清民律草案》在《大清律例》的基礎上,認為寡妻具有“繼承人”的獨立法律地位,實為一大進步。
關于寡妻遺產繼承的權利,《大清民律草案·承繼編》第9條規定:“無前二條之繼承人者,依左列次序定應承受遺產之人:第一,夫或妻。第二,直系尊屬。第三,親兄弟。第四,家長。第五,親女。直系尊屬應承受遺產時,以親等近者為先。”[9]552該條規定在無直系卑屬的情況下,寡妻得以先于直系尊屬承受夫之遺產。其立法理由稱:“以夫或妻列首者,因其人與所繼人為夫婦,生前既共為一體,則一造死后,自應與以先得之權。”[9]552
《民國民律草案》第1316條則賦予寡妻遺囑執行的權利:“繼承開始后,立嗣者除本人立有遺囑應從其遺囑外,若所繼人有妻,由其妻行之。”[9]832
此外,《民國民律草案》第1338條規定:“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在立繼以前,得代應繼之人,承其夫份,管理財產。”[9]836第1342條稱:“所繼人之妻,于繼承開始時,按遺產總額及其本人與遺產繼承人之需要情形,得酌提遺產,以供養贍之用。”[9]836上述條文又賦予寡妻財產管理、必要處分之權利。相較于《大清民律草案條文》,《民國民律草案》規定的寡妻權利更為豐富。
但上述兩部草案并未頒行,不能作為正式的審判法源,僅能作為“條理”法源援用。在民法典正式頒行之前,最高司法機關大理院將“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作為第一位審判法源(1)。其中,“立嫡子違法條”承繼《大清律例》的規定,其條例四謂:“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9]21在“現行律”中,寡妻“承夫分”獲得的并非是上述民律草案所規定的“繼承人”的角色,而是代夫擇繼的權利,實際上將寡妻排除在繼承權利之外。
三、民初大理院對寡妻繼承權利的裁判
(一)寡妻享有繼承權利的前提條件
如上所述,“現行律”僅以“婦人夫亡無子守志”作為寡妻享有的前提。但大理院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判例詳細解釋“婦人無子守志”的內涵,闡述寡妻享有權利的前提。
第一,大理院認為所謂“無子”,包括無親生子兼無嗣子,若夫生前已立嗣,則不屬于“無子”。在這種情況下,由嗣子承繼亡夫之宗祧與財產,寡妻無需行使立嗣權利。
大理院4年上字第585號判例稱:“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等語,律文所謂‘無子’蓋指無親生子兼無嗣子而言,如夫亡時已有嗣子,則夫之遺產自應歸嗣子繼承,婦人絕無繼夫之權。”[10]228以及大理院7年上字第24號判例亦稱:“所謂夫亡無子,自系指夫無親子,且生前未經擇立嗣子而言,其于生前已擇立嗣子者,則守志之婦自無更行擇嗣之余地。”[10]346大理院認為,若夫生前已立嗣子,則寡妻的擇繼權利就隨之喪失。
第二,律文所稱“婦人”,僅指正妻,不包括妾,唯有正妻才可主張“合承夫分”的權利。大理院3年上字第385號判例稱:“惟據本院判例,認為立繼及發繼之權,惟有妻之身分者得完全享有,至僅有妾之名義者,則此權不屬。”[10]158此后的判例均作相同的解釋(2)。
但是,妾在“兼祧另娶”的特殊情況下,可獲得與寡妻相同的繼承權利。大理院13年上字第341號判例有云:“查民事條理,出繼人因兼祧而另娶妻者,其后娶之妻雖僅得有妾之身分,但當時如確系因兼祧另娶,且有以其所生之子另繼該兼祧之意思,則后娶之人于夫故無子時,自得就該兼祧之房另為其夫立嗣,而于其夫本房遺產與兼祧房之遺產至后混同時,亦得請求分析,在所立嗣子未成年以前,并得有管理該遺產之權。”[10]756大理院認為,在兼祧另娶的情況之下,妾雖不能取得正妻之身份,但妾可以獲得“合承夫分”之權利。
第三,寡妻所享有的權利,因嗣子年齡而有所不同。若嗣子未成年,寡妻則可代替嗣子主張權利。大理院5年上字第53號判例謂:“夫亡由守志之婦承其夫分,嗣子如未成年,無論係屬親生或係過繼,均由守志之婦管理其亡夫財產,及為其子主張其遺產上之權利。”[10]739大理院6年上字第784號判例亦持相同觀點:“婦人夫亡無子,合承夫分,或有子而幼,亦應代管遺產”[10]791。
嗣子成年后,管理財產的權利歸嗣子所有,也意味著寡妻自然喪失遺產代管的權利。在大理院4年上字第2331號判例中,上告人趙賈氏(寡妻)與嗣子趙安成因管理趙震普(亡夫)遺產涉訟,此時嗣子已成年,寡妻仍主張對丈夫遺產的管理之權。大理院駁斥了寡妻的訴訟請求。
大理院認為:“按現行法例,婦人夫亡守志,為夫立繼者,嗣子未成年時,其承繼財產應由守志之婦代為管理,若嗣子已經成年(十六歲為成年),并無特別約定,或歷來已歸嗣子管理者,仍應由其嗣子管理。”大理院認為嗣子成年后,遺產應由其以承繼人身份管理,寡妻無權主張管理權[10]266-268。
大理院6年上字第803號判例也說明同一結論:“承繼人如已成年,固有管理承繼財產之權,但于處分之時,須得其母之同意。”[10]321
雖然寡妻權利發生變化,在嗣子成年之后喪失財產管理權,但在傳統“同居共財”的生活模式之下,寡妻仍擁有嗣子處分家財的同意之權(3),嗣子的權利仍舊受到寡妻的制約(4)。
(二)民初寡妻的立繼權利及其限制
在傳統中國繼承制度中,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共同構成完整的繼承體系,但宗祧繼承的重要性甚至勝于財產繼承。到民初,宗祧繼承制度已綿延千年,其頑強之生命力大抵與根源于宗法制度的男子本位的婚制和家長權本位的家制息息相關[11]。對于寡妻而言,其喪夫又無親子,為了延續夫族的宗祧,擇立嗣子則成了必要選擇。法律賦予寡妻擇繼立嗣權利,“現行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雖然寡妻享有為夫擇嗣之權,但寡妻的擇繼權利也受到種種限制。
1.在“家務統于一尊”前提下行使立繼權利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依身份而確定尊卑關系,尊長的意思不可違抗,卑幼應當服從尊長之教令,即“家務統于一尊之義”。雖然法律賦予寡妻排他性的擇繼權利,但寡妻的立嗣應當在尊長同意的前提下行使[4]65。
大理院多個判例將“家務(政)統于一尊之義”作為裁判理由,認為寡妻在行使立繼專權的過程中,應當得到尊長之首肯,甚至尊長可以通過遺囑代為立嗣。大理院4年上字第2433號判例稱:“本院按現行法例,無子守志之婦固有為夫立嗣之權,惟依家務統于一尊之義,被承繼人如尚有直系尊親屬存在者,非得該尊親之同意,則該尊親自得主張撤銷。”[10]276
大理院6年上字第1383號判例中,胡春華(上告人翁)在遺囑中擇立胡憲章為嗣子。上告人胡蕭氏(寡妻)表示自己并未同意立嗣行為,該立嗣應無效。且嗣子胡憲章與自己素有嫌隙,寡妻主張廢繼。
大理院駁回上告,稱:“本院查現行法例,被承繼人亡故之后,如有守志之婦存在,其立繼之權自在守志之婦。惟其直系尊屬茍因不忍其子之無后,指定某人入繼,立有遺囑,而守志之婦亦已表示同意者,則依家務統于一尊之義,自應認該遺囑為有效。至長支長子出繼或兼祧他支,在現行律上并無禁止之明文。”大理院查閱訴訟記錄,認為寡妻當時“未經表示異議”,應認為“守志之婦已表示同意”,先翁通過遺囑立繼的行為有效。至于寡妻主張廢繼的訴訟請求,大理院認為應當提出“素有嫌隙”的證據另訴[10]341-344。在案例中,大理院更加傾向于維持“家務統于一尊之義”的倫紀關系。事實上,在判例中并未有寡妻同意的記錄,參考大理院5年上字第850號判例,“子亡而有守志之婦者,立繼須由守志之婦為主,其翁僅有同意之權。凡由翁做主立嗣,而守志之婦并未對之表示情愿之者,當然不生效力”,應認為寡妻未同意,則該立繼行為不生效力[10]292。但大理院將寡妻行為解釋成“已表示同意”,并認可了尊長以遺囑形式立繼的行為。
盡管大理院再三強調立嗣應當經尊長之同意,但同時又限制了尊長同意權的行使。大理院認為尊長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寡妻所擇繼之人選。
大理院7年上字第1254號判例“又按現行法例,依家務統于一尊之義,無子守志之婦為夫立嗣,其直系尊親屬如尚存在,固應得其同意,惟守志婦擇立之嗣于法茍無不合,其尊親屬無正當理由,即不得拒絕同意。”[10]399若尊長無故拒絕寡妻提出的人選,寡妻可訴請審判衙門救濟。大理院8年上字第181號判例稱:“按卑幼之擇繼雖因家政統于一尊之法例,須得直系尊長之同意,然要不容蔑視守志之婦本有擇繼權,故尊長如無故拒絕同意,得以審判衙門判決代之,此本院判例迭經說明者也。”[10]418
另一方面,尊長同意寡妻擇嗣后,不得無故反悔。大理院6年上字第1133號判例稱:“按現行法例,守志之婦有為夫立嗣之權,其直系尊親屬不得反于守志之婦之意思代為立嗣,必守志之婦與被承繼人俱亡故時,始有立繼專權。惟依家務統一尊之義,守志之婦亦非得其夫之直系尊親屬之同意不得立繼,否則該尊親屬得以主張撤銷,然如果實已得同意,則其立繼行為自係合法,即亦不得無故翻悔。”[10]327
2.寡妻的立繼權利不受立嗣時間、繼單形式等客觀要件的限制
現行律對于立嗣時間并無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大理院認為寡妻不得長期拖延立嗣,但具體的立嗣時間,并不作要求。大理院3年上字第300號判例謂:“本院查現行律例對于被承繼人之立繼權應于何時行使,并無明文規定,則在被承繼人固有絕對之自由,及其死亡由守志之婦行使立繼權,法文則有須憑族長之語,是雖無時期(如被繼人死亡時)之限制,要不得由其婦之任意延宕,則無可疑。”[10]140
大理院8年上字第1188號判例中,徐松林身故無子,其堂弟徐松年(即被上告人)欲以子徐洪福入繼徐松林,寡妻徐馬氏推諉,徐松年遂與其訟爭。原審認為“守志之婦立繼不得任意延宕,判令上告人召集親族會議,從速擇立昭穆相當之人為嗣。”大理院反對,理由謂“查現行律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等語……夫既認為上告人為守志之婦,乃按之前述律例,實有未當。”[10]444-446
大理院認為寡妻的立繼行為,并無特定的立繼憑證(繼單)和立繼程序。大理院3年上字第568號判例稱:“查現行法例承繼并非要式行為,故訂立繼單不為承繼有效之條件,乃被上告人係因未立繼單,攻擊其承繼無效,實非允當。”[10]555
對于現行律規定的族長見證的形式,亦無特殊要求。大理院5年上字第569號判例稱:“守志之婦為夫立繼者,固應得尊長同意,而同意之方式,則不必限于畫押,即以言辭或其他動作為之,亦無不可。”[10]287大理院5年上字第1489號判例亦有類似說明:“婦人行使立嗣權者,照現行律為夫立嗣之例,雖應以族長為憑證,而族長之到場畫押究非立嗣要件,不得以其未經畫押遂謂為無效。”[10]306
大理院通過司法解釋,將立嗣時間等客觀要件排除在寡妻立嗣的必要之外,可以在寡妻立繼的過程中賦予寡妻選擇、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也更好地保障寡妻的權利。
3.翁姑教令對寡妻的立繼權利的限制
“家務統于一尊”是寡妻立繼權利的前提,而尊長(尤其是翁姑)的教令則能具體地、現實地限制寡妻的立繼權利。上文已提及,寡妻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自主的擇繼權利,但這種擇繼的權利是建立在“寡妻”之身份上的。若翁姑命令寡妻改嫁,脫離“寡妻”的身份,則當然排除了寡妻的擇繼權利。
大理院14年上字第1283號判例曰:“翁姑勒令改嫁脫離親屬關系,雖屬未經改嫁,要不得仍為守志之婦,即不得主張其有擇繼之權。”[10]124在家庭中,翁姑對于寡妻的行為有主導、命令之權,雖然法律賦予寡妻“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的權利,但是也無法阻止翁姑通過排除寡妻身份限制寡妻權利的行為。
清末民初,西方“個人主義”風潮逐漸進入中國,與傳統的“家族主義”并存于同一時空。大理院繼受西方民法理念,在直系尊長與寡妻的立嗣爭議中,更加重視對寡妻權利的保障(5)。
族長在寡妻擇繼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寡妻擇繼法定要件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族長僅是見證人的作用,不能憑借族長身份干涉寡婦自主行使權利。大理院3年上字第1160號判例稱:“至若族長或其他親族不得守志之婦之同意,而逕自為其夫立繼者,其所立之嗣非經守志之婦合法追認,于法當然不發生效力。此本院認為至當之解釋也。”[10]183其后,大理院4年上字第1211號、5年上字第566號判例均作出相同解釋(6)。
大理院將族長在寡婦擇嗣中發揮的作用解釋為“憑證”,有學者認為,族長在寡妻立繼中發揮的作用很小,且并不是立繼成立的要件[8]142-143。然從現行律而言,若無族長的見證,該擇繼行為算不得合法的行為,但并非無效(7)。
(三)寡妻的財產權利及其限制
在傳統社會中,強調寡妻“為亡夫守節”的倫理觀念,強化了婦女的權利,特別就財產繼承而言[4]4。但對于寡妻而言,寡妻財產權利的大小,取決于兩個問題:一是寡妻是否具有繼承人的資格,擁有對夫之財產的所有權;二是寡妻對于亡夫的財產是否具有處分的權利。
寡妻是否能以“繼承人”的資格承受夫之財產?就清末民初的立法而言,《大清民律草案》第八條承認了寡妻“繼承人”的身份。但在大理院的司法實踐中,則否認了此點,認為寡妻并不具有“繼承人”的身份。
大理院4年上字第567號判例稱:“本院查現行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等語,尋繹律意,不過謂無子守志之婦于立繼以前,得代應繼之人承受其夫應分之財產而管理之,并非即認守志之婦為承繼人,此現行法上至當之解釋,案經本院判例采行者也。……本院按現行法例,夫死婦人守志者,其夫之遺產雖應歸于繼承人或將來應繼之人,然守志之婦之生活費用則固不能不取給于財產,至其生活費用所需之額,應視其家之財產狀況及其人之身分地位定之。”[10]580-581在判例中,大理院雖然否認了寡妻以“繼承人”身份承繼夫之遺產的權利,但寡妻仍具有因“生活費用所需”而處分亡夫遺產的權利。
寡妻對夫之遺產是否有處分權?大理院認為寡妻對于夫之財產僅有“管理權”和必要時的“處分權”(8)。大理院6年上字第474號判例稱:“現行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等語,是無子守志之婦人,對于夫之繼承財產當然有管理之權,且于必要時更有處分之權,其屬于共有者,亦得依法請求分析。”[10]790大理院將寡妻的處分權限定在“管理權”和必要時的“處分權”,并非具有“所有權”。雖然寡妻不具有“繼承人”身份,但實際上寡妻才是遺產的掌管者(9)。
除了“管理權”與必要時的“處分權”,寡妻的權利還有所擴張:第一,妻可與嗣子約定對財產的支配之權,從而獲得獨斷處分的權利。大理院5年上字第801號判例:“子已成年,雖應由子得母之同意處分家產,僅母自己之獨斷處分原不能有效,惟入繼之子若于繼約議定得由所后之母處分者,則所后母仍有獨立處分之權。”[10]667第二,若亡夫留有遺愿,則寡妻可以依夫之遺囑獲得財產的全權處分的權利。大理院7年上字第761號判例稱:“本院按夫故之妻依夫遺囑而為遺產之處分者,與其夫自為之處分無異。”[10]613第三,寡妻有權在無子嗣的情況下,承受夫之私產。在家族式的生活方式中,同居共財是維系家族延續的重要手段,這些共同的財產即族(或家)之公產[12]。至民初時,個人本位的思潮西漸,子孫獨立擁有自己的私財已司空見慣,也不為法所禁止。寡妻對于夫族之公產當然無處分的權利,但大理院賦予其承受夫之私產的權利。
在大理院3年上字第1140號判例中,兩造爭議焦點在于寡妻所承受的財產是否為公產。上告人張德明稱,張德勝所遺財物為自己與其共同經營的公產,不應由寡妻張朱氏承受。
大理院認為:“本院按,現行律例雖規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能分析家財,然無禁止子孫不得蓄有私財之明文,故子孫以自己勞力所得之財產,未經提作公有者,即不能作為一家之公產。至子孫亡故又無子嗣,而其所遺之私有財產,自應依‘婦人無子守志,合承夫分’之條類推適用,應由其妻承受,是無庸疑。”大理院查閱訴訟記錄,認為兩造所爭之產為張德勝私產,與公共財產無涉,寡妻具有保有亡夫私產之權[10]561-565。
但寡妻的財產權利仍會受到一定限制。其一,寡妻在對亡夫遺產進行管理或是處分時,若亡夫對其中有遺命,寡妻則應當遵守。
當亡夫指定妾為遺產管理人時,寡妻則應遵從。大理院6年上字第1417號判例稱:“本院歷來判例所謂遺產管理應屬于守志之婦者,無非指被承繼人未有特別意思表示時而言,若有合法成立之遺囑存在,則為尊重被承繼人之意思起見,其遺產之管理權自不得不歸之遺囑指定之人,而其指定之管理人縱系居于妾之地位,亦不發生違法問題,斷難僅以妻之身分否認該遺囑為有效。”[10]792
當亡夫通過遺囑指定女兒為遺產管理人時,女兒得代父對遺產進行處分。大理院3年上字第669號判例稱:“父有遺囑命女為財產上之處分,而由母嗣后執行遺命者,則與父自為之處分無異,即非母自己獨斷之處分可比。”[10]558
其二,寡妻繼承財產應當尊重債權人利益。寡妻代管財產時,對于遺產債務,亦負清償之責。大理院6年上字第784號判例有云:“婦人夫亡無子,合承夫分,或有子而幼,亦應代管遺產,對于其夫所負之債務,當然有以故夫遺產供清償之責。”[10]791
在大理院的司法實踐中,寡妻擁有“代夫擇嗣”的權利,雖然立嗣權利受到傳統倫理、尊長的限制,但是寡妻的訴求大多能獲得大理院的支持。就財產繼承而言,寡妻雖然不具有繼承人的資格,但其仍擁有較大的權利。一方面,寡妻擁有財產管理權和必要時的財產處分權,另一方面,寡妻還有處分家產的同意權和被贍養的權利。清末民初,隨著西方民法中“個人主義”的思想逐漸傳入中國,傳統的“同居共財”的財產模式受到沖擊,在家庭中,法律不反對子孫保有私產,亦使得家族成員愈加重視個人的利益。而立嗣權利與財產權利是緊密聯系的。如呂思勉先生所說:“無如世俗爭繼的,口在宗祧,心存財產,都是前人所謂‘其言藹如,其心不可聞’的。”[13]對于寡妻而言,對于嗣子的選擇與其后對財產的管理、個人的養贍關系密切。司法實踐中,無論是族人爭產,還是寡妻擇嗣,其本意絕不單單是宗祧的承繼,而是對個人財產的保有。大理院4年上字第585號判例稱:“惟繼子之身分與所繼之財產有兩不可離之關系,繼子一經廢繼,則其所繼財產權當然隨之喪失,而移于此后應繼之人。”[10]228是否成為繼子,具有極大的利益差距,這直接導致了宗祧擇嗣案件在大理院繼承的司法實踐中數量最多(10)。
隨著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中華大地中生根發芽,對于女性的權利保障也愈受重視,“男女平等”“男女平權”等理念也時常被作為斗爭的口號。寡妻作為女性群體中特殊的一部分,在法律上的權利不斷擴大。但在司法實踐中,女性權利提高的過程迂回曲折。大理院通過法律解釋,賦予了寡妻更多的權利,但在賦予寡妻權利時又為其設限。這種漸進而又緩和的方式,雖然有保守的傾向,但從長遠來看確實促進了婦女地位的提高。雖然大理院的裁決具有擴大婦女權利的效果,但是這并非是大理院的任務和目的[4]62。大理院通過法律解釋在賦予寡妻權利的同時又限制了寡妻權利的發揮,從客觀上促進了女性整體地位的提升。一言以蔽之,這既是限制,也是進步。
[注釋]
(1) 即《大清現行刑律》中可以適用于民事審判的部分。關于刑律如何轉換為民事法源適用,參見黃源盛.民刑分立之后——民初大理院民事審判法源問題再探[J].政大法學評論,2007(98).段曉彥.《大清現行刑律》與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對“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適用[J].法學研究,2013(5).
(2) 大理院5年上字第644號判例稱:“現行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成夫分,須憑族長擇立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等語,尋繹律意,所謂守志之婦系指正妻而言,即為夫立繼之權,惟正妻有之。(現行律戶役門立嫡子違法條例第四)”;大理院6年上字第184號判例:“現行律內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等語,尋繹律意,所謂夫亡無子守志之婦人,自指正妻而言,故亦惟正妻始可承受其夫應得之分,妾則當然不在此限。”;大理院7年上字第386號判例:“本院按現行律立嫡子違法條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合承夫分,應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為夫立繼。’所稱守志之婦,係指正妻而言。若夫亡婦人未及立繼而故,自應由其直系尊親屬為之擇立,若無直系親屬,即由親屬會議公同議立。至妾雖系守志,亦不得有專行立繼之權,惟于親屬會議中應占重要地位,故其所主張如有正當理由,則親屬會議之立繼即應經其同意或追認,始能完全生效。”參見黃源盛.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承繼編)[M].臺北:犁齋社,2012:289,310,376.
(3) 大理院4年上字第1710號判例稱“惟依律文卑幼不得私擅用財之規定,其子非得母之許可,仍不得處分繼產。在現行法上至當之解釋,迭經本院判例采行者也。”參見黃源盛.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承繼編)[M].臺北:犁齋社,2012:660.
(4) 徐靜莉認為,嗣子受到的制約主要表現在,嗣子處分家財、分家析產均須寡妻同意。參見徐靜莉.民初女性權利變化研究——以大理院婚姻、繼承司法判解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199-202.
(5) 依據盧靜儀的統計,九個守志寡婦與直系尊長立嗣爭議表中,直系尊長勝訴的案件只有一個。參見盧靜怡.民初立嗣問題的法律與裁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89-90.
(6) 大理院4年上字第1211號判例有相同之結論:“律文所謂須憑族長云者,本不過謂婦人擇嗣須憑族長之證明,以昭大公,故所擇何人,茍于昭穆倫序無失,即族長不得橫加干涉,而族長意存偏向不為憑證者,尤得請求審判衙門以裁判代之。”大理院5年上字第566號判例作出司法解釋:“律稱須憑族長云者,乃以族長為憑證之謂,并非認族長有代守志之婦擇繼之權。”參見黃源盛.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承繼編)[M].臺北:犁齋社,2012:235,286.
(7) 白凱將這種現象稱之為“不合法繼嗣的合法性”,即若無有告爭權之人的告爭,即使是不合法的繼嗣行為,亦能夠生效。參見白凱.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72-75.
(8) 徐靜莉將這兩種權利表述為“財產代管權”與必要時的“代管財產處分權”,并認為寡妻對于亡夫財產具有“中繼”性質。參見徐靜莉.民初女性權利變化研究——以大理院婚姻、繼承司法判解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87-197.
(9) 邢鐵考察考察了寡妻繼產承戶的情況,他認為在孤兒寡母承受家產時,名義上是兒子代位繼承,但實際上寡妻才是遺產的掌管者。他對于這種無繼承之名卻有繼承之實的現象,以“繼管”稱之。參見邢鐵.家產繼承史論(修訂本)[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2:77-81.
(10) 參見根據盧靜怡女士的統計,繼承編案件共283件,涉及宗祧繼承的有186件,占66%。參見盧靜怡.民初立嗣問題的法律與裁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7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