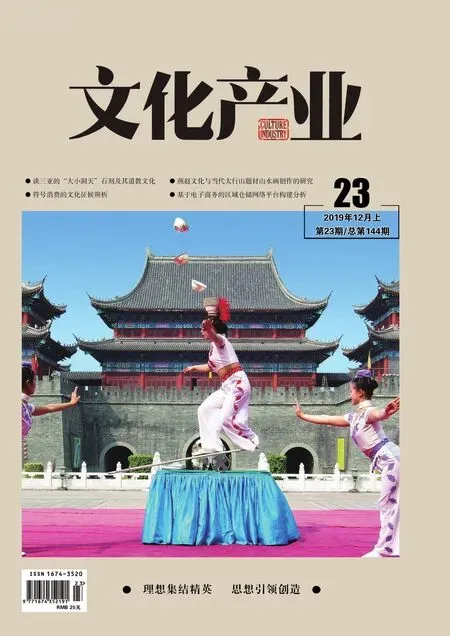於梨華小說中“棕櫚”意象探析
◎王卓歡
(廣西大學 廣西 南寧 530000)
《周易·系辭》早有“立象以盡意”之說,美國詩人龐德認為意象是思想和情感的復合體。意象是主體和客觀事物融為一體的形象,表現主題的思想情感。於梨華的長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以復式結構的“又見棕櫚”為題,文中也五次出現“棕櫚”形象,而何為“又見”?初見又是何時?因此,對“棕櫚”作意象解讀對于理解文本主題具有關鍵性意義。
本文按時間順序重新整合原本打亂時空順序的小說結構,把“棕櫚”意象作為切入點進行分析,對不確定和空白的文本進行再創造理解。“棕櫚”的五次出現和一次隱退,構成了牟天磊出國前至回國后曲折迂回的心理變化歷程,它們之間呈現了遞進、深化的關系,象征著主人公堅定信念、迷惘、重拾自我的幾個人生階段。“棕櫚”正是獨立勇敢、有追求、有根的自我主體的意義象征,它出現在牟天磊不同人生階段中重要轉變的路口,見證并引導了牟天磊對自我的追尋[1]。
一、精神的支撐
小說中的主人公牟天磊,曾是一個沖勁十足的青年,擁有“你會做,我做得比你更好”的氣魄。畢業之時正好趕上留學熱,即使與戀人分開有些許不情愿,即使只身前往異國他鄉開始全新的生活難免不安,但出國這股潮流波濤洶涌,他認為自己的未來擁有無限的可能,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所以,他勇敢地拋下一切,攥著“學成、業就”兩個希望,懷著前往美國實現自己文學夢的抱負踏上了旅程。
在前往美國之前,他又來到臺大的校園,看著熟悉的校園里一排排高大挺拔、直沖天際的棕櫚樹,他感到充滿了力量,他向棕櫚樹許愿,希望自己早日學成歸來,然后和初戀女友眉立結婚。棕櫚樹見證了出國前那個有理想、有抱負、充滿斗志、獨立勇敢的牟天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棕櫚樹就是那個建構了自我主體性的主人公的象征。
二、自我的缺失
旅美十年,牟天磊在外人眼中是個令人羨慕的留美人士,他是那般春風得意,取得博士學位、在學校任教、工資豐厚、功成名就。然而,風光背后掩藏的艱辛卻不為人知。十年間,他因為語言比不過英語母語的學生被迫放棄自己的文學夢想轉到新聞系;做過很多兼職,也曾食不果腹;不但因為種族問題融不入美國人的圈子,也因為性格的原因融不入美國的華人圈;好不容易拿到博士學位,卻因為學文的地位遠遠不如學工的,遲遲找不到滿意的工作,最后只能在大學里教水平很低的中文……人前風光,卻只能冷暖自知。牟天磊對自己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所以他并沒有像圓心皇一樣因為別人的阿諛奉承而驕傲自大,也沒有跟童志遠一樣因為他人對美國的向往而大肆吹噓,相反地,他陷入了另一個極端。和大多數的留學生一樣,曾經的理想逐漸被現實消解,只剩下消沉和茍且,他無數次地痛心時間逝去自己卻一事無成,卻再也找不回過去的那股干勁,最終“學到了不做夢”。他無法適應美國的生活,臺灣也回不去,漸漸地失去了自我認知、迷失了自我,成了沒有根的人。
於梨華結合自身經歷對牟天磊留學生活無助、艱辛、孤寂、落寞的生活狀態的再現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這也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成為留學生文學濫觴的主要原因之一。留學生們都抱著無限美好的向往出國追夢,可是出國之后更多的卻是無奈和妥協,被現實弄得面目全非。在這十年間,曾經給予他生命那么大能量的棕櫚樹已然退場,作為“自我主體”象征的棕櫚樹形象的退場正符合了牟天磊失去自我、放棄理想、喪失勇氣的現狀。他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那股拼勁、自信和勇氣,變得落寞、孤寂、膽小怯懦,每天渾渾噩噩的,找不到方向[2]。
三、理想的見證
(一)呼喚
以見女友意珊為由逃避在美現狀,牟天磊出國十年后第一次回國。原本只是想探望父母家人,再是和意珊家討論結婚事宜,可是,街坊鄰居、親戚朋友、新聞媒體的阿虞奉承逼得牟天磊喘不過氣來,某些人對美國的盲目崇拜也讓他感到反感,女友意珊甚至把和他結婚當成前往美國的跳板,如果他決定留在臺灣,意珊很有可能會和他分手,生活對于他來說充斥著不安全感、虛偽和迷惘。他考慮過不再回美國而留在臺灣發展,可是父母和女友意珊為了他的前程都希望他能回去美國,孤苦的心境和家人的期待使牟天磊陷入矛盾之中,他想要逃脫這樣的生活,但又不愿讓父母失望也不想失去意珊。關鍵是,在文學夢失落之后他已經不知道自己該往哪兒走,所以只能跟著別人的方向往前走。
直到與舊友兼師長的邱尚峰先生傾吐自己的困惑,邱先生告訴他,一個人活著的意義,最基本的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看到邱先生仍然一人堅守在那擁擠臟亂的小窩,即使有機會出去留學也舍不得、離不開,這給了他很大的震撼。邱先生知道自己想要的就是這么一個安安靜靜做學術的環境,因為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即使孤獨、即使無法揚名立萬,于他也無妨。
那天邱先生送他到路口候車的時候,他又看到了多年未見的棕櫚樹,他忽然感到一切熟悉又陌生。牟天磊感到熟悉又陌生的是什么呢?正是邱先生對理想的那種執著使得牟天磊勾起了對過去那個不顧一切追尋理想的自己的回憶,當他看到棕櫚樹,過去那個在樹下信誓旦旦許下承諾的青年正在逐漸被喚回[3]。
(二)引領
當牟天磊走在臺南傍晚的街道,棕櫚樹在涼爽的風中飄動,清爽而舒適的環境使他的內心逐漸平靜下來,他想象著在這兒居住的人們簡單而靜謐的生活,忽然發現這就是他現在的向往,他又想起了邱先生對他“為自己而活”的鼓勵,當下決定要留在臺灣落地生根。可是,當他意識到自己想要留下來,過與世無爭的鄉村生活,和邱先生一起重新研究自己喜歡的文學時,他仍然擔心戀人會因此離他而去,擔心父母會失望,擔心會失了面子,他陷入了矛盾之中,拿不起、放不下,遷就別人做違心的事他終將不會快樂,拋棄一切活出自我他又缺乏勇氣。
臺南鄉下的棕櫚樹營造出的靜謐溫馨的氛圍使牟天磊意識到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可是他還不具有追求自己想要生活的勇氣。
(三)化身
邱先生去世是小說中最重要的轉折點。當牟天磊在留下來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和遵循家人和女友的期望出國繼續那暗無天日的迷惘中間又決定選擇后者之時,傳來了邱先生在給他寄信的途中發生車禍去世的消息。通過邱先生的書信,牟天磊才深入了解到邱先生活出自我的生活方式所表現出的孤獨與勇敢、純真與堅持。他也許說不上是成功的、完滿的,但卻是充實的、清醒的、自主的,他生活的方式就是:不計功名,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但求不負我心。邱先生對自我的那份執著給牟天磊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他覺得邱先生就像是那一棵棵矗然直立、孤寂而勇敢的棕櫚樹,是他想要成為卻始終做不到的那種人。牟天磊的夢想從最初的“學成、業就”變為擁有寧靜平和的生活狀態,然而,只有從邱先生身上他才感受到了他一直不具備的堅持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勇氣[4]。
回顧前幾次棕櫚樹出現的環境,其實也與邱先生有關,回國后第一次與邱先生交談,牟天磊便感到棕櫚樹熟悉又陌生;在臺南棕櫚樹的靜謐氛圍之下想要過與世無爭的生活的他又想到了邱先生要他為自己而活的囑咐。邱先生其實一直是牟天磊追尋自我主體的動力。出國前,牟天磊就因為邱先生對他文學天分的肯定而堅定了學文不學工的理想,在不得已放棄文學之時也聽取了邱先生的建議,選擇與文學相近的新聞專業。回國后,對未來一籌莫展之時,也只有與邱先生的交心才能給予他安慰和啟示。
在邱先生去世之后,牟天磊終于堅定地留下來,繼續完成邱先生開辦雜志的遺愿。邱先生在牟天磊心里已然成為棕櫚樹的化身,是他追求的目標,他從邱先生的死亡之中才找到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決心。
(四)見證
最終決定在臺灣留下之后,牟天磊又走到臺大的棕櫚樹下,要它們作見證,見證他留下來的決心,見證他不再任人擺布、想要追尋自我的勇氣,見證他將會像邱先生一樣昂首闊步向前,不畏懼他人的眼光,不局限于利益之中,做到不辜負自己、堅持自我的赤子之心。這個場景和他出國前向棕櫚樹許愿的情景形成了循環和對應,牟天磊完成了自我主體的追尋—解構—重新建構主體的歷程,也找到了自己在臺灣的根。
在牟天磊的認知里,棕櫚樹是高大挺拔、不懼黑暗的,它象征著獨立和勇敢、堅強和美好,希望自己能像棕櫚樹一樣勇敢地生活。追逐文學夢的愿望落空了,他也隨之迷失了自我,但在見過邱先生之后,一切本已陌生的景象似乎又熟悉了起來,好像自己從未離開,這可以看作是與邱先生的對話喚回了當初那個知道自己想要往哪兒走的少年。在臺南感受到鄉村生活的與世無爭之后,他更堅定了要為自己而活的想法,然而,戀人、父母的不理解,虛榮心作祟又使得他猶豫不決,他沒有沖破一切障礙的勇氣。最終,邱先生的死徹底震撼了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覺得邱先生就像是那孤獨而又獨立的棕櫚樹,不計較得失,勇敢地活出了自我,但求不負我心。牟天磊最終決定留下來之后望向棕櫚樹的情景正好和他十年前出國前對著它們發誓的情景形成了照應,他似乎變回了那個帶著沖勁追逐理想的少年,只不過在這次重新建構自我的過程中,他終于找到了在臺灣的根,更清楚自己內心的追求,也更有勇氣。
對六次“棕櫚”形象的意象探析,表現了留學生生活的艱辛和孤寂,褒揚了小說中牟天磊和邱尚峰先生追尋自我理想的勇氣和堅持。
四、結語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講述的是畢業之時趕上出國熱的青年牟天磊,從一個懷抱理想、對未來滿懷憧憬的斗士,經過十年的留學生涯之后變得膽小怯懦,帶著超出年齡的老成,回國之后,在邱尚峰先生的指引和幫助下,逐漸追尋到理想中那個勇敢的自己,他終于找到了在臺灣的根——繼續創辦雜志,繼續追逐文學夢,過平和靜謐的生活,不追逐名利,只求活出自我。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時空交錯結構產生的不確定性和空白,形成了文本的召喚作用,使得讀者可以創造性地進行解讀;“棕櫚”意象是文本中不容忽視的不確定因素之一,根據它的六次出現呈現出主人公牟天磊自我主體的解構和逐漸重構的歷程。筆者認為,“棕櫚”正是健全自我主體的象征,而不計得失、努力為了自己而活的邱尚峰正是棕櫚樹精神的化身。通過對“棕櫚”意象地探析,於梨華作品中留學生的苦悶、孤獨、迷失、無奈的無根狀態躍然紙上,突出了主人公對自我主體的尋回和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