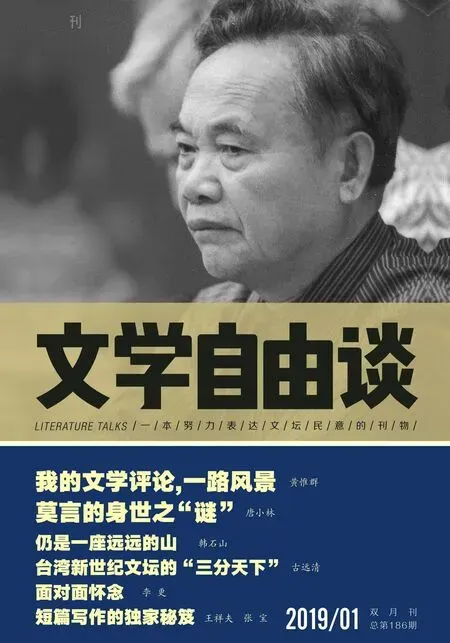文學里的“真假”(外兩篇)
□唐 詩
大約是六年前的事了,我去某個部門辦事,遇到一位姓黃的公務員,聽到我的名字,立即說看過我很多小說和散文。我心中凜然,想到但凡這樣的開頭后面免不得就是一通恭維,令人手足無措。可他卻不,話鋒一轉,這樣說:“你的有些小說寫得很真,有些寫得假了!”我表示愿聞其詳,他不再作多余的客套,遂一一道來。
說的是我寫的一篇關于單親媽媽的,她如何將孩子試圖放到老家給父母帶,又如何無可奈何帶著孩子四處打散工。生活中的細節勾勒自然是真實的,壞就壞在對話。女人離婚后,她爸指著她的鼻子罵:“別的女人就算是做‘雞’,一晚上也要好多錢,但你咧!白白被人睡了這么久,一分錢沒拿回來,現在倒好,還帶個拖油瓶回來噠……”公務員說:“你這樣的寫法不符合人之常情,哪有爸爸會對自己的女兒這樣說話啊!”我當下莞爾。我無法說這就是照實從生活里搬過來的,我無法說這個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有原型又怎樣?你寫假了就是寫假了。換句話說,將真實的事件寫假了。這可是件要命的事。
后來我仔細想了想這個問題,找到了讀者認為“假”的癥結處:事實上,讀者不是不能接受一個父親說出這般污辱性的言語,而在于小說對話前期的處理上。按常理,一對意見不合、積怨已久的父女,在一來一往的對話中必定是話趕話的,那種瞬間的憤怒非常復雜,充滿了矛盾和不公。勢必是女兒做了什么令父親傷心的事,說過什么令父親傷心的話,再經過時間的發酵,這才將話說到了決絕處。說到底就是細節的鋪墊。
談到小說里的真假,有些作家難免得意,因為很多時候他們虛構的場景、人物、對話,都能被讀者當成真的來看。把假的寫真了,考驗的是作家的功力,另一方面還有讀者群的問題,或者作家虛構的那個世界就是讀者向往的世界。
照我看,小說讀起來是真的還是假的,還在于小說語言。我曾接觸過一個內刊雜志的校對,他指著一篇小說,評價里面存在的各種語法常識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他知道廁所的味道。”味道是要用舌頭嘗過才會知道的,這樣的用法就很不合理。我反駁他說:“照你這么說,那詩歌里的通感手法要怎么解釋?”關于文學語言,或者說小說語言,南翔老師曾說過這么一件生活里的小事:在小區里碰到一對母女,孩子兩只手都拿滿了東西,媽媽又讓她拿另外一件東西,于是,孩子說:“媽媽,你幫我拿,我沒手了。”這就是小說語言。換句話說,小說語言也是生活語言,生動、形象、跳躍。若我們將這個小情景寫到小說里去,突兀地寫孩子說這句話,就會產生歧義——這孩子怎么就沒有手了?明顯寫假了。但如果前面交待清楚了,孩子兩只手都拿滿了東西,她再說這句話,就變得合情合理,真實無比。
關于《談看書》記
抓人、耐看的文字能令讀者忽略真假與否的問題,甚至聯想到現實生活中聽過的傳說,認為作者寫的就是真實存在著的。我看張愛玲的《重訪邊城》,里面有《談看書》,說到“棉內胡尼”,那些語言、故事、場景一下子就俘虜了我。
《談看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寶、四寶的故事: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三寶和四寶,隨父母逃荒,路上被賣到同一個大戶人家。后來四寶被收房作妾,三寶抑郁而死。四寶哭著訴說,她一直還指望有一天能團聚,現在沒指望了。長嚎了幾聲,跳樓死了。轉述這個新聞的人下評語說:“異哉此婢,亦貞亦淫,不貞不淫。”惋惜她死得太晚。很多人知道張愛玲的白描手法,在這里尤其高明:略略幾筆的勾勒,令人置身世態炎涼的場,周圍都是旁觀者,連讀者都是。多么諷刺。太多時刻,我們隨眾心理嚴重,習慣人云亦云,懼怕逆流而行成為笑柄,于是卑微、不知所謂地活著。人性里有多少復雜、多變,就有多少無奈和面目可憎。張愛玲對人性看得如此透徹啊。
我感興趣的是棉內胡尼。據說夏威夷有個侏儒的種族,稱為棉內胡尼(Menehuni),像愛爾蘭神話中的小人,與歐洲大陸上的各種小精靈,都是當地早先的居民,身材較瘦小。他們晝伏夜出,有時候被迫替征服者造石階等。后來大概絕了種,或者被吸收同化了,但仍有人在山間小路上,看見怪異的侏儒神出鬼沒。棉內胡尼讓我記起小時候聽我媽說過的故事,一個傳說:在我家鄉的深山里,五峰山上——我媽說的就是我大姨嫁去的那個地方——山里藏著很可怕的動物,似人又不像人,在夜幕降臨時會搶掠婦女,將人搶去做老婆。有一個婦女在趕集時經過深山,便被搶了去,幾年后逃出來,已經不會講話,是用手腳比劃才道出了事情的經過。這駭人聽聞的故事讓我深信不疑,從此便不敢再嚷著要去大姨那過暑假。現在想想,將我大姨那村莊里的婦女掠奪去的可怕動物,是否就是沒有被同化的“棉內胡尼”呢?想必我媽說那故事也不只是為了嚇我,該是有些根據的。
又說歐洲的小精靈里面,有一種小妖叫勃朗尼(Brownie,即褐色的東西),人形而極小,是成年男子。脾氣好,會秘密幫助人料理家務,往往在夜間,人不知鬼不覺就給做好了,與棉內胡尼如出一轍,不過一個在家里當差,一個在戶外干活。這勃朗尼就讓我聯想到田螺姑娘的故事——美麗的田螺姑娘夜間出來為人做好噴香的飯菜。我小時候就認為這些都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勃朗尼是成年的男人。有成年男人,當然該有成年女人的,還是說這種褐色的人形東西,如果是女人就不叫勃朗尼了呢?歐洲沒有小黑人,亞洲的小黑人是從非洲去的,但兩處的小黑人并不相像。非洲的小黑人頭大身小,臂長腿短,不像亞洲的勻稱。黑人行多妻制,有時候貪便宜,娶小黑人做老婆。黑女人卻沒有肯嫁給黑人的,估計是吃不了剛果森林里生活的苦。有人推測,非洲小黑人是因為干旱避入森林,適應環境才縮小的,這樣行動方便,利于在林間活動。啊,有道理。但究竟非洲小黑人是否就是黑人變小的,還是個疑問。也許黑人本身的來源就是個謎。
字典上,勃朗尼歸入“小仙人”(fairy)之類的。小仙人有翅膀,會飛。那小仙女、天使是不是就是這樣來的呢?另外有一種穿綠衣的小人叫艾爾夫,大都在山區,常在草叢出沒,愛捉弄人,所以漸漸給說成頑童。運氣好的人遇見他們,若他們高興,會讓你發現一壇金子。我覺得喜歡寫科幻故事的寫手應該從這方面入手,寫寫勃朗尼;喜歡寫愛情小說的人也有必要挖掘這條途徑,寫一部人類與艾爾夫戀愛的言情小說——這種故事,安排一個灰姑娘是再合適不過的,艾爾夫能改變她的命運,讓灰姑娘變得多金而富有。想想吧,現實中一個男人愛上灰姑娘,讓她變得多金而富有,這完全是不符合邏輯的。
還有一種丑陋的老頭子叫諾姆(Gnome),住在地洞里守礦或看管寶藏,像守庫神一樣,會嚇唬人,使可怕的事故發生。諾姆與一種隱形的叫格軟木林(Gremlin)的小人一樣調皮淘氣,同屬妖魔類,都對人類不懷好意……
張愛玲的散文大氣、通透、不膩。《重訪邊城》需要細讀,從中不難窺見作家的性格和體溫。個人覺得她的散文更加完美地呈現了她的寫作天賦。《談看書》后面一篇是《談看書后記》,已經不是講人種學了。張愛玲稱自己是外行掉書袋,實在可笑,說自己大概是向往遙遠與久遠的東西。這大概就是文字的魅力:我看到這句時又想到了自己。我總是迷戀那些不可知的東西,外界的神秘總能輕而易舉攫住我;人群中,那個不愛笑、不愛吵、不愛鬧的保留著神秘感的人總是能擋住我的視線,莫名其妙的。我自己呢,也是這樣,曾經想過要裝出神秘的樣子來受人關注。實在是內心孤獨而單薄得可憐。
皮膚主義
跟郭建勛老師認識好多年了。印象中,他愛開玩笑。在“皮膚主義”微信群里,乍一看到他提的“皮膚主義”,我也開了玩笑。我說,“皮膚”兩個字容易讓人聯想到“膚淺”。緊接著又說:“這詞合適我。”玩笑歸玩笑,細想一下就有了那么些小感慨,想到了“貼著皮膚寫作”。
嚴格地說,我的作品里,貼著皮膚寫的只有《清秋筆記》:寫我和我女兒的生活,一點一滴,文字記錄了生活的表面,稍深入一點,立即有痛感,一如在皮膚上劃出個口子,哪怕是點小傷口,也是有感覺的,會留下痕跡,會有血,會疼。我曾寫過這樣的句子:“每天晚上,她貼著我的皮膚入睡,我熟悉她的每一寸皮膚……”這樣的熟悉你了解了吧?到了每一寸皮膚的程度,那是何等的清楚明了。
撇開“主義”不談,光說“皮膚”。女人通常是愛皮膚的,希望皮膚光潔,白嫩,希望皮膚好。當你說女人的皮膚真好,幾乎就是在夸她漂亮了。這樣說來,皮膚果真是個好詞。我們知道皮膚覆蓋全身,它使體內各種組織和器官免受物理性、機械性、化學性和病原微生物性的侵襲。人和高等動物的皮膚由表皮、真皮(中胚層)、皮下組織三層組成。皮膚并不膚淺。延伸到寫作,貼著皮膚寫的作品必定是身體的一部分,它和內在思想和精神密不可分。它是有血肉的,它有痛感,它是豐富的,是自己的臉面,是龐大的機能,而絕對不會是無病呻吟,胡編亂造。
我想,我內心一直在渴望能夠“貼著皮膚寫作”。貼著皮膚寫,才能貼著靈魂寫,貼著大地寫。是真正的貼著皮膚,你是明白的吧?寫淺了,你不會有感覺,稍寫深一點,你便會痛得叫起來,喊起來,變得不那么害臊和怯懦。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惦記著保養皮膚,想方設法吸收各種營養,使得你的皮膚有光澤,好看,使得別人愿意多看你兩眼,稱贊你兩聲。倘若你懶惰成性,你的皮膚年久失修,終究變得皮粗肉糙,讓人不忍直視,看幾眼便會后悔半年,倘若運氣差點,你點背,遇到個火爆脾氣,給你一頓好打,打得你皮開肉綻,從此一蹶不振,豈不哀哉。
皮膚總是在第一時間內給我們最直接的信息。健康的皮膚紅潤光滑,生了病,過敏、蕁麻疹,腫大、疼痛和流血,包羅萬象。皮膚病有輕有重,無法忽視。輕者無關痛癢,頂多礙眼,重者關系生死。寫作這回事,往淺了寫,誰也不關心,寫深了,必定勞苦功高。那么,選擇貼著皮膚去寫,我們更愿意得到哪種結果?總而言之,我理解的皮膚主義,更多的是提倡一種認真的寫作態度。這種態度是任何一個把寫作當成終身事業的作家都應當了解的責任和義務,是作家應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