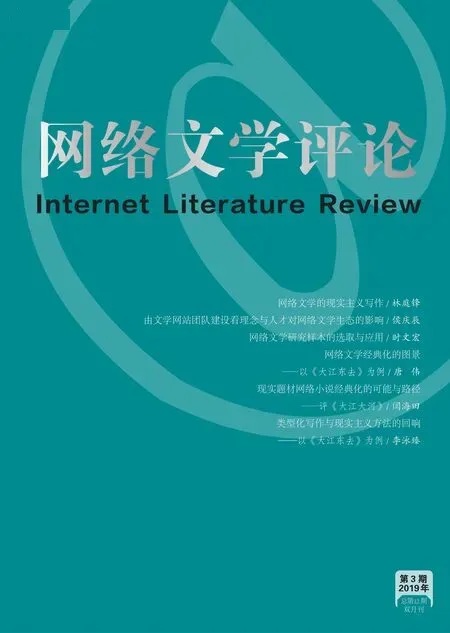從小詩到微詩
——以熊國華微詩為例的考察
陳宛頤
一、從小詩到微詩
中國小詩濫觴于中國古典詩歌,并受到印度泰戈爾短詩和日本俳句的影響,孕育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小詩潮流中。到20世紀80年代,小詩的說法已經不盛行,但并不意味著小詩的文體喪失了,相反,不少詩人的詩歌也可以看成是小詩。例如顧城的《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北島的詩歌《生活》只有一個字“網”,便是當時小詩的翹楚之作。而后蔣人初、王爾碑、流沙河等詩人先后出版了微型詩集,微型詩創作漸成氣候。1996年重慶的《微型詩》刊出版,主張除了標題之外只有1-3行的詩歌是微型詩。只不過跟小說中的“微型小說”這個概念相比,“微型詩”這一概念并未廣泛流傳,人們更愿意用“小詩”的概念。2011年微信誕生,“微詩”逐漸在微信蔓延。
當代微型詩是由現代小詩孕育而生的。“五四”時期,中國文壇白話新詩興起并掀起一波熱潮,然而早期的白話新詩寫實化和直白化的弊病凸顯,于是一種緊湊精簡又詩韻悠長的新型詩體——“小詩”應運而生。冰心、宗白華、朱自清、郭沫若及汪靜之等諸多詩人都創作過許多精美的小詩。1923年,隨著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華的《流云小詩》這三部“小詩”集的相繼問世,小詩創作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冰心的小詩與絕句和詞中的小令有些相似,但她的小詩不拘于嚴整的章法和格律的限制,句式排列和音節起伏隨著詩情流轉①。“冰心體”引領著早期白話詩由拖沓、寫實的文風轉向對人們內心微妙感受的表現。
宗白華的小詩實踐偏重哲理,淡雅中見深沉。宗白華的詩歌創作美學基于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結構,從內心深處升華出富有詩意的生命情調和宇宙意識。他將對個體生命和宇宙萬象的靜觀默照,交融互滲在星光與明月、花香與林木、云靄與細雨等自然意象當中,在經過錘煉的白話中點綴古文,從而在他的小詩中呈現出境與神會、靈動深靜之美。
小詩的“小”,是指它的字數,體式偏短,往往三五行為一首。小詩在意境情調和美學思想方面講究在凝練中寄情。觀其物象意境,便收覽眾宇之大千萬象。小詩以其形式短小見長,集中表現詩人的哲理體悟、瞬間的心理感受與美的情思,但一般不觸及重大的歷史和政治話題,僅僅是詩人生命之樹上的一瓣心香,因而難以表達更為復雜的內容和情緒。隨著現代人的情感世界日趨豐富,現代社會復雜多變,難以容納下“現代”這個復雜場域的小詩逐漸甘于寂寞,退出主舞臺。
周作人曾對“小詩”這樣詮釋:“這種小詩在形式上似乎有點新奇,其實只是一種很普通的抒情詩。我們日常生活里,充滿著沒有這樣迫切而也一樣真實的感情;它們忽然而起,忽然而減,不能長久持續,結成一塊文藝的精華。②”“小詩”非功利性更強,不像“微詩”那樣以求瞬時使讀者明悟,帶來即刻的審美震撼感以獲得心靈治愈。“小詩”言說的不是一種當時人們迫切的生存問題,而是純粹貼近自然的藝術。
現代小詩和當下“微詩”都旨在以簡短冷峻的語句,使讀者不消工夫便達到直覺頓悟的藝術效果。與小詩相比,微詩則顯得直白通俗。以熊國華的微詩為例,熊國華很注意詩歌語言的通俗流暢性,在乎一眼即明,不為精簡字數而將句子古文化,致使詩句晦澀難懂;兼顧視覺、聽覺媒介的傳播特性,將難以直觀的詩意和哲思化為簡明扼要的日常化語言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想象或留白化語言。例如熊國華倡導四行內微信詩歌寫作,在《熊國華微詩選》中收錄的所有詩都不超過四行,每行字數控制在十個字左右,在極有限的空間內精字煉意,以達到只言片語、以少總多的藝術效果。微詩吸取了四言絕句的精華形式,不同于其古典的高度凝練字句,微詩的語言策略要求明朗易懂中帶有言外之意的想象空間。
我們不應該把微詩僅僅看成是速效的碎片化讀物。微詩可以給予讀者即刻抵達的心靈感悟,但不代表它是粗淺直白的,當然也不是艱澀難懂的。微詩能有長足的發展空間還要得益于它的親切易懂性,它能更大限度地貼近讀者的當代情感需求,它通過簡短、哲思性、“及物”性書寫的特點獲得當今讀者更高的接受度。讀者能從微詩中得到即時的心靈撫慰,逃離繁忙的功利化的生活。
王小妮曾提出“重新做一個詩人”的概念③,新時代的詩人應該在商品經濟時代守住自身,將個人話語與社會公眾的“共通性情緒”互通,從日常生活場景中挖掘美妙的詩意。詩歌也要沾染人間的煙火氣息。客觀而言,微詩也符合這一期待。甚至可以說,微詩在一定程度上是“詩體解放”。
二、微信與微詩的傳播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詩歌逐漸處在被冷落的邊緣化狀態。隨著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文學逐漸走向社會生活的邊緣,而詩歌也便成為邊緣的最邊緣。步入新世紀,新媒體語境給予詩歌發展一種新的可能,互聯網給予詩歌一個嶄新的生存環境。
2011年,微信作為一種移動傳播媒介和即時溝通平臺應時而生,而后逐漸成為我國用戶群體最大的移動傳媒之一。微信成為價值取向的有效推手,深刻地鍥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更新了現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隨著掌上移動終端實現了與文學的聯姻,文學發展路徑得以拓寬,文學創作去精英化成為可能。在微信的土壤之上則孕育出微信文學,其隨處可讀的便利性和適應現代閱讀習慣的多維感官沖擊,使之成為當下最為重要的一種新媒介文學形態。
不是所有文體都適合“微”平臺的承載和傳播。詩歌這一以躍動靈巧的小體型獲得即時的審美震撼的文學形式,是最理想的微信文學體裁。微信拓展了詩歌閱讀中的感官享受和想象領悟空間,具有強大的承載、生產和傳播功能。它解決了傳統詩歌公共空間發揮效用的不足,兼容不受限制的私語空間以及開放自由的公共空間,微信詩歌讀與寫一般都能在短時間完成,讀者可以隨時進行翻閱分享、自由評論。微信詩歌通過詩人在詩歌群與詩友切磋交流,并且發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眾號,完成其傳播過程。微信公眾號相當于文學期刊和專業報紙的新媒介形式,但它是以訂閱推送的方式進行傳播的,相比而言更為大眾化。朋友圈,是一種僅限于個人小圈子內的私密分享交流領域,隨意性和主觀性較強,而其對于某些重大話題的轉發討論則容易迅速擴散、傳播到微博等不同平臺,從而形成突爆式影響。微信群則類似于一種虛擬平臺中的文學聚會和文學雅集,群內成員可自由地進行交流創作,激發創作熱情,促進彼此進步。微信文學滲透性強、傳播力強和日常生活化的特點使這些傳播方式盡情地各放異彩④。
微信作為一個日益成熟的視聽平臺,改變了詩歌的接受程度和傳播生態。微信詩歌依托微信平臺的多媒體技術,配上符合情景的圖片、視頻、音樂,各類藝術元素相輔,實現圖文合一、音畫兩全,在視覺和聽覺方面雙重呈現出文本交互影響的效用,使讀者更便捷、立體地理解詩歌中的意蘊。
微信給予了詩歌一個集結的地標,微信詩歌的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國際華文微詩群的群主熊國華教授提出“四行微詩”的新概念。一般意義上的微詩,可以指所有“微型”的短詩,也可以專指在“微信”上發表的詩歌。
當今時代,移動互聯網使我們進入一個嶄新的“微時代”。在微信平臺發表的“微詩”,也分廣義和狹義。廣義的“微詩”,指發表在微信平臺上的所有詩歌;狹義的微詩,指在微信上發表的篇幅短小的詩歌。熊國華所定義的“微詩”則指的是四行以內,配圖發表在微信平臺的微型詩。他以為:首先,微詩若加上配圖發在朋友圈,文字超過六行就會被隱蔽,必須點擊“全文”才能全部顯示。四行的詩歌加上標題和作者的姓名(或用一個符號把標題和正文隔開),正好六行,不用點擊“全文”即可接收全部信息,符合微信刷屏的閱讀習慣。其次,從中國詩歌傳播歷程來看,短小精煉的唐詩宋詞流傳最廣,尤其是四行的絕句。以四行為標準的現代“微詩”,可吸收古代四言絕句的精粹。同時,以熊國華為首的國際華文微詩群探索出以組詩的形式來擴大微詩的容量,如《熊國華微詩選》中的五則組詩《大地生態》《生肖節令》《異域風情》《瞬間滄桑》《叩問生命》,每首微詩都可以獨立成章,幾首微詩組合起來理解又構成一個意義整體,這一先鋒性實驗在專家和讀者群體中得到廣泛的認可。
這種詩歌形式是契合微信平臺的傳播形式而誕生的時代弄潮兒。其短小精煉、圖文并茂、瞬間閱讀、即時互動的特點緊貼著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和審美趣味。
三、以熊國華微詩為例分析當今微詩的類型寫作特點
近年來熊國華教授大力提倡微詩理論,也在微信上寫作微詩,成為國際華文微詩群的群主,在《羊城晚報》《詩刊》《詩潮》《新大陸》等海內外紙媒上發表微詩,并且出版《熊國華微詩選》。一般而言,“微詩”本身的短小形式是難以承擔更復雜的感情和更宏大的敘事。這關鍵在于詩人是否善于發現尋常中被遮蔽的本真意義,然后由這一極簡的藝術呈現方式托載而出。熊國華就是如此,他試圖由具象中窺見抽象的超現實意義,使得微詩也能燭照復雜的時代。
(一)戲謔出現代城市百態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質和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三個因素。其中“環境”因素是構成精神文化的一種巨大的外力。楊克曾形容廣東詩歌的文化生態特征獨具“海洋文化氣韻”⑤,善于吸納、溝通與包容。廣東滯悶濕熱的自然環境使其原住民迫生出寬和平靜地看待人事的樂天心態,不至于時常心生郁氣。生活在嶺南的詩人也很少在作品中表現出激憤怨懣之氣,而往往通過一種諧謔、揶揄式的反諷隱晦語氣看待不平之事。
廣東得益于新的時代發展機遇,成為得改革風氣之先的經濟發達地區。在廣東精神文化里,物質生活常常高于精神生活。廣東有最多的“流浪詩人”“打工詩人”,廣東詩歌的“草根性”特質很強,即從本地文化土壤里自然地生長出來,具有鮮活生命力的詩歌。
熊國華長年居住在廣東,受廣東本土文化的濡染,他的詩歌中既有一種溫情閑適的市井草根性,又有深刻的戲謔性。熊國華的詩歌創作具有即興性,他隨機拾取日常隨處可見的生活事物,展現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的精神狀況和生活狀態。經過藝術變調后,消解其原有屬性,變成耐人尋味的調侃。蘇軾說:“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熊國華的微詩帶有一種后現代嬉戲的意味。他如此言道:“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藝術,毫無意義的東西有時可能就是最有意義的東西。”他將“小蠻腰”看作“明星一般的大眾情人”,頌揚如“在誘惑中保持潔白優美的本色”的“小白鷺”般的廣東南沙原住民的質樸本性。他試圖營造古代與現代的時空對話,對文化和思想進行另一種進化的解讀,在非詩意空間重建城市中的詩學。
古代精神的氣定神閑和現代精神的急躁浮夸在熊國華的微詩中形成鮮明對比。他贊頌嵇康在死亡的大刀將揮下時還能視生死如浮云的淡然風骨,調侃“洋蔥”“比人類更加表里如一”,嘲諷《五羊雕像》越秀山上屹立著代表“羊城”的五只石羊,山腳下卻充滿酒店里吆喝消費的羊肉煲,穿著虛偽羊皮的現代人的這個崇尚消費與習慣虛假的時代。
他在《紀念》中調侃端午節本身深厚的悲劇意義發展到現代被消解成了一出熱熱鬧鬧的喜劇。人們不再從傳統節日本身去體悟其歷史價值,使端午節慢慢演變成膚淺的娛樂活動或者純粹的放假休息的時間。《故鄉記事》感慟于現代文明對自然的破壞,歌頌原生態力量的自然健美。《生肖節令》對中秋、冬至等傳統節日的緬懷與珍視。寂靜的游淌和浮躁的快速、永恒與急瞬在明晰的比照中凸現深刻意義。
熊國華由現代景觀追尋過去的歷史痕跡,追思其文明價值,試圖重新尋回與中國傳統斷裂的血緣紐帶,以時代精神重建曾被我們失落的詩歌傳統。由小處叩問世間萬象,從感官嗅讀歷史。正如柔軟的蚯蚓融不進城市堅硬的鋼筋泥土,詩人渴望一個清白的世界,他為充滿了“血污和病毒”的地球瘡痍哀怵,祈望觀音來洗滌世間的污垢。熊國華為基于社會現實語境而作的詩歌中注入了敬畏,是因為對現代冰冷機械的不信任,才轉而敬神憶古。他將現實與古典神話、歷史傳說進行多維的時空組接,在故作輕松的筆調中厚重的悲憫情懷悄然地于紙面暗涌。
(二)對當下自我的思考
熊國華基于世俗生活的百態,挖掘心靈與世界、情感與物象的雙向會通關系,以圖探得高于生活之上的宇宙人生的真諦之一角,獲得某種程度的自我超越。此處的“自我”有兩重含義,遭現代工業文明包圍隔絕的孤獨自我,以及在堅守中重構被現代化經濟與技術壓制的主體。熊國華在詩中十分重視個體生命的存在體驗,期望在凡俗世間當一個“菩薩一樣的自在人”。在快節奏的“消費時代”要寬恕從容地處世,堅守自己。
市場性和消費性覆蓋了人的主體性和個性,舞臺是公共的,狂歡消費隨心所欲,速度與浮躁伴生。“名片”崇拜也是對名利的崇拜,而名利再多也及不上靈魂豐盈。貯藏于詩人心中的詩情和詩性從未被商品經濟的利欲沖散,生活中的詩意需要在詩中堅守。
例如《同病相憐》中“一個影子對著光桿苦笑。”孤獨是現代普遍的癥候,四周都是虛空,自己形只影單地屹立。人精心修筑一面“墻”,隔絕了外界,將自己封閉其中。或許他是敞開的,但他最自我的東西永遠隱蔽在“墻”之內。
例如《現代烏鴉》中小小的烏鴉“刺入地心”留下“巨大的背影”。能在偉大處看到狹小,在渺小中窺見無限,個人所能站立的空間是狹窄的,但內心足夠廣闊,便足以心生萬象。
例如“從古至今都有拼爹的胎記,我寧愿獨立行走一生。”“拼爹”一詞有著濃厚的現代印記,“寧愿”一詞里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強烈,充滿現代性的反叛。
文學創作的雙重指涉對象包括對外指向社會大眾,以及對內指向作者自我。虛擬化的媒介空間易造成個人主體的退隱與消解,并日益左右詩人的歸屬感和認同感⑥。但人是需要有個人空間的,以求不被群眾空間的喧鬧吵擾內心。
例如《圣誕麗人》寫的是過生日時,將窗簾拉上隔絕了外界的黑夜,在自己的空間點上蠟燭,“我”更愛蠟燭的光勝于夜色,一個人的生日也自得其樂。現代人認為人生由自己自控,不喜歡被束縛,同時他們在失去文化氣息的失舊無根的狀態下往往又有著精神失落的孤寂感。
熊國華在這類詩中表達了對個體經驗與集體意識沖突的反思。魯迅曾主張:“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⑦”具有現代性語言表達應該是屬于“自己的”“活著的”與“直白的”。而我們深陷被集體話語主宰的境遇里,是否還能堅守屬于自己的人格和個人空間,保持與消費社會,與“眾”形成的適度的距離感?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三)社會關懷意識
熊國華的“微詩群”是以詩歌形式劃分的流派,不是由主題風格定型的,而他吸收了別具一格的新詩形式,以獨具社會意義的選材,作最契合現代人閱讀習慣之詩。文學生產始終與時代格局構成深層互動關系,寫時代之詩不難,難在如何在文學風雨飄搖的危機中秉持文學本性,使它真正契合時代需求又獲得崇高的藝術價值。
在網絡平臺的護持下,詩人的話語權不再受制,詩歌創作的自由化和書寫向度逐漸敞開。網絡詩人在藝術宗旨、主題選擇方面得以非功利化和去政治化⑧,然而互聯網資訊的便捷即時的紅利帶來的是當今詩歌的社會功能反而被重新審視。這不同于20世紀90年代之前面向無名大眾的宏大政治抒情,更不同于九十年代一味強調詩歌創作技巧或商品經濟大潮下,宣泄私人情緒的自我吟詠。值得贊詠的是許多優秀的詩人是懷著深厚的社會責任意識,創作深入公眾世界的詩歌作品的。近年來的地震詩潮、打工詩歌等獲得不俗影響都脫離不開新媒體的傳播效力。打工詩人鄭小瓊曾言:“雖然詩歌在這個商業化的時代已沉入了物質的海底,但是它永遠是我用來拒絕我精神坍塌的內在力量,是它支撐著我的內心不會隨著商業時代的到來而倒塌。⑨”真正有責任感的詩歌應該做到深刻地關切社會問題,極力傳達公眾的聲音。
于是詩人通過具有廣東打工文化色彩的《農民工》《留守兒童》現象,對瞻前不顧后的“羊城”指出調侃式的譴責。《農民工》受生活所迫不得不流落到另一個生存空間,青春在此耗費。《留守兒童》與父母長期相隔異處徒生茫然的思念。《野渡》中的空巢老人在破敗的原鄉“老舟自橫”……
對社會邊緣問題持續關注的責任意識是古往今來中國知識分子自詡的使命。他們對于“邊緣”有著異常的敏感和警醒,企圖將邊緣推至中心,不管是詩歌本身還是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于現代文明對天然的破壞,詩人們以一種物傷其類的哀憫情懷,恰切地描繪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現代農村空心化現象與繁華城市灰暗面。
(四)學者之詩的特點
現代小詩的代表詩人宗白華是學者,微詩的致力創作者熊國華也是學者,然而二人的學者之詩是有差異的。宗白華的小詩作為“學者之詩”,它往往是以“道”為生發點作詩,又以“道”為歸宿的。詩人將“道”寄寓于詩,意圖使讀者從詩中體悟出“道”,從而獲得精神境界的升華。宗白華作為純正的學人姿態和濃郁的詩人氣質合而為一的現代學者,既受古代佛教禪宗的審美情趣影響,同時又浸染了西方康德和叔本華等哲學思想,基于古典詩學,將“道”融入高于俗世的人生哲學高度。而熊國華作為當代學者,他筆下更多是熔鑄新時代生活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貼近平民大眾的啟蒙情懷。
而熊國華的微詩也具有哲理化的特點,表現出現代平民化的精神特征。從《斷臂的維納斯》的“斷臂”中遐想出“人生在世,該斷的還是要斷”,詩人不從斷臂本身去思考它的藝術意義,而是旋轉到另一種處世方式的思考維度。這是具有現代性的解讀方式,拋離本身而言他,詩句間充滿十足大膽的跳躍性思維。另外,熊國華在其微詩中表現出強烈的正反對峙又彼此共生共無的色彩。如“每一朵火焰中都藏有天使與惡魔”“舍與得是通向永恒的天梯”“貧賤與富貴一同流向大海”……當中有游戲式的玩味,也有玩味之上的哲理。世間萬物往往相對而存,貌似正反兩極,但也互為一體。如《世界之窗》“把窗口天天握在手中,透過窗口探世界。”這些詩歌或多或少都具有學者的理性化或哲理化的色彩。
四、結語
比起微型詩,微詩的概念更容易被人接受,這主要歸因于微信的作用。而相對于小詩而言,微信寫作與傳播和市井關注,應該是微詩的特色。然而客觀而言,微詩還不算成熟。不僅寫作未發展成熟,微詩的批評能力也良莠不齊,還未能建構起一套成體系的“微詩”審美標準。如國際華文微詩群為代表的微詩群更像放大版的“微信群”,人們可以在這個開放性的廣場里自由地交流,進行同題詩寫作和互相唱和便是國際華文微詩群的一大亮點。這種詩歌交流形式的好處在于,一旦有人寫出一首詩,另一個人要在他的基礎上努力寫出更好的詩,這樣良性激勵的方式使得詩歌標準隨之提高,詩人的創作水平也能因此提高。當然,它也可以是面向國際的詩歌平臺。《熊國華微詩選》收錄于《中外現代詩名家集萃》,其出版前言寫道:“叢書力求充分展示中外現代詩藝術體裁和表現手法的多樣化,盼能對中外詩的交流產生積極的影響。”而熊國華在當中也寫了相當一部分的外國風情詩,這樣推向世界的創作格局是值得贊賞的。
然而,我們必須理性地認識到微詩的大幅度創作和閱讀活躍是好事,雖然活躍不一定代表其生態環境是健康的,但當微詩紛繁浩渺,那么也定能淘洗出真正有質量的優秀作品。微詩的發表不需要經過審查,讀者可以隨意評判,這是其優點。只是,自媒體導致的價值多元化使得微詩美學標準紊亂,使得真正有質量的詩相對較少,使得詩歌缺乏公信力。雖然我們期待詩評家給予當代微詩一個標準,期待微詩的理論批評到位有力,但是關鍵還是在于微詩作者本身的藝術修養,微詩界目前還沒有出現一位杰出的詩人領袖,沒有出現微詩人中的標桿,未能將詩與藝術、社會、道德的關系盡善盡美地展現。
一言以蔽之,詩歌文體本來自民間,它是為大眾的,也是現實的,人人可以讀也人人可以寫。現代傳媒正是借對新詩藝術的傳播,傳播了一種現代的平民文化精神⑩。古詩詞沒有白話文那樣通俗易懂,當代不少受眾拒絕深入理解當中的濃深詩韻,只想做一種淺層的符號消費,這是快節奏的消費時代的心理需要,微詩可謂應運而生。我們可以引導現代讀者去接受古典時代的詩歌,但更要倡導現代詩人和讀者去創作屬于當代的優秀詩作,去領悟當代社會的詩意。而這,也是微詩詩人的任務。
注釋:
①何群.試論冰心宗白華小詩的審美特質及小詩衰落的必然性[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2).
②周作人.論小詩[J].覺悟,1922(6).
③王小妮.重新做一個詩人[J].天涯,1997(3).
④王大海.解析微信文學的存在方式及功能取向[J].神州,2017(19).
⑤楊克.天羊28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73.
⑥⑧孫曉婭.新媒介與中國新詩的發展空間[J].文藝研究,2016(11).
⑦魯迅.魯迅全集四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5.
⑨鄭小瓊.夜晚的深度[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120.
⑩周海波.傳媒時代的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