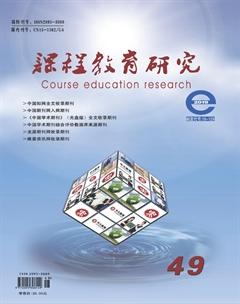日本文化的簡(jiǎn)素和崇物
【摘要】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社會(huì)呈現(xiàn)出越來(lái)越多的混血、多元的后現(xiàn)代特征,其文化精神也變得撲朔迷離。為了加深對(duì)日本文化的理解,本論文擬以日本當(dāng)代思想家岡田武彥的理論為基礎(chǔ),對(duì)日本文化中的一對(duì)相輔相成的范疇:“簡(jiǎn)素”和“崇物”進(jìn)行研究。
【關(guān)鍵詞】日本文化? 岡田武彥? 簡(jiǎn)素? 崇物
【中圖分類號(hào)】G131.3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5-3089(2019)49-0008-02
一、日本文化的簡(jiǎn)素精神
(一)簡(jiǎn)素的意義
簡(jiǎn)素是日本文化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所謂簡(jiǎn)素,就是表現(xiàn)受到抑制,而原有的內(nèi)面精神則變得愈加豐富、充實(shí)以致深化,這就是簡(jiǎn)素的精神,這就是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基本世界觀和審美觀。”簡(jiǎn)素并非岡田的首創(chuàng),但以往關(guān)于簡(jiǎn)素的論述大都限于日本文化的某個(gè)面向,沒(méi)有上升到世界觀和審美觀的高度。在文化交流過(guò)程中,日本向來(lái)都是以此為根本,積極地將外部先進(jìn)文化“簡(jiǎn)素化”,也就是日本化。其中,徘句是最為簡(jiǎn)素的文體。岡田引述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響。”并將其與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以及韋應(yīng)物“空山松子落”等詩(shī)句相比較,認(rèn)為芭蕉之句更加言簡(jiǎn)意賅,也就是更加簡(jiǎn)素,他認(rèn)為芭蕉的“簡(jiǎn)素”綜合了傳統(tǒng)的物哀、幽玄、靜寂、輕微、余情、細(xì)膩等范疇,又不僅僅局限于審美領(lǐng)域,在內(nèi)涵上更加還原,在外延上更為超越。
越是要表現(xiàn)深刻的精神,就越是要極力抑制表現(xiàn)并使之簡(jiǎn)素化,而且越是抑制表現(xiàn)而簡(jiǎn)素,其內(nèi)在精神也就越是深化、高揚(yáng)和有張力這就是所謂的簡(jiǎn)素精神。
(二)簡(jiǎn)素的精神表現(xiàn)
1.埴輪的心境
日本列島開(kāi)始使用陶器大約是在一萬(wàn)二千年以前,這正是繩文時(shí)代開(kāi)始的時(shí)候。那個(gè)時(shí)代的陶器種類非常多,并且被刻上各種紋樣。繩文陶器濃重而執(zhí)拗,富有超自然的過(guò)度裝飾性和獵奇性;奇特而神秘,具有魔術(shù)般的想象空間;既熱情飽滿,又滑稽可笑。
進(jìn)入彌生時(shí)代,由于實(shí)用性的關(guān)系,許多陶器沒(méi)有了裝飾性,變得簡(jiǎn)素清晰起來(lái),而埴輪則更加趨于單純化。埴輪是一種黃土色的土偶,足部成圓筒狀,而樣姿則被制成直立型的,反映出被日本風(fēng)土熏陶出來(lái)的素直而溫和的民族性。埴輪這種土偶,爽直得給人一種兒童般天真爛漫的感覺(jué),其造型藝術(shù)超越了客觀性和寫(xiě)實(shí)性而極富印象性,因而是極其簡(jiǎn)素的東西。而這種簡(jiǎn)素,不能不認(rèn)為是對(duì)單純裝飾性的否定。應(yīng)該看到,這正是當(dāng)時(shí)的裝飾文化走向集約,人工上回歸自然的必然結(jié)果。本文所謂的簡(jiǎn)素,其真意就在于此。
2.日本文化的特質(zhì)
通觀日本文化之全體,說(shuō)日本文化始終貫穿著簡(jiǎn)素之精神,恐怕并不為過(guò)。這里面蘊(yùn)含著日本文化的特色。若比較一下日中文化在日常生活態(tài)度上的表現(xiàn),就不能不承認(rèn)兩者的明顯差異。
中國(guó)的建筑物一般在色彩上是豪華絢麗的,中國(guó)的烹飪具有濃厚的人工味;與此相反,日本的建筑物是清純而質(zhì)素的,日本料理是品味鮮活而淡白的。
中國(guó)人擅長(zhǎng)理知性的論辯,這已在古代思想里表露無(wú)遺。比如古代中國(guó)人就寫(xiě)出了《周易》那樣的不朽著作,用消極和積極的陰陽(yáng)二極,根據(jù)交錯(cuò)、往來(lái)、循環(huán)、相生相克、調(diào)和等對(duì)立因素,詮釋了世界的全部現(xiàn)象,而且在古代就已提出了類似于西洋形式論理學(xué)的學(xué)說(shuō),產(chǎn)生了與古希臘時(shí)代同樣的詭辯派,出現(xiàn)了記述秘密克敵制勝的權(quán)謀術(shù)策那樣的著作。
即使立足于超越神秘主義的道家思想,例如《莊子》的《齊物論》篇,讀了后也會(huì)對(duì)其縝密的思辨性和超克的論理性驚嘆不已。而這些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幾乎看不見(jiàn)。
二、日本文化的崇物精神
(一)崇物的精神
與簡(jiǎn)素相表里,作為“日本思想文化的根本理念”的崇物,源于自然崇拜的民族心理。神、人、自然三位一體,神話、歷史一體兩面。日本文化具有極大的通融性,既能無(wú)礙地受容外來(lái)的文化,也能輕易地完成讓外人費(fèi)解的自我轉(zhuǎn)變,比如“二戰(zhàn)”時(shí)期從全民立誓“一億玉碎”到天皇一聲令下無(wú)條件投降。日本人的“暖昧”之處,不妨從崇物神道的角度去理解。
(二)日本崇物精神的表現(xiàn)
1.制物與崇物相互作用
西方的民族性因自我主張型而趨于理知化,日本的民族性因自我抑制型而趨于情緒化。西方人具有制物的思維方式,而日本人具有崇物的思維方式。
為什么會(huì)有這樣的差異呢?原因大致可以到兩者不同的自然與歷史環(huán)境中去尋找。
(1)自然原因
具有綿長(zhǎng)海岸線的、鋸齒形的日本列島,本來(lái)與大陸是相連接的,后來(lái)由于地殼運(yùn)動(dòng)而出現(xiàn)斷裂,從此氣候變得溫暖多雨,森林繁茂旺盛。這些都是大自然給予日本人的恩惠。日本的國(guó)土,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極富雅趣。所以,日本人對(duì)大自然的恩惠懷有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心,于是便產(chǎn)生了自然崇拜和萬(wàn)物崇拜的民族性。
(2)歷史環(huán)境
①日本人屬同一民族,且使用相同的語(yǔ)言,人與人之間的想法容易相通,沒(méi)有必要特意用論理的方式來(lái)表達(dá)自己的意志。
②日本民族與歐洲大陸民族不同,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與其他民族的殊死戰(zhàn)爭(zhēng),這種特有的被恩賜的自然人文環(huán)境,對(duì)保持日本的民族性無(wú)疑具有極大的幫助。
正因?yàn)榇耍毡救送曌匀慌c人為一體,而西方人則往往把它們看成是對(duì)立的關(guān)系,他們是為了控制自然才去探求自然的法則和原理的,由此而產(chǎn)生了使自然為人類服務(wù)的思維定式。也就是說(shuō)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制物的,而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是崇物的。
2.物是靈的存在
日本人自古以來(lái)就認(rèn)為物是有尊嚴(yán)的、有靈的存在,就像人有人格一樣,物也是有物格的。同樣,如果把人格視為有尊嚴(yán)的存在,那么也就不能不說(shuō)物格也是有尊嚴(yán)的存在。而且日本人還把這種尊嚴(yán)稱為神。所謂神,當(dāng)然不是西方文化那樣的一神教之神,也不是多神教之神。這是因?yàn)椋锉旧硎怯徐`的,所以物本身即是神。而且日本人尤其尊崇靈性這一純粹之物、偉大之物,將它作為極其敬畏的東西來(lái)崇拜,并把它作為祭祀的對(duì)象。
3.“崇”的意蘊(yùn)
從中國(guó)哲學(xué)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崇”若被解為崇敬,則類似于中國(guó)宋代程朱學(xué)派所謂的“居敬”。按照朱子的說(shuō)法,“敬”有以下三層意義:一是“心中不容一物”,此為尹和靖之說(shuō);二是“整齊嚴(yán)肅”,此為程伊川之說(shuō);三是“常惺惺”,此為謝上蔡之說(shuō)。
在上述三種意義中,朱子重視的是程伊川之說(shuō)。這是因?yàn)椋熳邮歉哌h(yuǎn)的理想主義者,所以為了達(dá)到伊川之“敬”那樣的境界,他便視物之理為整齊嚴(yán)肅的存在。而且朱子還把“敬”貫穿于動(dòng)靜之全過(guò)程,并以靜坐為入手之功夫。
但“崇物”與“居敬”,卻是貌合實(shí)不合。朱子學(xué)所謂的“居敬”,是為了探求物理,強(qiáng)調(diào)的是窮理之學(xué),所以以知之學(xué)問(wèn)為先,以居敬實(shí)修為后。因此,在朱子學(xué)那里,作為物質(zhì)要素的氣與理是被分開(kāi)的,理即氣之法或說(shuō)原理,窮理就是要究明知性之理,而“居敬”不過(guò)是對(duì)理的實(shí)修。
而崇物論,由于是直接對(duì)物本身的崇敬,所以不同于朱子學(xué)的“居敬”說(shuō)。具體地說(shuō),也就是與朱子學(xué)把氣與理分開(kāi),把敬作為理之敬的理知型做法不同,崇物論是對(duì)物本身即物之靈的崇拜和崇敬,故而屬于宗教式和情緒式的。
三、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簡(jiǎn)素是日本文化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其背后的哲學(xué)思想基礎(chǔ)則是崇物。
崇物論與儒、釋、道相比,對(duì)物的態(tài)度既有積極面,又有消極面。之所以這樣說(shuō),是由于佛、道皆主張超脫,故而對(duì)物的態(tài)度是消極的,儒教以經(jīng)世為目的,故而對(duì)物的態(tài)度是積極的;而崇物論所強(qiáng)調(diào)的自我抑制型的修行功夫,雖亦可稱作“退步思量”,但較之儒教,崇物論對(duì)物的態(tài)度要明顯積極得多。真正的崇物論,是主張物各得其所的,用儒教的話講,就是使其“物各付物”。但與儒教帶有明顯的理知傾向不同,崇物論所凸顯的乃是活潑和情意。
參考文獻(xiàn):
[1]岡田武彥.簡(jiǎn)素:日本文化的根本[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6.
[2]徐靜波.日本歷史與文化研究[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0.
作者簡(jiǎn)介:
孫雄燕(1978.08-),女,漢族,云南省保山市人,日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