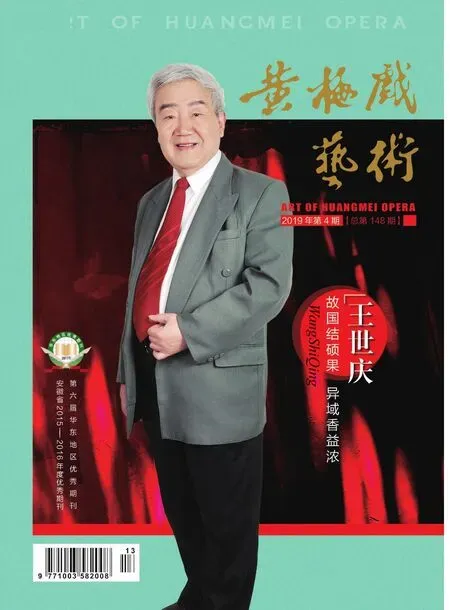地域文化成就黃梅戲
□ 余培蘭
位于長江中下游的宜城安慶是皖江文化的核心區域,素有“萬里長江第一塔”之稱,特殊的地理區位決定了其文化特征既不同于吳越文化的婉約柔媚,也不同于湘楚文化的瑰麗絢爛,而是呈現質樸清新、平易近人的風格。這里山川秀美,文風鼎盛,歷史上,皖江文化曾孕育出方苞、左光斗、姚鼐、方以智、陳獨秀、朱光潛等杰出人物。靈秀穎慧的自然人文生態不能不影響到黃梅戲的文化特質和藝術風格。“黃梅戲既不同于昆曲、越劇的柔媚幽雅,也不同于漢劇、湘劇的蒼涼高亢,黃梅戲是山野農民的田園牧歌,并在發展中逐漸受到城市文明和當地文人的浸染。”正因為如此,才得以呈現出黃梅戲質樸而不失悠揚、世俗而不失生趣的美學風貌。
黃梅調,其中有采茶調,每年谷雨后,成群結隊的青年男女,邊采茶邊唱民歌,而成了有名的歌鄉,而這些民歌歸納為黃梅調。
黃梅調在安慶發展過程中,和民間歌舞慢慢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載歌載舞的藝術形式,主要在元宵燈節時活動,所以又稱花燈。清道光前后,形成以演唱“兩小戲”(小丑、小旦)、“三小戲”(加小生)為主的民間小戲。后吸收徽調和流行在安慶地區青陽腔的音樂和表演藝術,演出了大戲。在形成的過程中,它還吸收了高腔、采茶戲、京劇、昆曲、漢劇、楚劇等眾多地方戲精華。由于在以安慶為中心的安慶地區長期流行,用安慶方言的念唱,逐步形成了獨特風格,故被稱為“懷腔”(因安慶府,懷寧縣同治),這就是今日黃梅戲的前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由于國家對地方戲曲給予足夠的重視,為加強藝術力量,國家陸續選派一些文學、戲劇、音樂、美術方面的專門人才參加了黃梅戲的改革工作。新老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黃梅戲的整體面貌煥然一新。黃梅戲從安慶小戲一躍而成為安徽省最大的劇種。至今,黃梅戲與黃山一起,并稱“安徽二黃”,成為安徽省的驕傲。
一、黃梅戲藝術多彩多姿,回味雋永
具有地方特色的黃梅戲藝術,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語言音調、生活習俗和審美觀念,地域性的民俗、民風等等差異,形成了民間文學和地方戲曲的五彩繽紛,它往往反映的是一個地域的生活色彩,洋溢著那個地域的鄉土氣息,這就使地方黃梅戲曲藝術,更具有風俗性和民俗性,向人們展現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畫卷,給人們回味雋永。
《夫妻觀燈》是黃梅戲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歌舞小戲,它的音樂唱腔,充分運用了我國民族民間的小調與調式發展的多種手法,是緊密地同劇本內容、體裁和表演風格相聯系的,隨著劇情的變化,有規律、有層次地交替使用各種調式的轉換,手法嚴謹、簡煉,凡是看過或聽過《夫妻觀燈》演出或演唱的人,都會對它的音樂留下絢麗多彩,深刻動人的印象。
黃梅戲《夫妻觀燈》,通過生動的歌舞表演,描寫了一對夫妻節日觀燈的情景,表現了他們對于生活的熱愛,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地方色彩,其歌舞表演源于勞動,卻又對勞動作了優美的衍化,使人領略到民間采茶舞的意味,加之地方風趣語言,鄉音土語,構成了黃梅戲風俗畫廊中的一幅幅色彩鮮明的圖畫。
黃梅戲劇種,以抒情見長,意味豐富、優美動聽,其唱腔如行云流水,委婉動人,根植民間,鄉土氣息很濃。唱腔卻明顯地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花腔為主要曲調 的“三小戲”,又稱“花腔戲”,只有二至三人表演,所反映的是農村生活片斷,比如: 《夫妻觀燈》、《打豬草》、《打豆腐》等等;另一平詞類則是正本戲,劇中人物多,表演一些民間故事、傳說,如大型黃梅戲《天仙配》、《女駙馬》、《山伯訪友》等等。對于黃梅戲的傳統唱腔,大體上它可分成兩個時期:一是解放前近百年歷史時期;二是解放后幾十年的迅猛發展與時俱進時期。這中間有源有流,有原生態、有現代的音樂氣息,它有中國的鄉村音樂之稱。這些音樂唱腔,經過長時間的考驗和廣大觀眾的認可,都是黃梅戲的寶貴財富,應該加以繼承和發展。這一系列的地方戲劇,大多是寫他們的勞動和愛情故事,其中有憧憬,有希望,也有諷喻、批評,譜奏成了一組原生態和諧田園的交響詩,向人們展示純樸的自然美。這種美又是生活的美、風俗的美,在戲曲百花園中爭芳斗艷,卻有自己的色彩、香味。
二、黃梅戲多以大團圓的喜劇為最基本特征
黃梅戲多以大團圓、喜劇的形式出現較多,其中的風土習俗有著極強的地域性以及風俗性,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了黃梅戲藝術的風格,它往往給異域的觀眾帶來清新的感受,所有地方劇種無不染上那個地方的風俗色彩,它使一個劇種能長期扎根在出生并哺育它生長的地方,并得以充分發展,民間藝術作品正是通過它自身的地域性即地方特色來顯示它自身價值的。
當現實生活中理想與現實相違背、結果與目的相反,現象與實質不相符,形成與內容不相符不相稱等不和諧因素時,觀眾的笑才會產生,產生了笑聲喜劇才會出現。
在美學中,喜劇性是作為說明和評價生活風尚習俗以及人的思想行為的一個范疇。喜劇除肯定正面的、進步的社會現象外,還引起人們對虛偽和丑惡現象的嘲笑、鄙棄和譴責。喜劇性的表現形式多種,除幽默和嘲諷外,還有怪誕等。在黃梅戲的劇目中,喜劇性的表現形成也不盡相同。《打豬草》、《夫妻觀燈》等從正面對健康的生活現象予以肯定,《打豆腐》則以主人翁之間的沖突和糾葛來體現其喜劇性。
黃梅戲小戲曲《打豆腐》主要體現著諷喻性。這出戲通過賣線紗和打豆腐兩個情節,一種是作為被贊美對象的妻子,勤勞、純樸;一種是被諷喻的對象,丈夫王小六,好吃、懶做。
黑格爾認為:“作為真正的藝術,喜劇所承擔的任務不是通過它的描述,把自在而又自為的理性表現為本身乘謬而又將崩潰的東西,而是相反地表現為:它在現實中,既不曾使愚蠢和非理性的、虛假對立與矛盾取得勝利,也不曾使他們持久地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