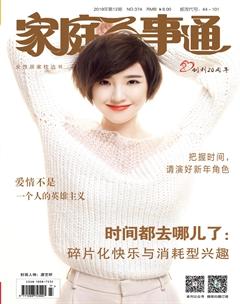小友,愿你面前的隧道都光明
1

在醫院當輪轉醫生時,給小朋友看嗓子的病痛可算作一件有難度的工作。我們常見的話術有三種——一是以溫柔的語氣說:“來,張嘴,給阿姨看你的牙牙白不白?”二是以神秘的語氣說:“張大嘴巴,啊——看看你嘴里有沒有蟲蟲”;三是舉著壓舌板心虛地說:“來,吃棒棒糖啦!”
其實,不管采用哪一種話術,我們“得手”后都少不了收到幾個來自純真的雙眼,卻像刀子一般冷酷的眼神。而且,根據我們的親身經驗,在出生8個月后,小朋友不僅學會了爬行,還學會了打人和扔東西砸人。
不過有次查房時,一位媽媽以其出色的應變能力折服了我。我像往常一樣說:“啊——張嘴就有糖糖吃。”勸說兩分鐘后,我借助壓舌板終于成功看到了小朋友的小嗓子。小朋友正預備大哭,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扭頭問媽媽:“糖在哪兒?”媽媽鎮定自若地答道:“剛才你張嘴時,哥哥直接丟進你肚肚里啦!”小朋友的注意力頓時轉向了自己的肚子,好像能透過肚皮看見那顆不存在的糖果。我們跟著松了口氣,趕緊趁機退場。
小孩子不光會哭,也有獨特的溝通技巧。他們溝通時最常見的就是以元音開頭,比如“Ahhh”和“Owww”。一位媽媽解釋道:“他們這樣做,一來是為了給自己壯膽,二來是為了嚇跑你們。”我們這些實習醫生雖然受到了“驚嚇”,但也感到一絲喜悅,畢竟孩子尖叫也是一種能便于我們看到嗓子的方式。哭可以裸露嗓子,喊可以裸露嗓子,亂吐唾沫也可以裸露嗓子,這都是讓我們感到高興的方式。
令我們頭疼的是另一種小朋友,他們牙關緊閉,雙眼緊閉,用一根手指死死地指著門口,仿佛一指就會有魔法,能讓眼前的人從那個地方消失似的。還有那些家里有二胎的,兩個孩子很容易互相傳染,他們的名字常常會成對地出現在掛號系統上,比如“14號麥克黃,15號麥克黑”之類的。這時詢問病情就會十分混亂,爸爸媽媽一會兒說老大,一會兒說老二,如果遇上服用退燒藥后的兩位小朋友重新打起精神,那就要看著他們繞著診室開始對戰。
但不管現場如何混亂,嗓子終歸要看的,畢竟炎癥于兒童往往首先體現在嗓子上。于是,在又一次想盡各種辦法撬開一名3歲小朋友的嘴巴后,他憤怒地用手指在我的前額比了個打槍的手勢,生動地表明了如果沒有槍支管理法,我們醫生將會面臨的命運。
看完嗓子后,小朋友都會異常委屈,一般是嗚嗚哭著要回家。聽到“嗚,我要回家”的哭泣后,有溫柔的媽媽把小朋友抱在懷里說“媽媽知道你想回家,先趴在媽媽肩膀上睡一會兒”;也有粗獷的外公用氣急敗壞的聲音吼“這么不聽話,回個屁”。但不管遇到的是溫柔,還是粗俗,獲得“放行”的小朋友都會如釋重負,因為,他們終于可以不用再見我們這些穿白大褂啦!
2
那么,我該如何形容這些小朋友呢?他們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的生物,他們充滿喜怒哀樂的生活溫暖了我的死水微瀾。他們的愛好十分奇特:“我不怕打針,我喜歡打針。”“阿姨可以送我個壓舌板嗎?”他們還常常答非所問:
“你最近咳不咳?”
“阿姨真漂亮。”
“上午拉了幾回?”
“這是個人隱私!”
這些都讓我想到生命的原初狀態——鮮活、純粹而美麗。
這種狀態在新生兒病房里體現得最為清晰。在那兒,一排排的恒溫箱里的嬰兒長期全體沉睡,間歇齊聲哭泣;多數時間是世外桃源,少數時間是百鳥齊鳴。在那里,人類的需求降到了最低——空氣、溫暖和乳清蛋白。嬰兒們集體沉睡時是如此安謐,我可以靜下心來想事情。
我想起很久以前,胚胎學老師在課上說:“胚胎最初沒有臉,面孔是從上下左右的突起向中軸愈合而成的,像花瓣向中心收攏,愈合不良的縫隙就成了兔唇、腭裂。所以在我眼里,每個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同學,都長得很美。”常常走神的我抬起頭,記下了這一刻。我看待人的方式,好像也從那時起改變了許多。
我又想起前幾天查房后討論一個患了川崎病卻沒有及時就診的小朋友。住院總醫師問:“這種華法林(藥名)要吃多久?”師兄答:“建議終身服用。”我立刻想,4歲起就要終身吃,要吃多少年呀,真夠煩的。住院總醫師接著問:“為什么要終生吃?”師兄冷靜地回答:“因為預后不良,壽命很短。”我突然愣住了。
3
兒科的輪轉即將結束,日子過得比較恍惚。有趣的事情天天有,但總體而言,我感到有些難過。
在俄國作家赫爾岑看來,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頭兩三年,是我們一生中最完滿、最優美的部分,它是惟一真正屬于我們自己的一段時光。人不知停頓地前行,總以為一生還在前面,直到有一天,經驗摧殘了春天的鮮花,才醒悟到生活實際上已經過去,剩下的只是尾聲。
現在的大人總是充滿焦慮,常常以犧牲孩子的童年和青春為代價,試圖換取長遠的終生的快樂。他們認為,成為精英才能使中年乃至老年都快樂無虞。但成年人所追求的那種快樂存在嗎?赫爾岑還說過:“完滿的、優美的快樂,我不知道,即使存在也是奢侈品或者贗品。”而小孩子的快樂,卻可以真切、純粹到令人怦然心動。無法推翻的事實是,這些孩子即將成為我們,而我們身邊的一些人,不管經歷多少精神污染,也都曾經是孩子。或者說,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成年人,在蒼老的世界面前,人即使是白發蒼蒼的老者,依然稚嫩如同嬰孩。
但稚嫩歸稚嫩,失落的東西永遠不會回來了。生命原初狀態的美、細密的感知力、豐滿的想象力,又或者生命力本身,永不再,永不再。再也不能以不成熟獲得諒解,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哭泣,再也不能無所顧慮地行事,這就意味著“被人所愛的時光已經結束了,現在該去愛別人了。”
很多人從沒得到過這樣的愛,卻突然被告知有愛人的責任。這有什么辦法呢,我們只能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抗住黑暗的閘門,給那些小朋友們爭取一些光亮。
在給小朋友們錄入就診信息的時候,我看到了“00后”“10后”“15后”,出生于2018年的、2019年的……我意識到了那個沉重的事實——歲月忽已晚,而等待我的小友們的,是同等或者更加艱難的環境。
一代人在成長的途中,失落的東西該向何處尋回?又有誰能補償呢?我不知道,今天保管著人類歡笑和眼淚的小朋友呀,請你們不要重復我們的路。但愿我們能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閘門,讓你們面前“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