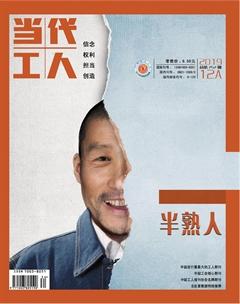兼職成傷
清桿
“看新聞沒,說咱公司欠銀行貸款快還不上了,二把手留下一封信,就卷錢跑了。”
還沒進廠門,老金就聽到工友們的議論,他忙下車,把自行車往身上一靠,掏出手機點開新聞搜索頁面,輸入所在工廠的名字。
果然,工友們說的前半句是真的,后半句雖無從考證,但估計也不是空穴來風。老金推著自行車往車間走,前天剛給備戰高考的女兒報了一個沖刺補習班,一節課800元,如果廠子沒錢了,工資獎金都斷了……老金不敢往下想,杵在半路愣了一會兒。
“不對啊,生產都正常,昨晚下班還跟什么都沒發生一樣,怎么說欠錢就欠錢了呢。”老金突然回過神,怎么都不能接受廠子因欠銀行巨額貸款還不上,導致資金鏈斷裂的事實。
走到工位上,老金無心工作,平時總喜歡給他加活兒,還愛刁難他的工作狂李主管,也轉了性子,一眼不瞧老金,翹起二郎腿,玩起手機來。
在車間繼續生產,坐辦公室的老金卻沒有任何工作的狀態下,挨過了春節,也按時發了工資。可春節過后,新聞開始迅猛地發酵了。
剛過完正月十五,老金等好幾個車間的職工都被通知,廠子資金鏈斷裂周轉不靈,為了不裁員一人,只能給大部分坐辦公室的職工放長假,這大部分人中就有老金。
“一個158人的車間,除生產一線外,只留了9個人,這其中包括車間主任。”作為一名普通職工,老金沒辦法抗爭,只能服從安排。
很快,廠子就與老金簽訂了一個長期休假協議,休假期間正常繳納保險,工資按一定比例發放,到老金這就只有500多元錢,至于具體的復工時間,協議說明要等通知。
老金回了家,女兒每周都要參加補習班,沒啥手藝的老金,只好翻出多年未用的駕照,在物流公司謀得一份司機的工作。因老金有單位,單位也給繳納保險,所以他只能與物流公司簽訂勞務合同,福利待遇自然比簽勞動合同的職工差一些。
老金倒是不在乎,他覺得自己早晚還是要回工廠的,“在那干了半輩子,不能半途而廢,現在來開車只是為了補家用,吃點兒苦不怕,權當磨煉自己了。”于是,老金平日開車特別賣力氣,別人不愿意接的遠活兒、累活兒,他都干。
畢竟老金好幾年都沒碰過車了,上路后多少有些生疏。這天出車因雇主耽誤時間,趕上了晚高峰,老金更緊張了,開出不到一公里,就冒了一頭汗,開到拐彎處,突然被一輛大卡車撞上了,他都沒反應過來,直接被撞傷了。
好在交警來到現場后,認定是對方司機負全部責任,老金才免除物流公司的責罰。老金被撞進了醫院,前前后后沒少花錢,這讓曾在工廠總為職工申訴需求的老金,突然想到一個詞,工傷。
于是,老金要求物流公司為他申請工傷認定,結果物流公司以老金原是工廠職工,與物流公司是兼職勞務關系為由拒絕。
多次要求被拒后,老金只好向當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這也讓老金看到了希望——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老金為工傷,物流公司應當承擔工傷保險責任。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專家觀點
納入司法框架才是最大的人文關懷
劉興偉? ?律師
雙重勞動關系是在我國特殊歷史原因下形成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勞動者自謀職業開始成為一種合法的就業形式,隱性的雙重勞動關系也隨之出現,一部分表現為返聘人員,另一部分則是停薪留職和第二職業者。
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產業不斷升級和推進,企業的人力資源開始相對過剩,為了安置相對過剩的勞動者,企業根據不同情況,對不同的勞動者采取停薪留職、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提前退休、直接下崗待崗,甚至因經營性困難、停產直接放長假等方式,以期達到分流過剩人員的目的。此時,雙重勞動關系正式從隱性走向顯性,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解釋(三)》),其中第八條對雙重勞動關系給出了明確的回應:企業停薪留職人員、未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內退人員、下崗待崗人員以及企業經營性停產放長假人員,因與新的用人單位發生用工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按勞動關系處理。可以說,這是將上述4類人員的雙重勞動關系的責任承擔作出明確劃分。由此就不難理解本期案例,老金屬于上述規定中企業經營性停產放長假人員。
雖然在上述4種情形中,勞動者與前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表面上尚未解除或消滅,但從實質上看,都是有名無實的,勞動者既不提供勞動,用人單位也不提供工作崗位,勞動者在此種情形下很難獲得滿足生活需求的工資報酬,用人單位也難以為勞動者提供職業保障和職業發展,更遑論為勞動者的人格發展提供條件。
再反向來看,勞動者與新用人單位間的用工關系,新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工作崗位,勞動者付出勞動,兩者間關系符合勞動關系的一切特征,如果不認定此種關系的勞動關系屬性,則會造成有實無名的狀態,這是認定勞動者與新用人單位用工關系為勞動關系的現實基礎。
對于《解釋(三)》,最高人民法院還表示,上述4類人員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生活水平低,生產技能落后,生存環境惡劣,更應得到社會的理解和法律的保護。法律理所當然的應當為這些人員的再次創業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以體現人文關懷。
誠哉斯言。對這些弱勢群體而言,司法領域能對其提供的最大關懷,莫過于將其納入到確定的司法框架中來,這本身也體現了我國司法的責任感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曾經一度有人認為,因社會發展帶來的問題該通過社會發展自行規范,然而,社會發展有一定的時間,在社會發展的夾縫中存在問題的人和家庭,卻是實實在在的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都是當下急迫的問題,不能統統推給歷史。如何將他們納入到統一的法律保障框架內,存在諸多技術上的問題,卻是司法領域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有將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放在心中,方能交出兼顧歷史與當下的出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