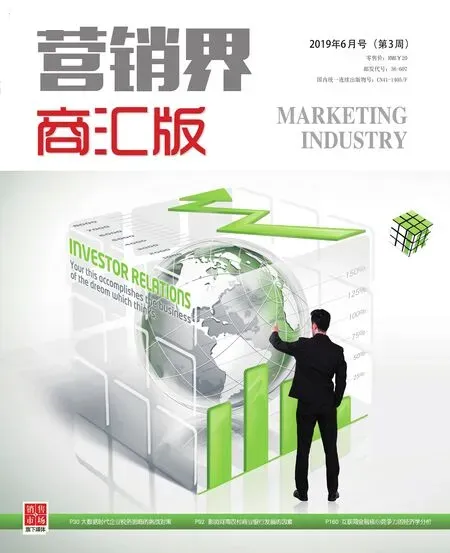企業管理視角下制造業企業知識創新能力維度測度研究
■李倩 何亮 李麗君 柳玉壽(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
一、研究背景
現階段關于創新能力研究共識是,企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企業的知識創新能力的增長方式也因其載體而體現出非線性增長特點。劉微微、李倩(2016)對知識創新能力的系統性進行分析,從群體智能視角,分析知識創新能力具有自組織、間通信、涌現性的特點。因為本文結合制造業企業的特點,從知識挖掘能力維度、知識共享能力維度、知識吸收能力維度對知識創新能力進行剖析。
二、知識創新能力維度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知識挖掘能力維度的測度指標
知識挖掘能力體現在捕獲外部知識的過程中,知識是分散的、隱藏的,需要企業具有辨識的能力,從浩瀚的知識中,尋找出有價值的信息。
(1)辨識可利用知識的速度(A1):企業內外部環境中存在者大量的游離的外部機遇,需要企業行使監聽者職能,搜尋、識別出有價值信息。
(2)引進外部知識的速度(A2):發現有價值的信息,并有決斷、有實效的快速對內外資源進行置換,為企業知識創新能力提升提供基礎。
(3)企業研發機構數及研發設備(A3):研發機構與研發設備是知識創新過程的重要載體,是知識轉化發生的集中場所。
(二)知識共享能力維度的測度指標
知識共享能力衡量的是指知識在企業成員間的傳遞強度,知識共享是區分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的重要指標。
(1)企業內部知識共享意愿(B1):這一指標可以衡量企業的組織文化是否適合創新,也能夠衡量組織結構與企業創新目標的耦合度。
(2)企業知識內部擴散程度(B2):企業的知識創新是一個流程、一個系統,有必要從知識鏈條的角度,分析知識的形成過程。知識在部門與部門之間傳播的范圍,決定了企業的協同性。
(3)企業與研發機構知識交流(B3):研發機構、產品銷售部門分別是知識創新的始端載體和終端載體,與之交流能夠保證知識的更新。
(4)企業組織結構對知識共享的匹配程度(B4):企業結構的層級數量管理幅度均會影響企業知識創新,能夠影響企業的創新效率、信息的傳播速度
(三)知識吸收能力維度的測度指標
知識吸收可以解釋為企業對知識捕獲、學習、接收和轉化等一系列活動,并對活動逐步優化,演化出持續搜羅知識的能力。
(1)整合新舊知識的能力(C1):外界知識紛繁復雜,企業必須分析自身條件基礎,與自身知識體系結合尋求可利用知識。
(2)當年企業發明的專利數(C2):制造業企業發明的專利是考核知識轉化效率的直接指標,代表知識轉化的速度
(3)將新知識提供給企業員工的速度(C3):知識存在顯性和隱性的區別,在職員中顯、隱知識的轉化依賴組織的支持,組織的培訓和交流是影響知識轉化的直接指標。
三、實證研究及結果分析
(一)問卷設計與數據收集
為了驗證維度劃分方式的正確性,本文設計了針對維度測量的調查問卷,調研共選取了天津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共3 所制造業企業為調研企業樣本。共發放問卷300 份,共回收242 份,其中有效問卷202 份,回收率為80.7%,有效率為67.3%。
本文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9.0 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對關于制造業知識創新能力構成維度的調研數據進行分析。
(二)信度檢驗
本文運用SPSS19.0 對卷數據進行信度檢驗,結果如表1 所示,三維度的Cronbach' sα 值分別為0.877、0.920 和0.923,均說明了因子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一致性,可以認為制造業企業的知識創新能力構成維度的測度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可靠性,數據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計算。

表2 知識創新能力構成要素的KMO和Bartlett檢驗
(三)效度檢驗及相關分析
本文對數據進行效度檢驗,利用巴特萊特球體檢驗、KMO 樣本充分性測度指標辨析指標之間是否存在統計相關關系。由表2 可知,KMO=0.862,Bartlett 球形度檢驗結果中的df 為55,Sig[0.001],達到顯著性水平,證明效度結構良好,此樣本可以繼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本文采用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共旋轉四次,正交化后識別出了三個因子,符合本文提出的知識創新能力維度劃分數量的假設,可以將知識創新能力拆分為知識挖掘能力、知識共享能力、知識吸收能力三個維度。
由表3 中的解釋方差可知,三維度共解釋了總方差變異的81.3%,其中知識共享能力占29.4%,知識挖掘能力占29.5%,知識吸收能力占22.4%,可以證明知識創新能力演化過程中,三維度起到的作用巨大且均衡
而后進行相關分析,從表4 數據分析,知識創新能力的三個維度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三維度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表4 知識創新能力各構成維度的相關分析
四、結論
本文通過文獻分析方法,發掘了制造業企業在培育知識創新能力的過程中,體現出了系統動力學的機理,并通過的PSO 原理對比分析,認為知識創新能力的演化可能在知識挖掘、知識吸收、知識共享三個方向有所體現,因而提出了知識創新能力維度的假設,通過因子分析、相關分析得出,該假設正確,為研究制造業企業知識創新能力演化打下了理論基礎,后續研究可在該維度劃分基礎之上,研究知識創新能力層次演進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