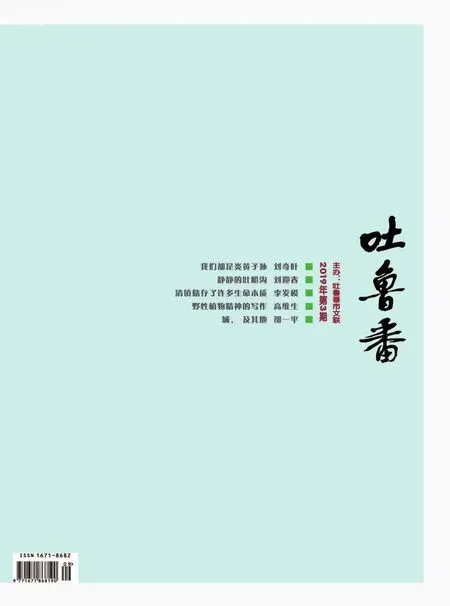何處尋覓黑氈房
任瑞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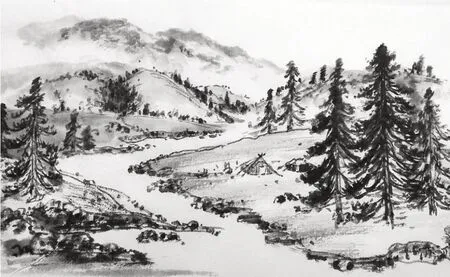
一
一場初秋的雨,洗去了夏的酷暑,風跟著行駛的越野車,肆意穿過草原,穿過豐收的麥田,穿過倒映著藍天白云山峰的蒲類海,在一排排嶄新整齊的村莊里駐足,凝望,哪里有黑氈房的影子?
呈現在眼前的是“它”被兩個壯漢,確切地說是三個,粗暴地抓住半個身子,用力地先將它褐紅色的頭部抬起來,生硬地搭到臟兮兮的雙排農用車上,然后一點一點往上推搡那個肥碩的后半身。
這里用“粗暴”“揪住”等動詞感覺實在不妥,只是無奈,都怪這個東西太龐大了,加上它還用力反抗,溫柔相待顯然行不通。
它痛苦地掙扎在初秋的陽光下,歇斯底里地吼叫著,驚恐或哀傷地望著圍觀的人群,好不容易躺在了車底板上,整個身子顫栗著,還沒來得及喘口氣翻起來,又被強行從車上拉下來放翻在地,將它的四個蹄子交叉捆綁在一起,重新抬上旁邊的磅秤。
人們的焦點,集中在它的體重上,聚光的程度似乎已將它融入一口沸騰的大鍋,濃香彌漫,79公斤有余的血肉構成的胴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居然趕上了一頭小牛,然而,它只是一只羊。
它被如此折騰也是因為太豐滿,忙碌的人們在圍觀一頭肥臀豐乳的奶牛時錯過給它留一個靚照的機會,為彌補這一缺憾只好委屈它第二次上磅秤稱體重。憤怒的羊,不明白人們的心,挑釁的雙目無意間與我對峙的那一刻,竟發現它沒有習慣思維上任人宰割的懦弱,倔強不屈,我膽怯,并敬畏一個生命的頑強。
我看到它眼里的仇恨,只是說不出來。事實上,人們是愛它的,如果它也有感知,它也知道四十頂黑氈房的前世今生,它會感激這一方水土讓它長成一個奇跡;如果它能聽到一個來自江蘇徐州的務工女子的話,同樣會感激這一方勇敢的人們,呵護它一如不會說話的兒子。
那位穿紫紅色外套、格子內衣的女子,稀疏的頭發在腦后扎成一束,瘦弱的肩上扛著一個長把鐵锨,精明能干溢于言表。她用濃重的江蘇方言告訴我,說是村民文化站的喧囂把她引來了。她說從江蘇徐州來這里將近10年了,之前跟建筑工地上的老板在自流井、吳家莊子修建富民安居房,今年又到了薩爾喬克。巴里坤的人真好啊,她順手指了指高遠的天,又補充一句:地方也好,天藍的像綢緞一樣,都不想回江蘇老家了。她嘿嘿一笑,牙齒白如玉。
二
順著她指的方向望過去,的確,明凈的天空掛著絲絲云彩,太陽已沒了盛夏的熾熱。縣文廣新局恰好選在這一良辰美景,與他們的哈薩克族親戚歡聚一堂,并展示他們半年以來的勞動成果。
牛奶誰家擠得多?羊兒誰家養得壯?花毯子誰家繡得好?得到通知的老老少少身著節日的華裳,肩上扛著、懷里抱著精致的刺繡掛毯,手里牽著羊,趕著牛,歡天喜地在村文化站大院里集中。
花毯子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直接鋪成艷麗的一圈,純手工藝作品,敞亮在高天下的大地上,構成一幅空前的絕唱。陽光斜斜地灑下來,他們在毯子上或坐或臥,溫暖、祥和。
一頭黑白花奶牛,被心急的男人們早早地牽來拴在鐵欄桿上,豐盈的奶水有噴涌而出的急迫,它忍受不住即將爆發的洪流仰天長嘯,牛不懂人的意圖,人又懶得去弄明白牛的想法,可憐可嘆。
孩子們滿院子撒歡,晃悠在健身器材上,翻滾在花氈上,奢侈地享受著開學前夕最瀟灑的一天。
江蘇籍女子癡癡地站在大門口,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滿院子走動的人群。她說,這里的人好客、實在、善良,不僅平時送牛奶給他們,遇到節日還請他們去家里做客。即便是偶爾路過,也喊他們去家里喝茶吃包爾薩克。
剛來的時候不熟悉,放在院子的東西還怕丟,后來發現,這些想法不僅多余,而且還是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不恭敬,更主要的是老鄉們從不欠工錢,讓他們干活的人很放心。她再次強調,你們巴里坤人真好!
來自遠方普通人,她只看到了她能看到的好,還有她看不到的好。她不知道,六十多年前,因苦難生活被迫遷徙的哈薩克牧民,告別大漠孤煙,黃沙落日,拖家帶口蹣跚而來的四十戶人家,在這個初升陽光照耀的地方卸下了一身疲憊,用三、四根木棍搭起被稱為“一撮毛”的氈房里棲息。毛氈因長年煙熏火燎,又黑又破佇立在天山腳下,久而久之,四十頂黑氈房取代了這個叫薩爾喬克的地名。那時,四十戶名義上是牧民事實上有二十多戶連一根羊毛也沒有,徒有虛名,想放牧卻沒有牛羊,想種地不會,前途迷茫,舉步維艱。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派遣工作組幫助他們開荒種地,學習耕種技術,徹底顛覆了祖輩千年流傳下來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變成了定居,由牧業又逐步走向半農半牧。
半個世紀過去,四十頂黑氈房被華章蓋世的富民安居房取而代之,象征著財富和地位的新氈房隨著現代文明奢華地鑲嵌在歲月的河床上,被歷史銘記。因而,四十頂黑氈房早已淹沒在滾滾紅塵中,不留一絲蹤跡。
三
而今,這里的人們,開天辟地從半農半牧又來了一個華麗轉身,在手工業、建筑業、運輸、餐飲等各行各業中大顯身手,且獨當一面。
一個叫朱馬別克的中年男子說,年初他承包了一個小工程,正準備要干時,對方說需要一個撒東西他說不上,他上初三的兒子接上說,要一個工程預算表,他爸爸不知道咋弄,就快快去找他叔叔吳同生幫忙,吳叔叔是文廣新局的局長(現已成為薩爾喬克鄉黨委書記),平時很忙,了解清楚他家情況后,就趕緊找人做了個預算表,最后就把活給承包下來。工程驗收后拿到工錢,他們一家都很開心。吳叔叔有空就去他家問家里還缺啥東西,還給他買吃的買學習用品,孩子一臉自信一臉笑意,滿滿的自豪感讓人心生愉快。
這一里程碑式的標注,值得大書特書,再回首時,他們從一無所知到無所不能,活生生的現實足以讓前輩們淚流滿面,讓后人們奮斗不止,由此可見,教會人們成長的,不是歲月,是經歷。
那個江蘇籍的女子還沒看到,9歲的古麗丹,一個機靈的小姑娘,說她的阿姨成冬云,每次來都給她買好多東西,過生日買蛋糕,書包本子還有清油、面粉,身為電視臺副臺長的成冬云就像她親阿姨一樣呵護她,關心她家吃的、穿的、住的好不好。
還有一個叫沙亞江的女孩,羞答答地雙手拽著廣電局記者左娟的胳膊,偎依在懷里,親熱地一口一個姐姐,她媽媽還給左娟手腕戴上了一個明晃晃的銀鐲子,左娟也是一臉喜氣,伸長胳膊讓同事們羨慕。
項目部主任王學峰,得知自己親戚家的孩子剛剛考上了大學,因來的匆忙沒帶錢,他特意借錢專程去看望……
四季更替,生活總有種種神奇的巧合與相似,隨時上演著不同的故事。六十年前,他們破衣爛衫住在四面透風的“一撮毛”里忍受饑寒交迫,是共產黨人領導他們與自然抗爭,才有了今天四十頂黑氈房的與眾不同。六十年后,仍然是黨的干部與他們牽手共謀發展,許多細枝末節的關照,無法一一記錄。梳理久遠的記憶,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榮譽感和自豪感。
我相信,這種感慨不僅僅限于我,還有見證了四十頂黑氈房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它改天換地的恢弘已根深蒂固滲透到生活中,蔓延之勢世代相傳。
因為這里是第一批巴里坤縣哈薩克族農牧民共產黨黨員的發源地;有第一批學會春耕夏管秋收的哈薩克農民;有第一批被毛主席接見的哈薩克干部;有第一所農牧民自己的學堂;有一大批走向領導崗位的少數民族干部;還有從“一撮毛”衍生出來的龐大豪華氈房,破天荒地走出國門,還有……還有……
這種不負皇天后地情感,不僅親歷者刻骨銘心,后來者也一樣感懷激烈!
那些呼之即出的靈魂,讓我在銀月灑滿一室微涼的夜,舍不得就此打住,在內心深處,虔誠地向那些從游牧到定居轉變的文明之始,不約而同地向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致敬,因為這種用生命、用智慧抗爭的精神,既關乎向一種未知物質生存方式的挑戰,又關乎一方人的精神獨立,這種為生存和發展的不屈不撓,正如“蘇吉”這個小村的名字一樣,從鴻蒙中蘇醒之后,在親愛的祖國這個大家庭里過得吉祥安康,值得我,值得所有生活在這塊熱土上的人們欣慰、敬仰、書寫、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