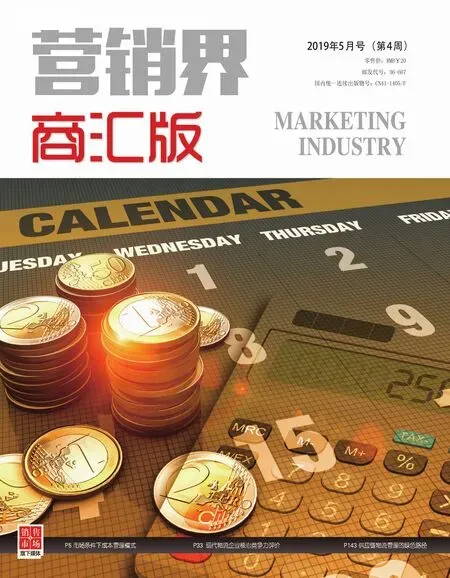個稅免征額提高對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影響研究
王玉娟 方可 王賽賽 龍天
一、個稅免征額改革歷程
我國的個稅制度的建立是一個從無到有并且不斷完善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還沒有建立統一的稅收制度。個人所得稅制度正式確立是在1980 年,其標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出臺,它規定免征額為800 元。由于當時改革開放剛起步,國內經濟水平較落后,國民工資水平普遍低,實質上有很少的人納稅。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收入逐漸兩極分化,為了更好的發揮個稅調節收入差距、保障社會公平的作用,2005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免征額提高到1600元。2007 年物價上漲,CPI 同比增長達6.9%,創10 年來的歷史新高,這就迫切要求進一步提高免征額,否則人民的負擔無形之中加重,因此2008 年免征額進一步上調到2000元。2010 年經濟高速發展,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收入和支出水平都普遍提高,于是結合實際2011 年再次將免征額提高到3500 元,至此7 年來,我國沒有調整個稅免征額。2018年,我國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達到5630.1 元,3500 的免征額顯然已不適用。2018 兩會激烈探討,反復斟酌,慎重決定于10 月份將個稅免征額上調至5000 元。
二、免征額提高對中低收入者影響
(一)免征額提高更多惠及中低收入者
據國家稅務局的相關資料顯示,剔除專項扣除等新政策的影響,2019 年第一季度個稅累計減稅1540 億元,累計已有9163 萬人的工薪所得即中低收入者無須繳納個人所得稅。對于免征額提高帶來的稅負變化如下:當扣除標準從3500 提高到5000 后,月薪5000 以下的無須承擔稅負,稅負降幅100%;月薪8000 的稅負在免征額提高前后分別為345 元和90 元,每月減少了255 元,稅負減少率為73.9%;月薪10000 的稅負在免征額提高前后分別為745 元和290 元,每月減少了455 元,稅負減少率為61.1%。同時進一步計算,我們發現可以歸納出月薪在5 千至2 萬的區間內,個稅稅負降幅大于50%,月薪在2萬至8 萬的區間,稅負降幅遠小于50%。就中國整體狀況來看,能達到月薪2 萬的人還是少數,在社會占的比重低,所以上述數據說明,免征額提高更多惠及的是中低收入者,而非高收入群體。
(二)免征額提高影響中低收入者整體消費水平
在現實生活中,影響個人消費的因素有很多,如收入情況、物價、利率、社會保障制度、風俗習慣等等。凱恩斯認為,存在一條基本心理規律: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是消費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此次免征額上調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了支付水平。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免征額上調會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水平。為了驗證實際情況是否符合理論,筆者從國家統計局網站搜集整理2007 年至2019 年1 季度中低收入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其中免征額經歷過3 次調整,將這些數據用stata 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到表1 的結果。以y 表示人均消費支出,以x 表示人均可支
配收入,表中便可以得到線性公式y=0.62+2168.75.這表明從2007 年到2019 年中低收入者人均消費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62,顯著相關,但是沒有達到0.8 以上的高度相關。所以,我們不難得出免征額上調給中低收入者帶來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促進消費,提高了中低收入群體的整體消費水平。

表1 中低收入者收入與消費回歸分析結果

表2 中低收入者各項人均消費支出占比
(三)免征額提高影響中低收入者消費結構
消費結構是指各項消費支出占總的消費支出的比重,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習俗和經濟發展水平。一般說來,一個國家如果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占家庭總支出比重很小,而教育、休閑娛樂、衛生保健、服裝等非必需品支出在家庭總支出中占很大比重,說明這個國家較發達。相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消費結構的特征是:基本生活必需品在家庭總費用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目前我國正大力推進消費結構升級,即從基本生存型向發展享受型轉變,形態上看從實物消費想服務消費轉變,
眾所周知,最新一次免征額調整正式落實為2018 年10 月份,為了保證數據的即時性,筆者選取了2018 年四個季度中低收入群體具體消費數據,經整理計算得到表2。從表中可以看到,第四季度相比于其他3 個季度來說,食品、衣著、
生活用品等剛性的消費支出占比下降,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占比明顯增加,說明免征額調整帶來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不僅滿足了人們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改善了消費結構,他們有多余的錢進行娛樂休閑,發展自我,提高了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幸福感。
三、結論及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免征額上調對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整體消費水平、改善其消費結構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僅依靠目前的免征額制度來刺激消費,作用十分有限。為了更好的發揮個稅改善民生、縮小收入差距、促進消費的作用,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國內外經驗,對我國免征額制度改革提出一些建議。
(一)國外經驗借鑒
我國扣除標準基本處于“一刀切”的模式,而國外充分考慮了人的生存發展權,將年齡、婚姻、家庭、收入水平等考慮其中。這種以人為本的扣除標準設置值得我國借鑒。
首先,要加快向綜合稅制的轉換步伐。綜合稅制更能體現公平,目前美國、日本、甚至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的個稅制度模式,都已全部或部分采用綜合制或混合制。其次,可以實行浮動制的扣除方法。以美國為例,其免征額的確定與各地的物價水平和當年的通貨膨脹率相關,是一個相對彈性的數字,具有時效性和真實性,人民的接受程度高。而我國就是預先確定的一個固定值,沒有考慮到地域發展差異和真實收入水平,有些年份難免會有失公允。最后,確定免征額應當將家庭因素作為重要參考標準。目前我國計稅單位為個人,而外國大部分是以家庭為單位,這樣可以考慮不同家庭的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體現了人性化,又能更好的調動了居民納稅的積極性。
(二)完善我國免征額制度建議
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專項扣除為輔的補充免征額制度,即規定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這四項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專項附加扣除。而對于專項扣除標準實施還需不斷細化完善。第一,教育和醫療支出扣除標準和核算方式需要根據居民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來決定,教育支出應該區分不同階段即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這兩個階段應實施不同的扣除標準;第二,住房貸款利息扣除要考慮個人房屋用途和房產多少的影響。對于住房和投資性房地產應建立不同的扣除機制,個人擁有多處房產的應出臺相關規定限制扣除;第三,住房租金實施不應該全國統一標準,而應該從實際出發,以地方為單位,根據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租房所在地房價綜合考慮,從而確定合理的扣除金額。
此外,部分勞動所得實行綜合征稅,單一的代扣代繳機制已不適用,個人自主申報的繳稅形式會逐漸推廣,要重視完善自主申報機制。結合今年剛出臺的反避稅條款,個人自行申報這一新制度可以運用互聯網和數字化技術,重點整合個人納稅信息和個人征信系統,大大降低征管成本,建立一個科學、全面、現代化的個稅征管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