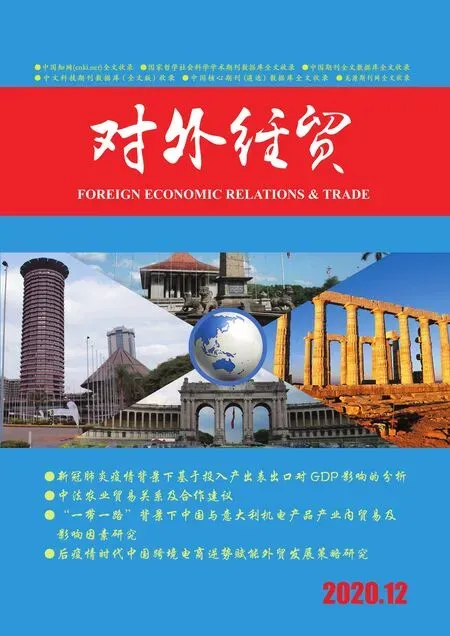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意大利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及影響因素研究
戴慶玲 侯靜怡
(湖州職業技術學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一、引言
意大利是最早同中國開展貿易往來的歐洲國家之一。中意兩國的交往始終貫穿著歷史文明和人類才智,展現出無可比擬的獨特性[1]。早在1970年兩國就簽署了建交公報,2004年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建立后,兩國經貿迅速增長。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顯示,2018年中意雙邊貿易額達544.18億美元,意大利已成為中國在歐盟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同時,中國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兩國在機電產品貿易的表現尤為突出,成為雙邊出口創匯的主要產品。2018年中向意出口機電產品占其全部出口的43.25%,同時意向中出口機電產品占其出口總額的37.72%。2006年后,中國與意大利機電產品貿易從逆差轉為順差,且順差額逐年增大。中意機電產品貿易總額由1992年的13.26億美元增長至2018年的223.65億美元,年均增速達11.97%,其中,中對意機電產品出口額由0.55億美元增至143.85億美元,年均增速達24.98%,中從意進口由12.71億美元增至79.79億美元,年均增速為7.62%。同時,中國與意大利機電產品貿易額占中國與世界機電產品貿易總額的比重逐年下降,其比重由1992年的3.02%下降至2018年的1.09%。
機電產品是中國向意大利出口和從意大利進口最多的商品類別,而這一大類下兩國相向出口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實際水平和結構。隨著2019年中意政府間關于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的簽署,意大利成為了“七國集團”首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重新審視雙方機電產品貿易現狀,深入分析其產業內貿易的水平及影響因素,對兩國經貿發展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
二、中意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測度
(一)產業內貿易衡量指標體系
1.靜態指標
利用1975年由格魯貝爾(Grubel)和勞埃德(Lloyd)提出的GL指數測算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靜態水平,具體公式為:

其中Xi、Mi分別表示中向意第i類機電產品出口額和中從意第i類機電產品進口額。GLi指數取值為0到1之間,GLi指數越接近于0,表明兩國第i類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越低,反之則表明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本文根據UN Comtrade數據庫SITC第三次修訂版,選取的機電產品為SITC第7類。
2.動態指標
為了彌補靜態指標不能完全反映產業內貿易水平動態變化這一不足,本文引用1994年布魯哈特(Brulhart)提出的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簡稱MIIT,作為衡量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動態指標,具體公式為:

3.分類指標
為了進一步了解中意機電產品貿易的質量差別和產業內貿易結構,本文引入1995年格林納威(Greenaway)、海因(Hine)和米爾納(Milner)提出的GHM法,該方法將產業內貿易分為水平型產業內貿易(HIIT)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VIIT),通過測算兩國貿易產品的單位出口價值(UVx)和單位進口價值(UVm)的比值來判斷產品的貿易結構。具體公式為:

(二)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分析
1.中意機電產品貿易規模和結構
根據UN Comtrade數據庫整理可知,中意雙邊機電產品貿易額逐年擴大,但貿易結構不平衡。首先,從兩國機電產品貿易增速來看,1992—2018年間,中意機電產品貿易總額增加了16.87倍,年均增速為11.97%。其中,中向意出口額增加了263.65倍,年均增速達24.98%,中從意進口額增加了6.28倍,年均增速為7.62%。可見,中意機電產品進出口額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且出口增幅尤為明顯。其次,從中意機電產品進出口種類來看,1992—2018年間,中意兩國機電產品進出口種類多樣化。1992年中意雙邊機電產品貿易以個別工業專用機械(72)為主,占中意雙邊機電產品貿易總額的50.41%。到了2018年,兩國機電產品貿易額排名前四的是一般工業機械和設備(74),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77),電信和音響設備(76)和個別工業專用機械,其貿易額占雙邊機電產品貿易的比重分別為25.23%、18.54%、15.58%和10.15%。第三,從中意兩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差額來看,1992—2005年間,中與意機電產品貿易呈現逆差狀態,1996年中對意貿易逆差額高達20.33億美元。2004年5月兩國正式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為中意關系注入了新的活力。2006年中與意機電產品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此后順差額在波動中上升。2018年中對意貿易順差額達64.05億美元。第四,從雙邊機電產品貿易結構來看,中國在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75),電信和音響設備(76),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77)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中順差額逐年增大,而在個別工業專用機械(72)、金屬加工機械(73)、道路車輛(78)和其他運輸設備(79)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中存在較大逆差。可見,技術差異是兩國機電產品貿易結構互補的主因。
2.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水平分析
(1)靜態指標測算結果
根據公式(1)測算了1992—2018年中意兩國機電產品的GL指數(如表1所示),總體來看,中意機電產品GL值由1992年的0.0823上升為2018年的0.7136,年平均值達0.65。可見,中意機電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由低水平轉變為了較高水平。具體來說,不同類別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有著不同的變化。首先,從機電產品兩位數細分類別的GL指數來看,發電機械設備(71)、一般工業機械和設備(74)、道路車輛(78)和其他運輸設備(79)的產業內貿易由較低水平上升為較高水平;個別工業專用機械(72)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近年來有上升趨勢,2015年其GL指數首次大于0.5,2018年上升到0.6251;金屬加工機械(73)常年處于較低水平的產業內貿易;而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75),電信和音響設備(76),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77)由較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轉變為了較低水平的產業內貿易。

表1 1992—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兩位數)產業內貿易GL指數
其次,從機電產品三位數細分類別的GL指數來看(選取2018年SITC7進出口貿易額排名前十的子項,該10大子項的貿易額占中意機電產品貿易總額的52.70%。結果如表2所示),旋轉式電力設備(716),未另列明的電信設備(764),未另列明的電動機械和設備(778)的產業內貿易由產業內貿易轉變為了產業間貿易。其他特種工業專用機械和設備及其未另列明的零件(728)長期處于產業間貿易,近年來其產業內貿易水平有所提升。加熱和冷卻設備(741),氣體壓縮機和風扇(743),龍頭、旋塞、閥門及類似器具(747),汽車的零件及附件(784)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了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自動數據處理機及其設備(752)處于較低水平的產業內貿易,且呈下降趨勢,2018年其GL指數為0.0752。小汽車或客運汽車(781)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呈現由低到高再至低的狀態,1992年其GL指數為0.0007,在2008年上升至0.9117,到了2018年下降至0.0788。

表2 1992—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三位數)產業內貿易GL指數
總之,靜態結果顯示中意機電產品已于1999年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了產業內貿易。此外,機電產品大類下子項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變化不同,一些產品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了產業內貿易,如發電機械設備、一般工業機械和設備、道路車輛和其他運輸設備等;一些產品長期處于產業間貿易,如個別工業專用機械和金屬加工機械等;還有一些產品由產業內貿易轉變為了產業間貿易,如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電信和音響設備,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等。
(2)動態指標測算結果
根據公式(2)測算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動態指標(如表3所示),1992—1998年間,中意機電產品的 絕對值大于0.5,表明該階段中意機電產品處于產業間貿易,1999—2018年間,絕對值中一半以上小于0.5,說明此階段以產業內貿易為主,且處于較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這與靜態測量結果基本一致。具體來說,從機電產品兩位數細分類別的 絕對值來看,與靜態結果一致是,發電機械設備(71)、一般工業機械和設備(74)產業內貿易由較低水平上升為較高水平;金屬加工機械(73)的 絕對值都大于0.5,且接近于1,表明其處于產業間貿易。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77)由較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轉變為了較低水平的產業內貿易。與靜態結果不一致的是,個別工業專用機械(72)1992—2005年的 絕對值大于0.5,自2006年以來,大多數年份的 絕對值小于0.5,表明其產業內貿易自2006年就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了產業內貿易,期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而靜態結果顯示該產品于2015年才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產業內貿易。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75)、電信和音響設備(76)的 絕對值在大多數年度都大于0.5,可見這兩類產品一直屬于產業間貿易,并沒有像靜態結果顯示的由產業內貿易向產業間貿易轉變的狀態。道路車輛(78)和其他運輸設備(79)的 絕對值基本大于0.5,說明這兩類產品屬于產業間貿易,并沒有像靜態結果顯示的已經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產業內貿易。

表3 1993—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兩位數)產業內貿易MIIT指數
從機電產品三位數細分類別的 絕對值來看(如表4所示),與靜態結果一致是,龍頭、旋塞、閥門及類似器具(747)的 絕對值于1998年前大于0.5,自1999年及以后小于0.5,可見,該產品產業間貿易轉變為了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自動數據處理機及其設備(752)的 絕對值在大多數年份大于0.5,表明該產品處于較低水平的產業內貿易。小汽車或客運汽車(781)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呈現由低到高再至低的狀態。與靜態結果不一致是,旋轉式電力設備(716)的 絕對值由大于0.5逐漸轉向小于0.5,期間存在一定的波動,從整體來看,該產品正由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轉變,并非靜態結果顯示的由產業內貿易轉變為產業間貿易。其他特種工業專用機械和設備及其未另列明的零件(728)長期處于產業間貿易,且近年來其產業內貿易水平并沒有像靜態結果顯示的上升。加熱和冷卻設備(741)、氣體壓縮機和風扇(743)和汽車的零件及附件(784)的 絕對值除部分年度外,基本大于0.5,表明該產品始終處于產業間貿易,并沒有呈現出靜態結果顯示的由產業間貿易轉變為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未另列明的電信設備(764)和未另列明的電動機械設備(778)的 絕對值除個別年份外,基本大于0.5,表明該兩大子項處于產業間貿易,并沒有呈現出靜態結果顯示的由產業內貿易轉變為產業間貿易的勢態。

表4 1992—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三位數)產業內貿易MIIT指數
(3)分類指標測算結果
根據公式(3)測算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分類指標,1992—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貿易排名前十子項的分類指數在(0,0.75)或(1.25,+∞)范圍內,可見,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以垂直型為主。具體來看,旋轉式電力設備(716)在大多數年份的分類指數值在[0.75,1.25]范圍內,屬于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加熱和冷卻設備(741)、氣體壓縮機和風扇(743)和未另列明的電信設備(764)有少部分年份的分類指數值在[0.75,1.25]范圍內,說明這三類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呈現波動,總體以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為主。其他子項如728、747、752、778、781、784的分類指數值常年在(0,0.75)或(1.25,+∞)范圍內,都屬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

表5 1992—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三位數)產業內貿易分類指數
三、中國與意大利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來源及符號預測
1.變量選取
國內外學者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強永昌(2002)較全面地將其概括為了兩個層面:一是國家層面,包括人均國民收入、經濟發展水平、國家規模、一體化程度、地理因素、要素享賦、對外開放程度、貿易失衡、國家政策和國家平均關稅水平等;二是產業層面,包括規模經濟、市場結構、產品差異化程度、國際直接投資和技術進步等因素[2]。本文將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GL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GL),選取的解釋變量包括人均收入差異、經濟規模、國際直接投資、技術進步、對外開放程度和“一帶一路”倡議。
(1)人均收入差異(DPCI)
林德(Staffan B.Linder,1961)的需求相似論指出人均收入水平對兩國產業內貿易產生一定的影響。當兩國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時,則相似需求的產品種類越多,兩國越有可能進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反之,當兩國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越大時,則相似需求的產品范圍越小,兩國越有可能進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3]。可見,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越小,消費需求越相似,產業內貿易開展的可能性越大。此外,若兩國國民收入提高,則會促進新的重復需要的商品的產生,從而貿易也相應擴大。用中意兩國人均GDP之差與人均GDP之和的比值來表示中意人均收入差異,具體公式表達為:其中PGDPi和PGDPj分別表示中國和意大利的人均GDP。
(2)經濟規模(ES)
丁伯根(Tinbergen,1962)認為,一國的經濟規模決定了其與他國進行貿易的比較優勢,且該國的出口供給能力和進口需求潛力與經濟規模成正比。從出口方面來看,經濟規模越大,表明其生產能力越強,生產規模的提高能促進出口供給能力的增強[4];從進口方面來看,經濟規模與產業結構關系密切,一國經濟規模越大,則市場需求也越大,制造業在國民經濟的比例也會越大,差異化產品越來越多,國內市場難以滿足不斷增加的差異化產品需求,進而進口需求潛力會更大。用中意兩國GDP的平均值表示兩國經濟規模,具體公式表達為:ES=(GDPi+GDPj)/2,其中GDPi和GDPj分別表示中國和意大利的GDP,下同。
(3)國際直接投資(FDI)
蒙代爾(Mundell,1957)和馬庫森(Markuson,1985)等學者探討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前者認為若存在國際貿易壁壘,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間是替代關系,提出了“替代模型”;后者指出國際投資與貿易間的關系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提出了“互補關系模型”。總結來看,國際直接投資與產業內貿易之間表現為替代或促進的關系。具體而言,國際直接投資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與投資動機密切相關[5]。若意大利對中國的投資動機是促進產品多樣化與差異化,則有利于兩國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提升;反之,則不利于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提升。本文用中國實際使用意大利直接投資金額表示。
(4)技術進步(TP)
弗農(Raymond Vernon,1966)的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技術差異化的產品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產生。產品需要經歷開發、引進、成長、成熟和衰退等階段,由于技術水平不同,各國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同一類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一般而言,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專注于技術創新和開發新產品,而技術水平較低的國家則主要通過引進新產品技術,生產已經完善、進入成熟期的產品。基于生命周期理論的技術差異化產品的存在,一國可能出口一種新產品并同時從另一國進口類似產品,產業內貿易由此產生。可見,技術的進步和創新能促進兩國產業內貿易的發展。一國的技術進步有兩種測度方法,一是該國的研發投入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二是該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占制成品出口額的比重[6]。本文采用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來衡量技術進步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具體公式表達為:TP=EHT/EMG,其中EHT和EMG分別表示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和中國制成品出口額。
(5)對外開放程度(OPEN)
巴拉薩(Balassa,1986)認為對外開放程度與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水平成正相關關系。若一國對外開放程度越髙,貿易保護較少,則該國經濟越能融入世界經濟中,其產業內貿易水平也隨之提高;反之,若一國貿易開放程度越小,對外貿易越不頻繁,則其產業內貿易水平也越低[7]。用中國與意大利的進出口總額占兩國GDP的比重表示,具體公式表示為:OPEN=(TEIi+TEIj)/(GDPi+GDPj),其中TEIi和TEIj分別表示中國進出口貿易額和意大利進出口貿易額。
(6)“一帶一路”倡議(BRI)
結合當前中國與意大利的實際貿易現狀,增設了“一帶一路”倡議是否提出這個虛擬變量。“一帶一路”倡議于2013年提出,變量BRI在2013年之前取值為 0,2013—2018年間取值為1。“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對兩國機電產品的貿易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
2.數據來源
被解釋變量即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GL)是根據UN Comtrade數據庫計算整理而得。除虛擬變量的解釋變量共五個,其中,中國與意大利人均收入差異和經濟規模數據均來自于世界銀行數據庫;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技術進步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對外開放程度數據根據UN Comtrade數據庫和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計算而得。筆者選取1992—2018年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
3.符號預測
結合前述理論,各解釋變量對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影響的符號預測及說明如表6所示。

表6 解釋變量的預測符號及說明
(二)模型建立及回歸檢驗
1.模型建立
本文以中意機電產品GL指數為被解釋變量,選取上述六個變量為解釋變量,分析中國與意大利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β1、β2、β3、β4、β5、β6為待估計參數,分別表示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受人均收入差異、經濟規模、國際直接投資、技術進步、對外開放程度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程度。α為常數,μ為隨機誤差項。
2.回歸檢驗
(1)單位根檢驗
運用統計分析軟件 Eviews 10.0中的ADF檢驗對模型中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LNGL、LNDPC、LNES和LNFDI的一階差分序列在1%的水平下平穩,變量LNTP和LNOPEN的一階差分序列在5%的水平下平穩。可見,時間序列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分析。

表7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2)協整檢驗
為了確定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間的長期關系,本文采用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1987)的兩步檢驗法。
第一步,利用最小二乘法對方程進行回歸(如表8所示)。根據回歸結果①可知,對外開放程度(LNOPEN)和“一帶一路”倡議(BRI)不能通過t檢驗。將這兩個變量剔除后,得到回歸結果②,LNDPCI、LNES、LNFDI和LNTP這 4個解釋變量都通過了 t檢驗,調整后的R2為0.9483,接近于1,D-W值為 1.1764,接近2,表明方程擬合度較好,最終得到如下解釋方程:


表8 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回歸結果
第二步,對回歸方程的殘差做單位根檢驗。利用ADF協整檢驗法對殘差序列的穩定性進行檢驗。若殘差序列穩定,則表明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回歸模型合理,反之亦反。對上述回歸方程變形得到如下殘差方程:

對殘差方程的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殘差的ADF統計量為-5.0245小于顯著性為1%的臨界值-4.4407,且P值為0.0030,拒絕了殘差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可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穩定,且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綜上,上述回歸模型合理的,可以用來解釋變量間的相關關系。
(3)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了進一步判斷上述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的變量間的因果關系,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進行檢驗(如表9所示)。檢驗結果表明,在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LNGL是LNES和LNTP的格蘭杰原因,即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是經濟規模和技術進步的成因,反之則不是。而LNDPCI、LNFDI與LNGL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即人均收入差異、國際直接投資都不是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成因,反之也不成立。

表9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3.結論分析
經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差異(DPCI)、經濟規模(ES)、國際直接投資(FDI)和技術進步(TP)對中意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對外開放程度和“一帶一路”倡議對產業貿易水平的影響不顯著。
(1)中意人均收入差異
回歸方程表明,中意人均收入差異(DPCI)與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呈負相關關系,人均收入差異每縮小1個百分點,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就會上升1.8789個百分點,這與預期符號相同。當兩國人均收入差異越小時,則雙邊消費需求就越相似,產業內貿易的可能性越大。此外,人均收入差異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程度最大。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人均GDP水平跨上新臺階,中意兩國人均收入差異逐年縮小,更有利于雙邊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的提升。
(2)中意經濟規模
中意經濟規模(ES)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產生一定的負影響,經濟規模每提高1個百分點,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將下降0.7612個百分點,這與預期符號相反。原因可能是,就中國而言,中國經濟規模上升,產業結構得以優化,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會減弱我國的出口依賴性;意大利方面,隨著意大利經濟規模上升,產品國內生產將逐漸替代國外進口,貿易也隨之減少。
(3)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
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FDI)對雙邊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有著促進作用,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雙邊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將提高0.2909個百分點。2004年中意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后,兩國經貿合作不斷擴大,加之2019年中意“一帶一路”倡議書的簽署,雙邊貿易平穩發展,雙向投資快速增長。機電產品是兩國經貿的主要產品,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勢必會促進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提升。
(4)中國的技術進步
中國的技術進步(TP)在回歸方程中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有著較大的正影響,中國技術進步每提高1個百分點,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將上升1.3392個百分點,這一結論與預期相同。自2013年以來,我國的研發經費投入僅次于美國,穩居世界第二,2019年科研經費預算占GDP比重2.5%,創歷史新高。不斷增加的科研經費投入促進了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有利于我國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也隨之增加,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得以提升,從而促進產業內貿易的發展。
(5)對外開放程度和“一帶一路”倡議
回歸模型顯示,中意對外開放程度和“一帶一路”倡議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影響不顯著。對外開放程度對產業內貿易影響不明顯的原因,可能由于目前意大利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一帶一路”倡議對產業內貿易沒有產生影響,原因可能是2013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雙邊經貿往來更加頻繁,2019年意大利正式加入,就目前的數據來看,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較弱。
四、研究結論和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以1992—2018年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作為研究對象,運用了GL靜態指標、MIIT動態指標和GHM分類指標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進行了測算和比較,分析了兩國機電產品的9大兩位數類目和10大三位數子項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和結構。總體來說,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處于中上水平,但該產品細分類目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表現出明顯差異。首先,從機電產品的9大兩位數類目產品來看,發電機械設備、一般工業機械和設備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金屬加工機械,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處于較低水平的產業內貿易;個別工業專用機械有所上升,近年來處于產業內貿易;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電信和音響設備、道路車輛和其他運輸設備一直屬于產業間貿易。其次,從該產品的10大三位數子項產品來看,除了龍頭、旋塞、閥門及類似器處于高水平的產業內貿易,旋轉式電力設備正由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轉變外,其他8大子項產品基本處于產業間貿易。第三,從雙邊機電產品貿易結構來看,中從意進口以高技術含量的機電產品為主,而對意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機電產品。中國在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電信和音響設備,電力機械、儀器和用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中順差額逐年增大,而在個別工業專用機械、金屬加工機械、道路車輛和其他運輸設備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中存在較大逆差。
為了進一步分析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原因,選取人均收入差異、經濟規模、國際直接投資、技術進步、對外開放程度和“一帶一路”倡議作為解釋變量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意人均收入差異、技術進步、經濟規模和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等因素對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產生影響。
(二)對策建議
1.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
實證研究表明,中國技術進步對中意兩國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產生較大的正面影響。我國政府應該進一步提高科研經費投入,同時制定優化產業結構的政策措施,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延伸機電產品產業鏈,提高出口競爭力。具體來說,我國與意大利在個別工業專用機械、金屬加工機械、道路車輛和其他運輸設備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機電產品貿易中,處于逆差狀態。因此,我國可以針對性地加大對上述產品的科技投入,不斷提升此類產品的技術含量,從而提升我國機電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加大吸引投資力度,提升外資利用水平
回歸結果顯示,意對華直接投資有助于雙邊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發展。意大利對中國直接投資經歷了1992—2008年的增長后,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意大利對華投資額逐年下降。因此,我國政府應繼續加大意大利對華直接投資引進力度,特別是鼓勵意大利對中國的投資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機電產品中去。同時政府應繼續加強外資利用水平,鼓勵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在技術、資本等領域的深度合作,促使我國機電產品外貿競爭力的提升,最終提高中意機電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