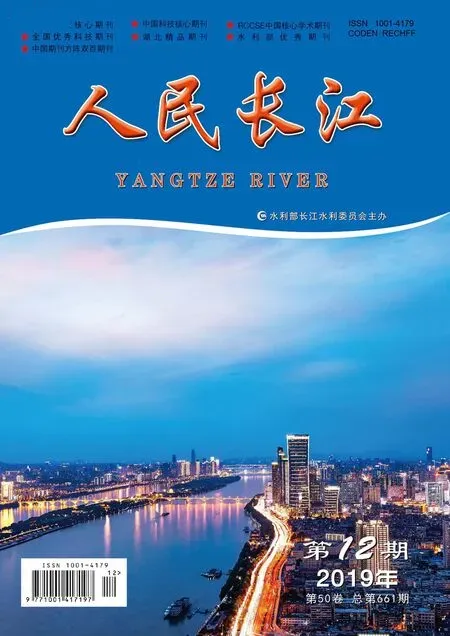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生態水文過程模擬初探
肖 洋,張 翔2,王 孟,鄧 志 民
(1.長江水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 湖北 武漢 430051; 2.武漢大學 水資源與水電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湖北 武漢 430072)
鄱陽湖位于長江之南,江西省北部,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是一個季節性漲水湖泊,具有“高水似湖,低水似河”的獨特自然地理景觀,其獨特的水文特征為植被群落的季節性更替創造了有利條件,為候鳥提供了良好的棲息地,是國際重要濕地之一[1-2]。
近年來,鄱陽湖復雜的江湖關系使得鄱陽湖水位年內過程發生了顯著性變化[3-4],由于洲灘地下水和湖水具有密切的側向水力聯系,比如鄱陽湖水位與蚌湖洲灘地下水位呈正相關關系[5],鄱陽湖水位的年內變化勢必會影響鄱陽湖洲灘濕地地下水分布,繼而影響濕地土壤水分時空分布[6]。濕地植被的生長及分布與土壤含水量密切相關,因此,鄱陽湖水位及相應洲灘地下水埋深變化對濕地植被種群密度、群落多樣性和植被高度等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7]。作為植被生長水分的重要來源,土壤水除了受地下水的影響外,還受降水的直接補給[8-9]。因此,洲灘濕地大氣、植被、土壤和地下水是濕地生態水文過程的有機整體,研究洲灘濕地大氣-植被-土壤-地下水系統水分運移過程對于探討濕地植被生長狀況具有重要作用。
鄱陽湖洲灘濕地生態水文過程研究目前以野外觀測實驗為主,已開展洲灘土壤濕度和地下水年內變化和洲灘地下水和湖水側向水力聯系等研究[5-6],受實驗尺度的影響,鮮有對洲灘濕地大氣-植被-土壤-地下水系統中水文過程的系統研究。數學模型是系統研究生態水文過程的重要手段之一。鄧志民等應用CoupModel生態水文模型和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研究鄱陽湖濕地苔草對水位變化的響應[10]。許秀麗等選取鄱陽湖濕地高位灘地的茵陳蒿和蘆葦群落為研究對象,運用 HYDRUS-1D 垂向一維數值模擬,量化了濕地地下水-土壤-植被-大氣系統界面水分通量[11]。盡管如此,在數學模型的應用中,對大氣-植被-土壤-地下水的完全耦合研究有待進一步完善。
本文以鄱陽湖國家自然保護區典型洲灘濕地為研究對象,選擇典型斷面,構建生態水文模型,初探氣象水文條件驅動下濕地土壤水和地下水動態變化情況,為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大氣-植被-土壤-地下水系統耦合研究提供數學模型支持。
1 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
鄱陽湖國家自然保護區(29°05′N~ 29°15′N,115°55′E~116°03′E)位于鄱陽湖西北角,贛江北支和修水的交匯處(見圖1),該保護區以永修縣吳城鎮為中心,下轄9個子湖泊(大湖池、蚌湖、大叉湖、沙湖、象湖、中湖池、常湖池、梅西湖和朱市湖)及其草洲,總面積331 km2。本文選擇蚌湖和修水之間的洲灘作為研究對象,該洲灘為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土壤質地以粉土為主,年內湖泊水位季節性波動顯著。隨著洲灘高程變化,由高到低依次出現南荻-狗牙根-苔草-菊葉委陵菜群落、南荻-苔草-蔞蒿-菊葉委陵菜群落和苔草-蔞蒿-虉草群落,植被的生態類型呈現出有規律的環帶狀變化。根據洲灘隨湖泊水位出沒情況,設置研究斷面如圖2所示,在非汛期該斷面灘地長度約1 100 m。

圖1 鄱陽湖國家自然保護區Fig.1 Map of Poyang Lak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圖2 研究斷面示意Fig.2 Scheme of study section
2 生態水文模型構建
由于濕地洲灘表層土壤的孔隙度較大,且地表枯枝落葉對降雨的滯留作用較明顯,降水經過蒸發截留過程后,洲灘匯流過程并不明顯。因此,洲灘水循環過程主要以大氣-土壤-植物系統水循環過程為主,同時由于洲灘與毗鄰的河湖存在水力聯系,河湖水與洲灘之間的雙向補給機制也是濕地水循環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構建生態水文模型時,重點研究洲灘上植被生長影響下的降水截留、蒸散發、土壤水運動和地下水運動過程,典型洲灘濕地水文過程如圖3所示。
根據典型洲灘濕地植被環帶狀分布特征,將典型斷面以150 m間距劃分為6個單元,編號1~6(見表1~2),在每個單元上以地下水為下邊界,由地表至下邊界以0.1 m間距劃分土壤層,同步計算各單位上降水截留量、蒸散發量、植被根系吸水量,在蚌湖和修水水位變化驅動下,完成地下水和土壤水的耦合模擬。

圖3 典型洲灘濕地水文過程示意Fig.3 Hydrological process at typical islet wetland of Poyang Lake

計算區間沙土/%粉土/%黏土/%計算區間沙土/%粉土/%黏土/%12.4193.983.6140.0096.533.4720.5997.302.1150.0097.492.5130.0096.843.1660.0097.422.58

表2 研究區植被群落結構Tab.2 Structure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typical islet wetland
注:計算區間編號由修水至蚌湖逐漸增大。
2.1 降水截留
本文采用Galdos等提出的模型計算降水截留量[12]。
I=S+E=P-TH-F-D
(1)
式中,I為總的冠層截留量,m/d;S為t時刻冠層儲水量,m;E為植被冠層截留蒸發量,m/d;P為降水量,m/d;TH為冠層間自由穿落的降水量,m/d;F為植被莖流,m/d;D為從葉片和莖干滴落的水量,m/d。其中,TH、F和D最終會降落到地表上,則降落到土壤上的降水量Psoil(m/d)可表示為
Psoil=TH+F+D
(2)
因此,截留模型可以簡化為
I=P-Psoil
(3)
通過聯合求解式(4)~(6),得到Psoil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從而得到不同時期冠層對降水的截留量I。
(4)
(5)
(6)
Smax=f·lg(1+LAI)
(7)
式中,Smax為植被冠層最大截留量,m;St-1為t-1時刻冠層儲水量,m;Ep為冠層潛在蒸發,m;f為冠層截留系數;LAI為葉面積指數,m2/m2。
引入單位面積植被覆蓋度FVC,得到研究區域實際的植被冠層截留量INT,m/d;進而得到實際降落到土壤上的降水量Pn,m/d。
INT=I×FVC,Pn=P-INT
(8)
2.2 蒸散發
根據Penman-Monteith公式和莫興國等對Shuttleworth-Wallace模型的改進,實際蒸散發量包括植被實際蒸騰量、冠層截留蒸發量和土壤實際蒸發量[13]。
如果確診是排卵期出血,一般不用擔心,對身體沒有別的影響。對身體是否有影響主要取決于出血的多少和長短。如果出血少、時間短,那就讓它去。假如出血較多、時間長,其實最好先做個診刮,可能有其他問題。
(9)
(10)
(11)
(12)
(13)
(14)
式中,Ec、Ei和Es分別為植被蒸騰量、冠層截留蒸發量和土壤蒸發量,m/d;λ為水的蒸發潛熱,取值2.45 MJ/kg;ρw為水的密度,kg/m3;Δ為飽和水汽壓-溫度曲線的梯度,kPa/℃;ρ為空氣密度,kg/m3;Cp為空氣的定比壓熱,MJ/(kg·℃);Rnc為冠層凈輻射,MJ/(m2·d);Rns為地表凈輻射,MJ/(m2·d);G為傳入土壤中的熱通量,MJ/(m2·d);γ為干濕球常數,kPa/℃;Wfr為葉面濕潤面積比例,取冠層儲水量與冠層最大儲水量比值的2/3次方;ra為源匯到參考高度的空氣動力學阻力,s/m;rac為冠層表面邊界層阻抗,s/m;ras為土壤表面邊界層阻抗,s/m;rs為土壤阻抗,s/m;rc為冠層阻抗,s/m。
2.3 植被根系吸水
植被主要通過根系從土壤中吸收水分,滿足其生長以及代謝等生理活動和葉片蒸騰。本文假設根系吸水S(z,t)是蒸騰Ec(t)以及有效根分布Le(z,t)的函數,在此基礎上對根系吸水加入土壤水約束[14-15]:
(15)
(16)
(17)
式中,k為根系主要分布系數;Z為土壤層厚度,m;Lr為根系的平均最大深度,m;f(θ)為土壤水約束系數,無量綱;D(θ)為土壤水力擴散系數,m2/d;θ為土壤含水量,無量綱;θw為凋萎土壤含水量,無量綱;θfc為田間土壤含水量,無量綱。
2.4 土壤水運動
土壤水運動不僅是水循環的重要環節,對于植被的蒸騰、土壤水蒸發、植被生長、生態系統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土壤水運動Richards方程為
(18)
其中,θ為土壤含水量,%;K(θ)為土壤水力傳導率,m/d;D(θ)為土壤水力擴散系數,m2/d;SE為包括植被根系吸水和土壤水蒸發的損失項,1/d。土壤水力特性曲線主要采用Clapp-Homberger模型[16]。
本文中,上邊界條件為
(19)
θ|z=ZWT,t≥0=θfc
(20)
式中,ZWT為地下水位,m。
2.5 地下水運動
在濕地或河岸帶地區,地下水對土壤含水量有著顯著影響。在研究區域,地下水除了受降水的補給外,也會因蒸發和植被根系吸水而損失水分,但相比之下,土壤水和河湖水則是地下水的主要源匯項。
地下水運動過程的研究主要采用Boussinesq方程,具體如下:
(21)
式中,μ為給水度,無量綱;K(x)為水力傳導系數,m/d;h(x,t)為t時刻距坐標原點x處的地下水水位,m;Z為隔水底板高程,m;f(x,t)為含水層與外界的水量交換量,m/d,主要受土壤水補給、地下水蒸發和植被根系吸水等的影響。
本文中,地下水運動的左右邊界分別為
(22)
(23)
式中,T為導水系數,m2/d,hXR和hBL分別為修河和蚌湖水位,m。
3 模型初始化
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水文模型的時間尺度可以是小時或日尺度,本文選用日尺度。模型的輸入包括逐日降水量、逐日水位和逐日葉面積指數、逐日冠層凈輻射Rnc、地表凈輻射Rns、傳入土壤中的熱通量G、源匯到參考高度的空氣動力學阻力ra、冠層表面邊界層阻抗rac、土壤表面邊界層阻抗ras、土壤阻抗rs、冠層阻抗rc。其中,逐日降水量通過中國氣象數據共享網下載得到(見圖4),逐日水位資料通過江西省水利廳網站水情信息頁面取得(見圖5),逐日葉面積指數通過逐月遙感影像產品插值得到(見圖6),其他變量通過DTVGM能量傳輸模型計算得到[17]。另外,模型的初始化還包括對土壤各層的初始時刻含水量賦值,本文中土壤含水量的初值假設為田間持水量θfc。初始時刻冠層儲水量S0和冠層截留蒸發量均設為0。
模型的參數為土壤物理參數和植物生理參數,如表3所示,其取值主要參考已經發表的文獻。本文中模型運行時間序列為一個完整的植被生長年(2月至次年2月)。考慮模型的預熱期,本文對2015~2016年兩個相同完整的生長年進行連續模擬,但重點對第二個完整生長年進行研究。

圖4 2015~2016年鄱陽湖降水日變化過程Fig.4 Daily rainfall from 2015 to 2016 in Poyang Lake

注:假設蚌湖水位與鄱陽湖水位保持一致。圖5 2015~2016年鄱陽湖水位日變化過程Fig.5 Daily water level variation from 2015 to 2016 in Poyang Lake

圖6 2015~2016年鄱陽湖濕地葉面積指數日變化過程Fig.6 Daily leaf area index variation from 2015 to 2016 in Poyang Lake wetland

模塊符號描述單位參考值方程說明降水截留f冠層截留系數-1.2(7)Galdos等[12]FVC植被覆蓋度-0.9(8)Lei等[18]植被根系吸水、Lr根系的平均最大深度m0.2(16)賦值土壤水運動、地k根系分布系數-0.5(16)賦值下水過程模擬θs飽和含水率m3·m-3計算獲得(18)~(23)Clapp等[16]θr凋萎土壤含水量m3·m-3計算獲得(17)~(23)Clapp等[16]θfc田間土壤含水量m3·m-30.4(17)~(23)李云良,等[19]Ks土壤飽和水力傳導度m·s-1計算獲得(18)~(23)Clapp等[16]ψs土壤飽和基質勢m計算獲得(18)~(23)Clapp 等[16]b0與土壤性質有關的參數-計算獲得(18)~(23)Clapp等[16]μ含水層給水度-0.2(21)賦值Z隔水底板高程m8.4(21)賦值
4 典型洲灘濕地水文過程模擬
每年汛期,五河洪水入鄱陽湖,湖水漫灘,洪水一片;冬春季節,湖水落槽,灘地顯露,水面縮小。受鄱陽湖水位季節性漲落和洲灘出沒交替變化的影響,濕地水文過程在一個完整的植被生長年內呈現雙峰變化模式。受汛期的影響,2015年7月10日至9月18日為研究洲灘的淹沒期,淹沒期前后則為研究洲灘的出沒期。
4.1 濕地蒸散發過程模擬研究
圖7是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計算區間平均日蒸散發模擬過程。模擬期間蒸散發量模擬總量為804 mm,實測蒸發量為813 mm,兩者相對誤差為1.1%,相關系數R2為0.92,納什效率系數NSE為0.83,模擬結果能夠較好地反映濕地的蒸散發過程。

圖7 典型斷面2015~2016年日蒸散發模擬過程Fig.7 Simulation of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of typical section from 2015 to 2016
圖8是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計算區間平均日蒸騰模擬過程。

圖8 典型斷面2015~2016年日蒸騰模擬過程Fig.8 Simulation of daily transpiration of typical section from 2015 to 2016
模擬期間蒸騰量模擬總量為97 mm,占蒸散發總量的12%。受洲灘出沒的影響,濕地植被蒸騰過程呈現雙峰變化特征。2015年2月1日至6月29日期間,植被蒸騰量大致從0 mm/d不斷增加到最大值4.1 mm/d,而在2015年9月2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間,植被蒸騰量日變化過程呈現拋物線模式,介于0 ~1.8 mm/d之間。淹沒期后,植被日蒸騰量顯著小于淹沒期前,這可能是受氣象條件的影響,比如淹沒期前太陽輻射和溫度月平均值均高于淹沒期后(圖9~10),有利于植被完成光合蒸騰等生理活動。

圖9 研究區多年月平均總輻射量Fig.9 Mean monthly total radiation from 1985 to 2013

注:圖9和圖10氣象數據來自于中國氣象數據共享網。圖10 研究區多年月平均蒸發和月平均溫度Fig.10 Mean monthly temperature and total evaporation from 1985 to 2013
4.2 濕地地下水位變化
圖11為2015~2016年計算區間平均逐日地下水水位模擬過程。從圖中可見,濕地地下水水位與鄱陽湖水位的變化具有高度一致性,表明濕地地下水與湖泊具有良好的水力聯系。在淹沒期前,鄱陽湖水位大致高于濕地地下水水位,而在淹沒期后,濕地地下水水位則大致高于鄱陽湖水位,這可能是因為鄱陽湖水量的消退速度大于濕地與鄱陽湖之間的側向補給速度引起的。從圖中也可以看出,濕地地下水位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特征,濕地地下水埋深介于0 ~ 6.62 m之間,這與許秀麗等[6]的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

圖11 2015~2016年日地下水水位模擬過程Fig.11 Simulation of daily water leval variation from 2015 to 2016
4.3 斷面土壤含水量變化
圖12是2015~2016年計算區間平均逐日土壤濕度變化過程模擬。由Richard方程可知,土壤濕度的變化主要受土壤水重力下滲、地下水和土壤水的水力擴散以及包括降水補給、土壤蒸發和植被根系吸水在內的源匯項影響。從圖可見,10 cm處土壤濕度的逐日變化過程較20,30,40 cm和50 cm劇烈,這主要是因為濕地植被的根系埋深介于0~40 cm之間,其中主要介于0~20 cm之間、近地氣象條件和根系吸水對0~10 cm土壤濕度影響較大。從圖12(b)可見,淹沒期前后,根系分布區土壤濕度分別呈現大致增加和減少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淹沒期前后分別對應濕地的漲水期和退水期所致。在漲水期間,鄱陽湖水位不斷上漲,使得濕地地下水抬升,同時降水補給的增多也是土壤濕度變大的原因,而退水期間則相反。

注:上述結果為計算區間平均土壤濕度統計結果。圖12 2015~2016年土壤濕度日變化過程模擬Fig.12 Simulation of daily soil water content from 2015 to 2016
5 結 語
本文以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為研究對象,從降水截留、蒸散發、植被根系吸水、土壤水運動和地下水運動5個方面構建了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生態水文模型,并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對模型進行初始化,對蒸散發、土壤濕度和地下水位進行模擬試驗。試驗結果能較好反映鄱陽湖典型洲灘濕地的生態水文過程特征。受野外觀測條件限制,缺乏生態水文過程實測數據,本文沒有開展模型參數率定和結果驗證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通過多途徑收集所需數據,完成模型參數率定和結果驗證,并進一步完善模型結構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