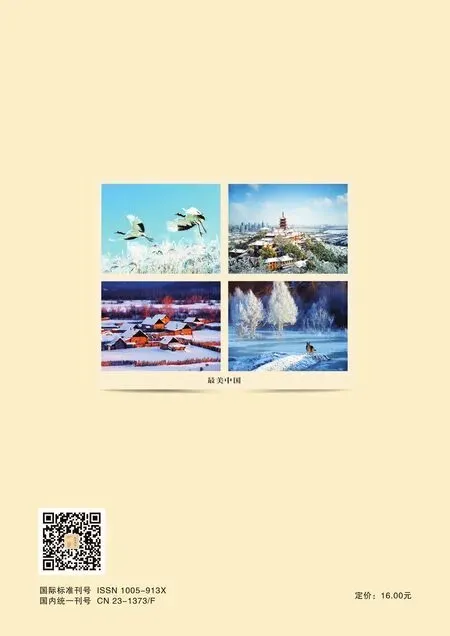環保投入、行業屬性及財務績效實證研究
梁晨瑤
(揚州大學 商學院,江蘇 揚州225009)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環境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將堅持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要把生態環境視為生命。為了讓公眾更好地了解企業的環境行為,同時促進企業進行環境治理提高環境績效,各國都積極完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我國相關部門也發布了多項制度明確要求企業披露環境信息。與寬泛的披露信息比較,諸多研究表明企業披露的環保投入額作為一項財務性的披露信息,不僅能夠直接反映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的情況,并且由于其客觀具體、容易驗證的特質更加具有可靠性。傳統經濟學認為,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勢必會對財務績效帶來不利影響,很多實證研究也認為企業治理環境加大了企業經營的成本,進行環保投入僅僅是出于滿足環境管制的要求。而以“波特假說”為代表的修正觀點則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壓力能夠促進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經濟績效。一直以來,我國企業的環保投入規模都較低,說明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的企業并不認可環保投入能夠帶來經濟效益,但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驗證,因此研究以披露環保投入具體數值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揭示企業環保投入給財務績效帶來的影響及該影響在不同行業中的異質性。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環保投入與財務績效
關于企業環保投入對其財務表現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負向作用、正向作用及不確定作用三種觀點。負向作用的觀點主要來源于早期的傳統經濟學理論,其認為利潤是企業經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企業獲得的利潤越多,其價值就越大。傳統經濟學認為:“公司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股東們賺錢”,環保進行投入則違背了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只會給企業經營帶來成本負擔。按照這種觀點,企業將僅僅基于政府的強制要求對環境保護做出努力,但是現實情況是很多優秀的企業主動承擔環境責任,積極投入環保資金卻帶來了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豐收(哈克,2016)。[1]對于這種現象,利益相關者認為是由于企業承擔環境責任能夠提高企業聲譽,從而能讓相關者滿意,降低了與利益相關者沖突的風險,同時企業樹立起良好的“綠色”形象能夠增加顧客粘度,獲得環境溢價。不僅如此,“波特假說”也支持這種觀點,該假說認為環境污染是企業未能充分利用好資源的結果,這依賴于企業的技術能力。當政府給予適當的環境規制后,投入環境資金較多的企業出于降低環境治理成本的目的進行技術革新,從而降低其自身的生產成本,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而較早進行環保投入的企業也將會依賴新技術得到“先發優勢”(Porter和Linde,1995)。實證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支持這種觀點,如Charkson等(2004)、張三峰等(2011)等發現企業通過環保投入能夠獲得更好的財務業績。基于此,提出假設1。
H1:企業環保投入與財務績效之間呈正相關。
(二)環保投入、行業屬性與財務績效
行業環境對企業的戰略決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行業意味著會受到經營環境及政府管制不同的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財務績效等勢必會因行業而異。由于重污染企業引發環境污染的可能性及危害性較非重污染性企業都較高,根據“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重污染企業理應承擔更多的環保責任,所以近年來我國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頒發了一系列法律法規重點規范重污染企業的環境行為。顯然,我國重污染企業面臨著更嚴格的環境規制,環保投入資金也越多(唐國平等,2013),在相關政策引導下,相比非重污染企業,重污染企業進行技術革新的壓力將會更大,這樣一來,重污染企業的環保投入資金重點會放置于相關技術、產品的創新上,“創新補償”效應將會更加明顯。不僅如此,重污染企業投入大量的環保資金,其環境績效也會得到較大的提高,能夠給外界傳遞環境良好的信號,對經營績效也會帶來更高的積極影響。而對非重污染企業而言,環保投入中大部分是治污支出,表現出來的僅僅是減少了違規成本,與技術創新、產品改良的關系不大,基于此,提出假設2。
H2:與非重污染企業相比,重污染企業環保投入對財務績效的正向影響更顯著。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定義
(一)模型構建
根據假設,研究構建了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全樣本回歸分析以檢驗環保投入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即假設1),并利用該模型按照是否為重污染行業進行分組回歸以驗證假設2。

(二)變量定義
1.環保投入
研究將企業投入的污染預防和治理措施的初始投入及維護支出、污染物的處理投入、生產產品及技術的改進投入、環保培訓費用等作為環保投入的內容。為了消除不同企業規模差異的影響,研究使用環保投入與平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環保投入強度。
2.行業屬性
研究根據原環保部頒發的《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分類,重污染行業主要包括了火電、水泥、煤炭、冶金等16個行業,如果上市公司屬于重污染企業賦值為1,非重污染企業賦值為0。
3.財務績效
以往涉及企業財務績效的研究已經較多,相關文獻中主要有兩類指標用來衡量。一類是以反映企業經營情況為主的傳統財務指標,另一類則用市場對企業的價值衡量做標準。由于本研究意在研究環保投入對企業生產經營情況的影響,希望財務指標能夠反映企業成本費用等方面的信息,故選用傳統類財務指標總資產收益率來衡量。
考慮到公司規模、償債能力、股權集中度、產權性質等因素也會對財務績效有所影響,故將其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定義如下。

表1變量含義及其衡量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研究以滬深兩市上市公司中披露環保投入金額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并以2015-2018年連續4年作為研究區間,剔除了金融類、環保類及ST公司,最終共獲得了349個觀察值。環保投入金額根據國泰安數據庫發布的社會責任明細表整理所得,財務績效和控制變量數據也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研究對所有連續型變量1%的顯著性水平上進行Winsorize處理,以消除極端值的影響。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針對2015-2018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中披露環保投入具體數額的349個樣本,對研究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從結果來看,樣本企業的環保投入強度在0.0001-7.686之間,均值大于中位數且數值較低,說明大部分企業的環保投入強度較低。行業屬性的中位數為1,平均數為0.562,說明樣本中重污染企業較多。

表2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三)回歸分析
如表所示,三個回歸的F值均顯著,且R2分別為0.3526、0.3833及0.366,說明模型能夠描述變量之間的關系,擬合性良好。在第二列全樣本回歸中,環保投入與財務績效的回歸系數為0.0083,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環保投入與財務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假設1得到驗證。除此之外,行業屬性與財務績效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122,說明與非重污染企業相比,重污染企業的財務績效較低。第三列與第四列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當企業為重污染企業時,環保投入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另一組則不明顯,說明非重污染企業環保投入對財務績效的作用不明顯,假設2得到驗證。

表3環保投入與企業價值關系回歸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以滬深兩市披露環保投入具體數值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了環保投入、行業屬性及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研究結論如下。一是環保投入與財務績效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二是與非重污染企業相比,重污染企業的財務績效較小,這說明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越小,財務績效越好。三是重污染企業環保投入對企業財務績效的正向作用較非重污染企業較顯著。
目前,我國企業的環保投入水平仍然較低,企業對履行環境責任仍然不夠重視。研究結論認為,長期來看,企業履行環保責任、積極投入環保資金能夠提高企業財務績效,且環保投入的正向作用在重污染行業中更明顯,因此,企業和政府都應當積極采取措施,推進企業和政府的可持續發展。
對政府而言,首先,應當加強環保投入等硬性披露的信息披露制度,研究發現能夠披露環保投入的企業寥寥無幾,這種情況難以實現信息披露制度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約束作用。其次,相關部門應當進一步宣傳環境保護理念,提高企業和公眾的環保意識,發揮好公眾的監督作用。最后,政府應該積極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適度提高環境規制強度,以推動企業積極投入環保資金、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而言,環保投入對財務績效具有正向作用是企業進行環保投入的動力機制。企業應當充分認識到環保投入對企業經營績效的積極影響,主動進行環保投入,改善企業環境績效,以樹立良好形象,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