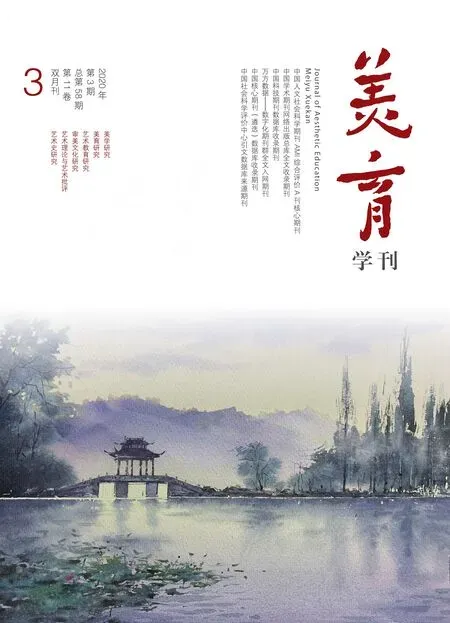當下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實踐的三點思考
孔新苗
(山東師范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14)
如果以李心峰在1988年《文藝研究》第1期發表《藝術學的構想》一文,到2011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新版《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藝術學”升格為與“文學”“歷史學”同等的學科門類為一個時段,可以說在世紀之交中國藝術學學科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推進。另一方面,從構成藝術學知識體系的三大組成部分: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來看,學科體系(學科門類建設)和學術體系(高校人才培養)兩方面建設進展突出,比較之下藝術學話語體系建設成果相對較弱。這既與藝術學學術共同體被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所聚集的歷史短,學科話語建設是“軟件”更需時間、成果和人才梯隊積累有關,也與作為整體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在具有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的道路上所面臨的階段性實踐課題有關。現針對藝術學學科話語建設問題提出如下思考。
一、兩個基礎問題
(一)“藝術學不是拼盤”[1]
張道一在藝術學建立之初提出的這一問題,聚焦了藝術學學科建設所面臨的系列問題的核心點,也表述了作為學科話語建設的核心關懷。在話語建設的意義上,藝術學學科名稱與西方學科系統命名不直接銜接的問題,藝術學學科基礎理論在與美學、文學理論的關系中如何獨成系統的問題,在各個門類藝術史如美術史、音樂史、電影史的基礎上是否有整體“藝術史”的問題等,這些涉及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的基礎性課題,皆在這一“不是拼盤”的警示中,凸顯了話語建設的主攻方向。
(二)西方“鏡像”前的中國藝術學
張法在回顧藝術觀念的《中國藝術觀念70年演進》一文中,列出了影響這一進程的四個方面:第一,中國傳統“文”為核心的藝術觀;第二,奠基于西方美學的“藝術”觀;第三,德國“藝術科學”學科體系;第四,對世界發達國家藝術學科體制的研究。如果基本認可這一梳理,西方美學、藝術觀和現代學科體制(占了四個方面的三個),正是中國藝術學“出現—關聯—發展—成就”過程中的主要“鏡像”[2]。那么是否可以這樣說: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的基礎語境,是在西方鏡像前的自我審視。也正因為有了這個西方鏡像,關于“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的問題才如此鮮明地成為當下的主題。明確這個語境的歷史性、實踐性情境特點,正構成了當下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的問題自覺與實踐自覺的基礎。
二、“鏡像”入思的方法論思考和比喻
當語言哲學成為人類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一個基本方法時,鏡子作為認識工具的比喻,褪去了它“客觀再現”的功能色彩。在拉康的“鏡像”與自我關系的理論描述中,鏡前的我與其說是通過鏡子在看“我”,不如說是在看我是“誰”——一個社會的、語言的他者。[3]90在這里,鏡像是社會生存的文化語境、意識形態、權力規訓對自我的命名、塑造途徑,并且這一過程伴有鮮明的“自愿”色彩,是建立在“自我”主體自覺或不自覺的欲望、選擇、理想追求之上的。西方現代美學、藝術觀念和藝術學科體制,正是20世紀以來追求“現代性”的中國藝術觀生成、學科意識自覺所使用的主要對標鏡像。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現代中國”的文化基因和鄉愁,又以“另一鏡像”的視角參與到現代性形象的體認、自塑的觀看之中。中國藝術學的現代發展史,正是不斷地在這兩個鏡像中展開對自身現代形象的自審與理想形象自塑的話語實踐。顯然,西方鏡像在這一過程中是強勢一方,在這一現代變革過程中已然引發了這樣兩個主要改變。
第一,在鏡前,它以鮮明的學科本體論、歷史目的論和學科范疇、邏輯的體系化,對比出中國傳統以“文”為核心的藝術觀、人才培養范式的“不現代”,凸顯了由傳統文人把持的書畫文化、上流社會音樂文化及私塾、師徒培養模式既是“非專業的”,又是脫離社會現實和勞動大眾的。從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到世紀中葉的學習蘇聯模式,從“革命文藝”語境下在傳統中鑒別“精華與糟粕”到改革開放努力對話西方現代藝術,再到21世紀以來對建設“中國話語”的訴求……西方鏡像如影隨形。整體看,參照西方藝術觀來反思傳統、建設中國藝術創作、傳播、教育的現代文化,是這一變革過程的基本走向;參照歐美學科體制、學校藝術教育范式建設中國的現代藝術教育,是變革的主要專業路徑。如此,中國傳統以“文”為核心(詩書琴畫一體)的文人審美生存觀就被改造為以“文藝”一詞為核心的現代社會藝術觀。在這一過程中,最能代表中國傳統審美文化與藝術創作智慧的“文學”逐步離開了現代學科狹義的藝術門類,進而完成了2011年中國藝術學“升門成功”后的建設周期。
第二,在鏡前,西方美學以“審美自律”“形式創造”的藝術價值話語,對比出與將藝術與人生關系置于首位的中國傳統藝術價值話語之間的齟齬,當“為藝術而藝術”“陌生化”“打破藝術與生活界限”成為“專業的”“現代”的評判邏輯,中國藝術的現代性實踐一方面獲得了創作主體“觀念更新”“語言解放”的能量釋放,也同時嘗到了與文化傳統、生存現實割裂和沖突的迷茫……
發現西方鏡像,是中國藝術觀的現代進程不可逆的歷史經歷,是中國藝術學學科建設走到當下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藝術傳統已然成為相對邊緣的另一現代性的“他者”鏡像——人類學、歷史學意義上的、跨文化比較中“曾經的自己”。這在近幾年展開的重溫、重釋中國藝術傳統的新潮中讓我們體會尤深。而如何以“兩個鏡子”(中國傳統、西方體系)來觀看、反思今天的中國藝術學科建設、話語知識生產實踐,則成為當下方法論選擇的中心議題。
當我們理發時,臨近結束理發師會提供正面之外的“另一個鏡子”,讓我們看到自己的背面。而這個“背面”之像又是從正面的大鏡像中映射給我們的。這就形成了本文對當下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方法論思考的一個比喻:中國現代藝術學學科建設在20世紀至今的許多重要時段中,是將審美、藝術的現代鏡像(西方藝術觀和學科體制)作為面前的主鏡,中國藝術文化傳統作為背面的第二鏡來自審形象的。如此,主鏡作為中介,成為思考傳統的語境依托。
“鏡”的比喻意在凸顯正面鏡像對背面鏡像具有某種“話語權力”——“背面”需要“正面”的映顯才能生效。據此,也有觀點主張我們可以反轉過來,用中國文化傳統作為“主鏡”去參考、反思西方鏡像。但顯然這個愿望的話語實踐條件目前看還有待學術共同體更多研究成果的支撐。或者說,20世紀以來中國藝術學學科建設的歷史積累是不可逆的。同時,如果我們超越中/西二元對立從歷史實踐的角度看,應看到“建設中國藝術學知識體系”這一愿景早已存在于中國藝術學學科現代性建設的初心之中。“藝術學”學科名稱與西方學科系統命名不直接銜接的問題,也部分體現了這一歷史進程的中國化追求。說到底,使用西方鏡像進行中國藝術觀的現代變革,目的也正是要最終建立那個“中國的現代”。在鏡像理論看來,作為社會存在的自我認知、自我塑造是不可能離開鏡像的,鏡像是鏡前觀者的社會存在和意識形態的直觀顯現。正如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一文中所言:“意識形態是個表象系統,但這些表象在大多數情況下和‘意識’毫無關系;它們在多數情況下是形象,有時是概念。它們首先作為結構而強加于絕大多數人,因而不通過人們的‘意識’。它們作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體,通過一個為人們所不知道的過程而作用于人。”[4]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鏡像不是真理的顯現,正如中國傳統俗語所說“鏡中月,水中花”。而是觀看者的歷史存在、變革欲望和生存訴求在活生生的話語實踐歷史過程中對經驗性目標的選擇。即你用哪面鏡子去照,用幾面鏡子結合而立體地看,怎么看,均是有其歷史條件性的。鏡像,就是歷史中人與生活現實間的想象性關系。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今天新時代的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的現實挑戰與歷史使命得以清晰:呼喚建立在鮮明文化自信意識中的中國藝術學話語實踐——文化自信為根,多維視角為徑。
“文化自信”是新時代的藝術學話語建設方法論思考的思想立場與價值觀定位,是對20世紀以“革命”“改革”為主旋律的“看西方”方法論選擇的歷史經驗反思。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通各種資源,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我們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
三、當下學科話語建設實踐的兩個要點
以目前中國藝術學學科門類由五個一級學科(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美術學、設計學)組成的結構看,實現“藝術學不是拼盤”的學科話語建設的重任,主要落在了“藝術學理論”學科。從研究的學科視角看,美術學、音樂與舞蹈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研究,更多是立足一方看對方或多方,唯有藝術學理論研究是將對藝術學各藝術門類的整合研究作為其基本定位。就這一問題,藝術學理論學者針對學術共同體研究成果中存在的問題和愿景提出了許多清晰的判斷,“作為一級學科的‘藝術學理論’,就是專門著力于闡釋、探究、建構藝術意識形態和藝術共有性與普適性學理體系的學科”。[6]這里要重點提出討論的是:在藝術學理論研究方法論的角度,跨藝術門類的學科理論研究如何做到“不是拼盤”?如何做到區別于美學、文學理論而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就此提出下面兩點。
(一)研究“銜接”的方法論定位
年輕的中國藝術學理論研究,深受已然成熟的美學和文學理論的影響。在美學作為“藝術哲學”(鮑姆加登、黑格爾)和更寬視野中定位(自然、社會、藝術)的“美的哲學”(柏拉圖、康德)來看,美學顯然是藝術學理論研究上位的哲學思想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學理論作為學科學術研究的價值,就是要探討關于藝術的觀念與創作的意識形態(學術背景是美學)是如何與藝術實踐(創作、傳播、接受)相銜接的。這個從“銜接”入手的方法論意識,正是藝術學理論不同于美學的學科研究定位的主要特點。
具體來說,“銜接”作為藝術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意識,力求定位于美學和各門類藝術創作研究之間,以此凸顯獨立的學科研究范式和自成系統的話語邏輯,即一方面與上層的美學“銜接”——自上而下;一方面與下層的各門類藝術創作現象、語言研究銜接——自下而上;進而橫向與藝術社會學、藝術心理學、藝術傳播學、藝術教育學等領域銜接,通過這種“銜接”的研究定位自覺,在把握各門類藝術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基礎上發現共通性,在解讀藝術的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教育學研究間的共通性關系中建構藝術學的話語闡釋。通過對這種共通性的理論建構,奠定藝術學“不是拼盤”的學科合法性。概言之,銜接藝術觀念與藝術實踐,銜接藝術的時代共性品質與不同藝術門類中個性化語言表達的特點,銜接價值理想與接受效應,是藝術學理論區別于美學、區別于門類藝術研究,建立藝術學理論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要點。例如,中國傳統審美文化中的“詩情畫意”,西方古典藝術中“美的法則”,就可以是銜接中西各自的古典時代中審美理想、藝術觀念與不同門類藝術創作語言特點、藝術教育范式、藝術鑒賞標準與風尚的共通性理論范疇。如此,藝術學理論研究提煉出不同時代的共性藝術觀念與門類藝術表達特點的銜接關系,理論地把握那個時代的審美創作品質、語言更新現象、典型作品特質,就形成藝術學學科不同于美學的學術話語貢獻。再擴大之,對民族文化中的藝術活動在全球視野下的特點把握與人文價值詮釋,正構成藝術學研究對一個民族的審美文化氣質、藝術智慧運用和傳統經典品質的理論解讀。通過銜接“虛的”精神氣質與“實的”藝術創作,銜接了特定語境下藝術理論關鍵詞與不同門類藝術表達語言特點間的內在聯系,建立起跨藝術門類的綜合藝術研究范疇系統,綜合各藝術門類的“整體”藝術史描述框架,正是藝術學理論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形象自塑。
在方法論的哲學意義上,這個以“銜接”定位的方法論意識,又以中國哲學的“一分為三”超越西方的二元論。即在感性/理性、經驗/理念、形式/精神、藝術語言/價值理想、媒介特性/思想主題等二元之間,通過闡釋如何“銜接”而引入一個理論研究的新對象,“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立足一分為三的思維范式,體現藝術學中國話語實踐方法論的哲學關懷。
(二)“系統自覺”的學術工作意識
中國傳統以“文”為核心的藝術觀,一直將研究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創作的詩學理論,作為廣義的一般藝術理論的核心,中國現代藝術觀和藝術學學科的建立,在狹義的“藝術”門類中以與文學的分離作為基本標志。盡管如此,傳統、現代文論、中西文論的研究成果和范式對藝術學理論研究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在這個語境下,建設中國藝術學話語體系就應充分利用好廣義的藝術理論研究成果,著重在狹義的藝術學理論研究對中國藝術問題的解答實踐中,在不同理論視角和觀點的交叉、碰撞中,提煉、生成藝術學理論的核心范疇。當下,藝術學學術共同體比較集中的一個話語實踐意識,是要強化對“中國古典藝術理論話語系統”的再研究、再認識。(關于通過“媒介研究”體現藝術學理論研究與文學理論研究的學理差異建構,限于篇幅將專文論述。)
這里提出所謂“系統自覺”,就是要在這一再研究、再認識中,突出關注對中西兩大話語系統之間差異關系的自覺,避免不顧系統的人文性質和文化歷史差異,表面地、符號化地拼接、互釋中西概念與范疇。落實到學術工作實踐中,是應注意對中國傳統藝術理論范疇、概念自身內涵的解讀與保護,避免孤立地在西方鏡像中看中國細節,或用中國符號裝飾西方系統以為“中國化”。
舉一例。“意象”在闡釋中國宇宙觀的史前著作《周易·系辭》中首現,在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中開始成為古典文論的重要范疇,又伴隨唐、宋藝術理論話語而成熟。20世紀80年代后被美學家、藝術研究者普遍關注,成為西方藝術理論風潮強勢吹來期間中國藝術理論范疇進入現代話語實踐的一個重要現象。葉朗自80年代后期的《現代美學體系》到2009年成書的《美在意象》,集二十余年時間將“意象”范疇提煉凝結為他的“立足點是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的美學體系建構的核心。葉朗表述這一話語建構實踐的用心是:用“美是意象”來解讀“美是在審美活動中生成的,美感不是‘主客二分’關系中的認識,而是‘天人合一’關系中的體驗”。[7]這里使用的“‘意象’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美學的理論和話語特點,也與西方現代美學的精神有著深層的呼應”。[8]葉朗的研究,體現了對古今、中西不同話語系統本質差異的關注與整合研究的意識。
而在另一些同樣使用這個傳統范疇的藝術研究文本甚至基礎教科書中,“意象”卻被移花接木地拼貼于“抽象”和“具象”兩個典型的西方藝術概念中間,拋棄了“意象”在中國文化史中從生成到成熟所攜帶的哲學觀和審美智慧,成為一個可有可無地對主/客二元兩極的中間形態的描述概念,郢書燕說。元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論詩的兩段話,清晰解讀了中國藝術審美中的“意象”生成,絕沒有在抽象/具象二元中間的意涵。“情景名為二,而實為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姜齋詩話》)“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截分兩橛,則情不足興,而景非其景。”(《夕堂永日緒論》)
要言之,中國藝術學話語體系的建構,關鍵要在深入、完整把握中國文化解讀世界的人文視角和藝術智慧的基礎上,理解其核心范疇在歷史語境中生成、演變的基礎涵義,進而在現代話語實踐的問題情境中形成與其他話語尤其是西方話語的對話,而不是斷裂性的“剪貼”。在此問題意識中,當下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實踐的“系統自覺”,是一個核心的學術工作問題節點。葉朗通過對“意象”范疇的研究及與西方現象學哲學的對話,為他的現代美學體系核心區敷上了中國色彩。但必須看到,這一學術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是需要學術共同體合力的宏大工程。學界對葉先生研究得失的討論[9],為我們探討對古今、中西藝術理論話語的超越性實踐,提供了啟示。踐行藝術學理論的中國話語建設,一定是在多方觀點爭論、不同智慧碰撞中推進的。
四、主體性自覺:話語建設的基礎路徑
中國藝術學學科話語建設,首先離不開“中國”。毋庸諱言,一段時間里中國藝術話語實踐在廣泛借鑒西方話語以求變的追求中,某些方面脫離了中國經驗,主體性變得游移不定。
關于“主體性”。從黑格爾的關系性自我意識“主奴辯證法”,到拉康的鏡像理論,描述了一個主體性建構的基本關系式:個體不能自我確立,它是在另一個對象化了的他人社會關系中認同自己的。拉康用嬰兒與鏡的關系比喻了“主體”的建構過程是一個文化—社會話語的“他者”對個體“原初自然”主體的取代過程。[3]184在這個學理之下,以“對象性”來討論中國藝術學話語實踐的主體性,可以歸納出主體性的四個層面:其一,對藝術創作、人才培養經驗的學科規律性總結,對藝術的人文價值、審美價值觀念的理論提煉,即由學科研究對象塑造出的學科屬性,或曰學科主體性。其二,對中華審美精神、藝術創作思維特點的詮釋和對民族藝術經典的研究,由對藝術傳統的繼承塑造出的民族主體性。其三,馬克思主義思想、藝術為人民的社會主義文藝價值觀,對藝術問題把握、研究、解讀的方向性引領,可稱為思想主體性。其四,作為個體的藝術創作、研究、教育學者,通過在學術共同體中承擔有學術價值、創新意義的工作,其成果和工作顯示的個性特點和獨特貢獻,可以稱為學科的個體主體性。顯然,這種個體主體性又需在融入前面三種社會主體性的實踐之中,才能生成個體的主體性實現。
從以上四個層面看,如果說學科主體性是對專業領域的認知,那么民族主體性和思想主體性就是學科建設的精神文化價值觀。問題在于,藝術學科究竟是一個純藝術的、知識論的學科,還是一個擔負民族人文精神傳承與創新發展責任的、價值論的學科,對此曾經一度眾聲喧嘩而莫衷一是。其中一些現象與理論言說,往往把藝術形式創造與審美價值理想割裂,把藝術個性表現與藝術社會責任割裂。在此問題意識中,當下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必須將主體性自覺作為話語建設的基礎路徑,否則一切都將在喪失了身份感的空談中迷失。
進而言之,主體性自覺,是要通過藝術學學科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性質與功能而顯現,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是通過學科性質與功能在實踐中的實現成果而互動推進的。作為人文價值認知型學科,無論是藝術創作、藝術理論還是藝術人才培養的實踐形式,既包含了藝術創作表達、藝術規律闡釋和人才培養等諸方面的知識論內容,也包含著對藝術發展和社會審美接受的應然狀態的理想化追求和精神價值詮釋的價值論內容。因此,藝術學學科的性質與功能,是主體性的集中體現,是話語建設的基礎路徑,集中表現為藝術的知識技能與人文價值理想的統一,藝術創作與理論研究的統一,專業人才培養與文化精神引領的統一。
行文至此,關于“主體性自覺”作為中國藝術學話語建設的基礎路徑的意義,可以歸納為:必須明確思想主體性,以亮出話語實踐的思想旗幟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高揚民族主體性,以建構文化自信的學術立場與學術工作的“系統自覺”;必須清晰學科主體性,以學科方法論、核心范疇提煉和人才培養的專業化水平,在實踐中實現學科性質與功能的全面顯現。在這一必然是長期的、艱巨的、閃光的事業進程中,個體主體性以在推動事業前進的學科共同體“合力”中留下個性的印記而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