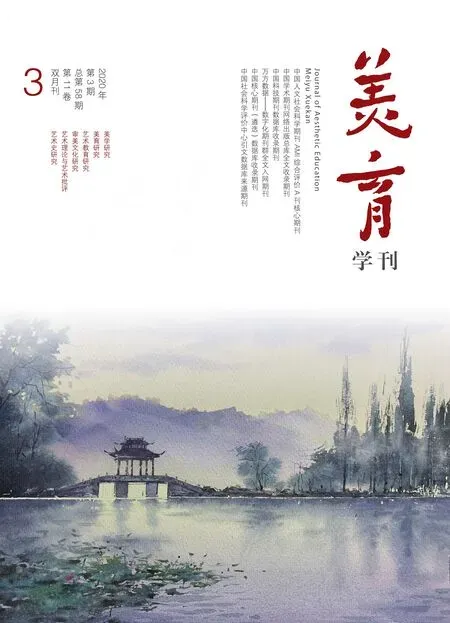新實用主義的美育觀
——舒斯特曼與羅蒂比較論
王 偉
(福建社會科學院 文學所,福建 福州 350001)
與傳統美學范式相比,西方后現代哲學、美學最為突出的特征莫過于反形而上學,或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形而上學可謂一把“雙刃劍”,它既開啟了美學生態的嶄新空間,也引發了熱衷解構、不事建構以及流于相對主義等諸多擔憂。正因如此,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曾嚴詞批評柏林(Isaiah Berlin)在堅決反形而上學時,往往流連于多元主義與反極權主義之類的主題,而對正義、同情或者團結等問題則漠然相向。[1]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反形而上學之后做什么這一方面,新實用主義陣營的羅蒂(Richard Rorty)與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二位學者的表現可圈可點。羅蒂以其《哲學和自然之鏡》(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1979)解構了傳統哲學的基礎主義,并在《哲學與社會希望》(PhilosophyandSocialHope,1999)一書中明確提出“泛關系主義”(panrelationalism)[2]的主張——一切均需在關系網絡中進行定位——取而代之,有效地堵住了相對主義的可怕漏洞。而其《偶然、反諷與團結》(Contingency,Irony,andSolidarity,1989)雖然從偶然的哲學立場起航,但落錨之處卻是經由美育去創造出共同體的團結。同樣,舒斯特曼現在也持這種偶然的觀點,也特別強調美育對促進共同體團結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舒斯特曼每每極力論證自己與羅蒂的不同,甚至不惜付出對羅蒂著作斷章取義的代價。因此,全面考察羅蒂與舒斯特曼的美學、美育思想,厘清兩者的差異與共同點所在,并進一步辨別其中的洞見與不見,顯得頗為必要。
一、舒斯特曼對羅蒂的誤讀舉隅
雖然羅蒂與舒斯特曼通常都被視為新實用主義的健將,但有意思的是,舒斯特曼不太樂意別人把他與羅蒂相提并論,尤其反感別人將他們的觀點混為一談。在回應馬格利斯(Joseph Margolis)“太深地落入羅蒂的咒語”的攻擊時,舒斯特曼一方面表示這可以理解,因為畢竟羅蒂強烈影響了他在實用主義中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又認為這種理解令人吃驚且具有誤導性,因為他與羅蒂的觀點有太多的沖突。通讀舒斯特曼的多本著作,不難發現,他時常批評羅蒂,并在與羅蒂進行論辯的過程中來彰顯、界定自己的觀點。遺憾的是,很多批評常常經不起推敲,有的批評甚至被舒斯特曼本人后來的著作所否定。
首先,關于形而上學或本質問題,舒斯特曼在《實用主義美學》(PragmatistAesthetics:LivingBeauty,RethinkingArt,1992)中明確表示,實用主義“必須反對不可改變的本質的基礎主義觀念,這種本質永久地定義我們的對象和概念的不同的同一性”。然而,緊接著他就開始指責羅蒂的反本質主義過于激進,甚至因強調個性和偶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成了“倒轉的反本質主義的本質主義”。(1)這種論斷未能明了羅蒂“偶然”范疇的內涵,難以成立。詳見王偉《羅蒂是倒轉的本質主義者嗎?——與舒斯特曼先生商榷》一文(載《華中學術》2018年第3期)。他主張,“后羅蒂的實用主義”既能與基礎主義認識論斷絕關系,又可以重新啟用本質的觀念。[3]119-119顯然,這是一種較為溫和、兩面討好的折中之舉,這一本質屬于歷史化的本質。耐人尋味的是,約莫十年之后,舒斯特曼的《表面與深度》(SurfaceandDepth,2002)繼續批評羅蒂“夸大了實用主義的偶然性觀念,賦予它一種獨特的任意性或隨機意外的意義”[4]255,卻對所謂歷史化的本質絕口不提。而在其最新著作《情感與行動:實用主義之道》(ActandAffect:PathsofPragmatism,2018)(2)該書源于舒斯特曼2017年在復旦大學的系列講座。中,開篇第一章“實用主義十原則”的首條即是“實在的性質是變動的、開放的、偶然的”。舒斯特曼指出,“生活和社會世界中的事物或事件是偶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是完全偶然、任意的,并因此不受任何可測、可知、可用的規律的支配。這即是為何盡管所有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都強調偶然性(皮爾斯[C. S. Peirce]稱之為‘偶成論’[tychism]),卻都懷有對科學和科學方式的積極信仰。當代哲學家中的后結構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包括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也時而吸收這種‘偶然性’,但并未導致懷疑主義或相對論立場,而是不時地推進了新實用主義視角”。[5]3-4時隔多年,舒斯特曼終于在哲學立場上向羅蒂致敬,就此與羅蒂“握手言和”。他現今對偶然的上述認識與闡述,恰恰正是羅蒂一直以來申述再三的觀念。不妨說,歷經長期的誤讀,舒斯特曼最后還是選擇站在羅蒂身邊,選擇維護新實用主義出發點的一致。因此,他在這個問題上才對羅蒂做出了完全正面的評價,當然也是客觀的評價。
舒斯特曼坦承,“我的立場有時候等同于羅蒂的立場,因為我們都清晰地表達了實用主義的杜威版,這種實用主義強調審美的維度”。[4]255雖然他們都從杜威的理論遺產中不斷汲取營養,但在具體取向上有時卻分道揚鑣。譬如,舒斯特曼對羅蒂拒斥杜威的經驗概念就非常不滿,他大張旗鼓地呼吁應予重振并付諸實施。準確地說,舒斯特曼抨擊的是羅蒂對經驗的語言化、闡釋化,因而,他針鋒相對地張揚非話語性的身體經驗。誠如馬萊茨基(Wojciech Malecki)所言,“羅蒂并不否認非話語性經驗的存在。事實上,他只是主張,我們在沒有用語言表達出來時,不能將非話語性經驗視為一種哲學上的工具”。[6]如果回到歷史的系譜,可以發現,舒斯特曼與羅蒂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可謂實用主義“語言”與“經驗”百年糾葛的重演——從皮爾斯的語言開始,經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的經驗,到羅蒂的語言,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經驗,再到布蘭頓(R. Brandom)的語言,實用主義在語言與經驗之間往復式拉鋸。需要說明的是,杜威的“經驗”概念涵義復雜,“既有真實的生物學所描述的特征,又有精神文化滲入其中,即便是最基本的感覺,也超越了純粹生物的特性而有思想和觀念的介入”。[7]換句話說,它包容了相互角力的兩個向度,而羅蒂與舒斯特曼則分別執其一端。正是針對羅蒂過于強調人類的語言活動與動物的非語言活動之間的差異,舒斯特曼起而推崇男男女女非語言經驗的重要性。基于此,舒斯特曼還批評羅蒂“忽視了愉快和美的美學,從而把藝術簡化成制造道德工具的詩學”。[4]257然而,與此顯然互相矛盾的是,當談到審美教化的社會效應時,舒斯特曼卻又武斷地斷言:“這就是我的新實用主義立場區別于杜威最有影響力的當代擁護者羅蒂的一個要點。羅蒂(雖然不同于本雅明)認為,美學理應限定在私人領域。”[5]213我們知道,羅蒂反基礎主義的結果包括兩個板塊,其中,存在主義與實用主義部分各自構成了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領域,兩者都深度關涉美學問題。實際上,舒斯特曼的兩次批評都遮蔽了另一部分,應該合而觀之方可看清全貌。不過,從這種無的放矢般的苛責中,倒是能夠一窺美學、美育被舒斯特曼及其批評對象羅蒂所賦予的力量,形塑社會共同體的巨大力量。
二、舒斯特曼與羅蒂美育觀的異同
舒斯特曼與羅蒂對審美教育的重視都受到杜威美育思想的影響,同時兩人又都有各自的發展與新創。杜威晚年著作《作為經驗的藝術》(ArtasExperience,1934)對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把詩人稱作“文明社會的締造者”贊賞有加,他強調美學的倫理效用,認為藝術比道德規范更加道德。因為后者“往往會變成現狀的供奉、習俗的反映、既定秩序的加強”,而藝術對現實可能性的洞察不僅可以轉換成新的生活圖景,指引著人們去不懈地追尋。設若風云際會,它們的想象性呈現甚至能夠成為政策規則,積極介入并重新塑造紅塵俗世。“藝術成了使得對某些目的和意義的感覺保持活力的手段,這些目的超過了證據,而這些意義越過了僵硬的習慣”。[8]425-426在援引杜威的這一論述之后,舒斯特曼《哲學實踐》(PracticingPhilosophy,1997)指出,既然美學擁有豐富個體經驗、造就公共世界的效力,那么,就可以在此基礎上推演出“民主的美學觀”,或者說,從實用主義美學的角度論證民主。它包括三個相關的層面,其一,個體與社會息息相關,相互作用。個體對民主生活的積極參與可以使其經驗與自身更為豐富,而民主制度則可為其提供更多的機會,為其審美生活提供可靠的保證。其二,民主實踐既是實踐手段,亦是目的本身,共享經驗堪稱最大的人類之善。其三,民主制度尊重差異性,鼓勵個體自由平等地參與制定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從而豐富個體的生命經驗。[9]109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內容幾乎原封不動地在舒斯特曼的新著《情感與行動》中再次重現,用以證明實用主義如何青睞美學構筑倫理與政治的偉力。不難看到,這些還被概括提煉成實用主義十大原則的第五條“共同體”,更鮮明地突出了美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對舒斯特曼而言,“共同體不僅是認識的主題,也是審美、倫理與政治的主題。它促進實用主義最根本的民主傾向。如此,實用主義哲學家為民主制提供了認知的、倫理的和審美的論證”。[5]7讓人不禁莞爾的是,考慮到實用主義的這種美學觀念不免使其與審美主義的主流哲學背道而馳,舒斯特曼特地簡要回溯美學史并申辯,對美育工具性力量的看重是世界美學源遠流長的傳統,而非美國審美貧乏和文化庸俗主義的結果。
與舒斯特曼一樣,羅蒂對審美與倫理的融會也來自杜威對藝術的理解——藝術不只是男男女女閑暇時的消遣,而是“人類交往中一種公認的力量”,“解放和統一的力量”。[8]426眾所周知,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描繪了一幅自由主義烏托邦的藍圖,其中,杜威與馬克思(Karl Marx)、穆勒(J. S. Mill)、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羅爾斯(John Rawls)等人一道,擔當著社會公民的示范。“他們共同參與一項社會任務,努力使我們的制度和實務更加公正無私,并減少暴虐殘酷”。[10]4羅蒂對團結的重視還淋漓盡致地體現在《筑就我們的國家》(AchievingOurCountry:LeftistThoughtinTwentieth-CenturyAmerica,1999)一書中。他激烈批評其時一些小說中四處彌漫的“民族自嘲和自憎”情緒,高度贊揚之前小說中展現的“民族希望和理想”思想。他認為,杜威與惠特曼(Walt Whitman)對民族希望與理想的形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他們眼里,講述國家、民族的故事絕不應停留于準確再現現實的水平,而更應該經由故事的重新描述努力培養一種精神認同,激發人們的參與感與自豪感。正因如此,雖然他并未采納布魯姆(Bloom. H)飽含激憤的“怨恨學派”一語,但依然完全贊同他對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等人文化研究路數的批判,依然完全贊同他對文學經典啟迪價值的竭力捍衛。
在汲取杜威美育思想,共同奔向團結的漫漫征途中,舒斯特曼與羅蒂所走的道路并不完全一致。舒斯特曼最引人矚目的是從經驗出發,舉起了身體美學、身體美育的旗幟。經歷過語言論轉向的羅蒂,自然批評杜威將經驗作為其哲學之中心難逃基礎主義的嫌疑。與之相反的是,舒斯特曼在承認杜威的經驗基礎主義的前提下,仍為杜威經驗概念的價值盡力辯護。他認為,“杜威的錯誤不在于強調經驗的統一性質,而剛好在于把這種性質視為一種在先的基礎,而不是一種重構的目的和手段”。[9]194舒斯特曼強調,經驗不僅在實用主義中仍然至關重要,而且,許多實用主義的價值恰恰在于那種直接的、非推論的經驗之上——它足以與被羅蒂指控的經驗區分開來。而這種經驗最顯著的構成是身體感覺,因此,身體經驗順理成章地成為問題的焦點。舒斯特曼直言,雖然自己賞識語言學轉向,但還是對其無所不在的籠罩趨向擔憂不已。所以,他堅持回到實用主義對身體和非推論經驗的傳統關注軌道。舒斯特曼大聲疾呼:“哲學需要給身體實踐的多樣性以更重要的關注,通過這種實踐我們可以從事對自我知識和自我創造的追求,從事對美貌、力量和歡樂的追求,從事將直接經驗重構為改善生命的追求。處理這種具體追求的哲學學科可以稱作‘身體美學’。在這種身體的意義上,經驗應該屬于哲學實踐。”[9]203若是在羅蒂的理論脈絡里,這種私人的完善與公共的目的斷然不必也不應統合起來,成為一個綜合性的理論,兩者完全可以各行其道、是其所是。但對舒斯特曼來說,自我完善則是通向、達到公共目的的重要工具。只要我們心儀那些目標并為之奮斗不息,那么,我們就理應尊重實現目標的工具。舒斯特曼之所以力倡身體美育,還與身體意識在傳統人文主義教育中所處的邊緣位置緊密相關。他認為,長期以來的一個偏見是把人文主義教育與自然主義相互對立,前者偏于精神方面而后者偏于生理方面,身體美育則致力于彌合這種分裂,將兩者融為一體。出于對經驗的重視,舒斯特曼還批判傳統的藝術概念與藝術制度狹隘地把通俗藝術視為美學上的非法存在物,有意遠離喧囂的生活實踐與活潑的日常經驗。他建議開放與擴大精英式的藝術概念,更多地關注社會與倫理的維度以持續推進它們的進步。明乎此,我們才能更深刻理解舒斯特曼為何樂此不疲地聚焦娛樂、拉普、爵士樂、鄉村音樂等話題,為眾多遭受貶低的通俗藝術家族發聲,不遺余力地展示它們被忽略的審美價值,以及它們對維護和充實生命的意義,論證它們的審美合法性與潛在的美育價值。
羅蒂的團結思想既閃爍著反本質主義的耀眼光芒,又攜帶著反諷主義的呼嘯激情——“反諷主義者是一位唯名論者(nominalisist),也是一位歷史主義者(historicist)。她認為任何東西都沒有內在的本性或真實的本質”。[10]107因此,討論羅蒂的團結思想,必須與偶然、反諷緊密結合。具體而言,羅蒂認為,“西方世俗民主社會中典型的道德和政治語匯,就是從這些歷史的偶然所發展出來的。隨著這些語匯被逐漸地非神學化和非哲學化,‘人類的團結’遂浮現出來,成為雷霆萬鈞般的有力修辭。我無意削減它的力量,只是企圖使它擺脫過去常被視為它‘哲學預設’的那些東西”。羅蒂“相信有所謂的‘道德進步’,而且這進步也確實朝著更廣大的人類團結的方向發展”,但他不認為“那種團結乃是對于所有人類共有的核心自我或人性本質的承認”。[10]273換言之,團結不再是對某一先在本質的朝圣與體認,而是一種特定歷史情境下的動態創造與建構。而且,羅蒂構想的團結頗具開放性,從理論上說其邊界有著不斷拓展的希望。這也暗示,與其沿著普遍主義的進路證明團結的必要性,不如從地方性視角來得更接地氣。不應誤解的是,放棄了內在本質的追求并不意味著放棄人類救贖的需要或美好生活的冀望,只是兩者要區分開來而非雜糅一處。否棄了不變的本質基點之后,反諷主義將團結感引至人類對危險共有的感受上。有意思的是,被舒斯特曼屢屢批評否定了經驗范疇的羅蒂,在這里恰恰主張正是這種人人皆有的非語言性的痛感,將蕓蕓眾生相互連成一體。問題在于,如何提高個體的敏感度,實現對陌生人的接納與認同呢?羅蒂十分贊同杜威想象力是善的主要工具的看法,在此基礎上,他更是提出整個文化應該詩化,從理論轉向敘述、從理性轉向想象、從知識轉向情感、從灌輸轉向感染。“逐漸把別人視為‘我們之一’,而不是‘他們’,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詳細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們自己的過程。承擔這項任務的,不是理論,而是民俗學、記者的報導、漫畫書、紀錄片,尤其是小說”。[10]7不言而喻,以小說為代表文類的詩化文化或文學文化針對的是先前的宗教文化與哲學文化。于是,它不再把精神教育的重任賦予學習宗教傳統或道德哲學等本質性的真理性知識,而是將虛構作品尤其是小說置于德育、美育的核心;它不再滿足于對神圣的服從,不再孜孜不倦地試圖發現真正的實在,而是盡力擴展人類的想象力、情感容納范圍的界限。羅蒂樂觀地展望說:“文學文化可以像哲學文化一樣成為民主政治忠誠的同盟軍。它不能被看作是反啟蒙運動的勝利,而應當被看作是用另一種更好的方式繼續啟蒙運動。”[11]
三、舒斯特曼與羅蒂美育觀的缺陷
舒斯特曼滿懷信心地宣稱:“比起其他大多數西方哲學家,我的實用主義哲學更加強調作為生活實踐的哲學的一個方面:培育有感知的身體,把其當作自我完善的核心手段,改善知覺、行動、德行和幸福的鑰匙。”[5]222這種對身體維度的極度凸顯,成就了舒斯特曼馳名中外的身體美學。比較起來,它在國內學術圈收獲了不少學者的熱捧,而在西方哲學界則遇到一些批評與質疑之聲。從學術的脈絡來看,舒斯特曼的身體美學主張通過身體訓練培養身體意識,打破了身體與意識截然二分的傳統窠臼,這無疑是其歷史意義所在,也是其受到肯定、追隨的重要原因。但在其身體美育的框架中,身體的訓練目前還滯留于自娛自樂的技術層面,與實用主義美學珍視的共同體原則仍然距離遙遙。或者說,我們尚未看到兩者接續的跡象。揆其根源,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身體“只是生活中的中性因素,本身并不能決定生活品質的高低”,舒斯特曼只觸及“活著”的層面,而擱置了“如何活”的價值選擇問題。[12]這種對身體價值維度的忽視,在舒斯特曼與張再林的一次對話中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談及身體意識的培養,舒斯特曼認為,中國古老的氣功、武術與印度的瑜伽等都是良好方式。值得留意的是,張教授馬上接過話頭,委婉地說:“您獨特的身體美育方面的思想與實踐,對于糾正我們當前對身體美育的片面理解很有意義。但我要補充說明的是,中國古人的身體美育不僅注重氣功、武術等身體訓練方式,而且特別注重通過‘修身’的方式來達到身體美育的結果。這種修身思想既強調對身體‘率性自然’的回歸,又不忽視對身體欲望‘發而中節’‘欲而不貪’的人文教化。如果說道家更多鐘情前者的話,那么儒家則更多地推崇后者。”[13]不難看出,張教授補充的恰恰是舒斯特曼遺漏的關于身體美育的價值問題。舒斯特曼對中國古代身體美學的誤讀或者僅僅表面相似性的勾連,由此亦可見一斑。所以,不必驚詫的是,當舒斯特曼被指責身體美學帶有揮之難去的自戀與享樂傾向時,儒家的“樂”“悅”之論才會讓他備受鼓舞。殊不知,儒家哲學固然將愉悅與認知緊密關聯,但儒家的“樂”是視野宏闊、治國理政的“樂教”,而非單純的感官快樂。《禮記·樂記》有言:“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4]254換句話說,這里的“樂”的主體絕非普通男女,而是圣人。“樂”的客體同樣也有限制,是為圣人所樂。因為樂乃人之常情,眾聲喧嘩不免趨于混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14]257兩相對照可知,舒斯特曼注意到了儒家善政離不開身體的一面,但并未明了儒家樂教對身體的詢喚及塑型、規訓與懲罰。儒家樂論與舒斯特曼實用主義美學的共同體旨規在精神上的確有些合拍,但與后者正面聯系快感與理解、欲望和身體實則又南轅北轍。
羅蒂敦促人們拋棄那種道德義務源于人性本質的理性教導,倡導通過文化的詩化進行美育,從而在想象與情感的擴容中建立鮮活可感的共同體或政治秩序。完成這一任務,小說確實擁有抽象說教難以比擬的優勢。正如德國思想家利希滕貝格(G. Ghr. Lichtenberg)所言:“我讀《一千零一夜》《魯濱遜漂流記》《吉爾·布拉斯》《棄嬰》要比讀《救世主》樂意一千倍;我愿花兩本《救世主》的錢去買一本篇幅不長的《魯濱遜漂流記》。”[15]盡管如此,理性認識仍有不可抹殺的必要作用,羅蒂實際上也未能將其徹底丟棄,它仍可作為一種有益的手段:“‘我們對于任何的人都有義務,只因其為人’的口號,正確的解釋方式乃是把它當作一種手段,來提醒我們隨時盡量擴充我們的‘我們’感。”[10]277進一步的問題是,羅蒂以廣義的小說來促進團結的大道,必須面對如下事實:文學既是鞏固意識形態的工具,同時亦是解構意識形態的利器。也就是說,小說美育正向的團結作用不容忽視,但它也有可能帶來分歧、對抗或分裂等負向的惡果。因此,關鍵還是怎樣的思想觀念在支撐、支配著美育的目標。毋庸置疑,它不可能擺脫主流意識形態的牽絆。形成較大反差的是,羅蒂在小說美育正向的坦途上高視闊步,而對負向的溝坎、泥潭與陷阱并未提及。在這方面,舒斯特曼的考慮顯得較為周全。他提醒人們,“或許我們不應止步于杜威關于藝術與社會之和諧有機的觀點。其實,藝術既帶來統一也帶來分離。比如,不同趣味群體之間的沖突是對創造力的有力刺激。除了統一的愉悅,在極度分離、不協調的和摧毀性的藝術體驗中也有審美、教育甚至社會價值”,“審美欣賞社會和諧也應警覺于不和諧之音,即遭掩蓋或驅逐的部分”。[5]212舒斯特曼還認為,藝術發展人的感性,提高道德感受與同情的能力,從而促進團結,這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觀念。它需要直面如下兩種指控:一是熱衷美育可能產生頹廢的審美主義,它不再有效刺激人們的道德感覺,反而助長了他們從惡劣現實中逃避;二是不應太相信藝術普遍的與民主的魅力,因為“美的藝術,通過其享有特權地區分于手藝、娛樂和通俗藝術,與其說是清楚明白地團結社會,不如說是將社會分隔開來并傳播那種分隔”。[3]208有鑒于此,對于從美育到團結的進發,還是保持低調的樂觀為宜。
結 語
盡管舒斯特曼對羅蒂多有一些不實之指責,譬如,將美學限定于私人領域、把藝術簡化為制造道德工具的詩學,等等,但作為新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實兩人都在反對形而上學之后致力于建構,都特別強調美育對促進社會團結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不同者,是由美育通向共同體團結的路徑:舒斯特曼強調非語言的經驗,高度凸顯了大眾審美與身體美育的功用;羅蒂則看重語言,訴諸詩化的文化。問題在于,舒斯特曼的構想囿于技術層面,缺少價值維度的引導;羅蒂則過于張揚想象在美育過程中的作用,對其負面效果未有顧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