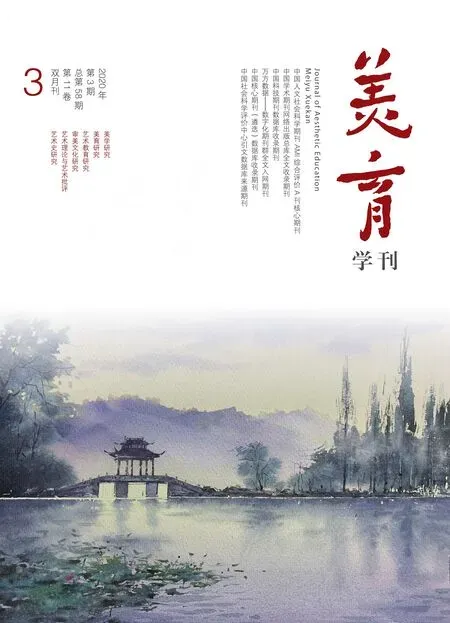王光祈國樂思想的當代價值
李沛健
(杭州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王光祈是近代中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音樂學家,是一位博學多才、學貫中西且以弘揚和傳播中華樂文化傳統為立學之本的杰出人士。他曾在國內外的大學里攻讀法律和經濟學等專業,最初理想是主張“實業救國”和建立“少年中國”,出國留學開闊視野后,根據實際情況改變初衷,改學音樂學,致力于在中國禮樂文化傳統基礎上建構新的國樂體系,以和諧“禮樂”推動“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為終身目標。
青年王光祈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致力于實業和教育救國,醞釀籌建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李大釗被特邀為發起人之一并參加了成立大會,王光祈擔任主要領導人。少年中國學會的總部設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及巴黎、東京、紐約等地設有分會,這是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學會,從成立到被迫解體短短的6年間里,共出版《少年中國學會叢書》32種,創辦了《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周刊》等刊物,使得少年中國學會成為五四時期規模最大、成果最豐和最具社會影響力的青年社團之一。應該說,為創建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通過少年中國運動改造中國社會,最終建立起能夠拯救中華民族脫離苦海,魏然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少年中國”。
追溯王光祈在五四運動中的杰出表現,他在重新選擇以“禮樂”之“民族特性”建立新的“國樂”體系,推動“民族復興”的道路之后,全身心致力于中西方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既向國內輸入西洋音樂的知識技能和理論體系,又殫精竭慮地充分發掘中華民族古老悠久的樂學傳統,將其精華和特色充分展現給西方世界等業績,這應該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如今通過挖掘王光祈鍥而不舍的奮斗精神、堅定毅力和解讀其偉大的人生,對我國當今美育與藝術教育全新格局體系的形成,獨具中國特色藝術學學科門類格局與話語體系的轉換,以及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引入西方樂學體系強身固本
為盡快實現少年中國的偉大夢想,王光祈于1920年4月遠赴德國法蘭克福留學,專攻經濟學專業方向。三年之后,當他進一步開闊視野和對世間萬象進行更加客觀全面的審視與分析研判之后,卻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經濟學專業和“實業救國”的主張,改學音樂學專業,致力于在中國古老悠久的禮樂文化傳統基礎上建構新國樂體系,即以“禮樂興國”為其終身奮斗目標。
他于1923年春放棄經濟學專業,開始拜師學習小提琴和音樂理論,1927年4月,終于如愿以償考入柏林大學音樂系,專門攻讀音樂學專業,成為較早在德國獲得音樂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在其之后的人生歷程中,他一方面將所學西方音樂的知識技能和理論體系傳入國內,一方面致力于將中國古代樂學體系與樂學思想的精髓傳向西方世界,充分展現了清末民初時期飽受災難和欺凌的愛國知識分子不畏盜寇、救亡圖存的博大胸襟和堅定意志。他的貢獻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有選擇地大量輸入西方音樂文論,二是通過全面比較研究確立國樂地位。
(一)介紹和引入西方音樂體系
經歷了在音樂學領域十年的艱辛拼搏,至1934年6月,王光祈終于取得波恩大學音樂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論中國古典歌劇》贏得廣泛好評。這期間,他一邊努力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一邊更加認真細致地對歐洲音樂的體系和特征等進行闡釋解讀,并第一時間將最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傳入國內。這方面的文論如《德國人的音樂生活》通訊10篇,在《申報》陸續發表后形成較大影響。著作有《歐洲音樂進化論》《德國音樂教育》《西洋音樂史綱要》《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制譜學提要》《西洋名曲解說》《西洋樂器提要》《對譜音樂》《西洋音樂與戲劇》《音學》《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等,涵蓋了歐洲音樂的方方面面。
王光祈的這些論著及時傳入國內,很快成為國人了解遙遠西方世界音樂文化的重要信息源,在當時剛剛起步的我國音樂學界及社會各界,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王光祈十分注重通過多種不同途徑和方式,向西方學界傳播中華民族的國樂文化。1933年10月,王光祈受聘于波恩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國文藝課講師,這就給了他充分展現母語文化才華的大好機會。
(二)通過比較研究確立國樂地位
當時國內學界對于如何看待中西方不同的歷史文化和音樂文化傳統,以及如何創建新時代的中國音樂發展體系,一直存在著頗多分歧和爭議。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有人主張全面恢復古樂體系,王光祈認為兩種主張都有其片面性,都無法適應現實和引導中國走向光明。經充分調研和深思熟慮,他提出了立足于本民族特性之上,創造偉大國樂的獨特主張。為實現這一宏大的理想和抱負,他曾傾注全力潛心于東西方樂制之間的比較研究,并通過一系列相關著作的出版,言之有物、言之有據地證明其論斷的正確性和實用性。
比如,他通過對中西方音樂的功能、屬性、特征和意義等的分析論證,尖銳指出激越而缺乏節制的西方音樂,可能會引發人的某些器官乃至精神疾患,而在中國禮樂互為表里相需為用的思想觀和價值觀基礎上生成的和諧樂音,則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凈化人的心靈,使人具有健全的身心和人格。故他認為,“禮樂”是“國樂”的基礎,而“和諧”是“禮樂”的核心,“和諧精神”是中國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
同時,由于他體悟到音樂中的“和諧”,與他所追求的“合理的社會改革”相吻合,故決心以“音樂喚醒國人”和用“音樂救國”。王光祈口中的“音樂救國”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是依照當時所處西方話語體系氛圍中的一種表述方式,其廣義的概念則是要以中國淵遠流長的“禮樂”救國興邦。他認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必須首先恢復自己的“民族特性”,中國的“民族特性”即“和諧態度”,而孔子所倡導的和諧“禮樂”,就是中國的“民族特性”。他說:“我以為,要喚起中華民族的再興,只有這‘恢復民族特性’的一個方法。什么是中華民族特性?簡單說來,就是一種‘和諧態度’。……這種‘和諧態度’,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存大地的根本條件,亦是我們對于未來世界的最大使命。”[1]
鑒于此,他以倡導和弘揚中華民族的禮樂文化傳統為立足點,致力于在此基礎上建構國樂體系,試圖通過對儒家和諧精神的傳播,引導和教化國民,改善國民的精神世界,消除近代中國社會積存的末世之風。關于如何定義國樂這一問題,他認為,國樂應該既能夠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向上精神,又能夠被國際學界所公認。因為,“民族性”既是民族生存的根本保證,又是這個民族的藝術文化能夠引起他國他民族關注的特色所在,故必須具備這個最重要的條件,方能堪稱其為國樂。而且這種國樂,要能夠簡捷生動地把中華民族“樂者樂也”的“和諧”精神表現出來,傳承開來,培養國民積極進取的愛國報國志向。
由此可見,王光祈的國樂觀牢牢地根植于母語文化的根基之上,因為他把民族性看成是民族生存的根源,認為民族性如若喪失則預示著民族的衰敗。由于他從小學習和養成了深厚的國學功底,身處歐洲又對當地的音樂文化做了深入系統的了解和分析,以至于當時能夠從元理論的深度對中西方的音樂文化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他的《東西樂制研究》《中西音樂之異同》《千百年間中國與西方的音樂交流》《音樂與時代精神》《中國樂制發微》《翻譯琴譜之研究》《東方民族之音樂》《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和《論中國歌劇》《論中國音樂》等著作,都是圍繞著建構華夏新國樂體系這一宏大主題而展開的。
王光祈最先把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引入國內,從而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同時,他通過對世界音樂的樂制體系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后,首次將世界樂制劃分為三大主流體系:即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這樣一種對世界樂制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研究,并作出既客觀科學又合情合理的結論的工作,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并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普遍認同,進而確立了中國樂制在世界音樂文化格局中的獨特地位。這給當時處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文化自信心嚴重受挫的境地中的中國學界,帶來無盡的能量和強勁的動力。
二、竭力挖掘國樂精髓對外傳播
關于如何區分華夏國樂傳統的精髓和糟粕問題,由于社會歷史的、政治的、階級的和倫理的等多種觀念的沖突,一直存在著諸多斬不斷理還亂的死結。比如對于古代宮廷雅樂、文人音樂和民間俗樂之間的關系及其優劣、價值判定問題,均囿于上述原因而存在不同觀點。
由于王光祈在國內曾系統接受傳統文化的教育,熟知我國樂文化傳統體系及其精神實質,留學歐洲之后,又對西方音樂的知識體系、思想內涵和價值觀念等做了全面了解和分析研判,而且當時恰逢西方學界漸興一種厭棄西方物質文明、傾慕東方精神的思潮,許多西方學者以談孔子、老子學說為時尚,斯賓格勒《西方之沒落》等書的風行于世和廣受贊譽,更為其創造了良好契機和增添了精神動力,以至于他從心底里發出了“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的豪言壯語。
綜合當時社會的多種思想文化元素,王光祈很快超越了固有的思維模式,跳出了社會歷史所形成的小圈子,從而能夠較為客觀科學地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他提出要提高中國人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創造新文化,對世界做出貢獻。另外他不遺余力地把中國五千年樂文化傳統傳向歐洲,其目的一是促使東西方文明有攜手機會,二是減少普通歐洲人輕視中國民族的心理。他認為,“國樂必須吾人自行創造”,而“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如此膽略和氣魄,展現了王光祈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王光祈對2500年前孔子的禮樂思想做了深入細致的考證研究,并和西方人在該領域的認知進行互通,尤其是對中國樂文化傳統在培養人的道德修養、健全人格與樂善好施性情等方面,恰如其分地做了既深入細致又通俗易懂的解讀。他論述道:“數千年來,孔子的世界觀始終占有統治地位。所以,這一世界觀也是中國音樂的建設性因素和基本思想。孔子所關注的思想就是:借助音樂來培養中國人的性格,從而使他們能與周圍的人們以及自然非常諧和地共同生活。因為有了這一學說,所以中國在數千年間沒有發生宗教戰爭,沒有權力崇拜。因而,中國是惟一的一個至今仍然根植于自己獨特文化傳統有著四萬萬人口的文明古國,而且,盡管時有內戰,但她仍保持著文化的統一和共生。偉大的中國哲學家老子(前604年)曾在其著名的《道德經》一書中提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所以照老子的看法,凡刺激感官的東西,皆應屏棄。相反,孔子認為,不應輕易回避人的各種享樂,但不應過度。所以,他的主要學說是‘中庸’,它在中國占統治地位達數千年之久。……孔子對‘善’的喜好,對中國后世的音樂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
毋庸置疑,像王光祈這樣一方面努力把歐洲音樂的知識體系輸入國內,一方面致力于將中華國樂傳統深入淺出地直接展現給歐洲社會,具有如此豐富學養和頑強毅力的學者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而這樣的雙邊互動,既讓中國人進一步了解了歐洲的音樂文化,又讓歐洲人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古老的禮樂文化,也的確實現了王光祈“促使東西方文明有攜手機會,減少普通歐洲人輕視中國民族的心理”的夙愿,且對于之后中西方音樂文化、學術文化、思想文化和社會文化諸方面的交流互通,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啟示性和引領性作用。
三、深入研判、影響至深
王光祈人生的最大亮點,是其在向歐洲學界介紹中國樂文化傳統精髓的同時,不失時機地運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針對中西方音樂文化的內涵和作用進行深度研判,區分優劣,對一些根本問題和要害問題提出自己獨立的見解和看法,廣泛傳播中國古代禮樂文化育人、樹人和改善調適社會風氣等多種獨特功能。
(一)對中西方音樂傳統的研判
首先是在音樂本體的聲響和功能作用方面,通過對中西方音樂不同的律制、聲響、風格、功能和創作實踐等方面的分析研判,王光祈十分尖銳地指出了西方音樂毫無節制的音樂聲響,對人的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他充滿自信地說:“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音樂并不怎么好聽,至少對歐洲聽眾是如此。當然,中國人保持了健全的神經。歐洲人患精神疾病的要比中國人多得多。即使在著名的作曲家中,就有不少耳疾患者和精神病患者,如重聽的有貝多芬和法蘭茨(FarnZ),精神病患者有舒曼、斯美塔那和沃爾夫(Woir),英年早逝者有莫扎特、舒伯特、韋伯、門德爾松、尼古萊(iNcolia)、肖邦和比捷等。音樂的過度刺激是否也是這類疾患的部分原因?對歐洲人而言,這并非是個無足輕重的問題。”[2]
其次是在音樂審美觀和價值觀等方面,針對西方人引以為自豪的法律和宗教問題,王光祈十分敏銳指出了二者在強行約束人的思想和靈魂的同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禮樂之邦”,而且歷經夏、商、周三代完善了“禮樂教化”這一先進的教育體制,使我國人民在樂(le)教與樂(le)學的過程中,節制其外部行為,陶冶其內部心靈。相比之下,西方國家用法律和宗教強行制裁人的行為,使人產生敬畏心理,是一種不可取的類似于野蠻民族的做法,故提出了以禮樂代法律宗教的鮮明主張。他一直強調:
“禮樂之邦”四字,是從前中國人用來表示自己文化所以別于其他一切野蠻民族的。但這四字,同時亦足以表示中西文化根本相峙之處。我們知道:西洋人是以“法律”繩治人民一切外面行動,而以“宗教”感化人們一切內心作用。所以西洋人常常自夸為“法治國家”與“宗教民族”,以別于其他一切無法無天的未開化或半開化民族。反之,吾國自孔子立教以來,是主張用“禮”以節制吾人外觀行動,用“樂”以陶養吾人內部心靈。換言之,即是以“禮、樂”兩種,來代替西洋人的“法律、宗教”。“禮”與“法律”不同之點,系在前者之制裁機關,為“個人良心與社會耳目”;后者之制裁機關,為“國家權力”與“嚴刑重罰”。“樂”與“宗教”相異之處,則在前者之主要作用,為陶養吾人自己固有的良知良能;后者之主要作用,在引起各人對于天堂、地獄的羨、畏心理。——因此之故,音樂一物,在吾國文化中,遂占極重要之位置;實與全部人生具有密切關系。[3]
如果說法律和宗教在歐洲國民的內外生活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的話,那這兩者自古就受到中國人的強烈抨擊。中國的偉大圣賢孔子認為,每個人都有良知(良心)。而只有良知得到教化,每個人才能約束自己。如果人只是敬畏國家的刑法和蒼天的懲罰,那為時已晚。孔子用禮樂作為國民教育的基礎來代替法律和宗教。禮應規范人的外部關系,但不能通過諸如國家權力機構來實施,而應通過自己的良知,即自省來自我規范。而樂則應平衡人的內心生活,不能通過諸如敬畏上帝來實施,而應通過獻身于音樂的安慰作用來實現。[2]
(二)在近百年來國內外學界的持續影響
王光祈作為少年中國學會領導人時,在緩解各黨派意識形態分歧和調解矛盾沖突等方面顯露出非凡的人格魅力,故包括國共兩黨的許多杰出代表人物都對其欽敬有加。如當年蔣介石曾專門致電:“如愿回國,當圖借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念念不忘和王光祈之間的深情厚誼,不止一次托川籍友人探尋其四川老家后人的下落。同時,許多中外知名學者和團體對其學術思想、學術成果和人格魅力等,不斷進行探討研究并作出有高度評價。
如冼星海評價說:“我們不能忘記這位音樂理論家王光祈,他推動了新音樂的發展,他的刻苦耐勞是我們從事中國新音樂的模范。”[4]1
呂驥認為:“王光祈是我國五四運動前后到抗日戰爭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愛國主義著作家,卓越的音樂學家。將東西方之音律,東方各民族之音律進行比較研究,始創于王光祈,這無疑是中國音樂學上一大貢獻。”[5]
沈有鼎在《東西樂制之研究》(書評)中說:“王君說:‘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這是何等深遠的期望!一般開明的中國人,以為中國沒有什么高尚的音樂,不是中國民族之所長。豈知中國古代,音樂是唯一的藝術,也代表了藝術的一切。古書上惟有關于音樂的記載,總是十足地表現著藝術的眼光的。……我們生長在現今這個混沌的時代,舊文化已結束,新文化還沒有產生,然而我們可以預先斷定:未來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動的文化,音樂的文化,社會性的文化。在某種意義內,中國民族確是世界上最富有音樂性的民族。”[6]
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卡勒教授的評價:“他努力介紹西方音樂的精華到中國去,并且應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還未有人碰過的材料;在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個前驅者。……他在研究院無時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確定的態度來工作,他是一個靜默穩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細細認識他,方可以了解他的偉大。”[4]1
波恩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希德瑪教授評價說:“他把握了西歐,特別是德國方面研究音樂的科學方法與途徑,由此設法與他的故鄉的音樂與戲劇的藝術相接近,這居然給他做到了!他已是一位受有嚴格教育的音樂學家。”[4]1
綜上可知,王光祈的國樂思想及其精神實質,包括他在各種著述中所提出的諸多救亡圖存推進民族復興的主張,不僅在當時我國的社會各界曾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在近百年來國內外學界都受到很高的贊譽。
(三)在我國當代美育與藝術教育中的作用
王光祈的國樂思想是一個綜合多元的宏大學術體系,他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古老的樂文化優秀傳統之基礎上,融入西方現代音樂理念和知識體系,從而使其既承載著深沉厚重的傳統文化底蘊,又具有五彩斑斕的現代藝術文化氣息。故筆者認為,王光祈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必將在當今和未來我國的美育與藝術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繼續發揮作用。
藝術學升格為第十三個獨立的學科門類,標志著我國以藝術教育為主體的美育教育進入一個劃時代的高速發展時期,文化強國發展理念的確立和完善,進一步推動著民族文化復興的步伐。而追溯歷史不難發現,中國思想文化和藝術文化的根,均源于上古三代就已經孕育成熟的“禮樂”傳統。那么,王光祈當年重新選擇以“禮樂”之“民族特性”為立足點,推動“民族復興”的主張,應該說是反映了他高度敏銳和堅定的文化自覺精神,是對祖先智慧的延續。
就藝術學相關一級學科的設置來看,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等一級學科,明顯延續著我國傳統藝術文化多元一體的綜合性特征,故在王光祈的時代,雖然由于當時社會積弊較多等原因,他的理想追求和宏大夙愿并未能夠完全實現,但卻為當今我國美育與藝術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成為中國藝術學諸學科話語體系轉換過程中一個重要的亮點和催化劑。
(四)在未來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國經歷了由經濟強國到文化強國的重大轉型,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新命題和新使命,它標志著我國實現了由物質文化建設為中心轉向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建設并舉,并以此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跨越。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物質文化建設還是精神文化建設,都必須以教育為本,而我國由來已久的“樂教”傳統,即以“樂”為統領的綜合性美育與藝術文化教育,對于人的道德、人格、審美、文化等方面修養,以及理想、信念、風骨、情操等的培育,包括整個社會的移風易俗和形成良好精神風貌等均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總而言之,王光祈當年選擇獨具中國特色的由“禮樂”轉化為“國樂”推動“民族復興”的道路,是經過全面考察和深思熟慮之后所做出的重大抉擇,因為他對中華民族的樂文化傳統有著充分的了解和深刻認知。遠古時代的“先王樂教”,夏商周三代進而完善為“禮樂教化”的系統體系,其“樂教”并非當今單一的音樂教育,而是包含有“樂德之教”“樂語之教”和“樂舞之教”,即含納了當今國家教育方針中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全面教育的大部分內容。
同時,從中國古代藝術文化發展和認知的角度,所有的藝術門類均以“樂”為統領,如沈有鼎所言“音樂代表了藝術的一切”。故在當今世界文化由單一科技文化格局轉向綜合創新文化格局的大趨勢下,王光祈當年在繼承和弘揚我國古代禮樂文化傳統基礎之上倡導建構新型國樂體系的努力,以及在對中西方音樂進行全面系統的比較研究之后做出國樂必須自主創建而不能強行照搬西樂模式的論斷,充分彰顯了國家危亡之際中國知識分子不屈不撓的奮斗與拼搏精神,可以說開啟了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序幕和前奏,這對當今我國學校美育與藝術教育的改革發展,以及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都將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