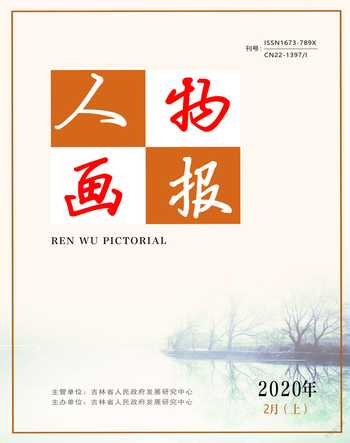民俗“枷鎖”下的紙扎藝術“舞蹈”
鄭欣欣
摘 要:喪葬文化是以特定禮儀來傷逝悼亡,喪俗的內容是對死者的悼念,是向死者告別的一種儀式,又是對活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傳授,應屬精神文明范疇。隨著社會進程的推進,紙扎作為陪葬明器得到了發展,是兼具審美價值和精神意義的載體,沉淀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內涵深厚的重要儀式,是藝術與民俗相互影響下的特殊產物。
關鍵詞:紙扎;民俗;藝術;喪葬
一、紙扎
中國的紙扎藝術是蘊涵著紙扎、貼糊、剪紙、彩繪等技藝,并將其融會貫通的民間藝術。紙扎是一門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技藝,最初是源于古代民間的宗教祭祀活動,并演變形成一種裝飾流派。除了滿足信仰心理和精神需要,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紙扎工藝同樣承載了藝術傳承的重要角色,盡管手藝人可能并沒有學過系統的藝術美學,但是充滿結構感、色彩感、材質搭配的構思與制作就融注在他們的作品里。紙扎的制作是一種結合了立體塑形、平面制作、色彩搭配的綜合藝術,紙扎先用高粱秸、麻稈等捆扎成骨架,然后用白紙以及藝人自制的面漿糊制作形象的外型,最后再用彩紙通過剪、刻、印、壓、揉、搓、畫等多道工序將扎制的事物模擬裝飾,使其相似于現實中的事物。紙扎開始時以剪為主要方式,后發展為包括裱糊等多種技藝并存,可以認為紙扎是剪紙藝術的延伸和三維化應用。
二、紙扎中的藝術語言
一是結構造型藝術。考慮到重心與重力,在大件紙扎作品如豬、牛、羊、馬等動物紙扎的底座上需要有方形加斜桿做三角形固定,即三角形的穩定性。同樣,立體構成在紙扎作品中處處可見,球體紙扎燈是將碾壓好的秫秸稈,連接兩端形成圓環,再將若干圓環通過尼龍繩交叉捆扎固定,最后形成圓球。以紙扎馬為例,馬腿作為整個骨架的支撐點往往需要較多數量的秫秸稈捆扎,在頂部通過傘形結構與其他部位互相連接和支撐,許多紙扎都做的十分高大,高達數米,因此龍骨的制作是紙扎的關鍵。潘魯生提到“供奉紙扎在造型上,不求物體的重量感,不強調對象的體積和質量,而以塑、繪、虛、實結合,表現一種空靈輕盈、色彩燦爛的物象景觀和氣氛,在世界雕塑史上,它是一種獨特的處理手法。” [1]由上,紙扎同樣可以看雕塑的另一重延伸,是以秫秸稈、紙張搭建的三維立體構成。
二是材質搭配藝術。無論是骨架材料的選材還是紙張的選取,都可以看到在紙扎藝術中造價與展現效果之間的平衡。這點與設計思維有著共通之處,根據不同用途在成本控制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材料,本來也是設計藝術的體現。高粱稈、竹篾等骨架材料的選取可以看出先人那種就地取材、天人合一的靈巧之處,并且根據不同地域的材料特性的不同,在紙扎的線條感與骨骼感上更是有所差別。紙材的選取更顯手工藝人的設計思維,紙質有軟硬、薄厚、滑澀之分,通過紙張肌理的變化輔以折疊、揉搓等手法制作的肌理可以打造出精彩紛呈的紋理變化也就給人以多彩的視覺感受。首先打底紙選用便宜、輕薄的白紙,便于調整和修型;在外面形象的塑造上使用量最大的花紙和色紙,質感啞光平滑給人以厚重、質樸之感;而細膩光亮的電光紙多制作紋樣進行裝飾;此外還有金箔紙可做金銀裝飾;褶皺紙可以制作扎花等。紙張的輕便性與經濟性,是決定紙扎應用的另外兩個因素,貧寒百姓也可為自己的親人辦一場風光的儀式,這也是紙扎得以傳承的重要原因。
三是色彩裝飾藝術。手藝人們多半并沒有系統的學習過色彩美學、色彩原理等院校科目,紙扎藝術中的創作多半是來自約定俗成的傳統和了然于心的經驗。紙扎的配色是傳統工藝美術中具有鮮明特點的一項,在顏色上紙扎不講求和諧而更強調視覺沖擊和裝飾效果。山東紙扎的顏色大都采用紅、黃等鮮艷的暖色為主體,再輔以一些綠、藍、紫等冷色,相鄰顏色多用對比色系,如黑白搭配、紅綠搭配等等,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極具裝飾效果。同樣在色彩不夠協調時,通過劃分色塊比例以及黑白顏色進行分割是常用的手法,這在藝術設計中也是常用的手法,類似于插畫中的描黑與描白。在裝飾上,紙扎工藝是集剪紙、刻花、繪畫、貼畫、印刷融為一體的藝術。以紙扎人為例,將黑色的紙張剪為條狀做頭發的質感,這種技法在紙馬之類的動物紙扎上十分常見。其次在服裝上,謹從現實社會的服裝款式,在過去的時代多采用繪制與貼花來對服裝進行裝飾,到了現代,印刷機器的產生使得服裝紋樣更加精美,傳統和現代的款式相映而行,服裝配飾等零件可提前預備,紙扎的制作時間和流程大大縮減。
紙扎這門傳統的工藝美術,是讓人敬畏的一種儀式、一種藝術。敬,是人們對于先人的哀思與祝愿,同樣寄托著對于美好生活的期許。畏,是在鬼魂觀念、宗教信仰影響下的精神結果,是動物本性在面對死亡的自然表現。人類數千年談“葬”色變的思想,在短時間內不會輕易發生改變,我們有理由相信,殯葬儀式會伴隨著“死亡”發展和傳承。正如任何一種傳統文化的傳承一樣,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現代紙扎的發展中,工業化的發展使得紙扎從業者有所增加,社會的發展也給紙扎的內容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原來的金山、銀山、米山、面山上逐漸被銀行、冥幣、糧米所替代,相機、四合院、別墅、雞翅、米線寄托著生者對死者的寄托與撫慰。從紙扎中,我們能夠洞見民俗、禁忌、鬼魂觀念在紙扎載體上的體現,它不僅僅是一種技藝,更是一個承載精神內涵大于審美意義的工藝。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多種殯葬方式被群眾所接收,紙扎的內容早已不再局限于紙人、紙馬等造型,米線、飛機、路由器等新奇造型層出不窮,從中可以看出生者對死者對愛護和祭思。盡管如此,喪葬紙扎也仍然是服從民俗、殯葬的禁忌、規定上創作,是民俗“枷鎖”下的靜默無聲的藝術 “舞蹈”。
注釋:
[1]潘魯生:《紙扎制作技法》,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2頁。
參考文獻:
[1]榮新. 魯西南喪葬紙扎研究[D].山東大學,2014.
[2]陸錫興.古代的紙扎[J].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04:106-113.
[3]潘魯生.民間喪俗中的紙扎藝術[J].民族藝術,1988,01:54-63.
[4]盧世主.基督教的傳播對中國藝術設計的影響[J].文藝研究,2010,06:145-147.
[5]陳成,陳敏.美術元素在湘西北地區鄉土喪葬儀式中的應用[J].科技風,2019,29:218.
[6]王滕滕,石禮華.山東農村喪葬問題調查與對策建議[J].農村經濟與科技,2020,3111:295-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