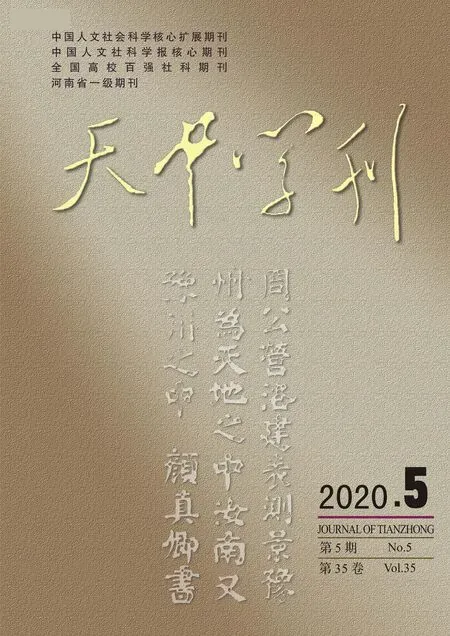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早期理論探索
李萬營
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早期理論探索
李萬營
(中山大學 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275)
1994―2004年,中國敘事文化學開始起步并獲得快速發展。寧稼雨開設的《敘事文化學概論》課程系統闡述了敘事文化學的范疇、對象和方法:一是形成了適用于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主題研究路徑、主題類型,且進行了成功實踐,并將故事類型索引編制確定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整體構架之一;二是逐漸確認敘事文化學的學科屬性,提出“以中為體,以西為用”的總體方針;三是提出“竭澤而漁”的文獻收集理念,不斷補充完善文獻收集方法途徑。學位論文基本遵照敘事文化學的研究思路,寫作模式由最初以時間順序設立章節到以故事情節文化要素設立章節;選題方面由選擇以人物為中心發展到選擇以事件為中心;文獻搜集方面由搜集常見材料到不斷收集方志、古跡、名物傳說等材料;文化分析方面由主要對故事演變的社會文化原因做探索,到對故事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做分析,呈現出積極探索的痕跡。在學科正名、敘事文化學框架體系的完善、故事類型索引的編制、敘事文化學相關理論的闡發與建構以及個案研究方面,敘事文化學有著廣闊前景。
敘事文化學;主題學;起步時期;課堂教學;學位論文
寧稼雨教授創設的中國敘事文化學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學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一門學科、一種理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其產生發展的過程,對此過程的回顧,可以為相近領域、學科、理論提供參考,因而具有學術史的意義。1994―2004年,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的起步期,這十年間,敘事文化學主要以課堂教學與學位論文的形式得到展示與實踐。筆者于2014年有幸成為寧門弟子,得習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成熟理論,雖未親歷起步期,但酌古鑒今,或許更有參考意義。
一、課堂教學內容中蘊含的理論體系雛形
寧教授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理論的積極思考,在課堂教學中得到系統闡述與不斷豐富、發展。1994年,寧教授為文學院研究生開設“敘事文化學”課程,旨在通過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初步了解和掌握主題學、文化學的研究方法,用以分析中國敘事文化學中的各類主題。本課程系統闡述了敘事文化學的范疇、對象和方法,并以相關研究作為主題研究和題材研究的示例。在課程開設之初,寧教授對敘事文化學的內容、目的和研究方法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即以文獻考據學方法,解決敘事文學作品的文獻、文本自身形態演變的過程問題。在此基礎上,以文本對象為基本視點完成對源和流進行解釋和闡釋的工作,分析、挖掘、解釋文本形態的面貌、動因。以此為中心,解釋了敘事、敘事文學、敘事文化等概念,詳細介紹了收集研究對象的文獻途徑以及對主題學、文化批評等研究方法的吸收與利用。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基本框架于此已具雛形,而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在課堂教學中不斷得到深化,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
一是在對主題學方面的吸收與利用方面,逐漸形成適用于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主題研究路徑、主題類型,并將故事類型索引編制確定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整體構架的三個部分之一,在研究方面也進行了實踐,并取得成果。
敘事文化學是在吸收主題學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主題學研究始于19世紀德國格林兄弟對民間文學的研究,側重分析民間故事的演變,主要思路是以主題、母題(以及意象、套語等)等為關注對象,研究不同時代、地域的作者對某一相同主題、母題的利用和改編等情況。寧教授敏銳地發現,主題學的研究對象民間故事與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在個體單元故事形態上具有很大相似性,即同一故事具有多種不同演繹形態。主題學研究以此作為方法成立的基本根據,這個根本點的相似為中國敘事文化學對主題學研究的借用提供了基礎和可能。關注同一故事在不同文體、不同文本之間的流動、演變,就是敘事文化學在借鑒主題學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基本研究思路。
在對主題學的認識方面,《敘事文化學》課程開設之初(1994年),主要向學生介紹主題、母題、意象、主題學、主題類型等概念,并指導分析如何辯證利用。1998年前后,在授課中開始深入分析主題類型的確定,在對臺灣金榮華《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元分類索引》以及國際通行的“AT分類法”分析、介紹的基礎上,思考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主題類型的特殊性,初步提出以人物、題材、具體事件、器物物件為對象的分類設想。2004年前后,已經形成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主題類型的成熟的分類標準,即自然類(非人工化的天然現象)、怪異類、人物類、器物類、動物類、綜合類六大類型,并提出將編制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主題類型索引作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三大目標之一。
與課堂教學所反映出的理論探索相對應的是,寧教授于1999年以《六朝敘事文學的主題類型研究》為題申請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該項目于2005年結項。2011年該項目成果之一《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獲得資助出版[1]。該書以天地類、怪異類、人物類、器物類、動物類、事件類六大類型為綱,對唐代以前敘事文學文本按照主題類型做了初步分類整理。在此成果的基礎上,寧教授將唐代以后的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編制也列入敘事文化學的研究計劃,目的在于摸清從先秦至明清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全部數量,并按照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體系需要,對其進行分類編號,便于從事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者的文獻檢索和參考。
二是在敘事文化學的理論思考方面,不斷摸索相關理論方法,逐漸確認敘事文化學的學科屬性,提出“以中為體,以西為用”的總體方針。
籠統地說,敘事文化學應該算作比較文學的一種研究范式,需要了解和借助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學科地位來站住陣腳,因而在最初的課堂教學(1994年)中,會強調敘事文化學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并將比較文學的主題學、原型批評、文化批評作為敘事文化學的具體方法。隨著對敘事文化學理論思考的成熟(1998―2004年)和對比較文學的了解加深,課堂教學會將敘事文化學與比較文學并列,分析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式——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在哪些方面能夠適用于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研究,從而可以為敘事文化學研究提供借鑒。相應地,將最初對敘事文化學具體方法的介紹,變為突出主題學研究與文化批評兩個方面,分析各自的適用方法。文化批評研究方面,最初的課堂教學(1994年)是從思想、身份、生活方式、文藝、物質、地域等方面介紹中國文化的類型;1998年前后改為總結與文學作品有關的教化精神、道德觀念、歷史意識、人生價值等文化批評著手點;2004年前后改為從神話學派、進化論學派、心理分析學派、歷史地理學派等西方學派的研究思路中尋找適合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因。
在對西方理論的深入了解和對敘事文化學的理論建構與研究實踐中,寧教授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中國文學研究不能簡單地奉行“拿來主義”,而應該將“以中為體,以西為用”作為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結合應用的原則,此方針后被貫徹為敘事文化學的總體方針。
三是提出“竭澤而漁”的文獻收集理念,不斷補充完善文獻收集的方法。
在課堂教學中,寧教授一直強調文獻考據學對于敘事文化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文獻搜集并不僅僅是方法或操作手段,它對于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它用“竭澤而漁”的理念和操作實踐,與其他意象主題研究和小說戲曲同源關系研究劃清界限,用文獻資源的無限擴大表示這種方法學術視野的宏闊寬廣,為故事類型的文化分析奠定充分的材料基礎。
正因其重要性,寧教授會詳細講授文獻收集的方法途徑。開課之初(1994年),擇要介紹敘事文化學研究適用的目錄、作品總集、類書叢書,如史書中的“藝文志”“經籍志”及常見的古代私人藏書目,以及《曲海總目提要》《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等11種小說戲曲相關書目,《類說》《清平山堂話本》《古本小說叢刊》等9種小說總集和《六十種曲》《古本戲曲叢刊》等14種戲曲總集,《古今說海》《稗海》等8種小說叢書。至1998年前后,課堂介紹的與小說戲曲相關的書目增加到14種,小說總集增加到16種,小說叢書增加到17種;至2004年前后,授課介紹的與小說戲曲相關的書目、詞典增加到37種,戲曲總集增加到17種。一方面增加了數目,另一方面詳細介紹各種文獻的版本、內容范圍等具體情況。1998年以來,寧教授在課堂上增加了對索引的介紹,將類書、史書、集部的重要索引介紹給學生。不但介紹各種相關書籍,還布置課下作業,使學生動手翻查介紹的書籍,真正鍛煉同學搜集文獻的能力。隨著文獻收集方法途徑的不斷補充與漸趨完善,“竭澤而漁”的理念成為可操作的可以無限接近的目標;而文獻搜集的“竭澤而漁”,保證了梳理與勾勒故事演變軌跡的科學性。
總之,課堂教學內容的變遷反映了寧教授對敘事文化學理論思考的逐漸成熟,教與學的互動也使敘事文化學在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中不斷成長。
二、學位論文對理論體系的實踐
在此期間,寧教授指導的學年論文、學位論文中均有實踐敘事文化學理論的個案研究,限于準備時間的充分與否問題,學位論文更能反映對敘事文化學理論的實踐情況,茲以此進行分析。
1994―2004年,寧教授指導的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學位論文共有7篇本科學位論文、8篇碩士學位論文。這些論文基本遵照了敘事文化學的研究思路,即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考察故事演變,分析故事演變的文化主題與動因。無論在寫作模式方面還是內容分析方面,這些論文均呈現了積極探索的痕跡。
在寫作模式方面,本科論文一般以時間順序安排章節,梳理不同時代的文本以及文本所呈現的演變軌跡,并結合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分析歷次演變的原因所在。這是將敘事文化學的方法思路進行了樸素的實踐,也存在著模仿主題學經典文章——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因素。當然,這種寫作模式也是適合畢業論文篇幅的寫作模式,而寫作者也在這種模式中積極探索創新。如王佳斌《劉晨、阮肇遇仙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按年代梳理劉晨阮肇故事產生、發展及造成變化的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而結語則從社會背景、文學形式、志怪小說的地位等方面總結了該故事演變的原因與動力[2],可以說是作者對故事演變研究的積極探索。朱恩貞《湘妃故事嬗變研究》亦是通過故事情節演變,分析此故事嬗變的緣由與文化內涵[3],不同的是作者對相關文獻做了列表式的敘錄,也是作者對敘事文化研究寫作模式的積極探索。
碩士論文在寫作模式方面的探索更為明顯。由于碩士學位論文相對于本科學位論文篇幅可以較長,在寫作敘事文化學研究論文時,可以對主題演變及原因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探索;而學位論文的科學性與格式化性質,也對寫作模式提出了挑戰。最初,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模式仍在起著重要的示范作用,如張文《楊妃故事嬗變研究》主體為三個部分:一是楊妃故事的文獻敘錄;二是楊妃故事的主題思想演變,以時代為綱,研究此故事,并揭示發生嬗變的緣由;三是楊妃故事的情節演變,透過故事情節演變,分析故事嬗變的文化內涵[4]。雖然該文將主題思想演變與情節演變分為兩章,但實際還是按時代先后對演變的梳理。牛景麗《“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國古代時差故事淵源考析兼論中國古代道教相對時間觀》不再純粹按照時間的順序,而是按照進化的邏輯,梳理時差故事的起源、發展、演變與成熟,分析了時差故事的產生與佛教時間觀念等思想的關系,而將仙話模式作為時差故事的發展,將冥界時差故事作為時差故事的演變,從而對時差故事與佛教、道教思想文化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5]。可以說,此文的寫作模式已經形成了突破。梁曉萍《西施故事流變及其文化探源》在將西施故事生成過程梳理清晰以后,將此故事涉及的文化因素分別設章,再按時間順序對每種文化因素進行梳理分析,形成西施故事與吳越文化、西施故事與歷史意識、西施故事與美女禍水、西施故事與生命情緒、西施故事與美人幻夢五章[6]。這種模式后來作為相對成熟的模式得到沿襲,如楊奉勤《木蘭故事演變及其文化觀照》重點對儒家文化與市民文化對木蘭文化的改造進行了分析[7],任正君《韓湘子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蘊》重點對韓湘子故事的修道主題、濟世主題進行了梳理分析[8],胡寶未《李慧娘故事情節演變及其文化意蘊》重點對李慧娘故事的歷史情節、愛情情節所蘊含的文化主題進行了梳理分析[9],夏習英《綠珠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重點對綠珠故事中的殉情、報恩、美女禍水等文化因素進行了梳理分析[10]。
下面筆者簡單地分析南開大學文學院相關學位論文對敘事文化學基本要素的實踐情況。
從選題來看,以人物為中心的選題最為常見,如本科學位論文中的西王母故事、劉晨阮肇遇仙故事、九天玄女形象、湘妃故事,碩士學位論文中的楊妃故事、卓文君私奔相如故事、西施故事、聶隱娘形象、木蘭故事、韓湘子故事、李慧娘故事、綠珠故事。這一方面是受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以人物為中心到對其他故事類型的關注,也顯現出對故事主題類型問題的探索。實際上,個案故事研究應當與中國古代故事類型的編制、研究相配合,以充分展現中國古代敘事文學與敘事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隨著寧教授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思考的深入,天地、怪異、人物、器物、動物、事件等六大類型被提出,人物故事以外,其他類型的故事也應該得到關注。學位論文中便有這樣的實踐,牛景麗《“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國古代時差故事淵源考析兼論中國古代道教相對時間觀》探討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虛幻世界與真實世界的時間差異故事,便屬于事件類的故事,通過對此類故事的研究,理清了佛教、道教文化在這類故事演變中扮演的角色,探索了道教相對時間觀[5];章劍《略論妒婦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蘊》探討的妒婦雖然是人物,但實際指向的是夫妻關系,亦屬于事件類的故事,文章對不同時代對妒婦故事的不同書寫與態度進行了分析與總結,由此探索了國家本位、家庭本位對此故事的影響以及故事流變所指涉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新變[11]。由此可見不同類型故事的演變研究有其獨特的文化觀照意義。
從對文獻的收集來看,敘事文化學要求“竭澤而漁”地收集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文獻。在這方面,碩士學位論文顯然比本科學位論文做得更好,雖然我們不能將兩者做絕對數量的對比,但從收集材料的類型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本科論文收集材料主要集中于史傳、筆記、白話小說與戲曲等敘事文學的材料,雖然注意到詩歌將故事作為典故征引或者將故事作為歌詠對象,但往往沒有對這些材料進行特別的關注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則不但關注傳統的敘事文學材料,對于傳統詩文材料也做到了關注和研究,如張文《楊妃故事嬗變研究》在梳理故事在唐代的發展演變時,便將大量唐人的詩作作為材料[4];夏習英《綠珠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不但在梳理發展演變時將詩文作為材料,在對不同文化主題進行專門梳理時,也涉及了大量詩作[10]。關注傳統詩文中的材料,本是敘事文化學研究的應有之義,寧教授提倡以故事類型為切入點來研究古代敘事文學,就是要探索同一個故事在不同文學體裁之間的流動。歷史地看,傳統詩文才是古代文人著意創作的體裁,透過傳統詩文的材料才能更真實地把握故事演變及文化意蘊在古代社會的樣貌。
隨著文獻收集方法途徑的不斷完善,可以搜集的材料無論是種類還是數量都比此前要多。如縣志、古籍、風物傳說等此前并未引起關注的材料,在后期的論文中也得到了應用,梁曉萍《西施故事流變及其文化探源》便統計了西施故里的古跡遺存,收集了不同時代的風物傳說[6],這些材料為西施故事的研究增添了新鮮血液。夏習英《綠珠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等論文也有方志材料的收集與分析。
如何處理相關文獻,不同的學位論文做了不同的處理,或以專門的章節做文獻敘錄,如張文《楊妃故事嬗變研究》;或將文獻在梳理故事發展流變的脈絡時做概要性介紹,如梁曉萍《西施故事流變及其文化探源》;或以文體類別為綱將不同時期故事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如夏習英《綠珠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這些處理并不能直接評判優劣好壞,但卻為以后學位論文的寫作提供了經驗。
從文化分析來看,一方面是對故事演變的社會文化原因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對故事所蘊含的文化因素的分析。相對來說,這與寫作模式的選擇有很大的關系,如《孟姜女故事研究》,一般的研究思路是按照時間順序安排章節,梳理不同時代的文本以及文本所呈現的演變軌跡,并結合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分析歷次演變的原因所在。這種寫作模式著重于對演變原因的文化分析。然而問題在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作者顧頡剛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極其精通的大學者,因而在對孟姜女故事的縱向梳理中能夠做到駕輕就熟,對故事的歷次變動能給出貼切的解釋。而學位論文寫作者在知識儲備、文化沉積、學養積淀等方面并不一定做好了準備,因而在對故事演變及其原因的分析中,很容易形成浮光掠影的套路式闡釋,對古代文化的固定印象比如“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元代的異族統治、明清的封建專制等,也會不加分別、不做具體分析地應用到闡釋中,將文本、作者、社會文化背景僵硬地捏合到一起,反而會影響所探討的演變原因的可信度。本科畢業論文,以及早期的碩士論文,或多或少存在這種問題。
而將故事涉及的文化因素分別設立獨立章節進行專門的探討,這種寫作模式對故事文化蘊涵的闡釋更為深入。比如梁曉萍對西施故事與吳越文化、歷史意識、美女禍水、生命情緒、美人幻夢等文化主題的闡釋[6],楊奉勤對儒家文化及市民文化對木蘭文化的改造的分析[7],任正君對韓湘子故事的修道主題、濟世主題的梳理分析[8],夏習英對綠珠故事中的殉情、報恩、美女禍水等文化因素的梳理分析[10],突出了故事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因素,這比對情節演變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強作解釋顯然更加具體、適用。
同樣的,早期的學位論文主要分析故事演變的社會文化原因,偏向于歷史文化的分析。后期的學位論文則不斷開闊視野,從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市民文化以及大小傳統等各個方面來觀照故事演變,在具體而細致地貼近故事演變的同時,也展現出中國文化豐富、廣博的各個側面。1994―2004年,學位論文已經探討的文化觀念主要有佛教及道教的時間觀念、吳越文化、歷史意識、生命意識、美人禍水觀念、儒家文化的孝道及貞烈觀念、市民文化中的兩性平等觀念、修道與濟世文化、殉情及報恩等文化觀念。同時,對于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蘊的專門探討,所得出的結論也會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如章劍《略論妒婦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蘊》通過對妒婦故事演變時段的勾勒與分析,進而探討宋代大傳統與小傳統的新變[11],此觀點無論對敘事文學研究還是傳統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學位論文是敘事文化學個案研究的重要成果,是敘事文化學理論的重要實踐,同時也是對敘事文化學研究論文寫作的思路、方法和模式的積極探索。
三、課堂教學與學位論文中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體系前景展望
1994―2004年,敘事文化學的理論要素在課堂教學與學位論文中得到摸索與實踐,蘊含著廣闊的前景。
一是學科的正名。這一時期,雖然課程名稱為《敘事文化學》,但學位論文中幾乎沒有提到過這一名稱,在研究方法上一般也只稱主題學。當然此時學界也沒有敘事文化學的論文和相關探討。這說明學科并沒有獲得正式的公開與承認。然而在課程設計與教學中已經出現了敘事文化學理論的大體框架,其目的、對象、方法也較為明晰,具備成為獨立學科的潛質。同時,這一時期“冒名”主題學而實際以敘事文化學的理論思路為指導寫就的學位論文表明,敘事文化學具有廣闊的研究應用前景,可以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嶄新的理論武器。一個學科的出現是要經過充分的理論準備,經過大量的論證和實踐,才能夠有其立足之地;相信隨著理論探索與個案研究的不斷積累,敘事文化學必將橫空出世,成為學界耀眼的明星。
二是敘事文化學研究總體框架的完善與充實。在課堂教學中,寧教授已經敏銳地發現故事類型索引編制的問題,在參考民間故事主題索引編制成果的前提下,提出編制適合于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故事類型主題索引,將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進行摸底,為進一步的個案研究奠定基礎。至此,索引編制成為一個獨立的部分被提了出來,并被作為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總體框架之一。那么敘事文化學的總體框架應該有幾部分,都是什么內容,各個部分有什么樣的關系,在這一時期的課堂教學與學位論文中并沒有獲得思考與呈現,這對于一門學科、一種理論是欠缺的。這一時期已經將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大體思路搞清楚了,這一思路對于敘事文化學的總體框架來說具有什么樣的意義?這一時期也有學位論文對敘事文化學的基本思路進行了實踐,這些實踐應該放在敘事文化學總體框架的哪一部分來看待?這其實和敘事文化學的自信與正名有關,當我們懷著充分的自信來為這門學科、這種理論正名的時候,這些問題必然會浮現出來,也將得到回答。
三是故事類型索引的編制。這是這一時期敘事文化學的重大創獲。從了解民間故事的類型索引,到提出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故事類型問題,再到編制《先唐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索引》,從理論到實踐,都在這一時期發生。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類型索引,旨在摸清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故事類型,為敘事文化學個案研究提供參考與指導,同時也為主題學、民間文學以及古代文學的其他學科提供研究的方便。在這個意義上,故事類型索引的編制應該繼續進行下去。寧教授從六朝敘事文學的主題類型研究入手,將范圍向前擴展,編制了《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唐代及以后還有大量敘事文學作品存在,可以抽繹出大量故事類型,這些也需要進行摸底,并編制故事類型索引。當然,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敘事文學作品數目龐大,編制索引時如何操作——以時代為中心?還是以作品為中心?這些問題也是需要思考解決的。總之,在故事類型索引編制方面,仍存在著廣闊的空間。
四是敘事文化學相關理論的闡發與建構。這一時期,課堂教學將敘事文化學的大體思路與方法做了介紹,但作為一門學科、一種理論,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闡發與建構。比如20世紀80年代曾有方法論熱潮,數十種外國理論被介紹進來。已經有如此多的理論可供應用,為什么還要創立敘事文化學?這自然與學術風潮的更新換代有關,與對待西方理論的方式有關,與偏重理論還是回歸文獻的思考有關,因此敘事文化學的創立,既可以說是對以往敘事文學研究方式的反思——一種建立在學術史基礎上的考量,也可以說是對學界新風尚、新思潮的引領。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的闡釋與梳理。
所謂理論,主要的意義還是在研究中的應用,是否能用、是否適用是檢驗一種理論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標準。那么敘事文化學作為一種理論,對于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的適用性在哪里?既然這一時期的學位論文幾乎只強調主題學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用主題學來代替敘事文化學,或者說這種理論是否只是披著敘事文化學“外衣”的主題學?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主題學雖然能夠為古代敘事文學研究提供方法與視野的借鑒,甚至讓我們注意到古代文學中大量存在的一個故事主題在不同文體之間的流動的事實,但主題學畢竟是西方理論,它與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并不能完美地接榫,主要的一點便是它只關注故事的“變”,并不太在乎“變”的廣泛性與適用性——是突變、畸變還是順理成章地演變、自然而然地變,而并不是所有的“變”都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有時候“不變”中反而蘊含著更重要的變化的信息;只有掌握了豐富的材料,才能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敘事文化學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更加符合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實際,其理論適應性與優越性也在于此。這些問題還可以做進一步的思考。
當然,理清敘事文化學與主題學的關系,實際上也是理清中與西的關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與西方理論的關系,理清它們之間的體用關系后,可以使我們更從容地面對西方理論,建構屬于中國的敘事文化學。實際上,不只是主題學的理論要素可以為敘事文化學所吸收利用,很多西方理論甚至是嶄新的理論,其合理因素都可以為我所借鑒、利用,比如人類學的理論、互文性的理論,只要它們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我們對研究對象的文化闡釋,并且能夠被挖掘出與古代文學的接榫之處,那么它們完全可以為我所用。這種“中體西用”的思路,正是在這一時期(1994―2004年)的摸索與嘗試之后的產物,以“中體西用”為指南的敘事文化學,還有廣闊的理論建構空間。
此外,敘事文化學主要的是一種應用性的理論,但并不能排除它不能生產形而上的理論思考的可能。相同的故事在不同文體之間的流動,同一個故事被不同的人所講述,是否蘊含著古人的哲學思考與著意選擇?中國的敘事文化能否抽繹出能夠為人類所共享的獨特的內蘊?這些問題也可以進一步思考。
五是敘事文化學的個案研究。這一時期的個案研究主要是本科、碩士同學以學年論文、學位論文的形式進行的個案研究,他們的研究已經表明,敘事文化學有其研究的應用價值,能夠為更多的人所應用、能夠用來研究更多故事主題。
從研究層次來看,這一時期的學位論文,碩士生的論文在文獻的搜集、故事演變的處理、文化蘊涵的分析等各個方面大都比本科生完成得好,這是否意味著——更高層次的研究人員,或許能更好地把握題目、駕馭題目,從而獲得更優秀的成果。碩士以外,接下來寧教授還將為博士研究生授課、指導博士論文的寫作,碩士、博士將成為實踐敘事文化學理論的中堅力量,敘事文化學的理論將獲得更多人應用,收獲更多更優秀的成果。
從選題來看,這一時期的選題很多都偏大,并不是本科學位論文、碩士學位論文所能很好地駕馭的。比如西王母故事,西王母是一個與歷史、文學、宗教、生活甚至文字學、生物學等學科都有聯系的人物,從西周時代就已經產生,后世的器具、墓畫上也有其形象,后來還演化出曾在仙女故事、西游故事等眾多神魔故事中出現的王母娘娘的形象來,所涉及的面廣,所蘊含的文化意蘊也豐富,而其中的演化軌跡則更為復雜,絕不是一篇本科論文能夠說清的。這樣的大題目應該由更高層次的研究者來完成。這也就是說,選題的適中方面,還需要斟酌。從內容方面來看,上文已經提及,這一時期的選題主要以人物為中心,這遠遠不能反映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多樣面貌。當然,這或許和《先秦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的出版較晚有關,但應該期待的是,寧教授總結的天地、怪異、人物、器物、動物、事件等六大類型,每一類型下面都有豐富的故事素材,未來的選題應該考慮這一方面。
從個案的文化分析來看,這一時期學位論文中的文化分析既有對故事演變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分析,也有對故事不同情節單元的文化主題的分析,上文已經分析,相對來說,后者的分析比前者要深入、透徹。但文化分析如何更好地操作,有沒有經典的模板可供參考?這一時期顯然更多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為模板,方法偏于情節分析與文史結合。是否可將探索原型批評、集體無意識等理論用于文化分析,這是值得期待的方面。
另外,文化分析能夠將故事演變的原因分析透徹固然重要,能夠挖掘故事所蘊含的獨特文化意涵也令人期待,或者可以說,以敘事文化學的方法來研究個案故事,以個案故事的研究來觸摸中國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這也是值得期待的方面。比如木蘭故事與易裝文化、鐘馗故事與斬鬼文化、唐明皇故事與梨園文化,等等,都是值得挖掘的個案。
從個案研究與故事類型索引的編制來說,目前來看,寧教授的故事類型索引為個案研究選題提供了參考與指導。實際上,反過來也可以期待,就是當某一個案故事的研究完成以后,在掌握了該故事的材料和演變軌跡的基礎上,編制此故事的類型索引或者演化索引。以韓湘子故事為例,可以抽繹出的故事主題有韓湘子奇術(如染花、造酒)及韓湘子藍關度脫。這兩個主題下的情節變異(分支)更為豐富,如從染花到開花,如從度韓愈到度韓愈全家,再到叔侄轉生,等等。以此編制單個人物的類型索引當然不成問題,而故事的異變是這種類型索引編制的特色。
總而言之,敘事文化學在經歷了這一時期的探索之后,無論在課堂教學,還是在學位論文寫作方面,都有廣闊的未來;而作為一種理論、一門學科,敘事文化學的成熟與定型,將為古代敘事文學研究提供新鮮的血液與動力,征程不遠,未來可期!
[1] 寧稼雨.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
[2] 王佳斌.劉晨、阮肇遇仙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D].天津:南開大學,2000.
[3] 朱恩貞.湘妃故事嬗變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01.
[4] 張文.楊妃故事嬗變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2000.
[5] 牛景麗.“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中國古代時差故事淵源考析兼論中國古代道教相對時間觀[D].天津:南開大學,2001.
[6] 梁曉萍.西施故事流變及其文化探源[D].天津:南開大學,2001.
[7] 楊奉勤.木蘭故事演變及其文化觀照[D].天津:南開大學,2002.
[8] 任正君.韓湘子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蘊[D].天津:南開大學,2003.
[9] 胡寶未.李慧娘故事情節演變及其文化意蘊[D].天津:南開大學,2004.
[10] 夏習英.綠珠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D].天津:南開大學,2004.
[11] 章劍.略論妒婦故事演變及其文化意蘊[D].天津:南開大學,2002.
I206
A
1006–5261(2020)05–0029–08
2020-03-25
李萬營(1986―),男,山東萊蕪人,助理研究員,博士。
〔責任編輯 劉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