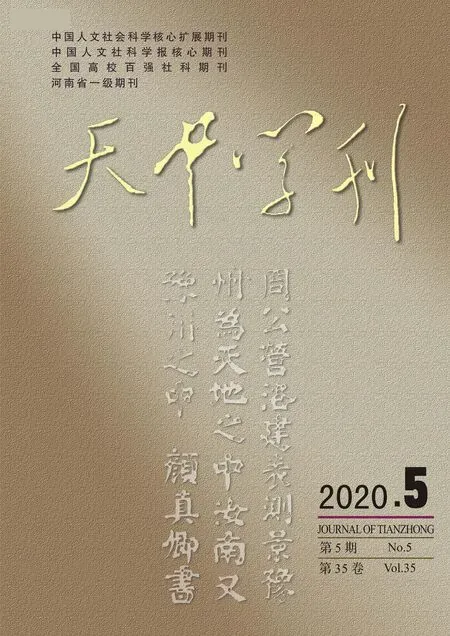試析新中國成立前中共黨報的“孝”話語建構
趙尚
試析新中國成立前中共黨報的“孝”話語建構
趙尚
(洛陽師范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洛陽 471934)
“孝”是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中國共產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領導、發動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過程中,必然面臨著如何對待“孝”的問題。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黨報的考察可以看出,自中共成立至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時間里,中共黨報對于“孝”的話語建構,經過了一個從否定、諷刺到遮蔽,再到提倡國家民族的忠孝而否定家庭的小孝,最后又到既肯定家庭之孝又努力建構國家民族、階級的忠孝并使之相統一的過程。這既是中共不斷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也是中共不斷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建構新型家庭關系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黨報;孝的話語
“孝”作為儒家文化的一個核心概念,在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護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論語》云:“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故以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歷朝歷代,大都推崇以“孝”治天下,正如民國時期經濟學家羅敦偉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孝國,從天子直至小百姓無不掛出一塊‘孝’字招牌,起初固然是一種‘倫理的孝’,后來卻轉到家庭生活上,乃至轉到社會生活上,如‘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都與‘孝’發生關系,于是‘孝’可以當作一切社會生活的主體……”[1]即使在進入近代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孝”的地位并無大的變動。比如,在1872年創刊、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民營大報《申報》上,就經常可以見到關于“孝子”“孝女”的報道,如《論聶氏二孝子萬里負親骨事》[2]、《論孝子剜臂奉母》[3]、《徐孝女事略》[4]等。但到了“五四”時期,作為封建倫理道德之一的“孝”開始受到猛烈的批判。此后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現代思想界一直都有非孝與擁孝兩種思想傾向。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民族解放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充分地領導、發動群眾進行斗爭,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如何對待“孝”這個在傳統社會與文化中根深蒂固,但在“五四”時期又飽受批判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問題。中共成立的1921年至新中國成立前,報刊一直是最為重要的宣傳與鼓動工具。因此,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黨報的歷時性考察,就可以管窺中共對于“孝”的意識形態的態度及其演變。
根據社會建構論的觀點,新聞報道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5]。本文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與社會建構論的理論視角,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前中共黨報上的“孝”話語的演變軌跡以及其中包含的經驗教訓的考察與解讀,力求為今天的執政黨科學地對待傳統文化、提高執政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論與歷史借鑒。
一、《向導》至《紅旗周報》時期在諷刺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孝”
《向導》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機關報,其秉承“五四”反對封建道德的精神,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屬于褒義的“孝”持否定的態度,視其為不合時宜的封建倫理,如一篇題為《戴季陶之道不孤矣》的文章這樣寫道:“……走狗荊嗣佑在長沙報上發表組織國民黨的談話說:‘……三曰申之以孝悌之義。’想用舊的道德文化救國之戴季陶……”[6]這里的“孝悌”之“孝”,顯然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是應該被否定的。不唯如此,在早期的中共人士看來,“孝”還代表了某種封建奴性。因此,為了喚起廣大民眾的覺醒,《向導》大量地在諷刺意義上貶義地使用“孝”:“中國真不愧一個‘倫理’的國,從前會忠孝君父,現在會忠孝洋大人。現在舊倫理將近崩潰,爹媽死亡不算什么傷心,同胞罹鋒鏑被殘害更不在意。獨對于洋大人則不然。從臨城案中,可看出長進的中國人(媚外的軍閥、官僚、政客、學者、報紙、商人以至國民領袖)努力建立新倫理(忠孝洋大人)之初定;從哈定之死,更可看出這種新倫理之確立。”[7]“他(吳佩孚)這樣輕視工人、畏懼土匪、孝順洋人的態度,真是中國軍閥官僚之代表。”[8]“(方本仁)簡直是與孝順日本和親媚英國的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張學良邢士廉及其他帝國主義的走狗如蕭耀南等是一丘之貉。”[9]《向導》諷刺有著某種崇洋媚外等奴性的“孝”的主體,如前面所說,包括軍閥、官僚、政客乃至國民領袖等一切崇洋媚外的反動勢力以及不開化、愚鈍的國民,其中又以封建軍閥為最多。《向導》所指的“孝”的對象,一般指日本、美國、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以及洋人,有時也指國內的商團、惡吏等。
在繼《向導》之后的《紅旗》《紅旗日報》和《紅旗周報》上,“孝”的話語亦沒有超出《向導》上這兩個用法的范疇——封建倫理道德以及諷刺意義上的“孝”。不過總體來看,在這三份報刊上面,“孝”的話語出現的次數比較少。之后,在1946年創刊的《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表示奴性的、諷刺意義上的“孝”的用法依然會不時地出現,但卻沒有再像《向導》時那樣成為主流。
二、《紅色中華》時期被遮蔽的“孝”
《紅色中華》時期,是中共首次掌握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也是首次以農民作為主要工作對象的時期。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共黨報宣傳的對象主要是城市人群,這些城市人群因受到“五四”精神的沖擊與洗禮而對待“孝”的態度存在著非孝與崇孝等復雜情況的話,那么蘇區(包括后來的陜甘寧邊區)的農民主體人群,對待“孝”的態度顯然有別于城市人群。當時的蘇區廣大農村是神權、族權與父權統治的社會,對于婦女來說,還要再加上一個夫權,這“四權”統治著的蘇區,是“孝”的觀念比較根深蒂固的地方。而這種“孝”的觀念,與黨領導的革命斗爭顯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與沖突。首先,就青年男子(紅軍戰士的主體)來說,儒家提倡的“父母在,不遠游”(《論語·里仁》)以及“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開宗明義章》)等觀念,與黨所倡導的青年男子應踴躍參軍打仗是相沖突的。其次,黨實施的提高婦女地位以及實行婚姻自由的法律法規,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婦女所受的神權、族權、父權以及夫權的壓迫。盡管在中共強有力的政權統治之下,神權與族權相繼土崩瓦解,但要求婚姻(當時的婚姻法規定只要男女任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即可離婚)、工作、生活自由的青年婦女,顯然與其丈夫(一般都不同意女方提出的離婚)及公婆(一般都要求兒媳在家里養兒育女、侍奉公婆、從事家務等)之間存在著矛盾沖突(青年婦女在過去一般被認為是家庭的私有物)。
就青年男子盡孝與黨的踴躍參軍政策之間的矛盾來說,解決起來尚不是非常困難。黨在當時實施了優待紅軍家屬的政策(除了在經濟上予以多方面照顧外,還安排專人幫助紅軍家屬耕種),經過宣傳鼓動,還是有許多青年男子,為了提高家庭地位(紅軍家屬不但受優待,而且很光榮)以及增加家庭收入(紅軍的工資收入)而踴躍地加入紅軍隊伍中去。針對參軍以后紅軍戰士的“孝”的問題,本著擴大紅軍隊伍、增強紅軍戰斗力的目的,《紅色中華》采取的話語建構策略大體有以下幾點:一是針對有些紅軍家屬或家鄉政府寄給紅軍戰士的信中容易激發“孝”思想內容,比如有些鄉政府給本鄉紅軍戰士寫信時,曾專門提道:“你母親有病哪!”《紅色中華》把其建構為應當反對與摒棄的“封建觀念”“家鄉觀念”,并指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各紅軍家屬的來信政府須負責查看其內容,內容不妥善的應向其家屬解釋,要他站在整個革命觀點上,慰問并勉勵他的子弟努力在紅軍工作,不要記念家中的話。”[10]二是在《紅色中華》上刊登一些父母寫給紅軍戰士的勉勵其奮勇殺敵、勿念家里(因受到優待而沒有困難)的家信。三是《紅色中華》大量地報道包括紅軍父母在內的紅軍家屬在家鄉被群眾光榮地優待、慰勞的情形,以解除紅軍戰士的后顧之憂。這實際上是以國家、社會等公共空間的優待與慰勞部分地代替與遮蔽了家庭這個私人領域的“孝”。比如《紅軍家屬到死都是光榮的》[11]這樣寫道:
……紅軍家屬到死都是光榮的,因為他(一位紅軍戰士的父親)是紅軍家屬,所以在蘇維埃的領導下,廣大工農群眾便募捐了大批的金錢,買了油烏頭棺木,剪了被席子及安葬需用的東西,而且有大批的少隊,兒童團,赤衛軍,到他家里去幫助轉動。尤其安葬上山時,又有全區幾百的群眾(特別少隊兒童更多)起來扛棺……
據筆者粗略統計,在《紅色中華》上,僅從標題就可以看出是關于優待、慰勞紅軍家屬的報道,達上百篇之多。
就青年婦女與其公婆之間的矛盾沖突來說,《紅色中華》上有為數不多的一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從維護青年婦女利益角度進行報道的,如《殺媳烹羹的楊嘉才槍決了》[12]、《黨秉祿老婆虐待兒媳》[13]、《反對虐待兒媳赤源縣第四政府應請注意》[14]。而關于青年婦女是否對公婆盡孝道的報道與評論,《紅色中華》則一概付之闕如。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曾有一篇介紹蘇區婦女情況的文章說:“婦女在赤區之工作成績實占有極重要之地位。而在各地之秘密活動,收效最大者亦多為青年婦女……占領時期,舊社會完全崩潰,推翻禮教,推翻神權,廟宇中塑像以及家庭所供之神主,悉被摧毀,破壞空氣,彌漫全社會,婦女界如癡如狂,一朝沖破四千年禮教重鎖之藩籬,其浪漫程度可想而知……其最影響社會風俗者,確為造成男女間無廉恥觀念,婦女習氣,極為囂張。開口自由,閉口自由。”[15]類似這些來自國統區人士的描述與評論雖然未必完全客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婦女們崇尚自由而近乎混亂的程度。毛澤東當年親自所做的調查也表明,當時蘇區“十個離婚案子,女子提出來的占九個,男子提出來的不過一個”[16]。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婦女與代表著傳統習慣勢力的公婆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我們提到的都是《紅色中華》上與“孝”有關但又沒有明確地提及“孝”的報道。關于明確而直接地論及“孝”的報道,據筆者查閱,只有一篇題為《好一個“父母在,不遠游”的干部!》[17]的批評性報道:
延川縣第三區的負責同志(名字不載),縣委決定調他到黨校去受訓練,該同志不但不遵守黨的決定,而且寫了一封信給區黨委,大寫著“‘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高堂上二老雙親無人奉養!”孔老夫子的名言,真不愧為孝子耶!
可以看出,當革命工作的需要與個人之“孝”發生矛盾時,《紅色中華》對于后者持否定的態度,但并未說明當革命者的雙親無人奉養時到底該咋辦。
綜合來看,因與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存在矛盾沖突,“孝”的話語在《紅色中華》上整體處于一種被遮蔽的狀態,這不僅有悖于蘇區(以及后來的陜甘寧邊區)農村幾千年來的傳統道德文化,而且不利于團結農村中的中老年群體,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當地群眾對中共的支持(在后來的延安時期,中共對此有專門的反思),再加上解除了“四權”壓迫的青年婦女與男子的矛盾沖突以及軍事戰略戰術上的失誤等原因,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因此,這種“孝”的話語在《紅色中華》上的被遮蔽,也屬于中共當時“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一部分。
三、《新中華報》前中期提倡國家民族之“忠孝”
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2月,中共致電國民黨,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等主張。此后,中共對于國民黨所提出的“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的口號予以認同[18],《新中華報》上刊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盡其至孝’,必須號召全國同胞實行這種最高的民族道德,這是對于古代封建道德給予了改造和擴充……因為一個真正的孝子賢孫,必須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職的人。這里唯一的標準,是忠于大多數人與孝于大多數人,而不是僅僅忠于少數與孝于少數……”[19]所以,與《紅色中華》相比,受國民黨主張的一些影響,前、中期的《新中華報》已經開始正視“孝”的話題,只不過是否定家庭的小孝,而主張對國家民族的忠孝。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王明對邊區的女性也提出了“孝”的標準:“女同志們不僅要做女英雄,而且要做新時代新式的賢妻、良母、孝女,中國歷史上有這樣的例子,教子精忠報國的岳武穆的母親,擊鼓助戰的韓世忠的夫人梁紅玉,代父從軍的花木蘭,在今天的意義下,就是這種能夠動員丈夫或代替父母上前線殺敵的賢妻良母孝女。”[20]王明提出的“孝女”標準——代父母上前線殺敵,也完全符合中共所提倡的國家民族的忠孝標準,而這種國家民族的忠孝在很大程度上對家庭的“小孝”是比較排斥的。《新中華報》還專門報道過這方面的典型人物:
羅化成同志……年老的雙親都被反革命槍殺了,他的老婆女兒被反革命捉去做老婆了,整個家庭完全被反革命殘害犧牲了。羅同志原是孝順素著的人物,他為了盡忠革命解放人民解放民族的事業,處此家庭這樣悲慘的犧牲,他雖是感懷孝念之情,痛念年邁雙親被殘害,但羅同志對革命不獨不生悲憤,反而更加強了革命奮斗的精神和決心,更加日夜不懈地奮斗著工作著。羅同志經常說:“我們革命者,正是為了解放社會解放家庭,所以需要犧牲一切為革命奮斗到底。”羅同志這種化孝子之心作革命忠勇之舉,實可為革命之模范啊![21]
這種“化孝子之心作革命忠勇之舉”的革命模范雖然令人肅然起敬,但卻有些不近人情。所以,前、中期的《新中華報》相比于《紅色中華》,雖然不再回避“孝”的問題而提出了為國家民族的忠孝,但卻沒能兼顧作為人之常情的家庭之孝,這不僅影響了包括中老年人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而且使外界出現了關于共產黨“不孝”“不慈”“無人性”等的造謠污蔑(其他的謠言還包括“共妻”“不國”等)[22]。
四、《新中華報》后期、《解放日報》與《人民日報》肯定家庭之“孝”與國家民族之“忠孝”的統一
最先關注到邊區青年婦女與公婆之間矛盾沖突的是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該委員會所主辦的《中國婦女》雜志(1939年6月創刊),在第一卷第七期就主張“家庭和睦”:“一方面反對丈夫和婆婆無人道地打罵妻子和兒媳,另一方面主張家庭里要有友愛的和睦。”[23]從該卷第八期開始,這一主張正式變成了“家庭和睦”的口號[24]。這一口號提出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爭取家庭中的老年婦女——如婆婆等[25]。1941年2月9日《新中華報》上刊登了《中共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其中專門提道:“過去婦女工作偏重在青年婦女方面,今后除繼續注意青年婦女工作外,必須注意動員和吸收老年、中年和成年各階層婦女參加婦女團體及其工作。”[26]1941年5月整風運動開始以后,中共也對之前的婦女、家庭工作進行了反思,指出由于之前未能正確地處理“農民婦女的關系,使工作遭受了若干損失”,“將婦女從家庭中孤立起來看,與其周圍的人不聯系,強調了婦女與家庭(農民)的矛盾,站在片面、狹隘的婦女利益上解決,造成兩性間及青老年的對立”,而只有“爭取團結家庭主婦與老年婦女,以求得她們的參加或贊助,這對青年婦女的活動會增加便利”[27]。為了照顧老年人的利益,解決革命工作與家庭之“孝”的矛盾與對立(如前面提到的《好一個“父母在,不遠游”的干部!》),邊區政府于1941年設立了養老院(7月正式投入運營),規定凡六十歲以上之公務人員,以及家庭里沒有勞動力的抗日軍人家屬,均可入院休養[28]。
正是在這種不斷地反思、糾正過去所犯“左傾”錯誤的背景下,中共黨報上“孝”的話語建構發生了歷史性變革。1941年春節前夕,《新中華報》上刊登了邊區婦聯會寫給各抗屬的一封信:“……親愛的老人們!你們想孩子嗎?那您應該愛護媳婦,領著她們好好過日子。親愛的姐妹們!你們想丈夫嗎?那您應該替他好好孝敬老人,好好勞動把日子過得快樂和安全……”[29]這是中共黨報首次對家庭之“孝”給予正面的肯定與提倡。在此后,1941年5月16日創刊的《解放日報》,以及后來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面,家庭之“孝”都已經成了被認可、提倡的顯在話語。具體來說,其“孝”的話語建構的具體內容與方式如下:其一,提倡子女對父母親的“孝”。一是發掘共產黨人的“孝”。1942年12月25日《解放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列寧的家庭關系》的文章,介紹了列寧與其母親的故事,并評價說:“(列寧的)母親是能教育兒子救國成名的模范習性……兒子是出乎天性,念念不忘母親的孝順革命家……”[30]該文著力發掘了革命導師之前不為人知的“孝”的一面。二是發掘模范、典型人物的“孝”。“在邊區政府的生產號召下,各地涌現出大批的勞動英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一)……(二)他們孝敬父母,使家庭和睦,如胡高拴因他父親有病,常勸他多休息,自己多做活。”[31]三是努力在下一代中間傳承“孝”,“要提倡學生寫字,注意勞動,鼓勵學生回家后幫助家庭工作,教他們懂得禮貌,孝敬父母……”[32]邊區教員教兒童寫作文時,也特別注意讓他們寫自己“與家中的關系,是否孝敬父母等等”[33]。其二,提倡青年婦女對公婆的孝。如模范抗屬劉金英“對待婆婆很孝敬。有時婆婆想兒子哭起來時,她還婉轉解釋,使老人家寬心”[34]。抗屬英雄折碧蓮“對平輩慈和,對長輩孝敬。十多年來,她從未對公公有過一句怨言。每天給公公做飯,供養老人,十年如一日”[35]。1949年2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鄧配蘭的男人原來要和她離婚,但自鄧配蘭參加了互助組以后,能勞動又孝順父母……”[36]其三,倡導家庭之孝與國家民族、階級之忠孝的統一。1944年年初,朱德總司令的母親去世,延安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解放日報》刊登了《朱母鐘太夫人傳略》:“總司令是永遠掛念著慈母的,但是總司令決心向全國人民盡他的大孝道,他要消滅那使母親(以及千百萬母親們)被侮辱和損害的社會原因,辛亥革命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于是他繼續奮斗追求,30余年間他不曾回家一次。”[37]朱德雖然“30余年間不曾回家一次”(這期間朱德曾把父母接到身邊,但父母留戀家鄉、慣于勞動,沒住多久就又回家鄉去了),但向全國人民所盡的“大孝道”,同時也是在盡他個人對母親的小孝道——“他要消滅那使母親(以及千百萬母親們)被侮辱和損害的社會原因”。因此,家庭之孝與國家民族之忠孝在這里被建構成了統一而非矛盾的關系。再比如,1947年12月,《人民日報》報道:“村指導員商文志說:‘俺家過去沒吃的,受地主的氣,沒法提。’”“當他們想起災荒年,一家分散到外討飯吃時,引起全家抱頭痛哭。”在他兒子要報名參軍時,他對兒子說:“你參軍走就算孝敬我了,打不倒老蔣挖不倒地主的根,咱別回家!”[38]在這里,“打倒老蔣挖掉地主的根”首先屬于階級的忠孝,另一方面由于之前“一家人受地主的氣”,所以“挖倒地主的根”也是孝敬父親之舉,家庭之孝與階級之忠孝被建構成在根本上相統一的關系。不僅如此,《人民日報》還建構了“不盡為階級之忠孝,就沒有盡家庭之孝的可能”的話語:針對青年男子參軍要面臨的“夫妻難舍”與“守孝父母”等問題,地方政府“普遍采取了對比算賬方法啟發階級自覺。如西火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李接運反省說:‘災荒年我家也有父母妻子,餓得沒法,四處逃散,我逃到吳村一年多,不敢回家,給人家來壺關牢村擔鐵貨,離家十里未敢回家,那時怎不孝順哩?那時怎舍得老婆孩子呢?’他肯定地說:‘只有打倒蔣賊,這一切才能談到。’蔭城劉瑞亭提出:‘想要得到忠孝全,青年必須把軍參。’”[39]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自中共成立至新中國成立前的28年的時間里,中共黨報對“孝”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否定、諷刺到遮蔽,再到提倡國家民族之忠孝、否定家庭之小孝,最后到既肯定家庭之孝又努力建構國家民族、階級的忠孝并使之相統一的過程。這是中共逐步認識到自身在傳統文化領域里所犯的“左傾”錯誤,并逐步地予以糾正的過程,也是中共在實踐中不斷地回擊外界對共產黨的各種“不孝”“不慈”“無人性”等的造謠污蔑并建構新型家庭關系的過程。比如,邊區婦聯組織還通過婆媳聯歡會、家庭座談會、祝壽聚餐等方式緩和家庭矛盾,邊區婦救會和邊區政府也通過表揚模范婆婆,樹立模范家庭、模范媳婦和模范婆婆典型等方式,努力建構新型的家庭關系[40]。事實證明,利用報刊以及其他途徑所進行的這種嶄新的家庭倫理關系建構,是卓有成效的:“在陜甘寧邊區及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農民家庭里,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家庭從未有過的現象:在家庭內部關系上(父子、婆媳、兄弟、男女之間),逐漸形成著一種民主的關系。這種新式家庭與舊式封建家庭糾紛重重的情形相反,是充滿了團結、和諧、尊長敬老、勤勞互助、人興財旺的幸福空氣的。”[41]這種包括“孝”的意識形態在內的新型家庭關系,有助于解放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及各根據地的生產力,從而有力地支持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是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能夠在全國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即使對于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價值。
[1] 羅敦偉.中國思想上之產兒制限反抗運動[J].家庭研究,1922(2):29.
[2] 論聶氏二孝子萬里負親骨事[N].申報,1872-07-10(1).
[3] 論孝子剜臂奉母[N].申報,1872-12-17(1).
[4] 徐孝女事略[N].申報,1888-10-13(1).
[5] 梵迪克.作為話語的新聞[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12.
[6] 戴季陶之道不孤矣[N].向導,1925(134).
[7] 和森.中國人應這樣孝哈定嗎[N].向導,1923(35).
[8] 獨秀.臨城擄案中之中國現象[N].向導,1923(26).
[9] 流金.方本仁媚外殘民[N].向導,1925(133).
[10] 早早.對于閩西擴大和擁護紅軍工作的批評與意見[N].紅色中華,1932-02-24(7).
[11] 紅軍家屬到死都是光榮的[N].紅色中華,1934-07-10(3).
[12] 日林.殺媳烹羹的楊嘉才槍決了[N].紅色中華,1932-09-20(7).
[13] 黨秉祿老婆虐待兒媳[N].紅色中華,1936-12-26(4).
[14] 反對虐待兒媳赤源縣第四政府應請注意[N].紅色中華,1936-01-16(2).
[15] 劉慶科.匪區社會中之婦女界[N].中央日報·婦女周刊,1936-03-04(2).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論文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9.
[17] 好一個“父母在,不遠游”的干部[N].紅色中華,1936-05-13(2).
[18] 許全興.毛澤東與孔夫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2.
[1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N].新中華報,1939-04-26(1).
[20] 延安各界婦女“三八”紀念大會告全國姊妹書[N].新中華報,1940-04-12(4).
[21] 張鼑承.追悼一位戰友:羅化成同志[N].新中華報,1940-03-19(4).
[22] 王明.關于保護母親兒童問題[J].中國婦女,1941(7):5–10.
[23] 中國婦女與憲政運動[J].中國婦女,1939(7):2–3.
[24] 葉群.贛江東西的婦女工作[J].中國婦女,1939(8):25–29.
[25] 董麗敏.延安經驗:從“婦女主義”到“家庭統一戰線”:兼論“革命中國”婦女解放理論的生成問題[J].婦女研究論叢,2016(6):19–27.
[26] 中共中央為“三八”節工作給各級黨委的指示[N].新中華報,1941-02-09(1).
[27]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G].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503.
[28] 民政廳開辦養老院[N].解放日報,1941-06-04(2).
[29] 舊歷新年邊區婦聯寫給各縣抗屬的一封信[N].新中華報,1941-01-31(4).
[30] 農泉.列寧的家庭關系[N].解放日報,1942-12-25(4).
[31] 李瑞山.向青年勞動英雄學習向模范學生學習[N].解放日報,1943-05-04(3).
[32] 邊區發出指示提倡小學民辦公助[N].解放日報,1944-04-23(1).
[33] 魏飛.我怎樣給兒童教作文[N].解放日報,1944-05-25(4).
[34] 綏德縣委.建立家務:記模范抗屬劉金英[N].解放日報,1944-02-11(2).
[35] 陳學昭.“熬勁大”:記抗屬英雄折碧蓮[N].解放日報,1944-12-29(4).
[36] 太岳分社.勞動英雄趙英梅:出席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介紹[N].人民日報,1949-02-20(2).
[37] 朱母鐘太夫人傳略[N].解放日報,1944-03-25(1).
[38] 商言城村互相啟發做到“四愿”才報名[N].人民日報,1947-12-09(2).
[39] 群眾自覺參軍滅蔣長治四區的參軍運動[N].人民日報,1947-11-25(2).
[40] 周蕾.沖突與融合: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家庭政策的變革[J].婦女研究論叢,2017(3):40–48.
[41] 孫曉忠,高明.延安鄉村建設資料:一[G].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448.
B82-051
A
1006–5261(2020)05–0068–07
2020-04-29
2017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7BXW008)
趙尚(1978―),男,河南遂平人,講師,博士。
〔責任編輯 葉厚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