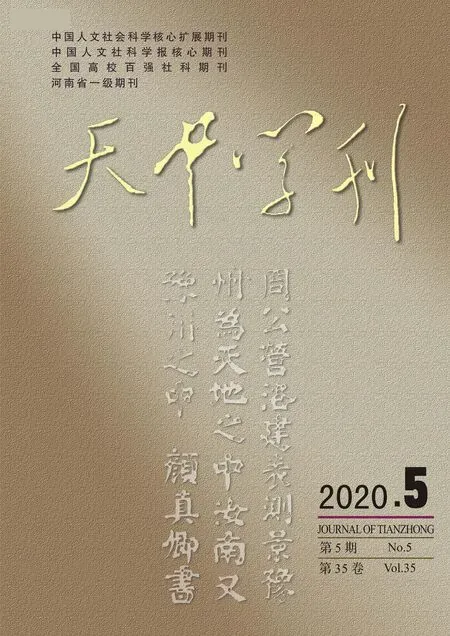情與禮的矛盾沖突——《鄘風·載馳》詩旨考辨
曹陽
情與禮的矛盾沖突——《鄘風·載馳》詩旨考辨
曹陽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目前學界對《載馳》詩旨的解讀主要有“歸衛不得”“歸衛吊唁”“至齊謀救衛”三類看法。由于創作背景的缺失和詩中詞語的多義,許穆夫人歸衛的細節難以明辨,但是《載馳》中所反映出的尖銳的現實矛盾和情與禮的沖突,正凸顯了許穆夫人對宗國強烈的忠愛之情,以及她充滿智慧、有膽有識的巾幗形象。
《載馳》;許穆夫人;詩旨
《載馳》篇內容見于今本《詩經·國風·鄘風》,《左傳·閔公二年》記載了《載馳》的創作背景: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冬,狄人伐衛,衛國戰敗,衛懿公被殺;衛國遺民逃往宋國尋求庇護,立衛戴公為君,暫居漕邑;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為交代清楚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僅對狄人滅衛的主要原因進行了詳細記載,而且對事件所牽涉人物間的關系進行了追敘與梳理。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1]265–268
衛懿公的荒淫逸樂引起了臣民怨恨,加之狄人入侵,導致身死國滅。衛人逃亡至漕邑后所立的國君是許穆夫人同母之兄,即衛戴公。與許穆夫人、衛戴公同母的文公由于衛國禍患太多,在狄人伐衛前便早已避至其母宣姜的宗國齊。衛戴公繼位數月后便去世了,國滅兄終后,許穆夫人作《載馳》。在這樣復雜的政治背景下,《載馳》的創作必然蘊含著特殊的政治意義與強烈的情感力量。
《載馳》文本如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2]289–292
第一章交代了作詩緣由,許國派大夫歸唁衛侯仍不能解除詩人內心的憂思。第二、三章抒寫了詩人想要歸唁卻不可得的矛盾思想與內心的郁結。第四章表述了詩人對救衛策略的思索和憂思。將詩中“歸唁衛侯”“許人”“女子”等信息與《左傳》所載詩本事結合來看,《載馳》應該是許穆夫人于閔公二年在衛國被狄滅后所作。
《左傳》對許穆夫人創作《載馳》的前因后果均有較為完整的記載,加之《載馳》一詩對寫詩起因和心中憂慮的直接敘寫,后世對《載馳》的創作時間、作詩緣由、作者并無異議。朱熹《詩序辨說》云“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正是對《載馳》有著明確創作背景的說明。但是對于許穆夫人究竟“是否歸衛”這一細節,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歸衛不得”“歸衛吊唁”“至齊謀救衛”三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揭示《載馳》的詩旨。
一、“歸衛不得”說
(一)“歸衛不得”說釋義
“歸衛不得”說即認為許穆夫人雖然憂心宗國,但是知道自己不能逾禮,所以并未歸衛,作《載馳》寄托自己對衛國的忠愛之情。
這一說法自《毛詩序》發端。《毛詩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2]287–288《毛詩序》認為許穆夫人欲歸唁戴公卻未能成行。《毛詩正義》認同上述說法,并對“義不得”的緣由進行了詳細解釋:“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2]288按照周禮,諸侯夫人父母逝世后不得歸唁兄弟。《禮記·雜記下》有“婦人非三年之喪不逾封而吊。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3]的規定,即《毛詩正義》解讀時所依據的是禮義規定。依照規定,閔公時,許穆夫人父親已經逝世,她“歸唁”的確不合禮制。《毛詩正義》對許穆夫人不得歸唁做出的解釋對后來學者評價許穆夫人和解讀《載馳》詩旨產生了重要影響。
晉時,杜預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中亦認為“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宋時,蘇轍在《詩集傳》中解《載馳》時承《毛詩正義》之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歸寧。于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為禮施于無,故而欲歸寧者耳……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以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4]蘇轍結合《載馳》一詩的內容與前人說法對許穆夫人歸衛一事做出了細致的解讀,即許穆夫人雖然憂心宗國,但是知己不可逾禮,于是終未成行,乃作《載馳》表達對宗國的忠愛之情。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詩經注釋》中亦認同《毛詩正義》中“歸衛不得”的說法,在注“不能旋濟”時,將《毛傳》與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進行了對比,提出“《毛傳》把有關系的兩章全講成作者的心思”,“朱熹則把‘不能旋反’和‘不能旋濟’說成實在的旅行的事”,“兩相比較,《毛傳》始終一致,顯然可取”[5]。
(二)“歸衛不得”說之演化
后來,“歸衛不得”說之下又演化出兩個分支,即“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和“歸衛不得,皆是設想之詞”。
1. 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
“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即認為許穆夫人起身歸衛,行至漕邑之時,被許國大夫阻攔,未能歸唁,作詩《載馳》。
這一說法在宋時占主流地位,王質《詩總聞》注“既不我嘉……我思不遠”句云“此當是既行至漕,為人所阻不能進,復濟漕而返也。不能旋濟,不能旋返,言猶徘徊,未即歸也”[6],認為許穆夫人前往漕地吊唁時,被許國大夫阻攔,并未歸衛。朱熹《詩集傳》亦認同此說,并對許穆夫人擔憂許大夫勸歸的心理進行了揣摩:“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7]朱熹解《載馳》時對許穆夫人的“義”進行了細致解讀與充分肯定。輔廣《詩童子問》承襲此說,并對許人為何之前允許許穆夫人歸衛,后來又進行阻攔進行了推理與豐富:“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于欲行之時乎?想其許穆夫人傷宗國之亡,不能為懷,既請于穆公,而穆公許之,故遂行焉。既而許之,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而穆公亦以為然。故使其大夫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要之其初必竟是犯不義,但能聞義而自克,為可取耳。”[8]輔廣認為許穆夫人最初能夠成行是因為得到了許穆公的同意,而后來許國大夫認為夫人歸唁不合禮制,因此許穆公又派大夫阻止許穆夫人。朱熹、輔廣等人關于許穆夫人歸衛的說法在元、明時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當時解讀《載馳》創作的主流觀點。宋人根據《毛詩序》等說法并結合詩歌內容對許穆夫人遵規守禮品德進行的發微,使得元代的學者在評價許穆夫人時常常盛贊其能“聞義而能自克”。這是繼宋前學者們贊揚許穆夫人“忠愛”之后,對許穆夫人形象的進一步豐富。
元人劉瑾在《詩傳通釋》中引用輔廣解《載馳》的說法,言“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要知其初畢竟是犯不義,但能聞義而自克,為可取耳”[9],其態度可見一斑。朱公遷在《詩經疏義會通》亦引用輔廣關于《載馳》的說法,曰:“馳驅已出,已犯義矣。聞義而能自克,不害其為賢也。”[10]二人均對輔廣的提法與對許穆夫人的評價表示認同。
明時,學者們也多承上述觀點,并對許穆夫人的遠見卓識進行了贊美。朱善在《詩解頤》中評價許穆夫人:“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于不敢往止乎禮義也。”[11]認為許穆夫人雖然憂心如焚,但是為了不違背禮制,還是選擇了返回許國。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曰:“夫人見大夫跋涉而來,心以為憂,亦知其義有不可者。特其歸唁之心已發,而不能自已耳,及其終焉不歸,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12]對許穆夫人的賢德行為亦表示贊賞。明人季本在《詩說解頤》中解《載馳》詩旨云:“夫人以諸侯無救之者,閔其將亡,而思歸唁之,其欲為衛圖存之情切矣,特為大夫所阻不得遂焉,故作是詩也。”他還盛贊許穆夫人賢德:“許穆夫人之思在于憂宗國覆亡,非為念親之私情也。婦人之見如此,豈不賢哉?世之丈夫多有所不及者矣。”[13]季本對許穆夫人遠見卓識的贊賞無疑是對許穆夫人形象的再次添彩。
清時,持“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說法的學者根據許穆夫人《載馳》中“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和齊助衛復國的后事對許穆夫人勝于丈夫的智慧進行大力褒揚。傅恒在《御纂詩義折中》中稱贊許穆夫人云:“智足圖存而貞能守禮,故圣人有取焉。”[14]對許穆夫人忠愛、守禮、智謀過人的品行進行了總結。姜炳璋在《詩序補義》中結合《左傳》記事對《載馳》的政治功用進行了解析:“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系以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則是詩有以激之耳,因依也。”[15]姜炳璋認為《左傳》在敘完許穆夫人賦《載馳》之后,接下來便記敘了齊桓公派公子無虧率兵援救衛國一事,不僅是對《載馳》所具政治意義與情感力量的強調,也是對許穆夫人智慧的慨嘆。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云:“夫人雖處巾幗,實勝丈夫。圣人取之,以見義憤之氣雖不激于男子,而猶存于婦人,亦將以媿許之君若臣耳。其后齊桓果復衛而成霸,然后嘆夫人之所見者遠也。”[16]稱贊許穆夫人之豪情、智謀遠勝男子。許穆夫人忠愛、守禮、智謀過人的形象,正是歷代學者在分析許穆夫人歸衛過程中所遭遇的波折與行為表現的基礎上得來的,倘若許穆夫人并未動身歸衛,上述關于許穆夫人的美好品行便會減損。
近現代以來,亦有不少學者持此說。傅斯年認為朱熹關于《載馳》的解讀是最恰當的,他在《〈詩經〉講義稿》中提出:“解此詩最善者,無過朱子。從朱子之解,詩中文義可通。蓋許穆夫人已至于漕,而許大夫追之使反,憤而為此詩。”[17]148高亨在《詩經今注》中認為許穆夫人“知道衛國遭此浩劫,要回衛國去吊問衛君,可是封建教條不許可,許國統治者不準她去。她走到半路上被追回,因此作詩”[18]。余冠英在《詩經選譯》中解《載馳》時亦持許穆夫人歸衛途中被阻攔后返回許國一說。張樹波《〈詩經·載馳〉矛盾辨析》、林奉仙《〈詩經·鄘風·載馳〉篇詩旨與章旨研究》、范學新《也談許穆夫人及其詩〈載馳〉》等文亦持許穆夫人“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一說。
持許穆夫人“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說法的學者在分析《載馳》詩旨時多認為,《載馳》首章“載馳載驅”“驅馬悠悠”描寫了許穆夫人動身馳驅欲唁衛侯于漕邑的場景;“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則是對許穆夫人得知許國大夫即將趕來告知自己于禮不可歸唁而心中憂慮無比的描述;第二章“既不我嘉……我思不閟”是許國大夫追上許穆夫人告知夫人其不可歸唁之義后,許穆夫人對自己內心想法的直接表述;第三章“陟彼阿丘……眾稚且狂”則描寫了許穆夫人陷入歸衛還是守禮的內心矛盾及現實沖突中,憂心忡忡;第四章“我行其野……不如我所之”描寫了許穆夫人無奈歸許的途中,憂心衛國民眾,提出自己的救衛策略,即控告于大國,請求救援。《載馳》整首詩抒寫了許穆夫人內心關于歸唁和守禮的思想斗爭與許穆夫人堅持歸唁、許人反對的現實矛盾。
2. 并未歸衛,皆是設想之詞
“并未歸衛,皆是設想之詞”即認為許穆夫人知道禮制不可逾越,實際上并未動身歸衛,作《載馳》以抒發對衛國的忠愛與心中憂慮。
這一說法約于清代出現。朱鶴齡《詩經通義》:“按《集傳》,許穆夫人將歸衛,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蓋據首章‘跋涉’二語然。此本據禮托言,非真有既行追留之事。”[19]朱鶴齡認為許穆夫人歸衛途中遭到許國大夫阻攔后返回一事本屬烏有,朱熹關于此事的說法只是為了彰顯守禮的重要性。陳奐《詩毛氏傳疏》注“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云“馳驅歸唁,驅馬至漕皆是設想之詞”[20],認為一切均是許穆夫人想象出來的。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許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如《泉水》詩之飲餞、出宿,皆想當然耳,非真有是事也。”[21]陳啟源認為《載馳》中所想馳驅之事與《邶風·泉水》中所言“出宿”“飲餞”均為臆想。此外,陳啟源還針對夫人初時告知穆公而行,后許人進諫,穆公又使大夫追許穆夫人于途一事的合理性進行發難:“吾不知夫人將出時告之于許君乎?抑不告乎?許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之乎?如知之,則應阻之于未出之先,不應追之于既出之后。如不知,則小君之尊適千里之遠焉,有倉皇就道,舉朝莫覺之理?且此時許君安在?乃坐視夫人之出,默無一言,直待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踉蹌往追之乎?”[21]陳啟源認為許穆夫人最初離開許國時,許國大夫未提出此舉違禮不合常理。宋人輔廣在《詩童子問》中的提法恰好與陳啟源的這一質疑相對,上文已論及,不再贅述。
持許穆夫人《載馳》“皆是設想之詞”說法的學者在解讀《載馳》一詩時均認為《載馳》中所描繪的“載馳載驅”“驅馬悠悠”“許人尤之”“我行其野,芃芃其麥”等場景為許穆夫人心中所想,實際上并未發生。而“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則是許穆夫人牽念衛國,憂慮重重中所想到的救衛策略。整首詩主要抒寫了許穆夫人內心關于歸唁還是守禮的矛盾。
綜上,“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與“并未歸衛,皆是設想之詞”這兩種說法是“歸衛不得”說發展而來的分支。他們均認為許穆夫人實際上未能歸衛,于是作《載馳》以表達憂憫宗國之情。在許穆夫人是否曾經動身歸衛一事上的分歧,使學者在解讀《載馳》的詩義時產生了較大的分歧,這一分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詩中行動和場景的虛實認識,二是對詩中所涉矛盾的理解。
二、“歸衛吊唁”說
“歸衛吊唁”說認為,衛國被狄人所滅后,許穆夫人馳驅至衛國遺民暫居之地進行吊唁,并作《載馳》表達自己的救衛主張。這一說法在解讀《載馳》詩旨的歷史上一直居于從屬地位,有少數學者持此觀點。“歸衛吊唁作詩”說的觀點可分為兩種:“作詩諷衛侯”與“作詩論復國”。
(一)作詩諷衛侯
“作詩諷衛侯”的說法認為許穆夫人回到衛國后,對衛侯不聽從她出嫁前的意見而選擇執意將她嫁往許國導致衛侯流亡在外的結果作詩表示譏諷。此說見于西漢時期劉向的《列女傳》。《列女傳·許穆夫人》篇云: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國也……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其后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于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吊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后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22]
劉向《列女傳》中詳細地追述了許穆夫人嫁往許國前的擇偶一事,且細致地描述了許穆夫人見衛侯作《載馳》一事,并對許穆夫人的遠見卓識進行了贊揚。“作詩諷衛侯”言之鑿鑿。然而,劉向關于許穆夫人歸衛作詩的說法在以下三個方面存在明顯的錯誤。第一,劉向在文中提出許穆夫人是衛懿公之女,事實上許穆夫人是衛公子頑即衛昭伯的女兒。清人錢澄之在《田間詩學》中便提出:“愚按夫人為宣姜女,懿公、惠公子,宣姜孫也。向以為懿公女,謬矣。”[23]第二,劉向在文中提及的“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衛侯遂奔走涉河”“衛侯于是悔不用其言”“衛侯因疾之”中的衛侯按文意皆指衛懿公。但是據《左傳》記載,閔公二年狄人侵衛時,“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衛懿公在狄人破衛時就去世了;“衛侯遂奔走涉河”應指衛國遺民逃亡時,渡過黃河,到達漕邑一事,此時的衛侯應是衛國遺民在漕邑所立的衛戴公,衛戴公是衛懿公的堂弟,許穆夫人的哥哥,在位幾個月后也去世了;齊桓公派兵援助衛國復國,立此前居于齊國的衛文公為君,所以劉向提及的“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之后的衛侯則應該是衛文公。傅斯年在《〈詩經〉講義稿》中也曾提出:“按此段所記與《左傳》《史記》皆不合,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妹,非其女。且懿公被殺,國亡,齊先立戴公,以城于漕,次立文公,以城楚丘。《列女傳》當是本之《魯詩》說,未采《左傳》《史記》。”[17]148第三,劉向提出許穆夫人出嫁前便考慮到一旦衛國有難,一定需要大國的援助,因而想要嫁往齊國,然而“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狄人破衛后,“而許不能救”,后來“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于是悔不用其言”。似乎是因為衛國國君目光短淺,未將女兒嫁往齊國,才沒有得到齊國的及時援助。事實上,衛國國君將許穆夫人的姐姐嫁給了齊桓公,《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中宣姜所生齊子為齊桓公寵愛的夫人,楊伯峻注:“齊子謂嫁于齊者。”[1]266《左傳·僖公十七年》記載:“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楊伯峻注:“衛姬有二,故分長少。《齊世家》云‘長衛姬,生無詭’,‘無詭’,《傳》亦作‘無虧’。無虧為名,武孟其字也。”[1]373《左傳》所敘“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中助衛的無虧即武孟。因此,“衛侯于是悔不用其言”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清代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疏解《載馳》第二章時云:“夫人既言跋涉心憂,追念前請于衛君事,云我所以請嫁于齊者,為欲系援大國,我之謀至嘉美也,既不我嘉,衛果遁逃而不能旋反其舊都,當日已視爾衛國不臧善也,我之思慮豈不深遠乎?”[24]260對劉向關于許穆夫人歸衛的說法表示認同,并且指出:“如夫人未往,涉念即止,烏有舉國非尤之事。若既已前往,則必告知許君而決計成行,亦無忽畏謗議,中道輒反之理。惟其違禮而歸,許人皆不謂然,故夫人作詩自明其行,權而合道,且其憂傷宗國,感念前言,信《外傳》所謂‘行中孝,慮中圣’者矣。”[24]263王先謙對“并未歸衛,皆是設想之詞”的說法提出了駁斥,認為許穆夫人確實違禮歸衛。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繼承了劉向《列女傳》中“作詩諷衛侯”的說法還對其合理性進行了闡發。然而,劉向所作《列女傳》意在教化,其中所收錄的故事多為臆造,并不能作為信史。姚際恒在《詩經通論》中亦言:“原向作《傳》之意,特因燕尾垂涎,輯閨范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故其書龐而無擇,泛而未檢,何得取以說《詩》!”[25]劉向、王先謙關于許穆夫人歸衛后見衛侯作《載馳》的說法顯然無法立論。
(二)作詩論復國
“作詩論復國”說即認為許穆夫人回到衛國后,在商議復國一事的時候,與衛國大夫觀點相左,作詩表達自己歸衛以及自力復國主張未被采納的現實矛盾。這一說法由王錫榮在《〈鄘風·載馳〉正解——箋〈詩〉臆得之二》一文中提出。王錫榮認為許穆夫人不僅確實歸衛,還與衛國大夫共同商議了復國之事,這一商議過程在《載馳》文本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王錫榮以“言至于漕”之“言”為“我”義及詩言“采蝱”“芃芃其麥”均為春末夏初之景為由,力證許穆夫人確實歸衛,并在此基礎上,對《載馳》各章詩義做出了解釋。他提出首章是“許穆夫人到漕邑以后,目擊衛君臣處境的感慨或吊問之辭”。第二章內容為許穆夫人與衛國大夫商議救國時提出了“靠自力更生返回故都沫的積極主張”,而衛國大夫并不贊同,認為“控于大邦”,求助于齊才是可行之策,許穆夫人以“誰因誰極?”作為對衛人策略的反駁。至于“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則是許穆夫人在其主張得不到衛人贊同時發出的哀嘆。第三章中“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是“許人大概看夫人與衛之執政者意見分歧,爭執不下,而出于私意,故對夫人亦有微詞”。“眾稚且狂”則是夫人對許人嘲諷的申斥之語。第四章中“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句表述了“許穆夫人堅持認為自己的主張正確,而對方(大夫君子)的謀慮則淺陋不堪”。王錫榮認為《載馳》是許穆夫人“歸衛以及自力復國主張未被采納而產生的一系列內心矛盾斗爭的描述”[26]。
王錫榮提出,許穆夫人的救衛策略為歸沫,衛人的策略為求齊,兩者之分歧是其解讀整首詩詩義的入手點。但是,無論是許穆夫人提出歸沫還是衛人與許穆夫人之間關于救衛策略的爭議,王錫榮均未提出事實依據,僅是憑借《載馳》詩句作闡發。反觀《左傳·閔公二年》記載:“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1]266–267衛國舉國之力尚不能敵狄人,倘若許穆夫人不愿依靠諸侯國的幫助而要求帶領五千衛人自力更生回故都沫,則似乎有些不切實際。王錫榮之說并未考慮狄人入侵后衛國的實際力量。
三、“至齊謀救衛”說
“至齊謀救衛”說即認為許穆夫人因衛被狄人所滅,憂心忡忡,不顧歸唁違禮到達齊國,求助于大邦。齊國派公子無虧出兵救衛,后來衛終得以復國。《載馳》作于許穆夫人前往齊國途中。
這一說法由清代龔橙在《詩本誼》中提出。龔橙解《載馳》云:“《載馳》,許穆夫人為衛亡,不辟歸唁,遂至于齊,謀救衛也。”認為許穆夫人實際上到了齊國,并與齊國當權者商議救衛。“夫人禮不得歸唁,故曰既不我嘉,又曰視我不臧,無我有尤。《左傳》狄人入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歸(虧)戍曹。明夫人之力也。夫人至齊因齊子也。”[27]283齊子,謂嫁于齊者,即許穆夫人的姐姐,公子無虧的母親。龔橙據《左傳》所載推測齊桓公派公子無虧救衛是許穆夫人至齊的結果,而許穆夫人趕到齊國的緣由則是因為齊子。此外,在解《載馳》前,龔橙解《泉水》時曰:“《泉水》,許穆夫人言志也。思歸唁兄又思至齊,因齊子以謀救衛也。”“諸姬謂齊桓公諸夫人。《左傳》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諸姑謂長衛姬,伯姊,少衛姬,即齊子也。”[27]283提及許穆夫人因衛齊的姻親關系將至齊求援,為解《載馳》張本。
龔橙在論《載馳》《泉水》詩旨時,均以《左傳》為依托,不難看出,其關于許穆夫人“至齊謀救衛”的說法源自對《左傳》所載史實的推論。《左傳》將“許穆夫人賦《載馳》”與“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接連敘出,或許有對許穆夫人身為女子大膽作詩抒發自己誠摯、熱切愛國之情的正面肯定。但是并未提及齊桓公使無虧救衛是因為許穆夫人至齊,許穆夫人“至齊謀救衛”的說法沒有充分的史實作為立論基礎,且齊國之所以出兵戍漕,并非全因龔橙所言“夫人之力”。齊國助衛復國應是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首先,齊國助衛復國符合其“親鄰、攘夷”的霸主強國外交策略。周朝在建立政權前后,姜太公呂尚屢獻奇計,對周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武王平商而建國后,論功將其師呂尚封于營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后來周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齊又“得征伐,為大國”[28]1479–1481。至齊國第十四任君主齊桓公時,齊國國力空前強盛。作為霸主,齊桓公結好鄰國、廣施恩惠的攘夷外交是其極其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在閔公二年狄人伐衛前,《左傳》記載齊國助他國“攘夷”的事件有:莊公二十八年,楚人伐鄭,齊與魯、宋聯合救鄭,“楚師夜遁”;莊公三十年,齊與魯共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閔公元年,狄人伐邢,齊人救邢。在救邢國之前,《左傳·閔公元年》載:“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齊人救邢。”[1]256由此也可見,齊國對受夷狄侵擾的諸侯國進行援助實際上是在其“親鄰、攘夷”的外交策略下做出的政治決定,是為了實現霸業。
其次,齊衛兩國的姻親之盟使齊具有救衛的情感可能。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秉承西周時期周王與諸侯國間外交的“親親”傳統,廣結姻親之盟。齊衛兩國在春秋初期便多次聯姻。隱公三年衛莊公與莊姜聯姻;衛莊公之子衛宣公娶齊僖公之女宣姜生衛惠公;衛宣公逝世后,齊人又使昭伯烝于宣姜。《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1]266其中宣姜所生齊子又是齊桓公的夫人。此外,據《齊太公世家》載“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28]1485,霸主齊桓公的母親也來自衛國。齊國與衛國數代間親密的姻親關系為齊出兵救衛提供了情感上的可能。此外,《左傳》所敘“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公子無虧即武孟,這也從側面證明了齊桓公出兵救衛時確實考慮到了姻親關系的影響。
最后,齊國救衛符合其從衛獲取政治利益的野心。作為霸主的齊國既有救衛的政治、軍事實力,又有救衛的情感可能,但是為何“冬十二月,狄人伐衛”之時不救衛,等到衛人所立的衛戴公去世后才出兵救衛呢?明代季本《春秋私考·卷七》解“十有二月,狄入衛”時云:“然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狄,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蓋非卯辰之月未為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余,城郭室廬未能完善故耳。齊桓方大合三國之師以城邢,而于衛則不之救焉。此許穆夫人所以為無所因極也。齊桓攘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于衛不救者,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至衛文公經營復國,而于齊亦遂心服矣。此衛避狄難,野處漕邑之本末也。先儒所謂衛為狄滅,桓公封之者,誤矣。”[29]其說可從。齊國不立即救衛是因為衛國對齊國霸主的地位曾表現出不尊重,而齊桓公之所以選擇在衛戴公去世之后救衛則是因為衛國將立新君。《左傳·閔公二年》記載:“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1]266《史記·衛康叔世家》載:“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筑楚丘,立戴公弟毀為衛君。”齊桓公幫助衛文公復國除了霸主公義,還存有想要控制衛國的私心。此前,《左傳》便記載過齊國干涉衛國立君之事。衛宣公逝世后,齊國為使齊女宣姜之子惠公即位,強使昭伯烝于宣姜。可見,此時救衛是齊國的政治手段。
龔橙“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明夫人之力也”的說法顯然夸大了許穆夫人在這一事件中的作用。在認為許穆夫人確實“至齊謀救衛”后,龔橙解讀《載馳》時提出“‘既不我嘉’四句皆為已歸唁”,“夫人禮不得歸唁,故曰既不我嘉,又曰視我不臧,無我有尤”[27]283,認為許穆夫人自知于禮不能歸唁,但是已經出行,所以以“既不我嘉……無我有尤”來表明自己出行救衛的心志、策略與緣由。
四、以情禮斗爭凸顯愛國激情
歷代學者對《載馳》詩旨的解讀主要取決于對許穆夫人究竟在何種情形下賦《載馳》的判斷。持許穆夫人“既行至漕,為人所阻而歸”說法的學者認為《載馳》不僅寫了許穆夫人內心歸唁、守禮的思想斗爭,還反映了許穆夫人欲歸唁與許人反對夫人歸唁的現實矛盾,從而突出了許穆夫人愛國、“聞義而自克”及遠見卓識的品行;持許穆夫人“并未歸衛,皆是設想之詞”說法的學者認為《載馳》主要描寫了許穆夫人內心關于歸唁還是守禮的思想斗爭,抒發了許穆夫人對宗國的忠愛之情。持許穆夫人歸衛吊唁時“作詩諷衛侯”“作詩論復國”說法的學者則認為《載馳》既寫了許穆夫人與許人的矛盾,又寫了許穆夫人與衛人的矛盾。前者認為許穆夫人與許人間的矛盾在于可否歸唁,與衛國執政者的矛盾在于出嫁前的擇偶一事。后者認為許穆夫人與衛國執政者的矛盾在于選擇何種方式助衛復國,與許人間的矛盾則在于夫人與衛人主張相左,許國大夫評價許穆夫人“善懷”,對其進行責難。持許穆夫人“至齊謀救衛”說的學者認為《載馳》確實描寫了許穆夫人內心歸唁、守禮的思想斗爭及許穆夫人欲歸唁與許人反對夫人歸唁的現實矛盾,但是許穆夫人在與這兩種矛盾斗爭之后,毅然決定至齊求援,《載馳》顯露出了許穆夫人堅定不移、有勇有謀的巾幗氣概。
縱觀全詩,《載馳》確實圍繞許穆夫人歸唁一事展開,四章中均有關于因歸唁引起的思慮或現實矛盾沖突的描寫,內容富于史詩性和戲劇性。第一章描寫了許穆夫人欲驅馳歸唁,而許國大夫追之于途的矛盾。第二章描寫了許穆夫人與許國大夫間關于可否歸唁的沖突。第三章描寫了許穆夫人與許國大夫的言語沖突后的自我思想斗爭,心情難以平復,反復思量之后仍然覺得自己的決定并無錯誤,錯在“稚且狂”的許人。第四章仍描寫了許穆夫人欲歸唁救國卻不可得的內心與現實的矛盾斗爭。由于史料中并沒有關于許穆夫人歸衛事件的詳細記載,因而我們并不能確定許穆夫人是否歸衛及其具體情形。但是無論《載馳》一詩描寫的是許穆夫人內心關于情與禮的斗爭,還是許穆夫人與外界的現實矛盾,抑或二者兼有,都恰好凸顯了許穆夫人這一懷著對宗國強烈的忠愛之情且富有智慧、有膽有識的巾幗形象。《載馳》詩篇本身包含的這種豐沛的感情,使得它在春秋時期被不斷傳誦。正如程俊英先生所言,《載馳》一詩“章章轉折,層層緊逼,其情愈激,其志愈決,其意愈明”,“而后人吟詠此詩,雖千載之后,猶如聞其聲,如見其人。”[30]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
[2] 毛詩注疏[M].鄭玄,箋.孔穎達,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 禮記[M].陳澔,注.金曉東,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93.
[4] 蘇轍.蘇氏詩集傳:第3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344b-0344c.
[5] 高本漢.高本漢詩經注釋[M].董同龢,譯.上海:中西書局,2012:147.
[6] 王質.詩總聞:第3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480a.
[7] 朱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1:44.
[8] 輔廣.詩童子問:第2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326b.
[9] 劉瑾.詩傳通釋:第3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365d.
[10] 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第3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365d.
[11] 朱善.詩解頤:第1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207c.
[12] 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第2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620a.
[13] 季本.詩說解頤正釋:第4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078b-0079c.
[14] 傅恒,等.御纂詩義折中:第4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060d.
[15] 姜炳璋.詩序補義:第4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077c.
[16] 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171.
[17] 傅斯年.詩經講義稿[M].董希平,箋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
[18] 高亨.詩經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6.
[19] 朱鶴齡.詩經通義:第2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055a.
[20] 陳奐.詩毛氏傳疏[M].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293.
[21]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第4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384c-0385a.
[22] 張濤.列女傳譯注[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94.
[23] 錢澄之.田間詩學:第2卷[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0453d.
[24]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M].吳格,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25] 姚際恒.詩經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8:49.
[26] 王錫榮.《鄘風·載馳》正解:箋《詩》臆得之二[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0(1):85–89.
[27] 龔橙.詩本誼[M]//續修四庫全書:第7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83.
[28]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9] 季本.春秋私考:第10卷[M]//續修四庫全書:第1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0.
[30]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M].北京:中華書局,1991:163.
I206.2
A
1006–5261(2020)05–0075–09
2020-03-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19TS097)
曹陽(1994―),女,陜西漢中人,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楊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