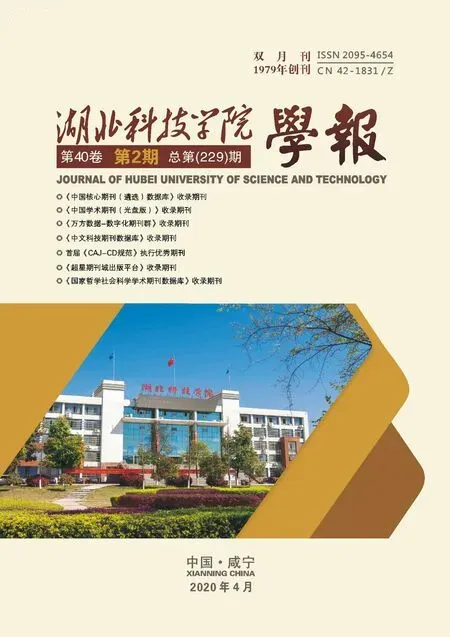淺析林庚白“狂癡”詞人形象
張 力
(廈門大學 中文系,福建 廈門 361005)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學衡,字浚南,號眾難、愚公,自號摩登和尚,筆名孑樓主人,福建閩侯(今福州市倉山區螺洲鎮州尾村)人。曾自言:“我四歲就會寫文章,七歲就能夠寫詩,一時有‘神童’目”[1](P64),“男兒奮發,要懷四方之心”[1](P67),志氣凌云的林庚白自幼狂傲多才,報考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預科時,因報名年齡的限制,十三歲的林庚白謊報十八歲,卻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在學期間廣結交,多唱和,與鄭孝胥、陳衍做詩鐘,十四歲與姚鹓雛合刊了《太學二子集》[2](P70),年紀輕輕就名聲大噪。后為同盟會成員、南社社員、國民政府鐵路局長、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立法委員、非常國會的秘書長。這位民國風云人物在香港宣傳抗日意外犧牲,年僅四十五歲,令人掩面嘆惋。
林庚白不僅是孫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更是民國極有代表性的文人,他一生筆耕無數,秉承先輩遺風,注入時代精神,與柳亞子詩分別代表了南社詩歌不同的藝術風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文稿在戰火中輾轉丟失。柳亞子將林庚白與其妻林北麗的詩輯為合集,周永珍輯成《麗白樓遺集》共計97萬字,成洋洋大觀。劉榮平先生辛勤搜討編輯《全閩詞》,據《麗白樓遺集》《民族詩壇》《詞綜補遺》《南社叢選》等收林庚白詞作共82篇,實在難得。林庚白作品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不僅描摹了清末民初社會的動蕩,而且折射出國民革命時局的緊張,無論是其社會價值還是文學成就都值得研究者重視。目前學界的研究側重于其人與其詩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林怡《民國文化奇人林庚白探略》《一代詩豪南社健將林庚白其詩其人》,金翔《略論林庚白與同光體》等,而關于林庚白詞作的研究尚有不少研究的空間。
一、林庚白的“狂”與“癡”
林氏是“少年天才”,也是“政界精英”,其短暫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曾閉關讀書,是鉆研詩詞、算命的“閑散文人”,卻又是混跡政壇和各大場合的“社交達人”;他是“情場浪子”,流連花叢、游戲人間,卻又是“癡情種子”,次次戀情皆將真心傾付,至情至性。其獨特多彩的人生體驗,為其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其少而失怙的敏感內心,使他對創作葆有靈感。他樂于將內心世界的萬千波瀾訴諸筆端,化為篇篇詞作。縱觀其作,可見出,而其中極為突出的個性特色是“狂”與“癡”,給人深切的感染力。
林庚白狂傲高調,有報紙曾專門撰文寫其狂:“詩人林庚白,才氣縱橫,嘗與某次宴會自誦其得意之作,旁若無人,且誦且曰:‘你們看著不是像老杜嗎?’須臾又曰:‘這一句簡直已超過老杜了’。”[3]他有自負輕狂的底氣,“以駢儷文與詩鳴于時,頗為閩中詩老所青眼”[2](P70),聞一多、章士釗等詩人評其詩詞“以精深見長”[2](P70),柳亞子評價他“典冊高文一代才”[4](P58),才華極高、實力非凡。
抖擻快意成文章,不少詞篇盡顯其四溢的“狂”意,如“袒臂輕紗新浴罷,帶幾分狂”[5](P2 206)的叛逆輕狂;又如“驀地起癡狂,難耐樓窗早晚涼”[5](P2 210)的相思癡狂;又如“聲聲雨,催教恨迸,賺得人狂”[5](P2 212)的羈愁成狂;還如“橫流急,狂瀾砥柱,舍我誰哉”[5](P2 212)的語壯言狂。可見,“狂”成為一種貫穿詞作的個性特質,為詞增添了搖曳生姿的浪漫色彩,而且他狂中帶“癡”,愈狂愈癡,愈癡愈狂,交織難分,極具情感力度!
“九一八”事變后,林庚白稱:“不打倭寇,中國的命運一定就完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林庚白夜以繼日撰寫《抗日罪言》[4](P263)。他愛國成癡,詩中自陳:“此身應是中華史”[6](P315),他的詞深度展現了愛國英雄內心世界。詞中充盈著山河破碎的心靈震顫與日夜難遣的愛國雄心,如“河北不堪問,日騎又縱橫”[5](P2 210)道出日寇難當的不堪。又如“樓臺沉夜氣。多少興亡淚。等是殖民羞。淞波空自流”[5](P2 209)見出被迫淪為殖民地的屈辱。再如“中原漸盡,喪邦無日”[5](P2 213)說出家國不幸的憤慨。他在詞中盡情傾吐羞憤與悲痛,愛國之情溢于言表,愛國成癡的詞人形象躍然紙上。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民國初年的舊體詩人“從不同角度憑吊過去,他們共同建構了傷心慘目的文學世界、荒寒衰敗的情緒。而且,它還顯透著此期文學的總體品格——衰老、疲頓、酸腐、凄惶、意興蕭索、眷顧戀舊。”[7](P325)面對慘淡的家國民生,他仍有盛唐才子般的樂觀豪情。詞中不僅沒有牢騷滿腹、沒有衰老與暮氣,而且充斥著奮發有為、重整乾坤的使命感,以及氣貫山河的狂氣,如:
鳳凰臺上憶吹簫·海行夜起
海色明樓,天風催曉,隔燈新月如杯。甚欲眠還起,思與腸回。無數濤聲拍枕,人世事、流水瀠洄。休惆悵,秋光負盡,尚有春來。 低徊。撫今念往,曾出塞投荒,百不能才。攬鏡朱顏在,堪掣風雷。依舊江山南渡,歌舞地、金粉成堆。橫流急,狂瀾砥柱,舍我誰哉。[5](P2 213)
這首詞情感層次豐富,首先上片實寫詞人海行中因為無眠,而遠望尚未破曉的海色,四野浸潤在一片茫茫的冷色調中,拍擊船身的波濤似乎也拍在枕頭,震得難以入眠。寥寥數語點破前路迷茫、心緒不寧的情狀。第二層情緒隨著拍枕的濤聲開始轉向內心世界,引發聯想,又分為兩度回轉:第一轉從實寫轉向虛寫,暗示出人世之事也如曲折流水般百轉千回,暫時迷茫乃常態;進而轉到“休惆悵,秋光負盡,尚有春來”的寬慰,依托自然規律道出了樂觀積極之心態。“流水瀠洄”也勾連出下片“低徊”的思緒,雖然是慨嘆之筆,但情緒不低反而驟然升溫,過往赫赫功績、鏡中未改朱顏,皆為筆下“堪掣風雷”的豪懷壯志而蓄力,最后說“狂瀾砥柱,舍我誰哉”,殷殷報國熱情噴薄而出。從迷茫無助到自我寬慰,層層推進,情緒不斷攀升到達高點后戛然而止,一片正氣凜然。愛國成癡的他,面對亂象叢生的國運,抑郁之情累積于心,發而為詞,鑄成“詞氣浩縱橫”的詞篇。
然而,風流倜儻、一往癡情,乃是林庚白詞人形象的另一面。據林北麗《我與庚白》,林庚白“眉清目秀,鼻子高挺,膚色潔白,有洋人像”[8],兼具西方紳士風度與中國名士風范。自古才子多情,他也不例外,18歲成婚,離婚后流連花叢。曾苦戀鐵道部女職員張璧,直到40歲時娶了林徽因的堂妹、年僅二十的才女林北麗為妻。其風流韻事頗為時人所樂道,報紙多次報道其花邊緋聞,但其率真癡情又早被其妻林北麗看在眼里:“在餐桌上,講起了他的舊戀人,忽然號啕大哭,嚇得我手足無措,從此這位矛盾的先生,又給我多了一個癡情郎的印象。”[8]歷史上有名的風流才子多不勝數,但是兼風流儒雅與志誠情癡的人卻少有,而林庚白就是一例典型。情路坎坷的才子林庚白,失戀期間吟哦無數,盡情吐露了相思難遣之癡、苦戀無果之愁、釋懷寬慰之望,將“癡情成狂”的詞人形象立體化。
如,因相思成癡而將詞寄予心上人聊遣相思:
憶璧(自度曲) 十月二十一日寄璧妹
春寒一紙關情甚,而今幾換春寒。官齋那次記相看。情參驚喜半,意在有無間。 三年信誓應無改。長是孩兒態。佯羞撒賴千萬般。莫遣吳波流恨繞鐘山。[5](P2 213)
據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林庚白手稿日記,不難見出他對張璧的念念不忘,如“很想念著張璧,不知道她此刻做什么……”“午后……拆開時璧的字跡,……同時不自覺地心在跳,真是奇怪。”[9](P180~183)如此日夜思念,怎不情癡?
但隨后張璧負他,林因此備受打擊,此后孤身數年,自號“摩登和尚”“孑樓主人”以自嘲[10](P114~119),由愛生恨,萬事成空,不免化作詞中呢喃,如這無眠的愁夜:
虞美人·寄璧妹
愁來一夜濃如酒。攬鏡添消瘦。思量事事總難忘。最有歡情和恨裂人腸。 前塵千億心頭住。心力難凝聚。生生世世夢魂牽。除是夢魂灰了不相憐。[5](P2 212)
而他擅長自我解剖這份癡心:
鳳凰臺上憶吹簫·雨夜無寐
更不成眠,何曾是醉,夜殘獨自彷徨。甚萬千塵影,三兩燈光。風際瓶花吹冷,映不冷、羈客心腸。聲聲雨,催教恨迸,賺得人狂。 相望。一江咫尺,嗟浩渺煙波,中有滄桑。剩酒痕如水,鬢角添霜。未信蛾眉負我,遮莫是、我誤文章。凄涼絕,魂兒夢兒,沒個商量。[5](P2 212)
他是多情才子也是癡情郎,分手后他仍然“未信蛾眉負我”,不愿面對現實,喝酒澆愁進而醉酒難眠,癡情男子形象立體而真實,頗引共鳴。但不空吟哀思,“甚萬千塵影,三兩燈光”,迷離醉眼看觥籌交錯,光與影交織,霎時冷風來一下清醒,想起身在他鄉,羈愁瞬間侵襲。他鄉殘夜獨醉,本就漂泊無依,加之雨聲點滴不絕,煩躁失眠、令人抓狂。僅僅上片就哀思無限,直抵讀者內心,身居政壇高位的人物在詞中不吝袒露自己脆弱一面。下片似乎是半夢半醒間的意識流動,愁腸百結而喃喃自語:愁催人老,苦戀許久誤了年華,百般告誡自己做個了斷,卻無力克制思念之情。一片癡心空許,惹人無限嗟嘆!
兒女情長韶華短,英雄情癡纏綿深,曲折的情感經歷鍛造了這些句句是思,字字是念的詞,林庚白的滿腔情愫化為滿紙癡嗔。
《孑樓隨筆》中他稱贊張紅橋《念奴嬌》:“詞中警句如‘漫道胸前懷豆蔻,今日總成虛設’,其于床第之愛,何等勇于自白?!‘封建社會’婦女中,欲求此類佳作,殆‘絕無僅有’,顧不堪使衛道之士讀之耳。”[11](P92)可見其欣賞勇敢吐露真情的創作方式,他也因其癡狂心性與先鋒做派,敢于寫艷體詞,如:
浣溪沙·有憶
曾見拋書午睡時,橫斜枕簟腿凝脂,小樓風細又星期。隱約乳頭紗亂顫,惺忪眼角發微披,至今猶惹夢魂癡。[5](P2 207)
其二
乍覺中間濕一些,撩人情緒褲痕斜,呢談曾記傍窗紗。悄問怎生渾不語,莫教相識定無邪,幾回鏡襤臉堆霞。[5](P2 207)
這類詞寫風花雪月,大膽凝視女性肉體,因而十分惹人注目,但是不似溫庭筠的香艷綺麗,多半是閑時所發,親切坦率亦無矯飾,所以寫艷語而不淫,有民歌式的輕甜,率真自然。其詞人形象不是依紅偎翠、見異思遷的浪蕩公子,而是專一率真的情種。他敢做風口浪尖的弄潮兒,獲譏于世而不悔,也是癡情的另外一種向度。
二、“狂”與“癡”的藝術表現
詩人與常人不同,其個性有特殊的一面,而詩人又往往用獨特的藝術方式去表現他的個性。林庚白的個性可謂不同凡響,其展現個性的藝術方式,又令人稱絕。
(一)捕捉情感瞬間的藝術直覺
情感的瞬間捕捉,如《西廂記》名句:“驚艷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12](P724)。電光火石之間萌生永恒不滅的愛意,瞬間情思凝聚成永恒的意象,此即黑格爾所言“充滿敏感的觀照”的藝術直覺。林庚白也具有極高捕捉瞬間感覺的能力,他不僅偏愛捕捉女子轉瞬即逝的嫵媚,而且能完整地把握佳人的神韻:“無端沾惹眼波恩”[5](P2 210)的眼波、“如玉亭亭含情處,臉暈梨渦微見”[5](P2 213)的嬌羞;“鬢角眉心幾點愁”[5](P2 206)的蹙眉凝愁;“一剪秋波渾昨夢”[5](P2 207)的夢里佳人;更將回眸一笑的瞬間定格化為整體意象,而值得在心中遍遍回味:“長記下樓徐一笑,這腰肢、恰似波光顫。朝到暮,思量遍。”[5](P2 213)內在直覺和客觀事物在瞬間得到統一,頗有一眼萬年之妙。
龐德在《意象主義者的幾“不”》給意象下的定義:在剎那的時間里表現出一個理智和情緒復合物的東西。[13](P152)如何在剎那間將理智和情感統一起來,則需要詞人運用富有透視力的藝術直覺,而才子林庚白恰恰有這份靈心,他善于將目睹與心擊、外物與感悟在瞬間糅合,達成王夫之所言的“即景會心”。
浣溪紗·譯法國詩人衛廉士《秋辭》
凄厲秋音去未窮。傷心不待梵琴終。黯然只在此聲中。 往日思量空濺淚,滿懷悲悒怯聞鐘。身如枯葉不勝風。[5](P2 209)
新事物入詞,向來是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庚白一大特色,但本詞的妙處不僅在于寫出以往舊體詞未出現的小提琴,更在于林庚白發現跨越古今與東西語境的觸發點——“即景會心”的藝術直覺。這首詞實際上是直覺驅使下的作品,在秋風蕭瑟、琴聲凄婉的外在環境濡染下心情隨之黯然悲傷,這是由景入心。下片憂思滿懷而心無定緒,因而如驚弓之鳥般敏感多驚,內心聽由琴聲的輕重而起伏,這是由心寫境。最后一句,將自己化身飄零的枯葉,或鐘聲突然加重,或秋風頓時揚起,暗示出自己對外界之變的無力抗拒。
(二)畫“夢”空靈,構境渾融
林庚白偏愛將夢入詞,詞中因夢而生色,幻化出“如夢復如煙”[5](P2 209)的萬端迷離情貌,“昨夢荒唐睡起遲。蘆簾細細漾風絲。此情除卻被兒知”[5](P2 206)的夢醒時候的意識朦朧游走的慵懶姿態。再如,“濃綠蔭窗紗。風絲碎落花。把檸檬、衾枕橫斜。開遍紅榴飄盡夢,留不住,是年華”[5](P2 205)的人生如夢、年華不駐的哀思;“好夢不曾溫,卻惹創痕”[5](P2 206)重溫舊夢溫香,現實卻是孤冷,癡情相思幾多酸楚,冷暖自知。
其“夢”還承擔敘事的功能,借用“夢”的第一人稱視角,將自己內心世界剖開、重組、呈像,凝縮成為一種整體意境。
念奴嬌·寄懷璧妹
輕盈吳語,記相逢,恰是寒梅時節。一剪秋波渾昨夢,爐畔燈光如雪。病榻深杯,車窗密吻,往事溫馨絕。荷香依舊,后湖曾幾圓月。 已自孤負花期,愿花開處,珍重休輕折。檢點心頭多少恨,不共斜陽明滅。海誓云情,鎖磨難盡,此意詩能說。團圞雙影,畫樓沉醉何夕。[5](P2 206)
吳儂軟語耳畔回蕩,若隱若現的荷香,夢中人眼波如水,輕柔親吻的溫存,爐畔如雪的燈光、缺月與粼粼水波相映,斜陽明滅,影中沉醉。利用燈、光、影營造迷離之感,不僅有忽明忽暗、影影綽綽的空靈光感,有好夢不在、花期易逝的惋惜美感,而且“四感”全通,聽覺、嗅覺、視覺、觸覺,利用夢的朦朧營造出一片渾融的詞境,妙不可言。更如:
琴調相思引·午夜聞歌
夜半歌聲似水柔。夢魂黯逐月光流。玫瑰床畔,倩影暗香浮。 情到疑深才是愛,心當碎盡不知愁。江風弦管,猶自繞高樓。[5](P2 208)
用蒙太奇手法呈現聽覺,一種聲音兩處心態,上片營造出精致迷離的鏡頭畫面:夜半歌聲、玫瑰暗香縈繞、佳人倩影、溫香軟夢、醉人月色幾個意象交織重疊,盈盈浮動,似夢似醒早已分不清,盡情勾勒一片柔情似水的氛圍。下片畫面驟變,江風弦管,獨自徘徊,夢境和現實的界限頓顯,“情到疑深才是愛,心當碎盡不知愁”,這番傷痛后的領悟,將兩種不同的聽覺畫面組接起來,虛實交疊,原來一切僅在舊夢中,相思凄楚,悵然無奈。
他不僅將聽覺用畫面呈現,而且更將心頭紛擾化為具象:
金縷曲·春柳
寂寞驛亭路。正春風、冶葉倡條,依稀無數。攀折偏增游子恨,裊裊含情欲舞。問那得、愁絲縷縷。夢醒隋堤人已遠,玉鉤斜、也算相思處。垂淚立,澹無語。 腰肢底事輕如許。但和煙、和月凄清,閱殘今古。記否靈和前殿事,嫵媚風流僅汝。便欲寄、纏綿容與。消息玉關何處問,又聲聲、玉笛吹愁去。空惆悵,日將暮。[5](P2 203)
這里利用“夢醒”打通古今之壁壘,也打通回憶和現實的界限,夢里與伊人含情纏綿,而夢醒時分隔兩地,唯有眼前裊裊飄舞的春柳之景,悉數呈現天涯游子心中翻騰的愁緒,如今獨自垂淚,在一片暮色中黯然自品。還如,將“夢”直接和“空”的意涵相關聯:
醉春風·午思
恨向簾波涌。悶與瓶花共。重重心緒百回腸,空空空。倦把愁添,愛將疑織,思牽情動。 長是擔驚恐。遮莫成欺哄。蘆簾下了日浮漪,夢夢夢。眼角春深,舌尖香膩,漲生桃洞。[5](P2 210)
林庚白父岑蓀是光緒年間的舉人,曾任英國駐華使館中文秘書[14],學貫中西的家學背景,加之其通曉西方文學,其詞中能見出西方意識流色彩。借陸游《釵頭鳳·紅酥手》之妙,呈現午休時候的思緒翻飛的心況、微吟呢喃的情貌,如其所言“人生何事不銷魂”,刻骨相思,字字盡癡。其詞中的“夢”從具象之夢,整體意境,空的意涵,一步步凝練升華,渾融達意。
(三)諧耳的音樂性和出新出奇的靈心
詞中每個字都躍然在口中,值得吟詠。所謂“筆端有口,句中有眼”[15](P173),林庚白毫不吝嗇在詞中吐露癡情與相思的筆墨,任何心中呢喃都化為筆下玲瓏:“人在心頭。秋在樓頭。倦登臨、意共風柔”[5](P2 206)作詞如說話,到了用筆如舌的地步,又如:
減字采桑子 ·雨夕書懷
雨外竹蕭蕭。不似芭蕉。卻似芭蕉。一樣秋聲兩樣秋。 拋書閑就窗紗坐,道是無聊。不是無聊。燭已成灰意未銷。(九月二十日南京)[5](P2 204)
長相思·本意,寄璧妹
似無情。似多情。心緒人前苦未明。青春暗自驚。 是鐘聲。是雨聲。點滴催愁眠不成。尋常語笑輕。[5](P2 209)
詞中沒有筆筆雕琢,卻更新鮮可愛,可吟可誦。但這種“自然”也別出蹊徑,他有獨特的膽力和前瞻力,強調出新,其詩中言“詠嘆無新意,常如口易干”[6](P486),也善于將新事物入詞,如寫看電影、騎摩托車、打乒乓球等新鮮體驗:
菩薩蠻 ·國泰影戲院書所見
柔腸悄與歌聲接。電光人意相明滅。如夢復如煙。情絲一線牽。 壁燈紅似血。怎似儂心熱。絮語不多時。殷勤問后期。[5](P2 207)
浣溪紗·有憶 其五
鬢角眉心幾點愁。亂蟬陰里綠如油。湖濱曾共系蘭舟。 雪夜記同摩托卡,晚春看打乒乓球。不堪往事數從頭。(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5](P2 207)
綜上所述,林庚白詞全方位展現一代民國狂士才子“癡狂交織”的立體人格,填詞寫心,將自己的內心剖開呈像,將其敏而多思的靈心安放在詞中,從詞作中能洞見內心世界的褶皺與隱溫、嬉笑與歌哭。其詞篇篇真情,字字心聲,盡情展現了癡情狂士的詞人形象,時而真誠熱烈,時而放蕩不羈,時而柔情纏綿,令人掩卷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