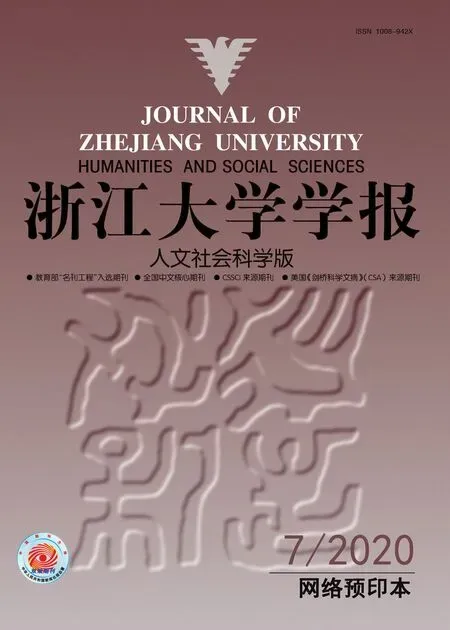論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
王冠璽 吳云軒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一、 問題的提出
在國內的司法實踐中,涉及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的案例屢見不鮮。精神控制通常指團體或者個人用一些非道德的操縱手段來說服某人按照操縱者的愿望改變自己,這種改變通常會給被操縱者帶來損害。精神控制的前身乃“洗腦”,指操控人的精神,使人的心理活動與行為活動發生異變[1]3。情緒勒索一詞由美國心理醫生蘇珊·佛沃(Susan Forward)博士提出,此乃控制他人行動中最有利的一種形式,亦即周遭的人會利用一種直接或間接的手段勒索某人。勒索者會暗示,假如不依照他們的要求來做,可能會有后遺癥。情緒勒索本身就是一種以威脅、恐嚇為出發點的要求,而且會以不同形態出現在不同情境,使得被勒索者陷入勒索者之意圖,而不得不跟著勒索者的想法走[2]47-52。
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極少在實踐中主張自己的民事權利,尤其是其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是否能夠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如能主張,其可獲得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如何?這些問題仍然缺乏明確答案。此類案件并非少見,且往往造成十分負面的社會影響,被害人的權利(益)亟須獲得保障。有鑒于此,本文將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司法判決、學說,以及比較法研究,分析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之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
二、 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主體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因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而構成侵權行為,并造成嚴重精神損害者,被害人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以下簡稱《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二十二條等規定,向加害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如果被害人死亡,其近親屬可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十八條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等規定,向加害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在此需進一步說明的是,根據被害人是否死亡,因行為人實施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而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主體有兩類:
第一類,被害人本人。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侵害被害人的人格權或健康權,構成侵權行為,造成被害人嚴重精神損害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1)《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由被侵權人(被害人)本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
第二類,被害人的近親屬。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侵害被害人的人格權、健康權、生命權,構成侵權行為,并造成被害人死亡(2)被害人死亡,有可能是因為精神大受刺激,直接死亡,例如心肌梗死或腦溢血死亡;或因為健康受損,隨即因病死亡,例如心臟病發,數日后死亡;或是因為人格權受侵害,深感受辱,因而選擇自殺而死亡。被害人之死亡過程非本文討論重點。于此所關切者,乃被害人之死亡與他人實施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有密切之關系時,其近親屬可否因而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3)《侵權責任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規定:“被侵權人死亡的,其近親屬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與《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4)《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規定:“自然人因侵權行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遺體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為原告;沒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親屬提起訴訟,列其他近親屬為原告。”該條文進一步明確了在被害人因侵權行為致死的情形下請求權人的范圍。規定,由于被害人死亡,其權利能力消滅,主體資格不復存在,不可能再主張任何權利,由被害人之近親屬主張精神損害賠償。
三、 我國司法實踐之現狀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極少在判決書中直接提及“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5)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精神控制”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找到161份判決書,其中民事判決書僅有48份;以“情緒勒索”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則未能找到相關的判決書。。究其原因,應系法院對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并不熟悉。但是,判決書中仍涉及許多可被認定為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行為。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涉及精神控制和情緒勒索的眾多案例中選取了兩類案例作為重點的分析對象:在涉及精神控制的案例中,將著重分析傳銷中的精神控制;在涉及情緒勒索的案例中,則將著重分析戀愛關系中的情緒勒索(6)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傳銷”和“精神損害”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找到215份民事判決書;以“戀愛”“情緒”和“精神損害”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找到228份民事判決書。在此基礎上,筆者從中選取了一些具有說明價值的典型案例作為分析對象。。
此外,由于在被害人健康受損和死亡的情形下,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人分別為被害人及被害人的近親屬,本文將對這兩種情形進行區分對待。
(一) 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致人健康受損
1.對于精神控制行為,實踐中法院往往認為此種行為不足以構成致人健康受損的侵權行為。
在楊某某與杜某某、姚某某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7)參見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人民法院(2016)皖1702民初3400號民事判決書。中,原告楊某某于2015年10月24日被帶至“天津天獅”傳銷組織內。被告杜某某、姚某某為該傳銷組織成員,其采取多種方式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至2015年11月6日,同時灌輸傳銷理論,要求原告購買產品并加入該傳銷組織。2015年11月6日下午,原告受言語刺激后感覺到自己逃脫無望,遂從陽臺跳下,身體多處骨折。
法院認為,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受法律保護。被告杜某某、姚某某等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致人受傷,侵犯了原告的健康權,系共同侵權,被告杜某某、姚某某等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原告楊某某在本起糾紛中也有一定的過錯,可減輕被告20%的賠償責任。故對原告楊某某的損失,被告杜某某、姚某某、陳某某、李某某共同承擔80%的賠償責任。關于具體的賠償數額,結合楊某某的受傷程度及精神損害情況,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為6 000元。
在該案中,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精神控制、非法拘禁等傳銷行為,并致使其從陽臺跳下。法院僅承認行為人的非法拘禁行為構成侵權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法院認為行為人的精神控制行為不足以構成致人健康受損的侵權行為。因此,行為人不需要因精神控制行為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2.對于情緒勒索行為,實踐中法院往往認為行為人不需要對被害人因情緒勒索而產生的健康受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在曾某某(女)與譚某某(男)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8)參見廣東省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法院(2018)粵1802民初5664號民事判決書。中,原告曾某某與被告譚某某為男女朋友關系。2017年5月底,原告跟隨被告一同來廣州同居生活,不久后來到清遠。原告想外出打工,卻被被告以各種理由阻撓,而被告每次只是幾十、一百地付給原告生活費用。原告與被告相處一段時間后,被告經常無故毆打、辱罵她。原告為此決定離開被告,但被告又是寫檢討書,又是寫保證書,希望原告再給一次機會。原告以為被告已改過自新。2018年6月23日,被告對原告頭部、腳部等部位進行毆打,使原告出現腦震蕩、頭皮血腫等癥狀。
法院認為,公民享有身體健康權,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身體健康權的,應承擔侵權責任。公安機關查明了被告在2018年6月23日8時許實施了毆打原告的行為并導致原告遭受人身損害的事實,因此,被告的侵權行為證據確鑿。被告作為侵權人應對原告因此而遭受的人身損害后果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本案不涉及傷殘,原告并未達到精神受到嚴重損害的程度,因此對該撫慰金不予支持。
在該案中,行為人對被害人既實施了情緒勒索行為,又實施了毆打行為。雖然法院僅認為行為人不需要對被害人因毆打行為而產生的健康受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但從法院的判決理由中不難看出,其實際上認為,對于被害人因情緒勒索而產生的(精神)健康受損也不應加以賠償,因為這種受損亦不涉及傷殘。
(二) 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致人死亡
1.對于精神控制行為,實踐中有法院認為行為人應當對被害人因精神控制而死亡的后果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在崔某清、成某某與崔某、李某某等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9)參見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3318號民事判決書。中,三被告均系名為“連鎖經營”的傳銷組織成員。2015年3月27日凌晨1時30分左右,崔某運(兩原告之子)被接到傳銷組織的所在地,3月27日16時左右從陽臺墜樓身亡。
法院認為,公民生命健康權受法律保護。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崔某運墜樓死亡與三被告的傳銷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三被告誘騙崔某運參加傳銷組織并騙取其錢財,同時不允許其離開,導致崔某運從陽臺墜樓身亡,崔某運的死亡與三被告的傳銷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同時,崔某運系自行跳樓身亡,其自身亦存在一定過錯,應當減輕被告的賠償責任。綜合考慮本案案情及被告的過錯等,法院確定三被告對崔某運的死亡后果連帶承擔70%的賠償責任。
崔某運的死亡給兩原告身體及精神均造成了損害,故對其要求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法院予以支持。根據侵權行為造成的后果、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受訴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被告的過錯等,法院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為60 000元。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行為人的傳銷行為(包括精神控制、非法拘禁等行為)導致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應構成侵權行為。此外,由于被害人的死亡對兩原告的精神造成了損害,法院支持了原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
但是,實踐中也有法院認為行為人不需要對被害人因精神控制而死亡的后果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在程某啟、張某某與馬某、楊某某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10)參見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4)楚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中,被告馬某、楊某某等在某出租房內進行“人際資源網”傳銷活動。2013年8月13日,程某靈(兩原告之子)到云南省楚雄市與其網戀女友楊某某見面。被告楊某某當晚將程某靈帶到該出租房內留宿,并提議一起參加“人際資源網”傳銷活動。該房內居住的人較多,當晚馬某即安排人給程某靈洗腦。8月14日6時許,程某靈從四樓墜落當場死亡。
法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實。本案中,死者程某靈系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對自己的行為和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具有判斷能力。程某靈系從四樓墜落當場死亡,而兩原告提交的證據不能證實其死亡系被告馬某、楊某某的直接行為所致。但程某靈從湖北省武漢市硚口區到楚雄與女友楊某某見面,當晚被告楊某某又將程某靈帶到出租房內留宿,提議一起參加“人際資源網”傳銷活動,并由被告馬某安排人給其洗腦,對程某靈的情緒變化造成一定的影響,這也是程某靈墜樓身亡的原因之一,故被告馬某、楊某某應對程某靈的死亡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但對于兩原告請求的精神損害賠償金,法院不予支持。
在該案中,法院明確承認,行為人的精神控制(洗腦)行為是被害人墜樓身亡的原因之一,故精神控制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已經成立。不過,法院同時認為,行為人不需要對被害人因精神控制而死亡的后果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2.對于情緒勒索行為,實踐中法院往往認為此種行為不足以構成致他人死亡的侵權行為,或認為此種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例如,在張某義、張某華侵權責任糾紛案(11)參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黑01民終1972號民事判決書。中,原告張某義、張某華(死者之父、母)訴稱,被告呂某某作為死者張某的女朋友,利用職權糾纏、精神折磨、殘酷迫害張某。被告以支行副主任的職權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不允許張某與女同事說話,不允許其給女同事開營業室的門,否則就發短信罵人。張某多次提出斷絕兩人之間的關系,但被告繼續采取各種方式控制張某,令其聽從自己的安排。在被告的折磨和威脅下,張某最終自殺身亡。
法院認為,本案為侵權責任糾紛之訴,張某義、張某華應對呂某某存在侵權行為及該行為與造成的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張某義、張某華舉示的現有證據并不能證明呂某某有何種侵權行為及該行為與張某的死亡之間存在民法上的因果關系,理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且張某與呂某某為戀人關系,本案案發時呂某某并不在現場,亦無法律規定其負有相應的救助義務,故對張某義、張某華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在該案中,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情緒勒索行為以強迫其聽從自己的安排。但根據法院的觀點,行為人的情緒勒索行為并不能構成致他人死亡的侵權行為。同時,情緒勒索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間也不存在因果關系。因此,行為人不需要因情緒勒索行為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又如,在連某、趙某某與賈某某、王某某侵權責任糾紛案(12)參見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嶺區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0766號民事判決書。中,原告連某、趙某某(死者之父、母)訴稱,被告賈某某與死者連某系大學同學,雙方在校期間開始交往,后于2011年6月15日正式登記結婚。在此后三個多月的時間里,被告賈某某對其妻連某的態度由2011年7月初的埋怨、怨恨迅速升級為瘋狂的人身攻擊、惡語謾罵、人格污辱。這一傷害以手機短信方式表現,數量達近百條之多。此外,被告多次對連某的個人隱私進行了用語十分陰毒的譏諷和恥笑,他毫不留情地譏諷和恥笑連某父母離異和連某曾因此誤服安眠藥的隱私事項,以刻意刺痛連某的心靈,加重對連某身心的傷害。2011年10月3日,連某因不堪重負自殺身亡。
法院認為,兩原告應當舉證證明被告實施了加害行為、導致了損害后果,且加害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行為人具有過錯;如不能證明,則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現兩原告提供的證據雖然能夠證明被告與連某之間存在誤解和猜疑,在連某自殺前雙方發生了爭吵,但連某作為一名成年人應當知曉生命的可貴并珍惜生命。兩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的言行必然導致了連某的墜樓自殺,即無法證明被告的行為與連某自殺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故被告不構成對連某生命權、健康權、隱私權的侵害,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在該案中,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情緒勒索行為,但是,法院認為,此種情緒勒索行為與被害人自殺的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因此,行為人不需要因情緒勒索行為而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綜上,在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時,我國法院往往會先判斷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是否成立。若該侵權責任可以成立,則法院將緊接著認定請求權人可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
此外,在判斷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是否成立時,部分法院未經詳細分析,即得出侵權責任成立或不成立的結論(13)參見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4)楚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黑01民終1972號民事判決書。。法院對此種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進行分析時,均聚焦于兩個構成要件的探討,亦即因果關系與過錯(14)參見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3318號民事判決書、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嶺區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0766號民事判決書。。有鑒于此,本文將以因果關系、過錯兩要件以及精神損害賠償范圍的分析為核心,試圖建構我國法上基于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理論體系。
四、 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理論體系
(一) 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發生,均須具備侵權行為要件。由此可知,在分析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所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時,首先應判斷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具體而言,在行為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僅侵害被害人的健康的情形下,請求權人為被害人本人。若被害人想要向行為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則須證明,行為人對自己構成侵權行為。但問題在于,在行為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時,作為請求權人的被害人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究竟要證明行為人對被害人(死者)構成侵權行為,還是要證明行為人對自己(近親屬)構成侵權行為?
對于這一問題,比較法上存在不同的見解。根據《德國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若被害人的身體、健康、性的自我決定被侵害或者被剝奪自由,其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此處有意未將生命列舉出來:致人死亡本身并不引起痛苦撫慰金請求權[3]232。《德國民法》亦無支持死者的近親屬因為死者的生命受到侵害而享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但是,德國司法實務認為,若被害人因受侵害而死亡,涉及的并不是第三人的損害不能得到賠償的問題,而是死者的近親屬自身受到了傷害。換言之,行為人的侵權行為不僅造成了他人的死亡,還通過該死亡進一步對死者的近親屬的健康造成了傷害[3]233。由此可知,在德國法上,被害人的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其須證明行為人對自己構成侵權行為。
另一方面,我國臺灣地區所謂“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四條則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關于不法侵害他人致死的損害賠償,此條雖設有規定,但此條文本身仍不足以作為請求權依據,尚須結合所謂“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條關于侵權行為成立的規定才能構成請求權基礎。易言之,即須以加害人對死者構成侵權行為為前提[4]313。需要注意的是,若第三人就其因被害人死亡而受到損害,欲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其原則上須依所謂“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條關于侵權行為之一般規定。但是,所謂“民法典”特設明文,規定特定范圍之人就特定類型之損害,可直接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是否符合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在所不問[4]320-321。前述第一百九十四條即屬于此種條文。因此,被害人的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僅需證明加害人對死者構成侵權行為,而不需要證明加害人對自己構成侵權行為。
在我國法上,作為請求權人的被害人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僅需證明加害人對被害人(死者)構成侵權行為。《侵權責任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的結構與臺灣地區所謂“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四條的結構比較類似,該段內容所提及的“承擔侵權責任”可包括精神損害的賠償。因此,在確定被害人近親屬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時,或可參考臺灣地區的相關解釋。
關于因侵權行為致死的精神損害賠償,《侵權責任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和《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雖設有規定,但此等條文均非請求權基礎,被害人尚須結合《侵權責任法》第六條關于侵權行為成立之規定向加害人主張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即須以加害人對被害人(死者)構成侵權行為為前提。
同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和《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的規定,特定范圍之人(被害人的近親屬)就特定范圍之損害(精神損害),可直接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是否符合一般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在所不問。因此,被害人的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不需要證明加害人對自己構成侵權行為。
綜上所述,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該請求權人須先證明加害人對被害人構成侵權行為。
我國法院在認定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時對“因果關系”和“過錯”的探討較多,本文也將聚焦于這兩個要件的分析(15)王澤鑒教授也認為,在判斷加害人是否對死者構成侵權行為時,應特別說明者有二:一是加害人須有故意或過失;二是侵害行為與死亡之間須有相當因果關系。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四)》,(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頁。。
1.因果關系
學者普遍承認,應將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作為判斷侵權行為法上的因果關系的標準[5-7]。但是,對于是否有必要將因果關系分為兩種類型,即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和責任范圍因果關系,學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學者主張,因果關系即指行為人的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客觀聯系,沒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劃分[5]72-73。也有學者主張,因果關系應當被劃分為兩種類型[6]91-92。
從比較法來看,德國法通說認為,侵權行為法上的因果關系可分為兩種,即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和責任范圍因果關系,前者是指可歸責的行為與“權利受侵害”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后者是指“權利受侵害”與“損害”之間具有因果關系[8]183-184。德國法上的這種區分值得借鑒,因為兩種因果關系之間存在顯著的區別:
其一,責任成立因果關系所要認定的是權益受侵害是否因其原因事實(加害行為)而發生。此種因果關系屬于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責任范圍因果關系所要認定的則是因權利受侵害而生的損害,何者應由加害人負賠償責任的問題[8]184。也就是說,它是侵權責任成立后用于確定賠償范圍的因果關系。
其二,侵害行為與侵害他人權利之間的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又可稱為初始侵害。侵害他人權利所生的損害應否賠償,乃屬責任范圍因果關系,又可稱為結果侵害。加害人是否有過失僅及于“初始侵害”,并不及于“結果侵害”,此等侵害應否賠償,系依因果關系認定[8]185。
由于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屬構成要件,本部分將對此種因果關系進行探討。對于責任范圍因果關系,則將在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時分析。
相當因果關系是由“條件關系”及“相當性”所構成的,故在適用時應區別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審究其條件上的因果關系,如為肯定,再于第二個階段認定該條件的相當性[8]186。
在我國的相關司法實踐中,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往往在加害人的逼迫下無奈采取跳樓等自害行為,并導致傷亡結果(16)參見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人民法院(2016)皖1702民初3400號民事判決書、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4)楚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等。。從條件關系(17)條件關系,指某甲的行為與某乙的權利受侵害(或某種損害與某乙之權利受侵害)之間具有不可或缺的條件關系。條件關系系采“若無,則不”的認定檢驗方式。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頁。上看,若不存在加害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被害人即不可能受傷或死亡,則可認為加害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與被害人的權利受侵害之間具有不可或缺的條件關系。反之,則應認為兩者之間不具有條件關系。
在前述與傳銷中的精神控制(洗腦)有關的案例(18)參見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人民法院(2016)皖1702民初3400號民事判決書、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4)楚民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3318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應依經驗法則,并綜合所有證據,從多數事由中認定何者系對被害人權利受侵害的結果負責的條件。若不存在加害人的精神控制行為,被害人即不會情緒失控,采取跳樓等自害行為,則精神控制行為與被害人的權利受侵害之間具有條件關系。若被害人采取跳樓行為僅是由于想要擺脫加害人的非法控制,則精神控制行為與被害人的權利受侵害之間不具有條件關系。
此外,相當因果關系說旨在以條件的“相當性”來合理界定侵權責任的范圍。關于“相當性”的認定,應認為其以“通常足生此種損害”為判斷基準。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則具有相當性;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即不具有相當性[8]195-196。
此時需要討論的問題是,被害人因自己的行為導致其權益遭受侵害時,在何種情形下會影響因果關系的相當性。在臺灣地區1987年臺上字第158號判決中,加害人陳某某駕車追撞前行車輛,造成連環車禍,并起火燃燒,被害人下車后,見火勢猛烈,唯恐車身爆炸,遂將橋縫誤為安全島紛紛跳下而造成傷亡。法院認為:“依此項客觀存在之事實觀察,如車身爆炸而不及走避,其造成之傷亡將更為慘重,且當時又系夜晚,更易引起慌亂,在此緊急情況之下,欲求旅客保持冷靜,安然離開現場,殆無可能,故依吾人一般智識經驗,上述旅客在慌亂中跳落橋下傷亡,是否與陳某某駕車追撞而造成之上述車禍,無相當因果關系,非無研究余地。”[9]93根據這一觀點,即使被害人自己跳落橋下傷亡,加害行為與權益受侵害之間的相當性也不會因此受影響。
綜合判斷之,即使被害人采取跳樓等自害行為,判斷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與權益受侵害之間的相當性的關鍵仍在于,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是否通常會導致被害人權益受侵害的結果。
關于判斷通常性所應考察的范圍,有采主觀說,以行為當時行為人所認識之事實為基礎;有采客觀說,以行為當時所存在的一切事實及行為后一般人可預見之事實為基礎;有采折中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可預見的事實及行為人特別認識的事實為基礎[8]196。
本文認為,若行為人在行為當時未得知一般人可預見的事實(條件),則法律沒有必要豁免其責任;另一方面,如果行為人因為特殊原因得知了一些一般人不可預見的條件,則該偶然所知的條件亦為基礎條件,蓋若不如此,行為人得為違法行為而不負其責任[10]170。
在前述張某義、張某華侵權責任糾紛案(19)參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黑01民終1972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兩原告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的情緒勒索行為與張某的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不難看出,法院做出此種認定的原因并非在于張某最終采取了自殺行為,關鍵應在于現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的情緒勒索行為通常會導致張某自殺身亡(生命權受侵害)。若兩原告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根據行為當時一般人可預見的事實及被告特別認識的事實,被告的情緒勒索行為通常會導致張某自殺身亡,則法院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和《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20)《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所提及的“自然人因侵權行為致死”,應不限于加害人的行為直接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被害人因受侵害而自殺身亡的情形,亦屬于“因侵權行為致死”。的規定,支持兩原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在判斷加害行為與權益受侵害之間是否具有相當性時,應有本土化因素之考慮,亦即法院必須斟酌中國社會之一般情況與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后做出判斷,以形成最終的心證。
2.過錯
《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條文明確將“過錯”認定為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學者普遍認為,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是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中行為人可歸責的主觀心理狀態[5,11]。同時認為,過錯的客觀化是侵權法理論發展的必然,指的是在對侵權行為人是否具有過錯進行判斷和認定時,采取一個客觀的行為標準來衡量與判斷。如果行為人符合該標準就認定其沒有過錯,否則就認定其具有過錯[5,12]。
故意是指行為人對于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并有意使其發生(直接故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并不違反其本意(間接故意)[13]139。不難看出,法院在判斷行為人是否有故意時,仍應采取主觀標準。
過失乃怠于注意的一種心理狀態[13]139。對過失的非難無論是指“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還是“怠于交易上必要的注意”,均指行為人可預見其行為的侵害結果而未為避免。因此,對侵害結果的預見性及可避免性(或預防性),構成了注意的必要條件[8]241。
對于過失的標準,解釋上應以抽象的輕過失為準,亦即行為人的注意義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準,若未盡此注意義務者,即認為有過失。采取這一標準的原因在于,若以重大過失為準,則行為人之責任失之于輕,不足以維持社會生活之安定;若采取具體的輕過失,則其標準必因人而異,且被害人對加害人之注意力之狀態舉證困難[13]139。這一標準的采納實際上體現了過失的客觀化。
綜上所述,法院僅在判斷行為人是否有過失時,應采取客觀標準;判斷行為人是否有故意時,則應采取主觀標準。
此外,要構成侵權責任,原告僅需證明加害人對“初始侵害”(加害行為對被害人權益的侵害)有過錯,而不須證明加害人對“結果侵害”(侵害被害人權益所生的損害)有過錯[8]185。
以前述的連某、趙某某與賈某某、王某某侵權責任糾紛案(21)參見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嶺區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0766號民事判決書。為例,兩原告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則應證明被告賈某某對死者連某的自殺(生命權受侵害)具有過錯。在判斷被告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時,應區分情形加以對待:(1)若被告對連某的情緒勒索旨在打擊其自尊心,甚至促使連某通過自殺的行為來顯示對自己的服從,則被告對連某自殺結果的發生具有直接故意。(2)若被告雖然沒有促使連某實施自殺行為的意圖,但其可以預見到自殺結果的發生,而此種結果的發生并不違反其本意,則被告對連某自殺結果的發生具有間接故意。(3)若被告怠于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本應預見到連某自殺結果的發生但未能預見,則其對連某自殺結果的發生具有過失。(4)若被告已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則被告不具有過失。
(二) 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
在確認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得以滿足之后,緊接著需要處理的問題是,如何認定請求權人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
對這一問題,可分兩個層次探討。首先,確認責任范圍因果關系是否存在。其次,若該因果關系存在,則討論精神損害賠償應如何量定。
1.責任范圍因果關系
不同于責任成立因果關系,責任范圍因果關系所要認定的是“損害”與“權利受侵害”之間的因果關系,易言之,即因權利受侵害而生的損害,何者應由加害人負賠償責任的問題[8]184。
在行為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僅侵害被害人的健康,但并未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被害人須證明其身體健康受侵害與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之間存在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從條件關系上看,若被害人的健康未受侵害,其往往不會遭受精神上的損害;從“相當性”上看,若被害人的健康遭受嚴重侵害(如因被迫跳樓而導致骨折),則被害人通常會遭受精神上的損害。由此可見,在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僅致被害人健康受損的情形下,責任范圍因果關系往往可以成立。
在行為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直接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被害人的近親屬須證明被害人的生命權受侵害與死亡損害之間存在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此種因果關系的存在是不證自明的。
問題在于,若行為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侵害被害人的健康,而被害人之后采取了自殺行為,或其因傷而死,此時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是否存在。從條件關系上看,若是被害人的健康未受侵害,就不可能采取自殺行為或因傷而死,則可認為被害人的健康受侵害和死亡后果之間具有不可或缺的條件關系。反之,則應認為兩者之間不具有條件關系。
從相當性上看,被害人的近親屬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其必須證明被害人健康受損的情形通常會導致被害人實施自殺行為或使其因傷而死。在臺灣地區1956年臺上字第520號判決一案中,上訴人之子即死者某甲于1954年3月13日遭被上訴人毆打成傷,至同年4月15日自殺身亡。上訴人以死者受傷無錢醫治,羞憤自殺,其死亡與傷害有因果關系,對被上訴人提起賠償精神撫慰金8 000元之訴。原審法院認為診斷書所載某甲前胸部受毆打成傷,治療期為10日,并無足以致死之情形,而自殺身亡在治療10日之后,難以認定其與傷害有因果關系之存在。上級法院亦采此見解,明確表示,“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惟此項請求權須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外,并以兩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系為其成立要件”,否定上訴人賠償撫慰金之請求權[4]315-316。在該案中,法院傾向于認為,被害人的健康受損通常不會導致其自殺身亡。因此,健康受損與自殺的結果之間并不具有相當性。
在前述的崔某清、成某某與崔某、李某某等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22)參見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3318號民事判決書。中,被害人從傳銷窩點逃跑時摔下受傷,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法院并沒有否認被害人健康受損與死亡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原因應在于:一方面,被害人健康未受損,則不可能因此身亡;另一方面,被害人此種健康受損的程度通常會導致其死亡的結果。
2.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量定
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應由法院自由裁量,就個案斟酌相關因素而量定。同時,精神損害賠償具有填補、撫慰、預防的功能,應作為量定其數額的準則[9]260。《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十條和第十一條確立了法院確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時所須考量的因素,其大致可分為兩類:
(1)被害人方面應斟酌的因素
第一,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在被害人方面應予斟酌的,首為侵害程度,即受侵害的人格法益(例如生命、身體、健康等)、侵害輕重(死亡、抑郁癥等)、時間(如醫療康復期)等[9]261-261。
第二,被害人與有過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十一條規定:“受害人對損害事實和損害后果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其過錯程度減輕或者免除侵權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被害人因加害人的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而健康受損,而被害人對損害的發生與有過失,則法院得減免加害人的賠償責任。
問題在于,在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他人死亡的情形下,如直接被害人(死者)對死亡的發生與有過失,則間接被害人(死者的近親屬)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時,應否承擔直接被害人的與有過失。對此問題,應采肯定說。間接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雖系固有權利,然該權利系基于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產生,自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若直接被害人于損害的發生與有過失,也應有與有過失規定的適用[9]330。在實踐中,有法院認為,若被害人采取自害行為(如跳樓)逃避加害人的控制,并因此而死亡,其自身存在一定過錯(23)參見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2015)蜀民一初字第03318號民事判決書。。若按照這種觀點,則在被害人自殺身亡的案例中,被害人的近親屬應承擔被害人的與有過失。
(2)加害人方面應斟酌的因素
第一,侵權人的過錯程度。在財產損害方面,其賠償金額不因加害人故意、過失的輕重而受影響。在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量定上,加害人故意或過失的程度應予斟酌。故意實施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須斟酌加害人的故意程度,才能撫慰被害人的精神痛苦[9]263。
第二,侵權人的獲利情況。精神損害賠償除填補、撫慰的功能外,亦具有預防功能。因此,若加害人因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而獲取利益,則法院在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時應將此種獲利情況考慮在內,從而使加害人有所感受,并引導其行為[9]264。
在實踐中,加害人實施情緒勒索行為的目的往往是在親子、情侶、職場關系中爭奪控制權,讓對方就范。因此,情緒勒索行為的實施一般不能為加害人帶來經濟上的利益。與之不同,加害人實施精神控制行為(如傳銷中的洗腦)的目的則通常在于獲取經濟上的利益。由此可知,精神控制的行為人往往應賠付更高數額的精神損害賠償。
五、 精神損害賠償與撫慰金的概念辨析及制度選擇
根據《侵權責任法》和《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的相關規定,若被害人遭受嚴重的精神損害,可以請求加害人對其進行精神損害賠償,或請求加害人賠償撫慰金(24)參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和《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八條第二款。。但是,關于我國法上“精神損害賠償”與“撫慰金”之間的關系,《侵權責任法》和《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均未提供明確的答案。有鑒于此,我們可以參考比較法上的做法。
(一) 瑞士法
非財產上損害,被害人可依法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在瑞士法上稱“慰撫”(Genugtung)或“金錢給付之慰撫”(Genugtung in Festalt der Geldleistung)[14]274。《瑞士民法》第二十八條規定:“Ⅰ.人格關系受不法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Ⅱ.關于損害賠償(Schadensersatz),或給付一定金額作為慰撫金(Leistungeiner Geldsummeals Genugtung),僅于法律就其事件有特別規定時,始得以訴請求之。”通說認為,損害賠償適用于因人格權受侵害而發生財產上損失的情形,慰撫金則適用于侵害人格權而發生非財產上損失的情形[15]57。為了避免報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訴訟,以及人格價值的商業化,立法者規定必于法律之特定情形下,始得請求慰撫金[15]58。但是無論如何,人格權遭受侵害發生非財產上損失時,得以金錢賠償是毫無疑問的。
(二) 德國法
非財產上損害,被害人可依法律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德國法上稱為“相當金錢賠償”(Billige Entschadigung in Geld)(舊《德國民法》第八百四十七條),在判例學說上多稱為“痛苦金”(Schmerzensgeld)[14]273-274。根據《德國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所示“非財產上之損害,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以金錢賠償”可知,德國民法上之損害賠償未如《瑞士民法》第二十八條那樣僅適用于財產上損害,而是亦適用于“非財產上損害”。
關于非財產上損害的金錢賠償的法律性質,在德國法上亦有爭論。1955年聯邦最高法院民庭會議曾為此形成決議(BGHZ18,149)。該決議的要旨在于:舊《德國民法》第八百四十七條規定的痛苦金請求權不是通常的損害賠償,而是特殊的請求權,具有雙重功能:一是對被害人所受非財產上損害提供適當的補償,二是由加害人就其所造成的損害對被害人予以慰藉(25)參見王澤鑒《損害賠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頁。關于本項決議全文,參見Markesinis, ″The Law of Tort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in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Vol.Ⅱ,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946-959。關于德國慰撫金之介紹,參見[日]普川道太郎《慰謝料額の比較法的研究─西ドイツ》,載《比較法研究》第44號(1982年),第24頁。。
(三) 我國法
如前所述,瑞士法上的“損害賠償”僅適用于因人格權受侵害而發生財產上損失的情形,而德國法上的“損害賠償”則可同時適用于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損害。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我國明顯采取了后一種立場(26)根據該規定,遭受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被害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對于《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八條第二款所涉及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本文認為,其應屬于《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所涉及的“精神損害賠償”的同義詞,理由如下:其一,從條文結構上看,《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八條第二款和《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的結構十分類似,即均以“被害人遭受嚴重的精神損害”為請求權人請求撫慰金/損害賠償的前提。其二,從比較法上看,各國均承認撫慰金(慰撫金)系就權益被侵害所造成的非財產上損害所支付的相當數額之金錢[14]275。若采此種觀點,則“精神損害撫慰金”應與“精神損害賠償”指向同一事項。
六、 結 語
本文將請求權人可基于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行為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情形分為兩類,即行為僅侵害被害人的健康和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在第一種情形,請求權人為被害人,其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須證明加害人對自己構成侵權行為。在第二種情形,請求權人為被害人的近親屬,其若要主張精神損害賠償,須證明加害人對被害人構成侵權行為。
判斷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是否成立的關鍵在于“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和“過錯”的認定。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為判斷因果關系的標準,其由“條件關系”及“相當性”兩部分構成。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對前者的判斷應采取主觀標準,對后者的判斷則應采取客觀標準。在確定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時,首先須確認責任范圍因果關系的存在,其次則應結合《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的相關規定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
應當承認,精神控制或情緒勒索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若能證明加害人對被害人構成侵權行為,且存在責任范圍因果關系,其應可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主張精神損害賠償。譬如,在前述的連某、趙某某與賈某某、王某某侵權責任糾紛案(27)參見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嶺區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0766號民事判決書。中,若兩原告(死者之父、母)可證明被告賈某某的情緒勒索行為與死者的生命權受侵害之間存在責任成立因果關系,且被告對自殺結果的發生具有直接故意,其應可依據《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十八條第一款前段與《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七條規定請求精神損害賠償(28)在本案中,被害人生命權受侵害與死亡的損害后果之間的責任范圍因果關系是不證自明的。。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則可結合被告(侵權人)的過錯程度、被害人(死者)的與有過失等因素進行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