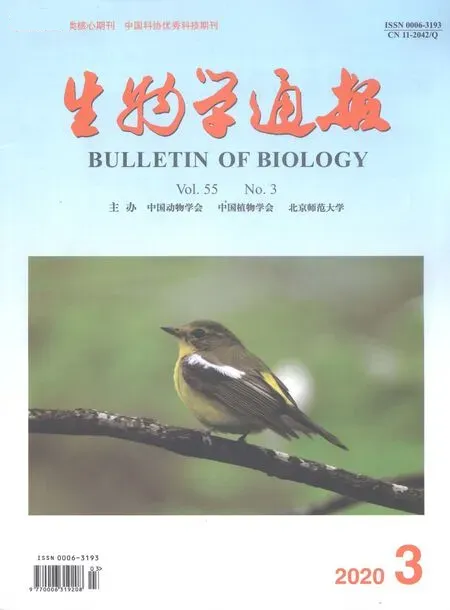植物入侵機制研究進展*
李小蒙 于 明 李 潔
(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北京 100875)
隨著國際交流和世界貿易的飛速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生物被有意或無意地轉移至世界范圍的廣大區(qū)域。當這些物種擴張至自然分布區(qū)以外的其他區(qū)域,并形成爆發(fā)式生長,對當地生態(tài)或經濟造成危害時,則被定義為外來入侵種。入侵物種不僅影響入侵地的環(huán)境和物種、群落動態(tài)及生態(tài)系統(tǒng)結構和功能的穩(wěn)定性,而且對當地的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危害。例如,喜旱蓮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普通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水葫蘆(Eichhornia crassipes)等作為外來入侵種,已對我國的經濟、生態(tài)系統(tǒng)和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嚴重危害[1]。因此,對生物入侵的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1958年Elton 的專著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animals and plants的發(fā)表,標志著生物入侵研究的開始。早期的研究主要使用一些常規(guī)的生態(tài)學方法,對生物入侵現象進行觀察并提出理論假設。隨著分子遺傳分析手段的融入,對生物入侵機制的研究有了大幅度增加,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植物入侵成功發(fā)生的假說和機制。
1 植物入侵相關假說
研究人員主要從2 個重要方面探究植物入侵成功的主要原因[2]:1)為什么某些群落比其他群落更容易受到入侵?2)為什么某些物種更容易成為入侵種?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研究人員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很多關于外來植物成功入侵的假說。這些假說主要從繁殖體壓力、非生物環(huán)境特征和生物特征3 個方面解釋植物入侵為什么能成功發(fā)生[3]。
1.1 繁殖體壓力假說 繁殖體壓力(propagule pressure),又稱引入強度,主要是指釋放到非原產地區(qū)域的繁殖體數量和釋放頻次。繁殖體壓力假說認為,植物繁殖體的大量引入和多次引入能通過高的遺傳多樣性、侵占當地種子庫、持續(xù)補給及較高的被引入適宜環(huán)境的可能性增加成功入侵的可能。單次引入的個體數量越多,引入越頻繁,繁殖體壓力越大。繁殖體壓力越大,被引入種群的遺傳多樣性則越高,因而更有利于外來種適應當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環(huán)境并成功建群[4]。同時,繁殖體壓力越大,尤其是引入越頻繁,入侵者被引入到條件適宜的環(huán)境下的幾率就越高。持續(xù)地引入還可為處于惡劣環(huán)境下或遭受瓶頸效應的入侵種群提供緩沖的機會。此外,大的繁殖體壓力可通過對侵入地種子庫的侵占增加拓殖和建群的可能性[3],并因而促進入侵的后續(xù)發(fā)生。
1.2 非生物環(huán)境特征相關假說 非生物環(huán)境特征主要指引入地的環(huán)境條件和資源可利用量。引入地是否具有友好的環(huán)境條件是入侵成功發(fā)生的重要條件;引入地資源可利用量的增加為入侵者提供了種群增長和拓殖的機會。資源可利用量的改變通常伴隨著人為或自然擾動。高程度的擾動事件通常伴隨著高水平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力,可能促進外來種成功入侵。而且,擾動事件能降低成熟植物的覆蓋度,增加外來種拓殖的空間,降低外來種幼株與本地種成株的競爭,進而促進外來種的成功入侵。與此相關的假說主要有環(huán)境異質性假說(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空生態(tài)位假說(empty niche)、機會窗假說(opportunity windows)和可利用資源增加假說(increased resource availability)等。環(huán)境異質性假說認為,環(huán)境條件多樣性高的棲息地擁有豐富的生態(tài)位,如果本地物種不足以利用所有生態(tài)位時,入侵就有可能成功發(fā)生。與此相似,空生態(tài)位假說認為當本地物種非常有限,不能使當地群落和生態(tài)系統(tǒng)達到飽和時,外來者就能占用未被利用的資源和生態(tài)位,從而成功入侵。機會窗假說則強調生態(tài)位的動態(tài)變化,認為生態(tài)位的可利用性會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發(fā)生改變。當合適的機會到來時,外來種就會成功拓殖、歸化,并進一步成為成功入侵種。
1.3 生物特征相關假說 生物特征包括入侵植物自身特征和入侵地本地種的屬性。入侵植物自身的一些性狀被認為與入侵力有關,例如理想雜草假說(ideal weed)認為具有某些性狀特征的外來種更容易成功入侵,例如,雜草型生活史、小種子、高的基因型可塑性和表型可塑性、快速生長、高的繁殖力及較早的繁殖,都可能導致該物種在與本地種的競爭中獲勝,從而促進入侵的成功發(fā)生[3]。此外,入侵植物與引入地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也會影響入侵的成功發(fā)生。與此相關的假說主要有天敵釋放假說(enemy release hypothesis)[5]、競爭能力增強的進化假說(evolution of improved competitiveability,EICA)[6]和新武器假說(novel weapons)[7]等。天敵釋放假說認為入侵者進入新的區(qū)域后,由于在新的棲息地不會受到原產地所具有的天敵的影響,因而能快速擴張。EICA 假說認為由于入侵植物在入侵地不會受到天敵影響,因而將更多資源分配給增加競爭力而不投入防御,所以入侵地個體比原產地更高大、繁殖投入更多。新武器假說認為入侵植物會釋放化學物質影響其競爭者,從而促進其成功入侵。當然,入侵植物與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也會阻礙入侵的成功發(fā)生,例如生物阻抗假說(biotic resistance)認為入侵者在侵入地所受到的競爭、啃食和病原菌感染都有可能對入侵者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影響其建群和入侵。
1.4 繁殖體壓力、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 入侵生物面臨的繁殖體壓力、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之間并不是獨立的,而是互相作用并共同影響外來物種的成功入侵。入侵種面臨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非常常見。例如,入侵者所擁有的某種競爭能力也許能幫助其順利地入侵至某一個棲息地,但是對環(huán)境條件不同的其他區(qū)域的入侵可能并無幫助。同樣,入侵者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直接影響其是否能充分利用入侵地更加豐富的資源[3]。研究認為,受到眾多數據支持的2 種入侵機制,天敵釋放假說和可利用資源增加假說,對生物入侵的影響具有交互作用,被稱為資源-天敵釋放假說(resource-enemy release hypothesis)[8]。該假說認為,天敵釋放給入侵種帶來的適合度收益會隨著可利用資源的增加而增加[8]。對生物入侵過程中天敵和棲息地生產力所進行的模型研究表明,傳統(tǒng)的EICA 假說所認為的在缺少天敵情況下入侵植物能進化出低防御、高生長力特征的說法并不絕對,而是受到棲息地生產力的影響[9]。該研究推測,天敵釋放只有在原產地區(qū)域生產力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才能導致入侵個體將防御投入轉移到個體生長上,而在原產地生產力較高的情況下,入侵個體則不會降低自己的防御投入[9]。因此,生物因素對成功入侵的影響受到了非生物因素的作用。入侵種的繁殖體壓力,也同樣受到了各種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的影響。入侵植物易于傳播的一些生物特征使得繁殖體壓力較大。而入侵地是否為入侵者提供了易于匯集的場所及容易傳播的途徑,都會影響入侵種的繁殖體壓力水平[3]。由此可見,生物入侵不僅受到了繁殖體壓力、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了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使得生物入侵的結果更加復雜。
2 植物入侵過程中的快速進化
盡管生物入侵假說日益豐富,然而大部分假說都是將入侵物種和入侵群落作為生態(tài)上和進化上靜止的物體來看,而忽略了入侵過程中經歷的一些生態(tài)過程和進化過程可能會對入侵過程產生動態(tài)的影響[10]。入侵過程中的生態(tài)過程,例如,繁殖體供應模式、氣候波動和生境擾動等,都會對入侵過程產生動態(tài)影響。同時,入侵物種在入侵地迅速擴張,通常會經歷一系列進化改變,包括由于入侵過程中伴隨的雜交或強烈選擇等作用導致的遺傳多樣性和遺傳構成的改變,以及表型性狀的遺傳改變[10-11]。入侵種在入侵地發(fā)生的快速適應性進化,對入侵植物的成功建群和迅速擴散起到了推動作用。因此,探索植物入侵過程中的快速進化對了解植物成功入侵具有重要意義。
2.1 引入過程中的快速進化 外來種能否被轉移及能否被引入到原產地之外的區(qū)域與該物種的生物學特性息息相關,例如種子形態(tài)和大小都有可能影響該物種被媒介傳播的可能性。因而物種特征的進化改變可能會影響該物種被傳播和引入外地的可能性[10]。例如,有些物種進化出了一些容易被人類傳播的特性。很多農業(yè)雜草進化出了與農作物類似的形態(tài)和生活史特性[12],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其混入農產品中被傳播的可能性。還有些物種存在預適應的現象,使得這些物種在被傳播、引入、建群和擴散的過程中都能成功地存活下來[13]。例如最常見的幾種入侵松屬植物(例如Pinus radiata,P.contorta,P.halepensis,P.patula,P.pinaster等)通常具有較高的生長率,穩(wěn)定而有規(guī)律的繁殖活動,以及較小的種子質量[14]。這些特征都有利于繁殖體的遷移與擴散。此外,有些植物的繁殖體進化出了適合附著于鳥類,或借助于水媒、風媒傳播的特性,有利于長距離遷徙[15]。
2.2 建群過程中的快速進化 外來個體在新環(huán)境中能否存活、能否成功繁殖并建立可維持的種群是該物種能否成功入侵的先決條件。外來種的引入通常伴隨著從源種群中的隨機抽樣,因而初始種群通常會經歷一段時間的小種群時期[16-17],因此在面對隨機波動的種群動態(tài)和環(huán)境變化時容易產生局部滅絕[18]。自交不親和的植物由于缺少合適的交配個體更難建群,而具有繁殖保障效應的單親繁殖(包括自交、無性繁殖和無融合生殖)能使小種群迅速增長,有效降低種群瓶頸持續(xù)時間,因而更容易受到選擇[19-20]。近些年已有部分研究開始關注生物入侵過程中繁育系統(tǒng)的進化改變[20-22]。在平滑網茅(Spartina alterniflora)、葉藍薊(Echium plantagineum)中,發(fā)現入侵地個體比原產地個體表現出了更強烈的自交親和性[23-24]。但這種異交向自交轉變的研究案例并不多見[25],這可能是由于自交過程中伴隨的近交衰退和遺傳多樣性的降低限制了物種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很多入侵物種是通過多次持續(xù)地引入繁殖體,增加初始種群的個體數量和遺傳多樣性,一方面能避免由于近交衰退和遺傳漂變帶來的滅絕風險[2,26],另一方面豐富的遺傳多樣性能進一步促進物種的擴散[27-28]。
2.3 擴散過程中的快速進化 成功入侵的外來種除了能在引入地建立可自我維持的種群外,還會擴散至初次引入地以外的區(qū)域。大面積的擴散使入侵種群面臨多變的地理環(huán)境帶來的選擇壓力[29]。在多變的環(huán)境條件下,入侵種有可能通過適應性的表型可塑性、適應性的遺傳分化、或二者共同作用以應對復雜的環(huán)境條件,從而達到成功存活和繁殖的目的[30]。適應性的表型可塑性是指植物通過沒有遺傳分化基礎的表型分化,在不同的環(huán)境條件下總是表現出最適合當地環(huán)境的表型性狀,從而保持較高的適合度[30]。適應性的遺傳分化則是通過表型性狀的遺傳分化適應不同的局域環(huán)境,從而表現出較高的適合度,達到成功拓殖的目的。良好的適應性對于入侵生物的成功擴散至關重要。很多成功入侵的物種在異質環(huán)境中擴散時都產生了表型性狀的適應性分化[31-33]。對于異交的物種來說,由于它們在長距離擴散時能保持較高的遺傳多樣性,因此在擴散過程中面臨不同的選擇壓力時通常被認為能產生適應性的進化改變,尤其是應對緯度梯度性變化的溫度、降水和季節(jié)性氣候環(huán)境時容易產生生活史性狀的適應性分化[20]。生活史性狀的緯度漸變性已在多個入侵植物中得到報道[32-35]。其中,開花時間的分化被認為在入侵種大范圍的擴張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36-37]。開花過早的植物個體可能會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源或合適的環(huán)境條件完成繁殖過程,而開花過晚的個體則有可能錯過利用所積累資源的最佳時間,而不能在生長季結束前完成繁殖,因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繁殖成功,最終影響入侵種的大范圍擴張[38]。
3 生物入侵機制研究對入侵物種防治措施的指導意義
生物入侵機制研究,尤其是生物入侵過程中快速進化研究,能為制定有效的生物防治措施提供重要的科學基礎。例如,入侵種的防治大都集中在新近發(fā)現的侵入種群,但這種措施并不能有效控制具有持續(xù)引入的入侵種。對于通過大的繁殖體壓力而成功入侵的物種來說,控制繁殖體進一步引入的路徑才是更有效的方法。其次,研究入侵成功的機制,能預測入侵物種的種群特點和空間結構,從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防治措施。此外,入侵過程中環(huán)境改變導致的進化改變,使得生物防控變得更加復雜。入侵種防御和生活史特征的進化,都會影響生物防控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