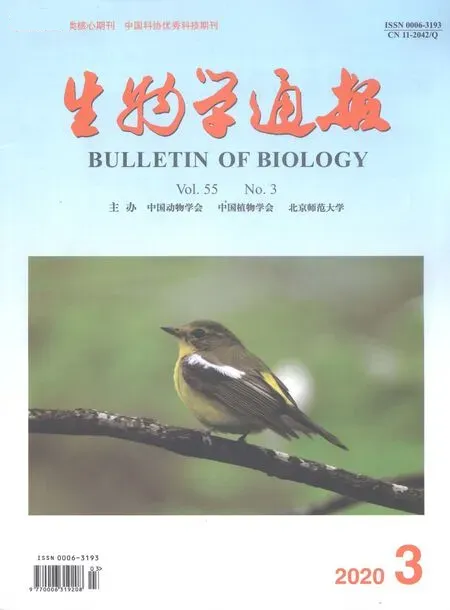低劑量的毒物對生物有益?
——比較毒物的單相劑量效應理論和雙相劑量效應理論(3)
朱欽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
(上接2020年第2 期第12 頁)
1.5 研究毒物雙劑量效應的意義 毒物雙相劑量效應Hormesis 和毒物線性無閾值劑量效應LNT 之間并不只是理論之爭,而具有非常重大的實際意義。
例如按照電離輻射的LNT 理論,任何劑量的電離輻射都是有害的,所以應最大限度地加以防止。這不僅導致有關防護措施的高成本,也在公眾中造成對電離輻射的恐懼心理。在蘇聯Chernobyl核事故發生后,估計有15 萬正常懷孕的婦女由于擔心生下畸形嬰兒而實行了人工流產。一些從事與放射性同位素有關工作的女性,也由于擔心生下有問題的孩子而不敢懷孕。而根據毒物的雙相劑量效應理論,低劑量的電離輻射不僅對生物體無害,還有促進健康的作用,因此不必“談輻射而色變”(見本文的第2 部分)。
對活性氧的LNT 理論也將活性氧看成是絕對的“壞東西”,因而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降低甚至“清除”體內的活性氧,即所謂的“抗氧化”。而按照毒物雙相劑量效應理論,低濃度的活性氧對身體有益,甚至是必須的。服用“抗氧化劑”不僅沒有好處,還會抵消體育鍛煉(增加體內活性氧的數量)帶來的有益效果(見本文的第3 部分)。
是盡量避免讓身體“受苦”(例如辛勞、饑餓、寒冷),過“豐衣足食”和清閑的“享福”生活,還是主動讓身體接受各種挑戰,也是養生中的大問題。
由于這些原因,無論是監管機構、醫療單位,還是個人,都應更多地了解毒物雙相劑量效應的理論和有關的實踐。在文章的第2 部分中,將詳細介紹電離輻射的雙相劑量效應。
2 電離輻射的雙相劑量效應
電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具有足夠的能量,能使電子脫離原子或分子,使原子和分子離子化,所以被稱為電離輻射,包括宇宙射線、γ-射線、X-射線、高能量紫外線,以及高速運動的粒子,例如α-粒子、電子(β-射線)、質子、中子等。低能量紫外線、可見光、紅外光、微波和無線電波,由于能量較低,不能使電子脫離原子或分子,不屬于電離輻射。
電離輻射可造成DNA 的損傷。按照LNT 理論,任何劑量的電離輻射都會造成DNA 的損傷,且損傷程度只與總劑量有關,而與劑量給與的方式無關(the total dose-and not the dose rate-was important)。但實際上,在總劑量相同的情況下,隨著電離輻射強度(單位時間內給與的劑量)的不同,對DNA 的損傷程度也不同。
1948年,美國科學家Warren Spencer 和Curt Stern 再次研究X-射線對雄性果蠅生殖細胞的影響,但使用的劑量范圍比Shultz 使用的更廣,從0.25 Gy 到40 Gy。他們發現,在此劑量范圍內,致命突變率也與劑量成正比,說明LNT 理論的適用范圍可低至0.25 Gy(250 mGy)。同年,美國科學家Ernst Caspari 和前面提到的Curt Stern 合作,研究γ-射線對果蠅生殖細胞的影響。他們使用的總劑量是0.525 Gy,與Spencer 和Stern 使用過的一個劑量(0.500 Gy)接近,但該劑量不是一次給與,而是分在21 d 中使用,因此每次的劑量只有1/21(25 mGy)。出乎Caspari 和Stern 意料的是,當將大致相同的總劑量分為21 次給與時,最后的突變率(0.0380%)只有一次性給與時的突變率(0.1466%)的1/4。
類似的結果也在小鼠實驗中被觀察到。1982年,美國科學家William Russell 及其同事用高強度(dose rate,每分鐘0.7~0.9 Gy,總劑量從3 Gy 到6.7 Gy)和低強度(每分鐘0.008 Gy,總劑量從0.4 Gy到8.6 Gy)的劑量照射小鼠,再觀察后代中7 個基因的突變情況。在這2 種情況下基因突變率都與劑量成正比,但是在同樣劑量下觀察到的突變率不同。2 條直線的斜率分別是7.32 和2.19,即用高強度照射時引起突變的幾率是用低強度照射時的3 倍。
這2 個結果都與LNT 理論的預期相沖突。按照LNT 理論,是總劑量決定效果的大小,將劑量一次性給與,或是分幾次給與,效果應該是一樣的。這就像開汽車,連續開2 h,還是分成2 次1 h,只要速度一樣,對機器的磨損應該是差不多的。這些看上去“異常”的結果意味著在生物體中,有修復DNA 損傷的機制存在,只要傷害的程度不太大,速度不太快,生物體是能修復一些損傷的。所以電離輻射的強度越小,最后造成的DNA 損傷程度也越小,盡管總的劑量是一樣的。這是對LNT 理論假設的,生物體只能被動地接受輻射傷害,沒有修復能力,所以損傷只會積累說法的有力挑戰。
但這些實驗所使用的最低總劑量(果蠅實驗中0.25 Gy,即250 mGy;小鼠實驗中0.4 Gy,即400 mGy),對于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劑量相比,還是太高了。多數人在一年之內受到的環境輻射劑量大約是2~3 mSv,如果輻射是X-射線或γ-射線,即相當于是2~3 mGy。一次胸部X-光檢查的劑量大約是0.25 mGy,乳房X-射線檢查(mammogram)的劑量大約是4 mGy,劑量最高的CT 掃描(X-射線),一次約為1~20 mGy,都遠低于上述動物實驗的最低劑量。
要評估這些低劑量輻射對人體的影響,靠動物實驗已經不現實了。由于低劑量輻射引起的突變率也很低,要得到有統計意義的結果,需要大量的實驗對象。在前面談及的動物實驗中,即使最低劑量仍然有數百mGy,使用的動物數量也是非常龐大的。0.0380%的突變率就需要至少5 000 只小鼠才能觀察到近2 個突變,因此被觀察統計過的果蠅數量以10 萬計;而在Russell 的小鼠實驗中,被觀察統計過的小鼠數目竟然超過100 萬。要觀察100 mGy 以下劑量對人體的影響,一個辦法是統計被高于本底輻射照射的人群中生理指標的改變。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研究。
2.1 原子彈爆炸引起的電離輻射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在日本的廣島(Hiroshima)和長崎(Nagasaki)投下原子彈。爆炸產生了強烈的電離輻射,爆炸瞬間產生的急性輻射劑量可根據離爆炸中心的距離計算。一些研究也用這個方法探討輻射劑量與癌癥等輻射引起的疾病之間的關系,例如美國科學院的電離輻射生物效應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BEIR)用這個方法研究的結果(稱為BEIR報告)表明,在高輻射劑量范圍內,癌癥發生率也和輻射劑量成線性關系,即支持LNT 模型,但是在低劑量范圍內,數值波動很大。雖然BEIR 報告和其他一些研究報告承認在100 mGy 以下沒有具統計意義的結果支持LNT 模型,研究者仍然認為任何電離輻射都是有害的,在低劑量范圍內線性關系仍然存在,可從高劑量區域得到的直線延伸至低劑量范圍內,并且由此計算出單位輻射量所引起的癌癥發生率的增加值。
但是一次性的高劑量急性輻射的生理效果,和長期持續的低劑量輻射的效果畢竟不同。原子彈爆炸產生的不僅有爆炸瞬間的急性輻射,還有爆炸產生的放射性沉降物發出的較低劑量的、較長期的輻射。急性輻射的強度隨著離爆炸中心的距離增加而迅速衰減,影響的人數比較有限。而放射性沉降物擴散的范圍要大得多,影響的人數也更多,有60 多萬,持續時間也更長,更接近于人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電離輻射,因而是研究低劑量電離輻射對人體影響的更有價值的材料。
例如聯合國電離輻射科學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UNSCEAR)在195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廣島的幸存者中,在零輻射(即沒有高于本底輻射的對照組)時,白血病的發病率為28/100000,在接受到中等劑量輻射(500 mSv)的人群中,白血病發病率增加到4/10000,說明中等強度的電離輻射的確能引起白血病。但是在受到低劑量輻射(20 mSv)的人群中,白血病的發病率卻只有8/100000,遠低于對照組。
類似的低谷也在其他類型的癌癥發生率中被發現。例如1988年,日本近畿大學(Kinki University)核能研究所的Sohei Kondo 發現,長崎的幸存者在1948—1987年的癌癥發生率中,白血病、直腸癌、乳癌和肺癌的輻射劑量-發病率曲線中都有一個低谷,劑量大約在60~70 mGy 區間。
這些結果說明,在低劑量范圍內,輻射與癌癥發生率的關系不再符合LNT 理論,而是有一個低谷。在這個低谷內,少量的電離輻射可降低癌癥的發生率。
除了癌癥發生率,Kondo 還發現,原子彈爆炸幸存者的孩子中,也沒有觀察到輻射的不利影響,包括死產、先天性身體缺陷、在出生后1 周內死亡、17 歲之前的死亡率、染色體異常等。但如果胎兒在子宮內受到100 mGy 或更高劑量的照射,17 歲時智障發生率會增加。
另一項由日本科學家進行的研究表明,在75 237 名幸存者的兒童中,盡管其父母平均接受到264 mGy 的輻射,這些兒童在62年后也沒有表現出任何不良的影響。
多項研究表明,幸存者的癌癥死亡率低于日本平均癌癥死亡率。即使按照一些LNT 理論計算認為在低劑量范圍內癌癥發生率增加的文章(1958—1994年癌癥發生率),在小于100 mSv 劑量的范圍內,癌癥發生率并未上升,或許還有輕微下降(零劑量時癌癥發生率為13.7%,3230/23493;劑量小于5 mGy 時發生率為12.8%,1301/10159;劑量5~100 mSv 時發生率13.5%,4119/30524)。只有劑量超過100 mGy 時,癌癥發生率才開始上升。
這些結果都不支持低劑量(小于100 mGy)范圍內LNT 理論的適用價值,而傾向于支持輻射的雙相劑量效應。
2.2 核事故造成的高電離輻射 核電廠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泄漏主要有4 次,分別是1957年英國的溫士蓋(Windscale)事故,1979年美國的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事故,1986年蘇聯(現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事故,以及2011年發生于日本福島(Fukushima Duiichi)的事故,其中以Chernobyl 事故造成的核泄漏最為嚴重。
1986年4月25日,蘇聯Chernobyl 核電廠第4號核反應堆發生蒸汽爆炸,使大量輻射物釋放到空氣中,并且隨風擴散至西北方向的大范圍地區,包括現在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丹麥、瑞典、挪威等歐洲國家。
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署2005年的一份報告(Chernobyl Forum 2005,Chernobyl’s Legacy,Health,Environmental and Social-Economical Impacts,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Vienna)說,在受到急性照射(劑量2~20 Gy)的大約1 000 名人員中,237 人得急性輻射病,其中31 人在3 個月內死亡,14 人因輻射導致的癌癥在隨后的10年中死亡,充分說明高劑量輻射對人的危害。
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3 國污染地區(平均接收劑量50 mSv) 約500 萬人癌癥發生率的研究表明,事發時0~14 歲的兒童由于攝入被碘-131 污染的牛奶而表現出甲狀腺癌發生率的增加(總數約為4 000 例)。碘-131 進入人體后,會濃集在甲狀腺中,極大增加局部照射強度。例如在烏克蘭,甲狀腺受到的平均劑量是770 mSv,在白俄羅斯是560 mSv,和體外電磁輻射平均照射的情形不同,這也許是甲狀腺癌發生率增加的原因。而在平均50 mGy 的劑量下,其他癌癥的發生率并沒有增加。
瑞典是最先發現核泄漏的國家。瑞典9 個縣,220 萬人的數據表明,在事故第1年中,由于銫-137 的污染引起的輻射劑量為3.6 mGy。將事故發生前(1980—1985年)和事故發生20 多年后(1986—2009年)的癌癥發生率進行比較,沒有發現癌癥發生率增加。
也有報告說,Chernobyl 事故中8 600 名清除污染的工人,各種癌癥的總發生率比前蘇聯的平均癌癥發生率低12%。
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引起的海嘯造成日本福島核電廠冷卻水泵失靈,使3 個反應堆溫度失控而融化,進而發生氫氣爆炸,導致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總量約為Chernobyl 泄漏的10%~40%,污染區域面積為Chernobyl 的10%~12%。事故發生后4 個月內,在附近的421 394 名居民中,99.4%的居民受到的輻射劑量小于3 mSv。這個劑量低于許多高自然輻射地區的水平,而這些高輻射地區的居民并沒有表現出任何不良影響(見下文)。感染區99%的0~14 歲的兒童甲狀腺受到的平均劑量為15 mSv,遠低于Chernobyl 兒童受到的劑量(560~770 mSv)。5年后,對200 476 名18 歲及以下的人員甲狀腺癌癥的檢查表明,沒有證據表明這次事故增加了其發生率。從養老院撤退的人的死亡率是不撤退的2.7 倍,說明心理恐慌造成的不利影響超過輻射本身。
在三哩島事件中,5 英里范圍內的輻射劑量不超過0.25 mSv,遠小于美國每年約3 mSv 的平均本底輻射劑量,這個區域內的人癌癥發生率也和區域外的人沒有區別。
英國溫士蓋核電廠反應堆火災釋放的碘-131是Chernobyl 釋放的1/2 378,銫-137 釋放 量是Chernobyl 的1/3 614。根據一項2010年的研究結果,清除污染的工人在隨后的53年中并沒有表現任何對身體不良的影響。
這些結果表明,大劑量的電離輻射(>1 Gy)會導致急性輻射病,而低于100 mGy 的均勻輻射并不會增加癌癥的發生率,甚至有可能降低發生率。
2.3 臺灣建筑材料污染事件 1982年,在臺灣省的臺北市,被鈷-60 污染的鋼材被用于建造180多棟樓房,包括大約1 700 個單元。從1983年開始,大約10 000 人搬進了這些住宅。由于污染事件于1992年才被揭露,這些居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照射了至少9年。從1983—2003年,居民受到的平均照射劑量為每年15 mGy,是臺北其他地區輻射量的10 倍左右。
2006年臺灣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受影響的大約10 000 人中,年癌癥死亡率為0.0035%,遠低于對照組的0.116%,即只有對照組的3%。先天性畸形的發生率而也只有對照組的6.5%。
據2006年臺灣的另一項研究,在7 241 個受到輻射影響的對象中,總癌癥發生率也降低(95例,根據對照組計算的“預期值”為160 例),只有白血病有升高的跡象(7 例,“預期值”3.3 例)。
2.4 自然環境中的高輻射地區 在有些地區的自然環境中,由于所含的放射性同位素較多,表現出高于其他地區的輻射水平,例如我國廣東的陽江地區(年輻射劑量6.4 mSv)、巴西的卡拉帕里(Guarapari)地區(年高劑量約131 mGy)、印度喀拉拉海岸(Kerala coast,年高劑量約70 mGy)、伊朗拉姆撒爾地區(Ramsar,年高劑量約260 mGy)等。
根據已有的研究報告,在所有這4 個地區中,都沒有發現癌癥發生率和輻射劑量的關系,說明這些劑量的電離輻射并不會對人的健康造成不利影響。
例如在我國的陽江地區,由于含有放射性元素鐳-226、鐳-228、釷-232、鈾-238 的孤獨石(monazite)的沉積,在540 km2的范圍內平均年輻射劑量為6.4 mGy,大約3 倍于10 km 外的本底輻射水平(2.3 mGy)。約125 000 人生活在該地區,90%以上生活了6 代以上。
對高輻射區的73 000 名居民和對照區的77 000 名居民的研究表明,癌癥發生率、染色體異常情況及婦女的流產率,在高輻射地區和對照地區沒有差別。31 種遺傳病和先天畸形率在高輻射地區還略有降低。高輻射地區居民中與癌癥密切相關的2 種蛋白,晚期糖基化終產物受體(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RAGE)和S100A6 都明顯降低。
另一項研究累計隨訪了125 079 人,發現1979—2002年,高本底輻射地區癌癥死亡率并不高于對照地區。中日聯合研究也未發現高輻射地區染色體畸變增加。
還有研究表明,在高輻射地區,人體內的過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等“抗氧化酶”的水平增高。由于電離輻射除了直接傷害分子結構外,還在體內(主要是通過水分子)產生大量的活性氧物質,這些對抗活性氧的酶水平的增高可看成是身體對高本底輻射環境的一種適應性反應。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