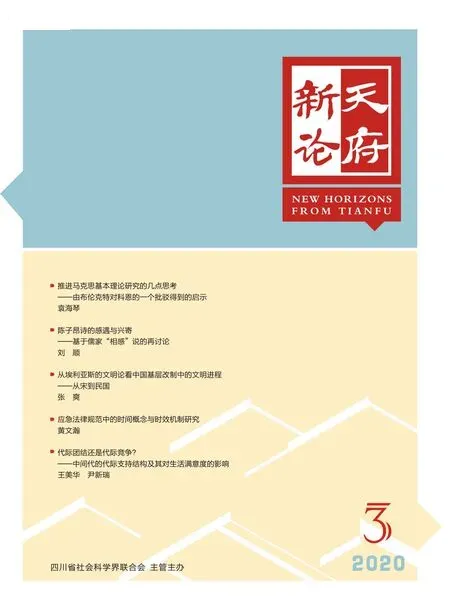“日常生活”離“現實”有多遠?
——李子柒短視頻中的田園幻象
李 昕
短視頻的發展與傳播在當下正如火如荼。根據時長,短視頻通常以時長約15秒的“抖音”和時長在4~12分鐘的vlog為代表;vlog,又稱video blog,是指以影像的形式進行故事敘述,以記錄、反映“日常生活”為內容制作重點,同時形成自己的主題與風格的一種類型的短視頻。當前,頗受大眾關注的李子柒短視頻便屬于vlog。它以“田園古風”為特點,在vlog中獨樹一幟,吸引了大量的關注者。由此,李子柒也成了“網紅”,并被《中國新聞周刊》評為“2019年度文化傳播人物”;她的作品在大眾視野和官方話語體系中均得到了認可,而這對于作為大眾文化工業之產品的短視頻而言似乎是意外而矛盾的。
李子柒短視頻的主題是古風田園生活,它展現了鄉村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同時涉及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節日、節氣以及與之相關的民俗文化。支持李子柒的人認為,她的古風短視頻再現了古典田園生活的美好,也為鄉村生活提供了發展的可能性和審美想象空間;而質疑者則認為,李子柒的短視頻不過是滿足了城市中產階級對于農村生活的想象,與此同時,也是對于真實農村生活的掩蓋乃至抹殺。
這些爭論無形中暴露出了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對于李子柒短視頻中“日常生活”之真實性的不同認識,而這些分歧背后所潛在的問題,實則就是大眾對于城鄉關系等現實狀況的認知錯位。鑒于此,本文嘗試從李子柒短視頻所展現的“日常生活”切入,分析其所契合的大眾情感意識,并分析隱藏在社會情感背后的以城鄉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階層之分異,從而揭示這種城鄉情感結構的裂隙,也就是李子柒短視頻所記錄的“日常生活”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一、田園生活之“現場感”:制造“日常生活”的幻覺
李子柒短視頻所展現的田園生活,具有鮮明的“現場感”。這種“現場感”以時間和空間兩種坐標為支撐,由日常勞動填充,以此構建起短視頻中古風田園生活的“現實”敘事。
首先,在短視頻中,就時間和空間兩方面而言,通過對于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細節的再現,李子柒的日常生活呈現出了一種田園生活所特有的秩序。在時間上,李子柒的生活節奏依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經常于晨光熹微時分在鳥鳴中醒來,用山泉水洗漱后,便開始一天的勞動;于暮色四合之際結束辛勞,與奶奶(也就是視頻中的婆婆)一起吃過親手烹飪的美食后,生活在夜色中歸于平靜。在空間上,李子柒和奶奶一同生活在四川綿陽的鄉下,空氣清新、環境自然,與土地為伴,是一處遠離現代都市的“世外桃源”。
李子柒短視頻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食、工藝與節日、民俗結合在一起,通過一系列手作活動來完成屬于“農業社會”的節日儀式感。例如,她在七夕節制作乞巧果,在中秋節手工制作月餅,在端午節佩戴親手編織的五彩繩,又于重陽節探究節日的歷史起源,并做應景的重陽糕吃;而在美食制作上,也順應了自然時節的變化,初春適逢桃花盛開,李子柒便以桃花制酒,用桃膠做甜品,初夏又是櫻桃成熟時,李子柒便用櫻桃制成果醬和蜜餞。與此同時,對于具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她也掌握了制作方法,比如將刀削面、牛肉拉面乃至馬奶酒的制作過程都一一呈現;而她在美食制作中所使用的種種器物,例如鍋碗瓢盆等都是鄉村生活中所特有的,其中的大部分早已被現代都市淘汰或淡忘。心靈手巧的她不僅擅長女工,掌握了蜀繡工藝,還學會了如何制作文房四寶;而通過搭秋千架、用竹子制作竹床、建面包窯以及進行木刻與活字印刷等手工工藝活動,李子柒不斷展示出她出色的動手能力和匠心獨運的創作能力。
由此可見,李子柒短視頻的內容生產所依托的是一種屬于鄉村或屬于“鄉土社會”的資源。正如王曉明教授所言: “今天來講鄉村的優長,勢必有一部分,是并非指向現實,而取自過去的狀況。”(1)王曉明:《“城鄉結合度”:一個新的社會進步指標》,《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當下,城市化發展對農村傳統生活的侵蝕,農村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打工所帶來的農村勞動力不足、土地荒廢、留守兒童等現實問題,都說明中國農村面臨一些危機。而與此同時,農村的“前現代”狀況也得以保留,繼承了“過去”的兩個基本形態——“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臥于山河田野之間,保持著深嵌于自然世界的歸屬感,至少不會如玻璃墻面的都市高樓那樣,令人以為可以完全存活于人造世界。其二,若干在長期自耕農式的生活中養成的精神遺傳:從容而模糊的時間感、自食其力的生活態度、對熟人群體的親近習慣,以及對許多‘界限’的缺乏敏感……也以日趨破碎的形態,繼續存活于鄉人的言行舉止中。”(2)王曉明:《“城鄉結合度”:一個新的社會進步指標》,《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而李子柒短視頻的內容生產,所依賴的鄉村資源,也正是取之于這兩種基本形態。
無論是對于節日和節氣的重視,還是對于民俗文化的展示,這些與田園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聯系起來,所呈現的都是一種遠離都市的、屬于農業社會的儀式感;而短視頻中“奶奶”的在場,則通過參與李子柒日常生活來增強這種“生活正在發生”的“現場感”,并為這種生活賦予內在的情感聯系,由此給予觀眾和粉絲一種“真實感”。與此同時,這種“真實感”屬于“隱逸式”的“田園”,而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如果說后者給人的印象標簽是“艱辛”,那么,前者所強調的則是一種“美感”。
在短視頻中,李子柒進行勞作和烹飪等農活的時候,一般都是以略施粉黛、穿著古樸而不失仙氣的形象出現,因此,許多觀眾也在評論中稱她為“仙女姐姐”,這種自然的“仙女氣質”與觀眾日常經驗中對于勞動和做飯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很不一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炒個菜就油煙四起,即使偶爾去郊區進行采摘活動,也會擔心被泥土弄臟衣服;而李子柒的過人之處恰恰在于,她在勞作中,完全沒有新世紀豌豆公主式矯情的小心翼翼,在短視頻的呈現中,她看起來十分享受這種自然、質樸、事必躬親的生活。無論是下田野還是進廚房,李子柒儼然把“柴米油鹽”的瑣碎生活過出了“琴棋書畫”的盎然詩意,這也正是她的短視頻對于許多觀眾的吸引力所在。
除了因循自然的生活作息節奏之外,李子柒在短視頻中所展現出的勞動能力也令觀眾驚羨。在短視頻中,李子柒的日常生活,似乎都是靠勞動建立起來的,她手起刀落、颯爽干練的日常生活技能,無疑營造出一種“現實感”,進而編織出一個鄉村田園日常生活之“現實”。比如,在烹制美食時,從原料采摘到制成成品,都是親自動手;搭建烤爐、駕馭水牛、編織手鏈等,無論是粗重農活還是手工細活,她都一一拿下,干練利索,毫不拖泥帶水,并且不失優雅。這種“勞動”,看似是回歸到最本質意義上的勞動:與都市生活中早已被商品化、符號化的“勞動”相比,李子柒的“躬耕”式勞動建立起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然感,同時也傳遞出一種“正在發生”的“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之田園“現場感”。
這種呈現“勞動”的方式,是將之與自然、土地、田園等元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帶著一種天然的“靈暈”,并喚起觀眾對于古早“勞動”的記憶,而這種“勞動”如今在城市生活中早已被邊緣化;更重要的是,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勞動”總是與“辛苦”、“塵土”、“汗水”等標簽聯系在一起,但是,李子柒短視頻中的勞動,雖然也不乏體力上的辛苦,傳遞給觀眾的卻更多是一種美感。這種美感充斥于李子柒短視頻中的田園日常生活,通過“鄉村美景”、“古典美人”、“精致美食”等元素體現出來。無論是世外桃源般的田園美景,抑或粗服亂頭卻也不掩國色、樸實優雅地周轉于農活和手工中的李子柒,還是擷英采華、用花果制成的應季美食,這些與衣食住行相關的行為活動,組成了李子柒的日常生活,傳遞出的信息都是,即使是繁冗瑣碎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是舉重若輕的,可以在具有實踐效果的同時,也蘊含著審美意義。
與此同時,攝影技術無疑也為這種詩意效果提供了支持。因為時間有限(短視頻大多在4~12分鐘),為了視覺效果,視頻在畫面呈現上也必須有所取舍。在拍攝技術上,短視頻采用了電影蒙太奇手法,將幾個鏡頭拼接起來,用以呈現在現實中需要幾小時甚至幾天方能完成的勞動。例如在拍攝搭建烤爐時,只是最開始展示幾個搭建爐子的動作,轉而過渡至已經搭建完成的實物。在此,真正的日常生活被壓縮為幾個畫面,開始與結果之間只需要短短幾秒,其余的留給觀眾去自行想象,或者說連想象的必要也沒有,由此構建出一種看似閑庭信步的節奏與悠閑自得的享受,實則這一切都是精心設計好的場景展示:日常生活中真切的辛苦不會被展現,而只有詩意化的勞作才有意義。
李子柒短視頻中所呈現的“勞動”,已成為一種塑造個人魅力的方式,一種滿足大眾審美需求的產品,一種提供田園日常生活之“真實感”的消費能指,一種用“現場感”來建構“現實”的手段。正如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所說, “它與其說是根據它滿足、愉悅生產者和創造者的道義上的、普羅米修斯似的職責的能力,還不如說是根據它滿足消費者、感覺的追求者和體驗的集成者的美的需要和渴望的能力來測度和評價的。”(3)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36頁。在此,勞動不再服務于某種共同體的當下與未來,而是成為僅屬于個體的樸素狂歡。
這種具有美感的世外桃源般的田園生活,與當下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形成鮮明對比,而李子柒短視頻對于生活在城市的、具有中產階級審美趣味的觀眾而言,確實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對于常年過著“朝九晚五”甚至“996”生活的上班族而言,生活節奏大多是以地鐵時間、堵車時長、交通高峰節點劃分,晚上下班后大多是吃完外賣躺平刷手機。因此,李子柒短視頻中的美好而詩意的古風生活,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上班族、白領以及都市中產的一劑“治標不治本”的安慰劑,看似隨心所欲的田園生活戳中這一代脫離了土地但又有直接或間接的鄉村生活經驗的人的集體記憶之軟肋,給經常處于“996”工作狀態的都市人提供了一絲懷舊與想象的空間。都市生活中的疲憊、焦慮甚至絕望,投射于鄉村生活中,便是一種逃離的企圖與懷舊的想象。
李子柒短視頻中呈現的古風田園生活之魅力也正在于此。它以“日常生活”的形式來進行一種具有“現場感”的敘事,因其具有“現場感”而進一步獲得“現實”之名。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日常生活的本質特征是“重復”與“習慣”。在此基礎上,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進一步指出:“日常生活與下述各類循環交替無法分割:重復、日與夜、播種與收割、工作與節慶、蘇醒與睡眠、生理需要與滿足。”(4)喬納森·克拉里:《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許多、沈清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3頁。而李子柒短視頻中的生活節奏,呼應了城市人對于真正的、尚未被異化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而觀眾對于李子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頗具前現代生活方式的追求,與其說是對農村或鄉村田園生活的向往,毋寧說是對于資本邏輯之于私人生活的入侵與規訓的無奈和厭倦。
二、作為“幻象空間”的古風田園:社會欲望的“現實”投射
對于“世外桃源”和“山水田園”的向往,古已有之,多是文人士子因為厭惡紅塵俗事和官場污濁而選擇歸隱田園。也就是說,田園與鄉村,在古人的眼里代表著簡單、自然、淳樸、自由,況且農業社會本就以農耕為主,因此,在古代,回歸鄉村意味著一種返璞歸真。隨著現代城市的興起,鄉村在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漸發生了變化,而在中國社會中,城鄉之間的關系也歷經了種種變遷,即從二元對立到彼此共存。城鄉之間的界限并非是一直清晰而分明的,種種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的出現打破了城鄉之間的界限,因此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問題,都無法脫離彼此來說明或解決。正如上海大學王曉明教授曾就此提出,要用“城鄉結合度”(5)王曉明:《“城鄉結合度”:一個新的社會進步指標》,《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來表示城鄉共存的現狀。隨著城鄉關系的變化,出現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而基于身份、背景、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別,不同階層的人們在城鄉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因而他們對于城鄉以及城鄉關系的認知也各異。與之相應,當下人們對于“鄉村”的情感投射,不僅與古代農業社會時期相比,早已發生了變化,而不同階層之間,亦有分裂。
具體到李子柒短視頻所呈現出來的鄉村田園生活而言,觀眾訴諸其中的爭論,也表現出了人們對于鄉村認識的錯位與對城鄉關系認知的分歧。例如,網絡上圍繞李子柒短視頻所產生的爭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討論“李子柒短視頻所展現的到底是不是真實的農村生活”,而這一爭論則折射出了當下中國不同階層與不同身份者對于農村生活認識的差異,并反映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城鄉之間所潛在的情感裂隙。
當下中國面臨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轉型。但是,鄉土社會仍是當下中國社會的底色,即使在城市化趨勢勢不可擋的今天。對于中國社會而言,鄉土記憶依舊是一種集體記憶。在許多人的個人記憶里,鄉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學者潘家恩先生指出,“雖然當下中國的城鎮常住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但鄉土依然是中國社會的底色,流動于城鄉之間的不僅有數億民工及其家人,還包括大量‘鄉生城長’的‘農二代’及雖然在城市出生并長大,但父輩或祖輩有著鄉村背景與親屬網絡的‘農N代’”(6)潘家恩:《城鄉中國的情感結構——返鄉書寫的興起、衍變與張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7期。,在這種情況下,依托鄉土資源進行內容生產的李子柒短視頻,被許多觀眾評價為“接地氣”的作品,而所謂“接地氣”,實則是喚起了觀眾的某種個人記憶,即使是對大部分生活、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而言,這些記憶或彌漫童年,或籠罩半生。雖然每個個體對于鄉村的記憶是不同的,但是,屬于每個人的記憶卻都深受集體文化的影響。正如揚·阿斯曼(Jan Assmann)在對個體記憶與集體文化之關系的闡述中所提到的:“雖然集體不能‘擁有’記憶,但是它決定了其成員的記憶,即便是最私人的回憶也只能產生于社會團體內部的交流與互動。”(7)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8頁。而在觀看李子柒短視頻時,這些受集體文化所影響的個人記憶被喚醒,視頻中的鄉村景象、田園生活,看起來是如此熟悉,并在追溯記憶的過程中沾染上一層靈暈,因而顯得愈發真實,使得被城市生活中的壓力和焦慮包圍的人們,得到一種短暫的想象性滿足。
而當有網友質疑李子柒短視頻中的鄉村生活“并不是真正的農村生活”時,有人認為,現實中的農村生活遠非如此,如果想要了解真正的農村生活,不如親自去農村住上一段時間。這一觀點遭到李子柒短視頻擁躉的反駁:“為什么有人就是見不得美好的農村生活呢?為什么農村生活就不能是美好的呢?”一方面,這些觀點認為,李子柒短視頻中的農村生活是存在于現實中的,農村生活的確可以像短視頻中所呈現的這樣美好;另一方面,這些觀點尚未言明的潛臺詞即為:即使我知道農村生活或許并非如此,但我依然愿意接受并欣賞這樣的農村生活,因為它是美的。更有甚者認為,為什么對李子柒的短視頻在報以如此密切關注的同時,不能稍微“寬容”一些,即使是就“網紅”層面的意義而言,李子柒和其他的以“生活方式”為分享主題的博主又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別呢,只不過她所分享的是鄉村田園生活,所以就受到諸多非議嗎?問題的癥結之一正在于此。李子柒短視頻的“鄉村田園生活”主題,恰恰擊中了當下中國城鄉問題中的晦暗不明且多面的部分,其所引起的爭議,也直指當下中國城鄉情感結構的裂隙。“情感結構是描述某一特定時代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普遍感受,其中飽含著人們共享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8)趙國新:《情感結構》,《外國文學》2002年第5期。, 因此,人們對于李子柒短視頻所呈現的田園生活的爭議,正是懷舊、焦慮等欲望和心理的投射,這種情感結構反映了一種社會經驗。雖然這些爭議往往被認為是個體性的私人經驗,但實則不然,這些經驗其實是社會性的,其背后所隱含的社會性問題,即在城鄉關系轉型之際,我們該如何定義鄉村的“現實”,而所謂的“現實”敘事,對于不同身份和階層的人而言,是否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呢?
如前所述,李子柒的短視頻在某種程度上喚起了人們的集體記憶,尤其是擁有直接或間接的鄉村生活經驗的人,許多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人,以及農二代甚至農N代,都由李子柒短視頻而再次生發對于童年的懷念,甚至有人認為,自己童年所經歷的農村生活正是如此,將這種古風田園生活視為“現實”的一部分。經由短視頻中的視覺生產與再現,使得短視頻觀眾對于“現實”或“真實”的認識產生了錯位。由此可見,短視頻中的視覺呈現,已然參與到了當下人們的記憶重構中,進而以“反映現實”之名重新書寫、建構現實。在此,大眾所經歷的“真實”的農村生活無從考證,而唯有在當下回溯過去而產生的幻覺以及對“真實”的誤認,構成了或許并不存在,卻在記憶和當下大眾文化產品所產生的縫隙中熠熠閃光的“現實”。
從圖像敘事中所謂的“有圖有真相”到以反映“現實”中的“日常生活”為名的短視頻,其背后所隱含的大眾文化與視覺形象之間的關系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大眾文化表征實踐在引導消費者選擇文化產品并獲得意義/快感的過程中,對視覺形象日益強化的依賴感。而這種依賴感,又是以視覺形象被剝奪自覺的反思意識為前提的。”(9)周憲:《當代中國的視覺文化研究》,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81頁。短視頻所展現出來的“現場感”,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消費主義引導下的對田園生活的想象。
由此可見,李子柒短視頻所建構起的古風田園生活,與其說是一種“現實”,毋寧說是一種“現實感”(sense of reality),是一種齊澤克(Slavoj ?i?ek)所言的“幻象空間”(fantasy space)。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展示,視頻營造出的田園生活滿足了觀眾對于古風閑適生活的想象,觀眾從中看到了自己對于日常生活的希冀、對于自然鄉村的追求以及對于快節奏都市生活的一種逃離,在此,觀眾的欲望在這一“幻象空間”中被展示出來。一直以來,質疑者對于李子柒短視頻的詬病在于,這種鄉村生活的展示只是一種美化后的鄉村面貌,而大部分農村生活,遠遠不是這樣的清新美好。農村生活中的簡單粗糙在此蒙上了一層精致的濾鏡,而農村生活的辛酸艱苦在這種展示中被虛化,這固然是李子柒視頻的一部分問題。但是,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李子柒短視頻的內容生產以“鄉村生活”、“鄉土社會”為依托,而當下,關于“鄉村生活”的敘事,僅僅只圍繞“鄉村”本身是無法解決的。“鄉村生活”與城市生活的邊界早已不再明晰,而“鄉土社會”當下也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城鄉結合”的社會現狀,而關于“鄉村生活”的認知、情感等,也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社會審美的區隔等產生錯位。
所以,李子柒短視頻所呈現的“田園生活”,并不是對“現實”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對現實所做的一種“反應”(reaction)。這種“反應”暴露出了觀眾的欲望。正如李子柒的經紀人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所言:“中國人都有山水田園夢,這也是她的夢,李子柒的成功是因為她把這樣一個夢呈現給大家。”(10)詳見《中國新聞周刊》官網:http://www.inewsweek.cn/people/2019-06-03/5958.shtml。視頻中的鄉村,并不是真實的鄉村,而是一個古風田園的幻象空間,滿足觀眾的山水田園夢,而在這個“夢”中,可以窺見這種投射于理想中的鄉村的社會情感與欲望。
三、“日常生活”與“現實”的距離
李子柒所打造出的田園生活,至多只能作為個人生活的田園詩,而難以作為屬于整個社會之理想前景的美好圖景;這種所呈現的田園生活,看似是一種存在于日常中的“現實”,但實際上,這種生活方式是難以被普遍社會化的。在短視頻中,除了李子柒,主要人物還有一位老人,也就是李子柒的婆婆(奶奶),以及偶爾映入畫面的名叫“民國”的樸實助手。奶奶在視頻中的存在,擔任著一位“他者”的角色:李子柒將在鄉間采摘來的花朵戴在奶奶的頭發上,新出爐的美食則往往讓奶奶品嘗,視頻中田園生活的每一天幾乎都在與奶奶共同享用美食中結束……這位鄉村老人的出現,不僅給整個短視頻增添了一絲溫馨的氣氛,營造出了一種“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世外桃源般的意境與古早的人情味;更重要的是,奶奶以一種遠離都市生活、日常生活在鄉村、講方言的老者形象,強化了短視頻中的“現實感”,以此佐證李子柒短視頻中所呈現的日常生活是一種“現實”。
鮑曼在談及隨著現代性的到來而產生的“個體化”模式及其問題時曾指出何為“個體化”,即“人們身份(identity)從‘承受者’(given)到‘責任者’(task)的轉型和使行動者承擔完成任務的責任,并對他們行為的后果(也就是副作用)負責”(11)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0頁,第74頁,第74頁。。換言之,在現代社會中,個體的確擁有選擇某種生活方式的權利。與此同時,如果個體沒有過上一種名副其實的美好生活,那么,這一原因也將歸咎于個體;而所謂的美好生活,卻早已被根據階層衍生而來的社會類型和行為模式所限制。
但是,“個體化”所存在的問題是:“在個體選擇的空間里,逃避個體化和參與個體化游戲的選擇,明顯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12)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0頁,第74頁,第74頁。。也就是說,作為個體有權利去追求某種集體和大眾之外的生活方式,而如果個體在追尋這種生活方式時沒有達到某種預期的或特定的效果,那么背后的原因,也一定出現在個體身上。正如鮑曼的舉例:“如果他們病了,便推斷說,這是因為他們在現行的社會保障體制下,不是足夠堅強和勤勞;如果他們處于失業狀態,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面試技巧,或是因為他們在尋找工作時不夠努力,或者不折不扣是因為他們羞于工作。”(13)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0頁,第74頁,第74頁。圍繞李子柒短視頻中的田園生活而產生的爭議所折射出的社會問題癥結正在于此。的確,李子柒有追求田園生活的權利,也可以選擇自己意圖在短視頻中所展示的形象和所呈現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這種美好的田園生活被關注者和輿論視為一種理想的、可以實現的鄉村生活,就會遮蔽鄉村生活中貧困、凋敝和衰敗的一面,同時也會產生這樣一種錯覺:這種農村生活的確是“真實”存在的、是一種“現實”。如果你認為農村生活不會是李子柒短視頻中所展示出來的樣子,那是你自己的偏見,而不是農村本身的問題。要么是因為你持有一種農村生活就應該是愚昧落后的刻板印象,要么是你站在城市中心主義的角度鼓吹城鄉二元對立而見不得農村生活有美好的可能性。這些錯覺恰恰表明了鮑曼所言的“社會生活仍然在制造風險和矛盾;正是應付處理這些風險和矛盾的義務的必要性,正在被個體化”(14)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4頁。。
值得注意的是,與李子柒短視頻同時涌現的短視頻中,也有大量以農村生活為主題的,但是與李子柒短視頻被視為“田園古風”甚至農村新形象不同,這些短視頻大多數被貼上了“土味”的標簽:短視頻平臺“快手”上有大量農民自己拍攝的短視頻,通過生吃蛇、狂喝白酒和跳冰河等獵奇甚至是自虐的方式來博取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農村社會經濟和倫理生活中的問題。對于農村生活的反映,李子柒短視頻和這類“土味”視頻中的“農村”可謂是天壤之別,二者之間的差異不只是因為反映了農村生活的不同面向而產生的。更重要的是,當受眾為李子柒短視頻所吸引、沉迷于觀賞視頻中亦真亦幻的“田園生活”時,即使大部分具有農村生活經驗的觀眾明知現實生活中的農村遠非如此,農民形象更是與之大相徑庭,但是觀眾還是愿意去接受、喜愛并支持這一風格的農村生活短視頻。在此,觀眾所關注的不是屬于情境層面上的事實,而是構成“現實”的“幻覺”。大部分人都知道農村生活的艱辛,但是當他們把這一美好的古風田園視為農村生活之現實反映的時候,他們表現得好像是自己不知道農村生活的這一面。引人思考的是我們不是不知道短視頻中的“現實”是刻意理想化的,而是我們明知如此,卻仍愿意接受、欣賞甚至與之一同陷入歡愉,而與此同時,還認為自己不會因為一個短視頻就忘記農村生活的真實。
李子柒短視頻中的古風田園所打造的“幻象空間”,滿足了人們一直以來所追求的“山水田園夢”,正是因為現實中,真實的鄉村生活無法滿足人們對于山水田園的期待,所以,觀眾才可以在觀看短視頻的過程中做做夢,通過將“夢境”誤認為“現實”,以此來逃避那些無法被反映為“現實”的真實情況。
隨著李子柒短視頻的關注者越來越多,李子柒也進入官方輿論的視野之中。2019年8月,經成都文化旅游局的授權和認證,李子柒成為首位四川成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大使,并且因為她的古風田園短視頻在海外視頻網站YouTube上也吸引了眾多粉絲,因而引發了關于李子柒短視頻是不是“文化輸出”的討論。隨后,李子柒獲得官方文化話語的認可,《中國新聞周刊》授予李子柒“2019年度文化傳播人物”,認為她“把中國人傳統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呈現出來,讓現代都市人找到一種心靈的歸屬感,也讓世界理解了一種生活著的中國文化。”(15)詳見:https://ent.sina.com.cn/s/m/2019-12-28/doc-iihnzhfz8940708.shtml。李子柒短視頻在海外的有效傳播,實則是個體敘事借助短視頻媒介所產生的影響力,趁著全球化的東風,又依托于現代性所造成的種種際遇與困境下所產生的社會意識,產生的一種跨文化傳播效果。而整個事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耐人尋味。
李子柒短視頻在并未加上英文翻譯的情況下,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網友。視頻中所展現的田園美景、古典美人和中華傳統美食等,都契合了海外對于中華文化的想象。有外國網友將李子柒稱為“田園精靈”,這與中國網友在短視頻彈幕中稱李子柒為“神仙姐姐”是異曲同工的,這種評論所針對的是通過李子柒強大的創造能力與實踐能力所呈現的民俗、美食、手工等。更重要的是,借助影像敘事所體現出來的“日常生活”,不僅具有美感,更有一種“現實感”。
如果說將李子柒短視頻中所體現的田園生活視為一種日常生活之美,也就是從審美的角度去考量這種“日常生活”,那么,對于這種“日常生活”與“現實”的關系該如何判定?以審美的態度來看待日常生活,也就是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在這一語境下,李子柒短視頻中的田園生活,成了一種景觀。當人們在觀看視頻中李子柒的日常生活時,便產生一種美化“現實”的想象,或者說一種“幻覺”,這種幻覺來自視頻中所構建的“正在發生”的“現實感”。正如齊澤克所言, “這樣的幻覺正在結構我們與現實之間的真實、有效的聯系”(16)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33頁。。
李子柒短視頻中的古風田園,并非對“現實”的全面“反映”。李子柒及其團隊在接受新聞采訪時,對于自己視頻中的鄉村的認識是,視頻中的鄉村,“并不是作為其本真,而是作為山水田園的擬態而出現”(17)詳見《中國新聞周刊》官網:http://www.inewsweek.cn/people/2019-06-03/5958.shtml。所謂“擬態”,其實就是一種復制品,就李子柒短視頻而言,其中的古風田園生活,則是對山水田園和鄉村生活的一種摹仿,而其所體現出來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之核心,也正在于此。而這種摹仿并非“現實”的反映,只是一種“類像”或曰“擬像”(Simulacrum),是“現實”的“反應”,有意無意間掩蓋了現實生活的“真實”。由此可見,當從審美的角度來考量“日常生活”時,似乎也認定了這種“日常生活”的現實意義,然而,卻極易忽視這種“日常生活”與“現實”的距離。
四、結 語
李子柒的田園古風短視頻,在國內和海外都頗受關注,進而又被官方話語征用,成為一種“文化輸出”的范例。它以田園日常生活為內容生產之依托,通過日常生活中古色古香的美食、手工、勞作等展示對于中華傳統文化、民俗文化等的傳承。短視頻所展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給觀眾一種“現場感”,似乎這是一種“現實”的鄉村生活;另一方面,借助影像建立起來的日常生活敘事,給觀眾一種美感,使人沉浸于這種“亦真亦幻”的田園日常生活。李子柒短視頻以“日常生活”為基底來打造古風田園,但是這種借以“日常生活”打造出“現實感”的田園生活,并非現實的“反映”,而是現實的一種“反應”。這種古風田園,是一種“幻象空間”,以滿足中產趣味的審美和想象,將之作為一種“美”的呈現來欣賞,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大眾文化工業之產物,作為一種消費主義與懷舊心態之合流的弄潮作品,我們在欣賞和贊美的同時,更應意識到被這種“美”所遮蔽的真實,意識到追逐這種古風田園山水背后的社會意識反映出的社會欲望,而這種欲望的投射背后,又隱含著何種社會問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書寫現實,但是,以“日常生活”為名的文化產品與現實之距離又何其遙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