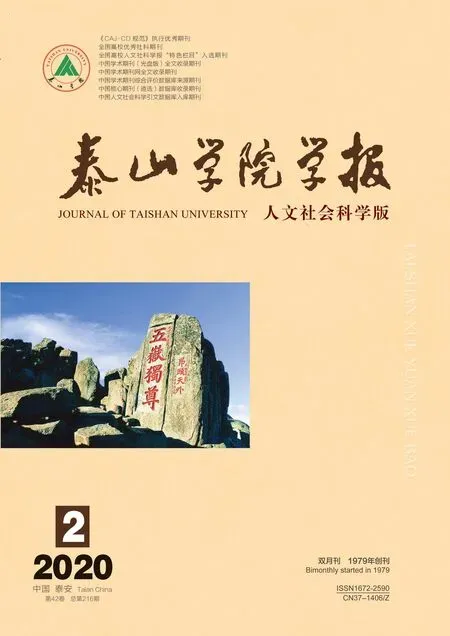歷代泰山辭賦創(chuàng)作述略
姜維楓
(山東社會科學院 文化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02)
本文所謂“泰山辭賦”是指書寫泰山的辭賦作品。所謂“泰山”,包括自然泰山與人文泰山、泰山本體與泰山近域等范疇;對于“辭賦”文體的界定,主要包括以“辭”“賦”名篇和賦體雜文。對于與“賦”體相近的“頌”體的歸屬問題,本文采用萬光治先生的觀點,“詩三百的頌降而至漢,一脈流為廟堂歌辭,成為漢人的頌詩;一脈流入賦域,依然沿襲著頌的名稱。……頌自流入賦域,雖然仍保留了‘美盛德’的功能,但因其擴大了自己的表現形式,已很相似于賦體”[1]。泰山自古就是中華文化的象征,早期頌體文學多借泰山、封禪發(fā)揮祝頌帝王之功用,故此本文將“頌”體歸入“賦”體,將“東巡頌”“封禪頌”等并入“泰山辭賦”的研究范疇。袁愛國先生主編之《全泰山賦》[2]采用“大泰山”觀與“大辭賦”觀,收錄歷代泰山辭賦164篇,盡管其于“主題”與“文體”方面不無寬泛之嫌,但對我們認識把握泰山辭賦文化的整體不無助益,本研究即以此為主要底本①詳見袁愛國《全泰山賦》,濟南泰山出版社,2011年.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所引泰山賦均據此本。。
先秦文學中沒有泰山辭賦行世。秦始皇即帝位后第三年(前219)沿馳道東巡,封泰山、禪梁父,并留下“親巡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3]等刻石文字,然秦代并無泰山辭賦流傳。泰山辭賦創(chuàng)作發(fā)軔于漢代,司馬相如的《封禪文》為泰山賦的開篇之作,后世泰山賦創(chuàng)作浩如煙海,歷覽各代泰山辭賦創(chuàng)作,內容含括封禪、都邑、室宇、飲食、書畫、草木、花果、言志、情感等多方面。本文以歷時為線索,嘗試探研歷代泰山辭賦的創(chuàng)作特點與變遷軌跡。
一、由頌美封禪到批判現實:兩漢六朝泰山辭賦的創(chuàng)作走向
兩漢時期的泰山辭賦熱衷于“封禪”主題,司馬相如的《封禪文》(又名《封禪書》)、揚雄的《劇秦美新》、班固的《典引》均以“封禪”為題,此外班固、崔骃、劉珍、馬融等為漢章帝、漢安帝東巡泰山創(chuàng)制的“東巡頌”,亦屬此類。同為封禪而作,馬、揚、班三大賦家著眼點不同,“司馬相如《封禪文》重在炳玄符,抑古揚今;揚雄《劇秦美新》致力渲染合符受命,尊古昭今;……班固《典引》頌揚炎漢紹堯、孔為赤制等。”[4]三篇封禪文“揚今”“昭今”“赤制”的指向一致,且氣韻宏闊,包蘊萬端,傳達出書寫者對漢王朝制度與文化的自信。
具體而言,司馬相如的《封禪文》采用對話體,假大司馬與天子的對話,敦請?zhí)熳臃舛U,頌美天子“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zhí)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chuàng)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稱美內圣外王與大一統(tǒng)思想文化;繼之闡述封禪理由“大漢之德,逢涌原泉”“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和封禪目的“舒盛德,發(fā)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賦末曲終奏雅,發(fā)警戒之語,勸諫天子兢兢業(yè)業(yè)、居安思危,“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fā)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于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揚雄的《劇秦美新》仿司馬相如《封禪文》,為王莽新政而創(chuàng)制,屬美新政勸封禪之作,歷來頗受爭議,被認為是揚雄的“白圭之玷”。賦文立足于“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勸勉帝王勤政不已“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與相如《封禪文》不同的是有頌美而無諷喻。
東漢光武中興之后,出現明章之治。漢章帝尤其推重儒家以德治國和禮樂教化,勸勉農桑,發(fā)揚孝悌古風。班固的《典引》創(chuàng)作于漢章帝元和三年(86),與馬揚賦“封禪”脈絡前后相續(xù)。作者基于漢明帝認為相如言封禪,頌述功德“賢遷遠矣”,乃創(chuàng)作《典引》,以超越“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5],成一部典實相參之作。《典引》寫漢之歷史、制度與符命,闡述漢典如何紹續(xù),并結合章帝制禮作樂的現實,將頌美與勸諫引導相結合,突出“仁風”“威靈”“勤恁旅力”等帝王德行,并以議論之筆寫天命所歸,圣上“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藪,肴核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充滿現實關懷。此外,以漢章帝元和二年(85)東巡為背景,涌現出一批以“東巡頌”為題的封禪文,如班固的《東巡頌》、崔骃的《東巡頌》等。
漢安帝延光三年(124),安帝東巡,以此為背景的創(chuàng)作,如劉珍《東巡頌》,寫東巡祭天、祀祖、規(guī)范典制、度齊俗、相人偽:“既臻岱宗,精享禋柴,望秩山川,類于上帝。遂祀祖宗,告虔展義。肆覲東后,同律頒瑞。壹度齊俗,兼相人偽。海外有截,休氣和帀。幽荒絕域,澤罔不洽。克厥天心,神望允答。”馬融的《東巡頌并序》表達繼承傳播儒家修德禮制思想,以邁種德、求失禮、增修德、襲令善。文末的亂辭,以山岳崇拜表達對國家享祚億載的祝愿。
兩漢泰山賦除“封禪”專賦之外,泰山亦出現在辭賦家的作品之中,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揚雄的《羽獵賦》。《上林賦》中假亡是公對子虛、烏有及齊楚兩國進行批評,之后筆鋒一轉,極力描摹天子上林苑的巨麗之美和天子游獵空前盛況,其中云:“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軒,后道游。孫叔奉轡,衛(wèi)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河江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后陸離,離散別追,……”[6]泰山作為眾岳之魁,與黃河長江并置,成為天子上林苑最為雄奇的構成之一——“泰山為櫓”(櫓,瞭望臺)。揚雄的《羽獵賦》作于漢成帝永始四年(前13),整體構思上沿襲了司馬相如散體大賦勸百諷一的作用,賦開篇云:“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以并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chuàng)業(yè)垂統(tǒng)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7]以古七十二帝封禪泰山比附天子校獵,闡明“各亦并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之理。泰山均作為天子游獵的襯托和賦家構思文章的道具,并非賦之主干,然從中亦可窺見泰山重要的文化地位。
總之,兩漢泰山賦以封禪巡狩為主體,泰山主要作為封禪巡狩的背景與載體,更多承載了帝王與家國層面關于禮制德行教化等文化。封禪主題之外,此期的泰山賦尚筆涉都邑、瓜果等,如劉禎的《魯都賦》《瓜賦》,無論文體或內容均別具一格。
六朝泰山辭賦與泰山文化展現出不同于兩漢時期的特征,由頌美轉向批判,以阮籍的《東平賦》《亢父賦》為代表。《東平賦》創(chuàng)作于魏高貴鄉(xiāng)公曹髦正元二年(255),據《晉書·阮籍傳》載:“及文帝輔政,籍常從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8]阮籍自請到東平任職,是為了躲避司馬氏與皇帝曹髦的政治漩渦,遠離是非。賦中從自然到人文,從民風到官場,無一是處,令人“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懷”,作者以東平象征司馬氏篡權亂政下的整個黑暗社會的意圖非常明顯。
《亢父賦》為阮籍的另一篇都邑賦。據清人記載,亢父“今濟寧州治古任城也,亢父城在州南五十里”[9],即今山東濟寧城南約50華里處。《亢父賦》的批判現實精神與《東平賦》同,篇章更簡短。賦文起筆寫亢父城之地理狀況“窮地”“卑小”“危隘”,田地物產“土田污除”“穢菜惟產”,民風“人民頑囂梼杌,下愚難化”。古今中外各類文體,如此開篇者實罕其匹。如此構思乃著眼于魏晉之交,世風日下之大背景,言在此而意在彼,作者認為導致人民“頑囂梼杌,下愚難化”“放散肴亂”“狼風豺氣”“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匿是從”的原因乃在于“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不肖群聚,屋空無賢”“鴟鸮群翔”“淳樸靡逞”。
從題材看,《東平賦》與《亢父賦》同屬都邑賦。都邑賦的創(chuàng)作,自東漢前期杜篤之《論都賦》開始,繼之有班固《兩都賦》、崔骃《反都賦》,東漢中期又有張衡《二京賦》《南都賦》等,均以大賦形式呈現。阮籍的《東平賦》《亢父賦》,題材上并沒有選擇通都大邑,而是選擇小城邑東平、亢父作為書寫對象,體現以小見大的文章構思。辭賦藝術方面,避開早期都邑大賦頌美揄揚、勸百諷一的體式特征,批判司馬氏集團的篡逆乖張,倒行逆施不僅有悖于儒家政治倫理,“禮義不設,淳化匪同”(《亢父賦》),“古哲人之枚貴兮,好政教之有儀”(《東平賦》),亦與道家所崇尚之“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東平賦》)的玄真清靜無為相乖忤。放棄漢大賦與早期都邑賦鋪采摛文的寫作模式,一變而為抒情小賦,然其抒情方式又不同于一般抒情小賦之或詠物以寄意,或抒發(fā)士人自身之挫敗感,如張衡之《思玄賦》《歸田賦》等。其書寫范式直接上承東漢中期以來辭賦及政論文中隱微的批判精神,如趙壹之《刺世疾邪賦》。阮籍《東平賦》《亢父賦》于“狼風豺氣”中懷孤抱憤的形象和批判精神與其同期《詠懷詩》中之“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離”“季葉道陵遲,馳鶩紛垢塵”的旨趣是一致的。在前期及同期的泰山辭賦創(chuàng)作中,阮籍辭賦的批判精神與憂患意識是獨樹一幟的。
南朝齊梁時期,泰山辭賦出現與兩漢泰山賦純然“封禪”主題相異以象表意的詠物賦。如王儉《和蕭子良高松賦》、謝脁《高松賦》(奉竟陵王教作)、張正見的《山賦》,三篇賦雖非專詠泰山與泰松,然與同期其他《高松賦》不同,三篇賦作均筆涉泰岱。以前兩篇賦為例,南齊王儉《和蕭子良高松賦》開篇即云:“山有喬松,峻極青蔥;即抽榮于岱岳,亦擢穎于荊峰。”高松抽榮于岱岳,松岱雙美的意象可謂峻偉之極!后文由物及人:“偓佺食和而輔性,墨翟昌言于宋圍。想周穆之長阪,念東平之思歸。若乃朔窮于紀,歲亦暮止。隆冰峨峨,飛雪千里。攬三秀而靡遺,望九山其相似。翔雁哀回于天津,振鷺驚鳴于川。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皓霰而爭光,延微飚而響起。”[10]以傳說與史載偓佺、墨翟、周穆、劉蒼、屈原等高節(jié)之典,稱美高松“貞華無已”“微飚延響”的品格。謝朓《高松賦》由品藻岱松至品藻人物的指向非常明顯,其開篇云:“閱品物于幽記,訪叢育于秘經。巡汜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提于巖以群茂,臨于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品評高松“性靈”“群茂”“宗生”“長壽”特質,后文由物及人“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詠其徂徠。乃屈己以弘用,構《大壯》于云臺。幸為玩于君子,留神心而顧懷”,以“岱畎”“徂徠”之松最稱高妙,“質兼上才”。兩篇賦由言及象,由象見意。泰山賦中的這一組詠物賦,出現在南朝齊梁之間,顯然是受到魏晉以來品藻人物的風尚及魏晉玄學關于言象意文化思潮等的影響。
此外,南北朝時期尚有程駿的《慶國頌并表》、虞通之的《明堂頌》,均與“封禪”無涉。前者表達了頌美圣德、申厚風化之意,勸諫君王重視農耕為本與民眾衣食,雖屬“頌”體,然并非一味頌美,包含勸諫之意,兼具“頌諫”特征;虞通之的《明堂頌》則包含建章立制以垂范后世、休光下盈等內容。總之,相較于兩漢泰山辭賦創(chuàng)作,六朝泰山辭賦多以“賦”名篇,題材內容則更加多元,富于批判精神。對于前代賦家熱衷的“封禪”題材,劉勰在《文心雕龍·封禪》加以總結,劉勰認為封禪功用在于“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yè)……茲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從文章學角度看,封禪文之結構、言意、主題特征為:“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于訓典之區(qū),選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于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11]
二、由高歌進取到沉靜內斂:唐代泰山辭賦審美特征
唐代泰山賦創(chuàng)作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初盛唐時期的泰山賦,以頌美“封禪”“明堂”為主,內容題材較為集中,以泰山象征國家一統(tǒng),辭賦充滿著高歌進取的盛世情懷,呈現出國勢上升期“勃承天光,禮樂克備”(張余慶《祀后土賦》)的文化氣象與風度。中晚唐時期的泰山賦整體處于“守謙靜”“沖淡平和”的文化氣局之中,題材內容和情感類型均相對多元,泰山成為感物抒情的背景,部分辭賦對前朝“封禪”“貞符”等予以反思與批判,部分辭賦在表達對前朝封禪泰山的崇敬之外,流露出對封禪的素懷與榮悴不時、人生苦短之嘆;晚唐出現泰岱詠物賦,象喻君子貞潔、忠厚之品格。整體上唐代泰山賦風格由高歌進取張揚而漸趨沉靜內斂平和沖淡,文化上由高度自信到懷念前朝。
首先,唐代是繼漢代之后于“封禪”主題最為熱衷的一個時代。相較于漢代封禪賦,唐代封禪賦文中關于家國自信的表達更加豪邁細膩。其一,進一步論述建章立制、禮樂文化的重要性,將禮樂與刑罰對舉,申述禮樂的教化作用,將封禪禮樂儀典作為意識形態(tài)載體,并以此伸張大國政治與文化自信。玄宗朝的封禪文往往先述國初之正統(tǒng)雄武,至本朝建章立制、禮作樂制、革故鼎新,縱向演進,一瀉千里,行文張揚著樂觀自信。如張說的《大唐封祀壇頌》,甫始即于儒家禮儀的框架內討論封禪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圣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蘇颋的《封東岳朝覲頌》稱:“傳不云乎:‘君子勤禮,敬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作樂,豫以動也。’慎矣哉!禮樂之為用,故執(zhí)禮者具,刪弊則質,宜之自我。”解釋了對待禮儀的態(tài)度為“勤敬謹慎”。其二,唐代泰山賦在紹續(xù)兩漢泰山賦禮樂文化統(tǒng)系之外,又傳達了明顯的大一統(tǒng)、正統(tǒng)和以華化夷等思想觀念,在文化自信之外又增添了天下一統(tǒng)的制度自信。如長孫無忌《請封禪表》云:“擊壤而謠,傳清音于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于皂隸”“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于冊府;四方夷狄,鑿其竅于靈宮。則普天欣賴,懷生再造,朝聞夕死,撲若登仙。”于“擊壤而歌”“耕田而食”的治國理政觀念中,增加四夷來歸,人文化成,天下一統(tǒng)等思想。劉允濟的《明堂賦》傳達出辨正朔、大一統(tǒng)、興禮樂,追求王道圣懷、功成道貞、無為自治的儒道精神:“統(tǒng)正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踵武。大禮興而三靈洽,至道融而萬物睹,其在國乎。……道不言而有洽,物無為而自致。向明南面,高居北辰。屬天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云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人。協(xié)和萬宇,懷柔百神。降虔心,啟靈術,采舊典,詢故實。表至德於吹萬,起宏規(guī)于太一。欣作之于有范,佇成之於不日。工以奔競,人皆樂康。訪子奧于前跡,揆公玉之遺芳;順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圓方。”描摹出百辟來朝、君臨天下的大一統(tǒng)圖景與天下安泰和諧氣象:“三陽再啟,百辟來朝;元曛霧集,旌旆云搖。湛恩畢被,元氣斯調。”
其次,中唐泰山賦從題材內容到審美風格均更加多元,格調沉靜,極富哲思。獨孤授《江淮獻三脊茅賦》,借稱詠三脊茅以彰美封禪,作品由稱美“物”之尊貴到思考“禮”之本質。“物”為“禮”之外在呈現,作者認為:“道未格也,雖有采而必無;岳可封焉,縱不求而自有。觀王者之得失,知禮事之臧否。”道未格則禮必無,岱岳可封,縱然不求而依然存在,因此封禪的本質不在山岳而在禮制,禮事臧否與政教得失相因果。柳宗元的《貞符并序》對歷代帝王欲封禪而矯飾“貞符”之舉進行反思與批判,認為“德實受命之符”“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德實受命之符”,真乃“以德治國”精神之先聲。作者從正反兩面加以例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柳宗元《貞符并序》的價值不僅在于其批判精神,還在于提出了“德實受命之符”的理念,和以“利安元元”為務的民本思想,體現出中國思想演進中國理性思辨的一層。此外,丁春澤的《日觀賦》:“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鳴雁,猶陰沉而不睹;忽聽晨雞,既曈昽而可愛。于是漸出旸谷,將離地維,巖巒既秀,草樹生姿,氣則赫赩,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不僅開后世頌日華章之先河,言辭間充滿對日觀的崇敬之情,懷有回首盛唐、可望不可即的仰望之情。
再次,晚唐泰山賦不再以封禪為宗,借詠物以稱美人格,泰山成為若隱若現的宏大背景,亦被賦予了人格之美。高孚,晚唐文宗時人,曾官許昌主簿,其《白云起封中賦》假漢客遭逢漢昌,從武帝登岱,睹白云效祥而賦,以稱美漢皇。我們說將文學背景置于漢代,是唐代文學作品的常例。然身處晚唐,依然稱詠登封,首先值得思考;與漢唐封禪賦相同的是,《白云起封中賦》對帝王的稱美首先著眼于帝王天下一統(tǒng)、制禮作樂的“外王”思想:“我皇德以靜人,威以平難,廓清諸夏,光啟大漢。俗既和兮考時巡,禮既備兮登日觀。”高孚此賦亦對帝王“內圣”之德加以稱美,與漢唐封禪主流辭賦不同,漢唐稱美帝王“內圣”之德主要集中于“道德仁義禮智信”方面,以張說《大唐封祀壇頌》為代表;高孚此賦以“穆清”“貞白”稱美帝王:“帝穆清以修祀,云故清其容;帝貞白以為心,云故白其色。豈徒然也?君為萬國所仰,岳乃眾云所屆。”“穆清”既是對天下政通人和的歌詠也是對帝王品格的稱揚。曹植《七啟》云:“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蔡邕《釋誨》:“夫子生穆清之世,秉醇和之靈。”“穆清”“貞白”固然與“白云”之“容色”特質吻合,但帝王的這種品格更接近“仁人”“君子”,其對應的文化心理訴求更值得思索。王棨的《神女不過灌壇賦》稱美太公“正直”“仁境”品格,傳達為人應懷敬畏之心;《闕里諸生望東封賦》,處于大唐江河日下之際,依然表達對盛世封禪的向慕,期許國家再度興盛;李曾的《山川出云賦》以山川云氣象喻君臣之道;路蕩的《拔茅賦》以菁茅比德君子品格,“傳其潔,守其貞”;李蒙的《娥女泉賦》歌詠女子端顏之貌,至柔如水的性情和真純不假、存道得仁的修養(yǎng)。總之,晚唐辭賦內容與審美風格均內轉內斂,與初盛唐時期文化的外向高揚不同。
三、由華麗虛妄到質實尚樸:宋代泰山辭賦的審美變遷
第一,宋初華麗虛妄的封禪文辭與文化。中華文化造極于宋世,然終宋一世并未實現一統(tǒng),但這并不影響宋廷上下封禪的愿望。《宋史》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已有封禪泰山之議,[12]而實現封禪的則是宋真宗,真宗趙恒也是歷史上最后一位封禪泰山的帝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與王欽若、王旦、陳堯叟等集體導演了“天書”事件,以封禪宣揚“天命”“正統(tǒng)”“夸示外國”。這一時期的幾篇泰山賦以封禪為主題,主要有田錫的《泰山父老望登封賦》、王旦的《大宋封祀》、陳堯叟《大宋封禪朝覲壇頌》、王欽若的《禪社首壇頌》。田錫的《泰山父老望登封賦》作于真宗咸平年間,為真宗封禪之前的作品,依然延續(xù)封禪文關涉“天意人心交泰”“厚德”“至仁”等意旨,篇幅簡短,缺少唐封禪文中關于“天下一統(tǒng)”“夷狄來歸”等內容,文章氣勢已遠不如盛唐。后三篇合稱“北宋三頌”,是專為真宗封禪而作。真宗的封禪,本基于“澶淵之盟”乃“城下之盟”的評價,加之君臣自導的“天書”事件,使封禪失去了敬天禱民的真誠的儀式感,淪為純粹自欺欺人的形式,不僅在后世飽受詬病,在當朝就受到來自朝臣的質疑,“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13]。因此,建立在虛妄不實基礎上的“北宋三頌”,盡管篇幅較長,內容豐厚,然言辭未免夸飾:“夷夏太和,天人交感”“萬國以朝,四夷接武”(王旦《大宋封祀壇頌》),“河海夷晏,巖廊穆宣”(陳堯叟《大宋封禪朝覲壇頌》),“不以功成而自大,治定而自矜,炳乾文,號神岳,仰懷天貺,不敢以怠遑,俯述世功,用歸乎德美。此實歷代之所未有,上圣之所獨臻也”(王欽若《禪社首壇頌》)。整體而言,文章結構單調,文辭踵事增華,已難見唐代封禪文所呈現的高度的政治自信。
第二,平易簡凈、質實尚樸的辭賦風格與文化基調。與真宗朝華而不實的三頌所描繪的虛飾繁華不同,宋代泰山辭賦與泰山文化還有平易簡凈、質實尚樸的另一路,范仲淹與羅椅的同名賦《明堂賦》可為代表,兩篇賦均以文化的禮儀建制為旨歸。范仲淹的《明堂賦》闡釋“何謂明堂”與“明堂之道”,此賦突破時代,不再夸飾封禪儀典,認為“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huán)之以水”,文章以明堂之四季與天下政治相關和,闡釋治國之道,認為依“春榮夏繁秋清冬靜”之法,以修明政治,追求和平、仁孝、止伐、民本、法制的理想:“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主張“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為其陋,奢不為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圣子神孫,億千萬期,登于斯,念于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范仲淹的《明堂賦》從治國之道的角度闡述明堂,不夸飾,其思想境界遠遠高于三頌,體現出范仲淹沉潛深思、效法自然之道的思想。南宋羅椅的《明堂賦》借賦明堂,傳達出尚質的文化特質:“茅茨采椽,至質之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別。”唐宋文化“就藝術風格而言,唐型文化華贍凝重而進取外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斂內省”[14],宋型文化“幽淡清新”“收斂內省”的風格于范羅二人之《明堂賦》可見一斑。
第三,沉潛內斂、極富哲思的文化氣質。范仲淹的《明堂賦》闡述儒道互融的治國之道,啟人深思,極富思想性。借賦明堂闡明政教,實質是對“明堂者,明政教之堂”[15]的闡釋,認為“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天子居明堂思萬物之消長,慎生靈之安危;明堂乃“天子布政之宮”,天子對民布施德政,明堂“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揖讓而治天下者,名堂之謂也”;將“齊和壽仁”的儒家之道與“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于自然”的道家主張合二為一,認為“此明堂之道也”。李綱的《有文事必有武備賦》為泰山辭賦中首篇以“文事武備”為題的作品,作者基于兩宋之際國家覆亡、朝廷風雨飄搖的大背景,從理論思想方面反復闡述“文事武備,全才必兼”之重要,認為“刑作教弼,文資武全。惟兩器之兼用,乃一道之當然”“勇不懼而仁不憂,固并推于達德;文足昭而武足畏,蓋有俟于全才”“不能全文武之道,何以致久大之勛?”“有國有家,惟仁惟義。雖誕敷于文德,宜克修于武備”“蓋以治安之本,在于文武之兼”,賦文傳遞出鮮明的愛國精神與憂患意識。在闡明文武兼?zhèn)渲匾螅磉_出于外患內憂之際,期冀得文武全才,以股肱帝室:“大哉武之于文,雖二而一。藏于無用之用,蓋以不必而必。方今外患侵而中國微,安得文武全才,以股肱于帝室?”范李二人的泰山賦呈現出兩宋辭賦文化沉潛內斂、極富哲思的一面。
四、由反思封禪到構建治國理路、從家國情懷到個人情感:元明泰山辭賦的情感走向
元明兩代泰山賦在“封禪”主題方面,呈現出新的面向——擺脫了漢唐以來“頌美封禪”的主流傾向,轉向對封禪的反思。楊維楨的《封禪賦》為元代唯一的封禪賦,賦文直書“圣主不封禪,而凡主之不應兮”,指明封禪之荒誕不經:“由人主之好名,紛佞臣之逢欲。故勞民而張費,貽一時之慘毒。崇封降禪,其祀兮何志?泥金涂玉,其秘兮何辭?上不足以格皇穹,下不足以福蒸黎。不過夸詡功德,而為長生不死之祈者乎?”此外,楊維楨在其《泰元神策賦》中以欲抑先揚的筆法,再次對封禪之荒誕加以嘲諷:“甲午災林光之門,乙酉焚柏梁之臺。祥瑞未至,咎征頻來……而又何必論秦穆之錫而昌,漢武之增而授者也?”梁斯立的《岱宗賦》,開篇頌贊“據中原而至尊……屹然居五岳之雄長,巍然為眾山之宗主”,繼之寫歷代君王徒炫封禪,侈銘功而頌德,曲解堯舜之巡狩,封禪徒荒唐而無益,指明“秦皇漢武之封禪,適足為泰山之羞”,歷代帝王行封禪棄文教,有如楚人買櫝還珠之舉,而足為萬代之式、于方今應效法者應為“唐虞之肆覲”,倡導圣皇御世,行“德治”“文教”“望秩之禮”,如此方能“裨泰山巍然,永鎮(zhèn)乎億萬年之封疆!”
首先看元代泰山賦。元代泰山賦在反思否定封禪的基調之下,呈現出兩個特點:
第一,側重治國理路的思考。以郝經《泰山賦》為代表。郝經的《泰山賦》不僅是辭賦史上第一篇直接以“泰山賦”的命篇之作,其開創(chuàng)性的價值還體現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多個方面。賦云:“中維岱宗,獨尊而雄;盤踞萬古,莫與比隆。……粵惟茲山,首出庶岳。……孰如茲山,中華正朔。建極啟元,衣冠禮樂。……孰如茲山,袞冕黻珽,朱弦疏越。純粹中正,崇高溥博。”首先,郝賦傳達出“大一統(tǒng)”“華夷一家”“以華化夷”的思想,這與郝經“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16]的夷夏觀是一致的,不僅如此郝經還認為“天之與興,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為之而已矣”[17]。郝經關于“天”“地”“人”“道”“行”的思想,可謂思想史上之“泰山”,足以俯瞰睥睨“封禪”。其次,郝賦以泰山象征“中華正朔”,突出泰山獨有的文化精神內涵,“視泰山為中原文明的象征與代表,將泰山精神與中華國魂緊密綰合”[18]。再次,郝賦于金元戰(zhàn)亂“霸道”橫行之際提倡“禮樂”“仁德”“王道”之治,“建極啟元,衣冠禮樂。天宇夷而皞皞,王道裕而綽綽”“有如是之神,儲膏溢澤,蒸為桑土。衣被天下,民無寒苦。……有如是之仁。既高而大,又神而仁。乃于岳麓,篤生圣人。續(xù)太皞之統(tǒng),萃奎壁之真……膏澤其民,堯舜其君。德與山高,名與山尊”,足見其治國理政之遠見。
另一元末明初唐肅的《日觀賦》也極有價值。唐肅的《日觀賦》以漢征和四年武帝親耕鉅定返駕泰山,封禪既畢歡朝甘泉為背景,設武帝與東方大夫君臣問答,突出泰山“山惟岳尊,岳惟東最”的獨尊地位。賦文以泰山象征帝王,“居高察卑”一小眾山,東方大夫委婉地勸勉帝王“以德化民”方能樂康的愿望。唐肅《日觀賦》的價值有二:其一,文學表達上,假托漢武帝關于泰山“高矣、極矣、大矣、特矣、壯矣、赫矣、駭矣、惑矣”的“八矣”之嘆,刻畫描摹出泰山峻極超拔、經天緯地的磅礴氣勢,堪稱“十六字而頌岱詩文之事盡”;其二,賦末關于儒道互鑒治國理路的思考:“收遠討之疲兵,罷求仙之淫祀。大開明堂,垂拱而治。”其思想不僅呼應同期郝經之論,亦上應魏征“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19]之論,更可上溯《易·系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20]由此可見,歷代士人一以貫之的治平思想與對國家治道的關心與思考。
此外,元代辭賦中祝蕃的《明堂賦》闡述了明堂價值意義,表達希冀圣天子建明堂,布政行仁的愿望。結尾云:“方今圣天子,襲世德,承天休。萬國獻圖籍,四海酣歌謳。靈臺嚴太史之測候,辟雍藹多士之藏修。獨明堂之未建,豈王度之靡周。蓋禮樂興于積德,正有待于皇上之黼黻皇猷也。……于赫皇元,車書同兮。文治聿興,千一之逢兮。厥惟明堂,王者之宮兮。制作有待,在皇上之躬兮。遹觀厥成,吾與子歌三雍兮。”歌詠天下一統(tǒng),倡導建制明堂,制禮作樂。
第二,詠物題材涌現。所謂“封禪漸替,山水方滋”,隨著宋以后封禪祀典不斷被質疑,以封禪為主題的泰山賦漸次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詠物題材的涌現。詠物抒懷,這一時期的泰山賦傳達出文人士大夫對于堅貞保節(jié)、靜處包容等人格修養(yǎng)的追求。戴表元于宋亡后曾一度隱居不仕,作《靜軒賦》《容容齋賦》(賦主均為東平人)。《靜軒賦》借賦“靜軒”,傳遞了宋元易代之際作者“學坐”“學默”“息交”“寡求”的人生體悟,作者認為“人之營營,與識俱生”,惟“大靜之士”方能體味“時然后出”“時然后處”“時然后默”“時然后語,不得已而語,則玉振而金聲”的道理。王旭的《鳴鶴賦》借鶴鳴之“氣高亮而非怒,聲清哀而不淫”的特質,表達自身優(yōu)游逍遙、結伴良朋、安心無累、潔身歸隱的處世態(tài)度。梁斯立的《汶篁賦》以歌詠汶篁播遷流寓燕地,堅貞不改、安固勁節(jié)、貞固保節(jié)的品格。此外,元代鞠志元和張本的兩篇《蒲輪車賦》,一方面歌詠元朝禮賢重士恢復科舉,一方面以賦體諷諫君王不能常懷敬德尊賢之心,“外仁義兮內多欲,侈宮室兮窮土木,求神仙兮蠱方士,勒驃騎之幾十萬兮墮威武。昔蒲輪招賢之車兮在何所?輪臺下留兮嗟何補”(張本《蒲輪車賦》)。
其次看明代泰山賦。明代泰山賦從賦體特征看,可謂散體大賦與抒情小賦并行,蘇志乾《岱山賦》與釋慧秀《岱宗賦》,篇幅已較元代泰山賦更長,多鋪排筆法;謝肇淛的《東方三大賦》、范守己的《泰山賦》、馬一龍的《泰山賦》散體大賦的筆法更加突出,篇幅更長,間或采用主客問答的結構形式,賦前有序,講究聲貌夸張,整體上有“情少而辭多”的傾向。“形式即內容”“內容即主旨”,明代泰山賦采用散體大賦體制,充分發(fā)揮大賦“長篇體制”與“體物”手法,極盡摹寫萬物,旨在宣揚文人的國家自信。
明代泰山賦從內容表述看,除表達泰山五岳“獨尊”的地位以及鐘靈毓秀之品格外,承元代對“封禪”理性認知的余緒,其否定的言辭并不激烈,間或流露“登封弗續(xù)”的復雜情緒。蘇志乾《岱山賦》:“此亦天下之瑋麗壯觀也!爾其皇風載融,帝道郅理。……穆穆藹藹,清寧康泰。埒造化而受功,德二儀而躋大。一人有慶,兆民共賴。皇哉皇哉,猗歟休哉!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guī)祝苤僦槐刂G,長卿之所不必書者也。”陳璉的《登泰山賦》與李兆先的《望岳賦》抒寫自己“登岱”“望岳”的情懷與所見繁復物態(tài),語言思想擺脫前代泰山賦膠著板滯的特點,形塑泰山鮮明的個性,可作為明代泰山賦抒情之作的代表。申旞《泰山觀日出賦》,寫景抒情,景情相生,作者將歷史與當下,現實與理想間相融合,抑揚起伏,完全擺脫了前代泰山賦頌美的主調,融匯自身的人生感悟,一派天真自然:“愿得歸田娛我情,靜觀無始契無名。周天一息千萬程,不出戶庭游八紘”,與帝王無關。李兆先的《望岳賦》,寫因迫歲序,家書催還,作者經泰山未能登臨的遺憾,“方解乎清濟之纜,徒悵望乎遙天之岑。興長嘆以遐眺,見萬丈之崎嶔”,作者認為“彼泰山兮可游,眷吾親兮不可以我留;彼天梯兮可躡趨,吾家兮不可以中輟”,泰山可再游,然親情不可中輟,這是一篇充滿親情關懷和溫度的辭賦,可視為明代泰山賦情感由宏大抒情到細膩親情抒發(fā)的一種轉向。
總之,明代泰山賦否定封禪,主張明德修政減少苛賦,在華夷之辨方面沒有明顯的書寫,出現更多歌詠泰山自然山水和詠物抒懷表達士大夫人格修養(yǎng)之作。
五、家國兼顧、情理兼容:清代泰山辭賦之集成
清代泰山辭賦創(chuàng)作數量為歷代之最,且題材內容更趨多元,以“賦”命篇者最多。清前期泰山辭賦與文化紹承元明兩代,對封禪傳統(tǒng)加以揚棄,以泰山為國家政治象征的指向依然清晰。高士奇的《登岱頌》與陳夢雷的《泰山賦》分別以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親祀泰山為背景,二賦在對前圣后王與當下的比較中完成對當下的頌美:“勿以省觀所至,勞我兆人”“不襲五載一巡、十二年一巡之轍,而告祭以時,成民是念”(高士奇《登岱頌》),“前圣尊為三公,爰舉懷柔之祀;后王侈言封禪,以希帝座之通”,而“我國家二儀共泰,六合攸同……乃陋秦漢之不經……問俗以觀風,爰望秩之是展”(陳夢雷《泰山賦》),“前圣”祭祀乃為懷柔,“后王”侈言封禪乃希冀帝座永續(xù),圣朝視后王封禪為鄙陋,而行問俗觀風、祝釐告虔,棄后王之不經,紹承追摹前圣“懷柔”之祀,一方面頌美帝德如堯舜,一方面流露出高度的國家自信。
清中期劉鳳誥的《僬僥戴泰山賦》和《泰山觀日出賦》具有一定的政治象征,前篇將僬僥與泰山比較,小大懸殊,情感最終指向國家一統(tǒng)、八方來慕:“我皇上壽獻罔崇,封增礪固。堯天共戴,徠雕題帕首之倫;亥步難周,辟輦谷梯峰之路。聽聲呼萬歲之祥,效頂祝八方之慕。”后篇始于泰山觀日而歸于頌圣,寫泰山“鎮(zhèn)于東”之位,客與我同游泰山登乎日觀,寫日出勝景“三壺懸圭,耀六岳八瀛之首;九龍銜燭,游五光十色之間”,在對泰山做了充分的蓄勢描摹之后曲終奏雅:“我皇上福曜重輝,壽山貞固。”
乾嘉時期的辭賦創(chuàng)作泰山作為國家文化象征的指向更強,如胡長齡的《泰山觀日出賦》開篇借秦皇漢武侈升中登封發(fā)歷史長久與短暫的感嘆,并以此作為泰山觀日之背景,之后在細膩地描摹日出的變化過程和壯觀景象“雖常新之光景,實天下之壯觀”之后,作者方集中筆墨歌詠泰山,感慨其歷史悠久處寰宇之重,“隆上祀之精禋,備史家之著述”,繼之在進行充分的體物抒情之余,作者自然地稱美帝王:“欽惟我皇上,舜日堯云,湯馳禹步,祛躛語之荒唐,修虞書之法度。”泰山作為歷史文化符號與國家象征,或為前景或為背景,最終的稱美乃水到渠成。李廷芳的《泰山不讓土壤賦》、程炌的《泰山之云賦》、汪鄴的《一覽眾山小賦》等均為此期代表之作。如程炌《泰山之云賦》云:“吉祥捧日,看赤縣之初晴;舒卷隨風,知齊州之欲……”吳育《岱頂看云圖賦》云:“顧瞻周道,將以為類兮。”這一時期,泰山辭賦沿著詠物-抒情-悟道的創(chuàng)作思路,如行云流水,自然清新,審美風格與前期宏大板滯單調的封禪禮儀道德說辭不同,傳遞出由自然到人文的親切與自信。
此期泰安知縣周藩的《泰山賦》,內容上不再因襲前朝頌美封禪的陋習,認為“若天書與靈芝,尤伎倆之狡獪”,借前哲“嘆苛政而心惻”表達了為官一方欲“思成民”又“懼蚊負而曠厥官”的責任擔當;藝術上融合了大賦體物瀏亮與小賦善抒情言志的雙重特質,讀來親切自然。布衣作家汪鄴的《一覽眾山小賦》中的泰山形象更加親民,泰山形象由仰不可及的神圣天尊到平民化的“任我流連,恣人延攬”,語言雖有夸張,但已脫盡康熙朝泰山賦夸耀恭迎阿逢之態(tài),抒情寫景更多表達了人間個體的追求和自信,以及對古人的尊崇。
清后期的泰山賦更多為懷念前朝、模擬前朝之作,如顧槐三的《擬李白明堂賦》、譚獻的《明堂賦》《明堂后賦》,作者身處晚清而將明堂背景置于漢唐,徒托空言,呈現出王朝末期的衰敗跡象。晚清賦家趙國華的《奉命祭東岳賦謹序》值得注意。此賦作于光緒十七年(1891),辭賦立意、創(chuàng)作態(tài)度與傳統(tǒng)辭賦以頌美為主調的風格迥異。趙國華此賦突破前代同類賦“夸飾祀典”的主調,主要寫人事、朝政、律令之是非黑白顛倒,作者痛下針砭,感慨世路江河日下:“舍律令而不用,充私言于公廬。官轉徙以為利,直更代而吹噓。態(tài)百出而莫窮,事一致而忘污。罪乞請而可貸,死無故而忽蘇。潰公錢于阱穴,豢盈路之鼷狐。召寅緣之四至,聚游手而不驅。長風氣之狙詐,壞人生之廉隅。”此種手法與漢大賦之通篇美圣德褒帝王頌國事,賦末“勸百諷一”不同,可謂“諷百勸一”,主要篇幅用以揭露社會、官場、世情之丑惡,曲終反而轉為“有一于此,神明必誅”的勸諫表達。
另外,清代泰山賦在關乎國家宏大情感之外,較前代泰山賦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情感更加真摯細膩,諸如鄉(xiāng)風、民俗、飲食、修養(yǎng)、親情、家族榮耀等的表達均有承載。孔昭焜為孔圣后裔,其《浮云連海岱賦》借杜甫《登兗州城樓》“浮云連海岱”之典,稱頌泰岱抒發(fā)了家族“兒孫九鎮(zhèn),襟帶神州”的榮耀;唐仲冕的《陶山賦》對父母邱壟難返湘水,深抱愆罪,對當年鄉(xiāng)邑士民率錢負土襄助起墳表達感念之恩;蒲松齡的《煎餅賦》描寫生動,略帶夸張,運筆輕松,立意以趣味為指向,傳遞出安貧樂道的人生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