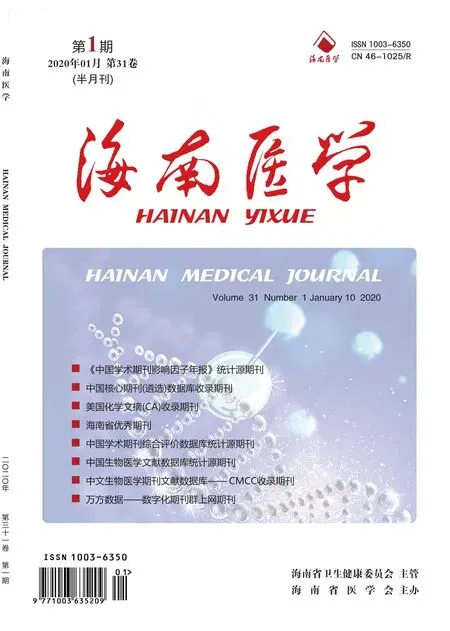IL-34在感染性疾病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趙方方 綜述 賀仁忠 審校
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呼吸內科,貴州 遵義 563003
白細胞介素-34(IL-34)是近年來新發現的一種與集落刺激因子-1的生物學活性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新型促炎細胞因子。近幾年研究發現,IL-34參與感染性疾病、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對其檢測,不僅可以協助診斷,對評估病情及療效均具有一定臨床價值。感染性疾病在臨床工作中是常見的疾病之一,目前對某些特殊感染性疾病臨床中仍無特效藥物治療,因此需對其發病機制深入研究,為疾病治療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和研究靶點治療提供新的方向。本文就從IL-34的各種感染性疾病的作用機制做一探討。
1 IL-34的概述
1.1 IL-34的基本結構 Il-34由單核巨噬細胞系統、上皮細胞、成纖維細胞等分泌,并于心臟、腦肺、肝脾等各組織器官中持續表達。人類IL-34基因定位于16號染色體q22.1,在生物進化中具有高度保守性[1]。人體中IL-34是由222個氨基酸組成的同源二聚體蛋白,在小鼠體內則是由235個氨基酸組成的同源二聚體蛋白,分子質量為39 kDa,其結構包含兩個β鏈、四個長螺旋、四個短螺旋,有一個反平行的四螺旋核心,這與集落刺激因子(CSF)-1相似[2]。
1.2 IL-34的受體及生物活性 IL-34的主要受體是CSF-1R,IL-34與CSF-1R結合參與調節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的增殖、分化及活性調節等多種生物功能[3],不僅能激活NF-κB、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磷酸肌醇3激酶/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PI3K/AKT)、酪氨酸激酶/轉錄因子(JAK/STAT)、細胞外信號調節蛋白激酶1/2(ERPK1/2)、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PKA)信號通路,還能激活caspase-3/8通路[4]。腦組織高表達IL-34,而低表達CSF-1R,質譜分析發現在小鼠腦膠質細胞及神經母細胞中,蛋白酪氨酸磷酸酶-ζ(RPTP-ζ)可作為 IL-34 的另一受體[2]。 IL-34 與RPTP-ζ結合后可抑制膠質母細胞的增殖、克隆以及轉移[5]。多配體蛋白聚糖-1(syndecan-1)在多種腫瘤性疾病中表達,可作為多種生長因子的共受體,近年來研究發現syndecan-1能促進IL-34誘導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受體(M-CSFR)信號通路的激活,是IL-34第三個受體。IL-34與syndecan-1結合可調節自身生物活性[6]。
2 IL-34與感染性疾病
2.1 IL-34細菌感染所致膿毒血癥 膿毒血癥是宿主對感染的反應失調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疾病。膿毒癥癥的特征是宿主免疫反應不能遏制感染,最終導致器官損害。世界每年約有3 150萬膿毒血癥患者,每年仍有530萬人死于該疾病,到目前為止,仍無治療該疾病的特效藥物,故進一步探討膿毒血癥的靶向治療有望成為治療新方法[7]。LIN等[8]研究發現膿毒血癥患者血清IL-34較健康人明顯升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但與評估敗血癥嚴重程度的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OFA)、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評估(APACHE II)指標無明顯相關性。用盲腸結扎穿孔(LPS)誘導膿毒血癥小鼠,檢測誘導24 h、48 h后血清、腹腔灌洗試液、肺組織IL-34水平,發現IL-34明顯上升,外源性注射重組IL-34蛋白可使小鼠體內的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增多,能提高小鼠的生存率及細菌清除率,而當外源性使用抗體中和體內的IL-34蛋白,則小鼠生存率及細菌清除率下降,由此推測IL-34通過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的介導作用在膿毒血癥的免疫應答中起保護性作用,可作為治療治療膿毒血癥治療及藥物開發的新靶點。
2.2 IL-34與病毒感染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慢性肝病常見病因,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引起。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世界約2.57億乙肝患者,2015年,全世界有80多萬人死于該病的并發癥,主要是肝硬化和肝癌[9]。目前治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主要藥物有直接抗病毒治療及免疫調節兩種,但目前,目前沒有一種治療方法能夠完全治愈HBV感染,需要進一步探索新的治療方法。CHENG等[10]研究發現,與健康人對比,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IL-34及外周血單個核細胞表達IL-34mRNA明顯降低,相關分析研發現,IL-34與HBV DNA拷貝、ALT、AST呈明顯負相關關系,IL-34可抑制HBV復制中間體、HBV總RNA、3.5 kb mRNA以及HBV核心蛋白的表達,由此推測IL-34可以抑制HBV的復制。此外,IL-34可通過多種途徑促進肝纖維化的進展具體如下:調節單核巨噬細胞趨化因子及受體表達,使病變區域單核細胞聚集,從而使肝臟的炎癥反應持續存在;誘導能夠促進纖維化進展的巨噬細胞分化形成,使TGF-B及半乳糖凝集素-3等HSC活化劑產生增加,從而促進HSC的增殖,也可以直接作用于HSC,使其發生表型轉換,合成大量的細胞外基質;還可以調節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的生成,加劇膠原纖維沉積,通過基底膜的降解來增加炎性細胞在肝臟的浸潤;下調金屬蛋白酶-1(MMP-1)的表達,促進纖維化過程;能抑制自然殺傷細胞合成分泌具有抗纖維的γ-干擾素細胞因子,以致HSC的凋亡減少,間接促進肝臟纖維化的發生發展[11]。綜上所述,研究細胞IL-34在乙型病毒性肝炎中的作用機制,不僅可為抗病毒治療提供新的靶點,也可為其并發癥治療提供新的方向。
艾滋病,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是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起的一種嚴重傳染性疾病,HIV是一種能攻擊人類免疫系統的逆轉錄病毒,由于有極強的變異能力,給治療帶來了極大困難。人類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感染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約3 800萬人感染,并造成3 200多萬人死亡,2018年有170萬人新感染[12]。目前治療的方式主要是抗逆轉錄病毒療法,但在終末細胞中建立病毒儲存庫是治療的主要障礙。HIV-1易感染巨噬細胞(Mφ),存在著潛伏的HIV-1病毒庫,被感染的Mφ與被感染的CD4+T細胞比較具有更高的HIV-1載量。PAQUIN等[13]實驗研究發現:由IL-34衍生的巨噬細胞(IL-34-Mφs)與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衍生的巨噬細胞(M-CSF-Mφs)比較對HIV-1感染的容忍度較低,高達表SAMHD1和APOBECs在內的細胞限制性因子,這使得IL-34-Mφs能抵抗HIV-1的進入、整合和基因表達[13]。這為未來克服抗逆轉錄病毒障礙研究指出新的方向。CHIHARA等[12]研究發現人重組IL-34可通過增加黏附分子CD54、Ⅱ型組織相容性復合物HLA-DR、清道夫受體、輔助刺激因子等表達抑制HIV在巨噬細胞內復制。綜上所述,IL-34在抵抗HIV-1感染中發揮重要作用,可作為未來研究治療抗HIV-1感染治療的重要新方向[14]。
甲型流感病毒(IAV)是具有高度傳染性單鏈RNA病毒,免疫受損的個體感染后可能會導致疾病損害,宿主細胞因子免疫反應作為IAV感染的防御線。YU等[15]研究發現,與健康對照人群對比,甲型流感病毒患者外周血清IL-34、IL-22水平明顯升高,且表達呈時間、劑量依賴性;在炎癥反應期間,甲型流感病毒是通過IL-22途徑刺激IL-34的表達,而IL-34反饋性抑制IL-22的活性。因此,IL-34在有望成為治療甲型流感病毒感染抗炎的靶點。
日本乙型腦炎(JE)是由日本乙型腦炎病毒(JEV)感染中樞神經系統而引起的一種急性傳染病,簡稱乙腦,JE發病的根本原因是JEV感染中樞神經系統引起神經性損傷。JEV的終末宿主是人。目前接種疫苗是一種預防JEV感染的有效的措施,但仍有許多人感染,且針對感染者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尚未開發。1年內由JEV引起的腦炎約67 900人,其病死率范圍為20%~30%[16]。因此臨床應深入了解其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機制,為開發新型、有效的治療方法提供新的思路。李宗端[17]通過對JEV感染小鼠研究發現,經IL-34處理過的感染小鼠死亡時間較對照組明顯縮短;以小神經膠質細胞為模型,與PBS細胞組比較,加入IL-34的細胞組上清病毒滴度明顯升高,由此得出IL-34能明顯促進JEV在腦內的復制,明顯促進乙腦感染的進程并縮短小鼠生存時間。這為治療JE開發新型、有效的治療方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腎綜合征出血熱(HFRS)由漢坦病毒感染引起一種嚴重的急性傳染病。中國是HFRS最嚴重的流行地區之一。漢坦病毒感染誘導免疫系統激活導致不受控制的細胞因子風暴,包括白介素1(IL-1)、IL-6、CCL2、CCL4、TNF-α。相關臨床研究指出,與健康對照組對比,HFRS患者血漿IL-34水平明顯升高,具有統計學意義,且經積極治療后下降至正常;HFRS患者血漿IL-34水平與白細胞計數和單核細胞計數呈正相關,而與血小板計數和血清白蛋白水平呈負相關,這提示IL-34在HFRS中具有潛在作用[18]。由此得出,IL-34參與HFRS發病機制,檢測血漿IL-34水平,不僅有助判斷病情,也有助于療效評估,進一步研究可為HFRS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2.3 IL-34與真菌感染 白色念珠菌是一種真菌,是人類的機會病原體。正常情況下,白色念珠菌以無害的形式存在,不會觸發巨噬細胞在皮膚黏膜中的炎癥反應,這可能是由于巨噬細胞對白色念珠菌的耐受性引起的。XU等[19]研究發現IL-34通過抑制M1巨噬細胞關鍵的白色念珠菌模式識別受體(PPR)的表達,即Toll樣受體(TLR)2和Dectin-1,從而減少了M1巨噬細胞產生所產生的TNF-α,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IL-34可能通過維持低水平的巨噬細胞TLR2和Dectin-1表達來抑制常駐巨噬細胞對白色念珠菌定植的反應。
2.4 IL-34與沙眼衣原體感染 2015年,病原體沙眼衣原體在美國引起了1 526 658人感染(自2014年以來增加了6%)。由于75%~90%的婦女感染沙眼衣原體后無無臨床癥狀,因此通常會錯過治療干預的最佳時機,常常導致女性不育,也是女性盆腔炎及異位妊娠的主要原因,且會傳染伴侶。目前沙眼衣原體致病機理尚不清楚,但宿主免疫力和衣原體感染之間的相互作用被認為是主要原因。沙眼衣原體感染后可與宿主細胞模式識別受體相互作用觸發細胞因子反應,這些細胞因子包括了炎癥細胞介質,而這些炎癥介質被認為是衣原體疾病相關病理的主要元兇。研究發現,破壞人類輸卵管上皮(hOE)細胞系OE-E6/E7中的Toll樣受體3(TLR3)功能可明顯減少由沙眼衣原體誘導幾種炎癥生物標記物的合成,如IL-34、IL-20、IL-26、IL-34、可溶性腫瘤壞死因子受體1(sTNF-R1),腫瘤壞死因子配體超家族成員13B(TNFSF13B)等[20]。由此可見IL-34在沙眼衣原體感染致不孕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3 IL-34與非病原菌感染炎癥性疾病
類風濕關節炎(RA)患者滑膜、血清及滑液中IL-34的表達增加,滑膜IL-34表達與RA滑膜炎的病理嚴重程度呈正相關,血清IL-34水平與疾病活動指數(TJC和DAS28)、炎癥參數(ESR和CRP),自身抗體滴度(RF和抗CCP),以及其他炎癥因子,如IL-6、IL-17、MMP-3呈正相關,治療成功后,RA患者血清IL-34水平較前明顯下降,因此IL-34有望成為RA診斷、療效評估的新標志物,且可能成為治療RA新的靶標[21-23]。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患者血清IL-34水平高與健康對照相比,不僅與SLE臨床特征的累積顯著相關,還與全身性SLE活性指數、抗雙鏈DNA抗體水平、CRP水平呈正相關,但與補體C3呈負相關,SL患者治療成功后血清IL-34水平較前明顯降低,因此,血清IL-34對SLE的協助診斷和療效評價均有一定臨床意義[24]。研究發現在IL-34在原發性干燥綜合征(P-SS)患者唾液腺呈高表達,且與促炎因子TNF-α、IL-1β、IL-17、IL-23p19呈正相關[25]。也研究發現潰瘍性結腸炎小鼠腸上皮細胞表達IL-34,并且與炎癥程度成正比,提示IL-34為炎癥性腸病的新型調制器;IL-34的表達受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的影響,阻斷NF-κB途徑會導致結腸上皮細胞TNF-α刺激IL-34表達量的減少,這提示TNF-α通過阻斷核因子κB通路調控腸道皮細胞IL-34的表達[26-27]。
4 展望
IL-34作為目前研究重要的促炎因子,隨著對其不斷認識,了解其在多種疾病中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進一步深入的探究IL-34在疾病中的作用機制,不僅可以為多種疾病的診斷及療效評估提供新的生物學標志物,也可為多種疾病尤其是炎癥疾病的治療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和研究靶點治療提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