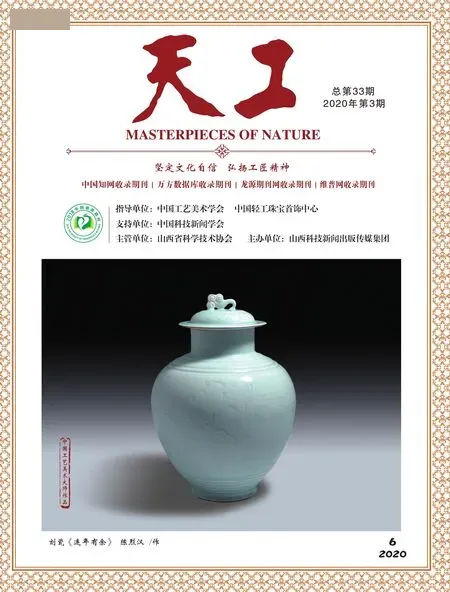中國古代早期玻璃的特點
文 王子凡
玻璃是石英砂經過高溫熔融后,變化成一種液態的無機物質,冷卻后在室溫中并不出現晶體結構。玻璃是一種硅酸鹽物質,其主要成分是石英,熔點是1750℃,由于條件限制,古代的燒制技術是無法達到這個溫度的,所以必須要在玻璃的主要原料中添加助熔劑,才能降低玻璃的熔點而制造出玻璃。多種不同礦物的不同組合,都可以幫助石英達成熔融的效果而制成玻璃。
一、“玻璃”與“費昂斯”
“玻璃”在中國古漢語中被稱為“壁琉璃”,或是簡稱“琉璃”。“琉璃”一詞原本出自外語,在西漢桓寬所著的《鹽鐵論》中第一次被記載:“鼲(hún)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漢書·西域傳》中記載:“罽賓國……出……壁琉璃。”《漢書·地理志》(下)中也記載:“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
從出土器物顯示,中國的原始玻璃最早出現于西周,而真正成熟的玻璃制品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才陸續出現。世界上玻璃最早出現于兩河流域地區,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種以石英為主要原料的粉末經過高溫熔融而產生的原始玻璃“費昂斯”。而真正成熟的玻璃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出現在古埃及和敘利亞地區。玻璃的概念和基本的制作工藝應該是從西亞進入中國的。但是根據從西周墓穴中出土的已知中國最早的“費昂斯”,其化學成分與西亞地區的化學成分略有不同。古埃及與兩河流域一直以來都是使用天然純堿加石灰作為助熔劑,被稱為“鈉鈣玻璃”。中國最早合成真正的玻璃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此時期的主要原料是石英,所搭配使用的助熔劑是含有鉛、鋇的天然礦物質原料,制成的玻璃稱為“鉛鋇玻璃”,在我國出土的戰國至兩漢的玻璃,大多數都屬于鉛鋇玻璃,成分與國外玻璃截然不同。這說明,雖然最早的原始玻璃是由西亞地區傳入中國,但是中國人在國外制作玻璃的原料基礎上改變了配方。
而“費昂斯”一詞出自意大利語,最初是指歐洲中世紀在意大利費安斯出產的一種藍色釉陶,歐洲人發現這種藍色釉陶與古埃及人制造的一種“原始玻璃”在外形和顏色上非常相似,便也將其稱之為“費昂斯”。之后,“費昂斯”便成為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人工合成的“原始玻璃”物質的統稱。雖然兩者在原材料上大致相同,但是其制造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費昂斯”是原始玻璃,也就是“玻璃”的前身。
二、原始玻璃的生產工序
古代原始玻璃的生產工序,可分為“造胎”“上釉”“烘燒”三個步驟。“費昂斯”胎芯部分的主要成分是蘇打、石灰、石英砂以及其他微量雜質。胎體塑造成型后先晾干,之后再加工修整、上釉。其釉料成分與胎芯成分一致,再加入銅礦作為著色劑,質地較胎芯更為光滑,其上釉方法主要有三種,每一種都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
風干法:“費昂斯”胎原料混合水分,塑成器物之后風干,氯化鈉成分升至表面結成晶體,入窯烘燒時與石英砂融合成光滑的表面。浸釉法:塑造成型的“費昂斯”經過風干之后,浸入釉料之中或者用其他方式涂上,即如陶瓷的浸釉法。埋粉法:“費昂斯”胎體風干后,埋于研磨細釉的釉粉之中,一同入窯燒成。釉粉與費昂斯胎體發生作用而黏合,其他不與胎體接觸的釉粉不會黏接在一起,燒成后容易清除。
以上三種施釉方式所得的效果各有不同,風干法造成原始玻璃的外露處較好,隱蔽處釉面較薄。浸釉法的胎體釉面較厚,可見釉料流動的痕跡。埋粉法,釉面不均勻,近火面比背火面的釉層要厚,釉層與胎體之間的分層明顯,沒有過渡區域。而中國“費昂斯”釉面光潔均勻,應該是使用浸釉法,有可能是受到當時制陶施釉技術的影響。
三、西周時期原始玻璃的特征
中國原始玻璃的特點是,造型單一,顏色單調,體積細小。器型主要分為管狀和串珠,色澤上只有松石綠和深綠色,以及其他的罕見色澤。中國出土的西周原始玻璃是利用石英砂成型的,再經過加熱使部分石英晶體熔融而成型,其外表也與西亞出土的“費昂斯”十分相似,燒成溫度在800℃~1000℃之間,露火部分的石英砂熔融效果較強,胎芯部分的石英砂熔融較弱,殘存的晶體也較為明顯,一般原始玻璃的外層釉料研磨較細,在加入染色劑后,外表光滑明亮。西周時期的原始玻璃主要器型為管形、球形、橄欖形、算珠形四種。
西周時期的原始玻璃所用的助熔劑配方并不統一,以氧化鋁和氧化鈣為主要成分,是利用當地或周圍所產的黏土摻和大量的石英所制成的。考古發現西周時期出土的原始玻璃器物,一般與各種玉石瑪瑙等材質在一起,通常在人體骨架的位置發現,作用應該是與這些玉石瑪瑙器物組合而成的配飾。
四、春秋戰國時期玻璃的特征
原始玻璃的制造工藝不同于冶煉青銅器和陶瓷,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早期玻璃制品都具有高度的專業水平。中國成功自制的較為成熟的玻璃的特點是利用鉛和鋇作為助熔劑,鉛和鋇的加入有效地降低了玻璃的成型溫度,改善了原始玻璃,從而生產了真正的玻璃原料。另外,戰國時期的湖北地區曾經生產過以鉀、鈉、鈣為助熔劑的熱加工玻璃珠。
春秋晚期,中國出現了新的玻璃品種,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在劍格上鑲嵌有兩塊半透明的淺藍色玻璃,兩塊玻璃形狀不同,一塊呈球冠形,另一塊形狀不規則,其直徑不超過1厘米。這兩塊玻璃顯然與西周時期的淺綠色且透明度較低的原始玻璃截然不同,經過分析兩塊玻璃的制作原料中不含鉛、鋇,應屬于新型的玻璃制品。這一時期有頗多的新型玻璃制品出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蜻蜓眼珠”。
“蜻蜓眼珠”一詞起源于玻璃珠表面上的紋飾,表面觀察為若干顏色套環,部分微凸起于胎體表面,很像蜻蜓的復眼。“蜻蜓眼珠”款式多樣,除微凸于胎體之外,并有一些平浮于珠面,也有凸起呈角錐狀,眼珠組合除了呈同心圓排列之外,也有離心圓。在玻璃坯體上配上藍白兩種色調的玻璃,做出乳釘紋。根據湖南省出土的“蜻蜓眼珠”玻璃及玻璃管發現,其原料中含有鈉、鈣成分,與西方的“鈉鈣玻璃”的組成配方一致。
戰國時期,是“蜻蜓眼珠”的鼎盛時期,中國出土的早期“蜻蜓眼珠”的造型十分簡單,不含鉛、鋇,屬于“鈉鈣玻璃”的范疇,顯示出此時的中國在制造玻璃的工藝上屬當時較為先進水平。根據中國本土自制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蜻蜓眼珠”的化學組成和風格分析,可以將中國的“蜻蜓眼珠”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組合型“蜻蜓眼珠”,紋飾結構復雜,珠體上不僅有眼的紋飾,而且還有不同顏色玻璃組成所構成的幾何圖案。第二類:小點網紋“蜻蜓眼珠”,其眼飾通常為交錯排列,再加上白色小圓點排列組成的網紋圖案作為分隔,部分網紋交織點再增加一個眼紋裝飾。其特點是填充更多的眼紋之間的空位并且使整個圖案排列得更為對稱,紋飾組合也要求系統性和規律性。第三類:陶胎“蜻蜓眼珠”,以赭色畫出實線的網紋,其眼紋裝飾由棕、黃、天藍等玻璃質涂料組成,底色為白色,可以更好地襯托出整體的斑斕效果,眼紋裝飾均微凸于珠面。第四類:方形“蜻蜓眼珠”,整體略做矩形立方體,圓角。表面的八個圓角都用淡綠色顏料進行裝飾,并在周圍圖繪棕色圓圈,圈的中間有棕色的小點,圈與點之間有白色料進行裝飾。
通過對中國早期玻璃特點的探究,我們發現中國玻璃自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普遍為鉛、鋇成分之外,其配方在不同年代都處于不停地改變之中,如西周時期的原始玻璃的主要助熔劑為鉛、鋇,但在春秋戰國“蜻蜓眼珠”十分流行的時期,其主要助熔劑成分為鈉、鈣,從而使中國的玻璃制造工藝達到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制作出了真正的玻璃。這樣的演變也是中國玻璃發展與西方最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