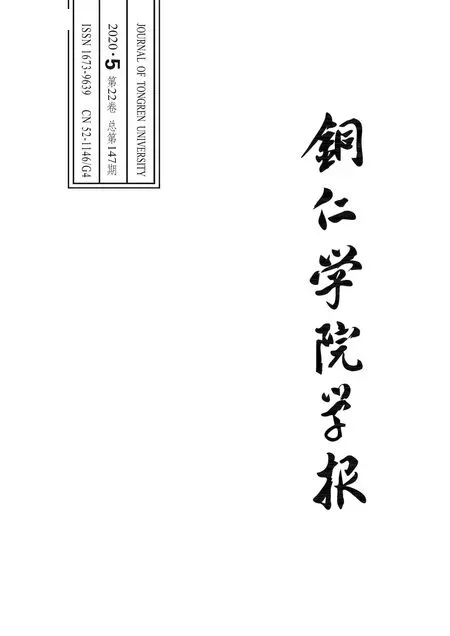疾病信仰與治療儀式:黔江苗族疾病的醫學人類學考察
向青松,孫 陽
疾病信仰與治療儀式:黔江苗族疾病的醫學人類學考察
向青松1,孫 陽2
(1.云南大學 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2.湖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
早期的苗族醫藥治療有一種說法“巫醫一家,神藥兩解”,苗醫被賦予了“巫術師”和“醫療師”的雙重身份,因而自古以來在苗族文化和苗族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位于武陵山區的黔江苗族中的苗醫至今也具有“巫醫一體”的特質。基于人類學的視角,探討黔江苗族的疾病信仰與治療儀式,深度剖析作為疾病治療主體的“苗醫”的身份象征與神秘性,最終形成對地方民族文化的認知,以此加深對民族文化異質性的認識。
苗族; 治療儀式; 原始信仰; 醫學人類學
一、問題的提出
在古代中國,醫學技術并沒有像現代醫學這樣發達,古人們更多地把疾病治療與民間信仰、宗教觀等結合起來,在特殊意識形態的指導下進行種種文化實踐儀式。現代的鄉村社會中,受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的影響,特別是地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影響,依舊沿用祖輩遺存的疾病傳統治療方式。從醫學人類學的視角來關注對于疾病的認知和治療方式,一直是人文社科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如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就特邀清華大學景軍在2019年11月開展了“人文社科”第一期的工作坊,圍繞公民健康、鄉村疾病與醫療以及醫學倫理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的探討,隨后又邀請國內外諸多學者開展了多期工作坊,并由此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也加深了學者們對醫學人類學的探討。老一輩人類學家中,許烺光先生根據在云南發生的霍亂,以個案的方式進行分析,并結合香港的鼠疫進行對比探討[1]。目前諸多學者關注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的少數民族疾病與治療方式,在獨特的靈魂觀念支配下,哈尼族社會中保存著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治療儀式,徐義強從醫學人類的視角對哈尼族的叫魂治療儀式進行了探討,指出哈尼人對疾病、死亡和健康的看法與其靈魂觀、身體觀密切相連。儀式治療的療效與選擇又與其地方文化知識體系和外部社會因素息息相關。因此,只有將叫魂儀式置于哈尼族豐富的社會文化脈絡中進行動態分析,我們才能發現哈尼族疾病與治療實踐的行動邏輯,得以了解傳統的儀式治療是如何起到維系當地社會運轉的重要功能[2]。潘天舒在田野實地考察、深度訪談和挖掘歷史記憶的基礎上,通過對2005年浙江海寧地區從各級政府和防疫部門到普通民眾應對禽流感威脅的策略和措施的分析,揭示了在危機過程中得以充分激發的“集體生存意識”,是如何促使傳統“調適性智慧”與現代流行防疫知識的有機結合,并融入了抗擊流行性瘟疫的現代實踐中[3]。趙巧艷對侗族傳統社會的主體醫療方式之一“收驚療法”進行了考察,這一傳統的宗教巫術性治療術仍然在侗族鄉村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療法與其侗族的靈魂信仰存在密切的聯系,靈魂崇拜與安魂儀式在這一療法中得以深深展演[4]。巴莫阿依指出,涼山彝族的疾病認知與其傳統信仰密切相關,初步認為在彝族信仰中疾病具有七類超自然的病源,分析了彝族儀式療者的類型及其特點;在歷史進程中,涼山彝族形成了集靈魂信仰、祖先崇拜、鬼神信仰、靈物崇拜為一體的信仰模式,祭祀、巫術、占卜、禁忌為其活動內容的原生宗教信仰,這些信仰影響著彝族人對疾病的認識與實踐,儀式醫療是彝族傳統醫療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5]。嘉日姆幾指出彝族人臨終關懷的實踐來源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從彝族人生死觀以及從占卜、察言觀色以及醫院診斷的方式來界定臨終狀態等方面來分析彝族人的臨終關懷行為,借助宗教儀式來實現對臨終者及其家屬心理支持[6]。看本加、林開強對絲路文化視野中的藏族護身符進行了研究,主要探討了護身符所體現的對疾病的認知和治療觀念,并力圖揭示藏族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審美觀,以及宗教信仰和身體之間的緊密關系[7]。醫學人類學視野中的疾病治療,根植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是一種綜合性的應對疾病的過程。楊躍熊從醫學人類學的角度對大理居民所患蕁麻疹進行了分析,大理居民將蕁麻疹的病因歸因于游魂“姑悲惹”附身,并因此進行了一系列的儀式操作,然而在這些儀式治療的背后展現了白族的生死觀、空間觀以及宗教觀,而“姑悲惹”治療儀式的背后更是展現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系[8]。羅鈺坊以興安村土家族的過關儀式為個案,從醫學人類學與象征人類學的視野,分析了興安村過關儀式請神上香、執符念降和斷卦、過關解煞、送茅船四個過程與內在的實踐邏輯,在共同文化形塑的疾病解釋模式下病人及其家屬在巫師構建的想象空間中的思想情感體悟以及儀式參與者對病痛治療的共同參與來分擔患者的病痛,最終使得患者和家屬獲得心理慰藉,同時構建新的社會關系[9]。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疾病治療儀式也各有差異,但都在這個特定的族群場域內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不同的民族對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都有自身的一套治療方法,與地方本土滋養起來的本土知識結合,形成了關于疾病的地方性知識,并以此來認知和詮釋疾病。目前學術界對于民間疾病傳統治療儀式逐漸予以更多的關注,而民間歷史悠久的傳統治療方式也被當地人所認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幾點:第一,民間對于疾病的傳統治療方式由來已久,在地方文化中根深蒂固,深刻地影響著當地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實踐;第二,現代醫療資源的分布不均,東部與中西部、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嚴重的資源不均;第三,現代醫療技術的發展,其醫療費用過高以及人們對于現代醫學的觀念存在一定的認知缺失。
黔江,《禹貢》為梁州之城;商周為巴國地;秦屬巴郡;漢初,為涪陵縣地。清光緒《黔江縣志》:“黔江,邑鄰五溪,界古黔州及施州,為川楚僻路,天下有事,易擾難靖。”[10]43這里,與彭水、酉陽、秀山等地聯片,史稱“蠻夷之地”。黔江現今位于重慶市東南邊緣,巫山山脈與大婁山山脈結合部,武陵山腹地,東北、北與湖北省咸豐、利川市交界,西與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相鄰,東南、南與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毗連,地處渝鄂咽喉之所。境內屬于亞熱帶濕潤性季風氣候,氣候溫和,四季分明;為山地地形,崎嶇不平;農作物方面,以種植玉米、紅薯、土豆等為主;在河谷地區,依據河流優勢,多種植水稻,一年一季[11]。境內的居民來源甚廣,主要有土著世居、巴人遺裔、以及移民遷徙、避難落籍、募民墾荒等方式遷移至此,多為苗族、土家族,小部分為漢族[10]583。黔江是重慶市主要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之一,是重慶市唯一的一個由土家族、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自治縣改設的少數民族區,黔江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悠久,其苗族、土家族的婚禮、葬禮都有著濃郁的民族特色。[12]民居建筑為桿欄式建筑,有較為傳統的吊腳樓、木制瓦房,也有較為現代的磚瓦房,當地的苗族、土家族大多生活在偏遠的鄉村。黔江處于武陵山區,偏遠鄉村交通不便,資源較為缺乏,因而在諸多鄉村地區還采用傳統的疾病治療方式,而這些傳統的治療方式與當地的苗族文化密不可分。綜上所述,一方面,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對黔江苗族地區進行過疾病信仰與治療儀式方面的研究,特別是缺乏從醫學人類學的視角進行研究,這將是對該田野點研究上的一個創新。另一方面,對于民間苗族疾病傳統治療方式的關注,能夠更好地了解苗族傳統醫療體系,以及其中所蘊涵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質,加深對民族文化異質性的認知。
二、民間疾病信仰
黔江苗族人對生與死有著獨特的看法,其獨特的看法的形成一方面是受當地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當地落后的條件所致。當有孩子出生的時候,被認為是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為此要舉行隆重的儀式。按照當地傳統的規矩,孩子出生十天后,就要舉辦一場宴席,名為“送飯”(為當地方言,主要是為了慶祝新生兒的到來和母子平安),主人家就會通知周圍的鄰居以及三親六戚,慶祝新生兒的到來。在孩子生下來的三十天之內,產婦和孩子都不能出門,只能呆在家里,這被認為是對孩子和母親的一種保護。而且對于飲食有著獨特的選擇,一般都是以肉類為主,蔬菜則少吃。一個月內不能出門的禁忌和飲食選擇的背后,展現了當地苗族人的一種原始民間信仰,即在孩子生下來這段時間,母親和孩子的身體是極其虛弱的,而新生命的到來也意味著靈魂投胎轉世的新生,但世間也還有一些游魂的存在,此時很容易依附于體質偏弱的新生兒和產婦身體,為了避免游魂作怪,所以孩子和母親在一個月內不能跨出家屋大門,因為家屋內有供奉的祖先在庇佑;而飲食的偏好選擇也是為了增強體質,避免不好事物的沾身。其“送飯”儀式的社會結構,一方面是為了讓當地的苗族人共沾新生的喜氣,實現苗族族群的延續;另一方面,苗族親鄰在“送飯”這一天共同聚集到主人家,使得親屬關系網絡再次緊密聯結,通過給孩子“認親”(是給新生兒認一個或多個干爹干媽,使得孩子在干爹干媽的庇護下得以健康成長)儀式使得新的擬親屬得以出現,實現了家庭與家庭間社會關系的再造。當人感覺到要離世之際,當然這里所說的“離世”主要是指自然死亡的人,多為老死之人。家人會聚集到一起,給將要離世之人準備一些好吃的食物,整個過程并沒有太多悲傷情境。對于當地苗族人而言,生老病死是自然的選擇,并不可強求。而在人去世之后,家中會舉辦隆重的葬禮來為逝者送行,并且也會為逝者尋找一塊風水寶地,之后由“亡人”身份轉換為“祖先”身份。事實上,葬禮作為“生者”向“逝者”的一種過渡,表達了對于逝者的認可和尊重,逝者最終會被納入進祖先的牌位坊之中,能夠被后人所祭祀和供奉,這在當地苗族人看來是一種功德和孝文化的展演。
早期的苗族醫藥治療有一種說法“巫醫一家,神藥兩解”,意思就是苗族人把巫術和醫藥治療從二元對立轉換成一元結合,最終發揮出其獨特的功效。當然這是把原始的宗教信仰與疾病治療結合起來。當疾病來臨,黔江鄉村的苗族人首先選擇不是去醫院尋求治療,而是去找當地的苗醫尋求幫助,傳統的苗醫在疾病治療儀式過程中不會使用現代醫學手段和技術,只是用一些在山上采集的草藥進行輔助治療,這就是民間一直流傳的“千年苗醫、萬年苗藥”。同時鄉村社會中的苗醫往往還具有一種民間“儀式”執行者的身份,通過一系列特殊的巫術儀式來找出隱性存在的“病源體”,在諸多儀式實踐過程中,苗醫的身份逐漸附帶了“巫術師”的身份。疾病治療不僅僅依賴于藥物的治療,同時也通過當地的民間巫術信仰來診斷和治療,最終形成了“巫醫一體”的身份和治療方式。
凌純聲、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指出,苗族人現在還保存的巫術有兩種:一種是“化水”,是一種白巫術,其作用是治病救人;另外一種是黑巫術,其作用是害人生病,比如放蠱[13]。由此可見,他們二人將苗族醫藥歸入為巫術的范疇,認為巫術是一種實用性的技術。在黔江當地,苗醫的身份也與凌、芮二人的描述近乎一致。但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苗醫承載著“巫術師”身份的背后,是與當地苗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有著深刻的關聯。當地的苗族人一直有著祖先崇拜、靈魂崇拜等原始信仰,每次遇到重大災難或者患病等都會先祈求祖先的庇佑,并在祖先的庇佑下得到治愈。逢年過節以及重大節日或者儀式時,當地的苗人都會帶上豬頭肉、白酒、香燭以及火紙(冥幣)等敬獻祖先神靈,在自家的家屋旁邊也會點一些香燭和火紙,其目的在于敬獻游離在家屋周圍的游魂,以防家人受到傷害。當地的苗族人相信家中所遇到的災禍,都是祖先需要后人盡孝的暗示以及世間各種游魂在作祟,故意在一些地方埋下禍根。所以,當地苗族人一直延續并信仰著這種原始的祖靈崇拜。這和許烺光在《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一書中描述的喜洲當地人有著類似的情景,喜洲人極度崇拜祖先和各種神靈,遇到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情時,人們都會積極地祭拜祖先,當地人認為他們自己所經歷的和所獲得的東西都是在祖先的庇佑下才得以成功,并且祖先和各類神靈是不可侵犯的,必須要及時地進行各種獻祭[14]。一旦對祖先不虔誠和不盡孝,那么這類人將處于祖先庇護的邊緣,成為危險的邊緣人。
三、疾病治療儀式
在當地苗族人祖先崇拜、靈魂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下,人們的各種行為實踐也緊緊圍繞著這個中心而進行。下面以一個疾病治療的實例來看待當地苗族人的信仰與疾病治療之間的關系。這一個例子是筆者在2019年田野調查時所獲取的資料。筆者在村子中發現一家人在做“儀式”,據了解,這家人中有一位少年不幸得了一場大病,而從當地苗族人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背景出發,一旦患病其首要選擇就是尋求當地苗醫的幫助,當時與這位少年交談得知他一直處于頭疼的患病狀態,總感覺頭隱隱作痛。于是,他的家人便去請了一位苗醫過來看病,苗醫觀看了他的身體狀況后,又圍繞家屋環視了幾圈,苗醫最終下了一個結論,即家中的一祖墳旁邊有兩塊石頭壓著。隨后,筆者跟隨他們家人去看了那座墳,旁邊確實有兩塊石頭因下雨從坡上掉落下來。然后在苗醫的指導下,把兩塊石頭搬離墳墓,又帶來一些香燭、火紙和豬頭肉在墳墓前獻祭祖先,苗醫嘴里也不斷的念叨著一些經文話語。同時,這位苗醫也給患病的少年備置了一些不同種類的草藥,錘成粉末之后放入溫水中喝掉。第二天患病少年就給我說他的頭疼狀態開始得到緩解。然而,幾天之后又出現了頭疼狀態,這時家人覺得去醫院檢查一下為好,然而在諸多大小醫院做了全面檢查,甚至住院了幾天,最后還是無功而返。而他們又不得不向周邊地區的苗醫尋求治療。后來在少年親戚的介紹下,認識了一位附近村子的苗醫。于是,他們就把這位苗醫請到家中,也是先檢查了患病少年的身體和查看了家屋周邊的情況。最終進行了三天的儀式,少年的病得到了痊愈。開始儀式的第一天早上筆者很早就趕到少年家中,發現苗醫在家屋的大門前擺了一張小桌子,然后在一張黃紙上畫了一道符,用刀輕輕割了一只公雞的喉嚨,滴了三滴血在那道符上,最后把這道符點燃燒為灰燼,放入裝有水的碗讓少年將其喝掉,舉行這個儀式的時候,苗醫嘴里也是一直在不斷的念叨著,但至于具體念的什么不得而知,儀式完畢,讓少年朝著家中祖墳的方向磕了三個頭。第二天,苗醫帶著少年和他的家人去到祖先的墳墓前,苗醫一直讓患病少年跪在墳墓面前,他則是把提前準備好的各種祭祀物品放在墳墓前,接著他拿出裝了一個稻谷和玉米的碗,將其稻谷和玉米撒在墳墓周圍并圍成一圈,而少年就在這個圈內,撒完從墳墓上采集了一種植物,讓少年拿回去熬水喝;最后,讓少年朝著家屋的方向又磕了三個頭。第三天,苗醫帶著少年在家屋前面走了三圈,也是邊走邊撒稻谷和玉米,苗醫手里拿著一個類似于經幡之類的東西,邊走邊念叨。經過三天的儀式治療之后,少年的頭痛癥狀確實有所減輕,苗醫臨走之前還留下了一幅類似于“觀音抱子”的畫卷,讓少年的家人一直掛在家屋大堂,并且告誡要連續七天在飯前獻祭祖先。經過幾天的儀式后,少年的頭疼狀態有所緩解并最終痊愈。
當時看來,苗醫的種種儀式行為在外人看來確實無法理解,甚至被很多人說成了“迷信”。殊不知這種疾病治療儀式是與當地的苗族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種種儀式背后,均與當地苗族的生活以及精神信仰緊密相連。這些儀式實踐所展現出來的是苗族人對于祖先的敬畏以及對于神靈的尊重,是當地苗族人延續著的歷史文化和記憶。近年來,筆者仍然見過很多人依舊采取這種傳統的治療方式,有些人在苗醫“巫醫一體”的治療下,疾病確實減輕以致最終痊愈。
一般認為,具身性思想萌芽于Lakoff和Johnsen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Lakoff和Johnsen在該著作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隱喻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無處不在,不僅在語言中,而且在思維和行動中處處都有隱喻的蹤影,其隱喻的本質是用該事物理解彼事物,用某一認知領域的經驗理解另一認知領域的經驗,是原始域對目標域的投射[15]。隨著人類學的出現,具身性(embodiment)也成為了人類學所關注的一個方面,其意指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差異,都可以通過人們的身體認知、身體觀念、身體體驗、身體感覺體現出來[16]。張文義從構詞角度來探討了具身性(embodiment)的概念,他認為英語中的body變動詞embody時有兩個意義:第一,把身體之外的社會放到身上,即身體再現了社會;第二,讓身體具有力量。綜合起來,embodiment就是社會的東西印到了個體身上,個體把它變成獨具特色的東西[17]。
在民族志的研究和表述中,身體的“缺席”不應該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我們需要對身體的存在和作用進行反思;具身性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物:我們對于世界的認識基于在世的存在的,只有以身體作為基本工具,我們才能與世界互動,進而理解;所以人類學必須立足于人們的內在感知,關注具身體驗,理解外在的社會文化是以何種方式來完成自我的建構,進而作用于個體日常生活的[18]。黔江苗族人在尋求苗醫的治療過程中,對于患者而言,具身性(embodiment)的展演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其一,家中有人患病,家屬會第一時間去幫助患者去請苗醫,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患者的請求,首先就在心理上建構了苗醫以及救治的這樣一個形象和功用,這時患者就把“主體(自己)”之外的“他者(苗醫)”放在了自己身上。其二,在儀式治療中,苗醫和患者的身份狀態出現置換,苗醫成為了儀式中的主體,而患者成為了“他者”,這時的“他者”在主體的藥物和巫術儀式治療下,身體體驗和身體認知逐漸出現反應。具身性展演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即患者在雙重治療后身體機能逐漸恢復,被認為是在苗醫的幫助下得到了祖先的再次庇佑,修復了人與神靈之間的關系,身體的恢復再現了祖先力量的強大。其實,身體的變化被視為一種技術的展演,身體也被視為一個承載族群社會文化的象征體系。
四、人類學視角下的“苗醫”
(一)“苗醫”的身份象征
苗族醫藥在苗族社會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于現代醫學上的西藥治療方式,苗藥大多從深山老林或者懸崖峭壁上采集,黔江鄉村社會中苗醫所使用的苗藥多為深林中獲取。這些藥物較為普通常見。苗醫采集多種植物,將其磨成粉末或者切成小塊,按照一定的比例調制。這樣經過混合調制才能形成最終的藥物,而單單一種植物卻無法成為治療疾病的藥物。遠古時期的苗族先民,對于大自然中自然現象和規律無法理解,如風雨雷電、生老病死等,于是他們對這些現象和運行規律產生了畏懼。當他們依靠自己僅有的常識無法來解釋這些事物的時候,他們便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具有保護意義的事物上,并對其加以崇拜和信仰,祈求靈物不要將災難降臨在他們身上。這樣就把人的屬性和自然的屬性通過崇拜和信仰的方式結合,于是就產生了苗族崇拜自然物的原始宗教。由于這些自然物所具有的“靈”,所以也把這些自然物當做“神”一樣來崇拜和祭祀。后來,由于人群知識的拓展和技術的發展,逐漸轉向對以“人”的崇拜和信仰,進而形成了祖先崇拜和靈魂崇拜。
黔江鄉村社會中的苗醫通過藥物和巫術儀式的結合,來治療人群所患的疾病。藥物治療也有其功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身體的疼痛,但當地苗族人認為這只是治標的方式,要治療疾病之本,還是要通過相關儀式進行治療,最終消除疼痛以及尋求精神上的安定。而巫術儀式的進行所受指導的是當地苗族社會一直以來延續的祖先崇拜、靈魂崇拜意識。其實,在當地苗族社會中,人群并不僅僅在疾病治療的時候需要尋求苗醫的幫助,而在家庭遭遇災禍之際,也會尋求苗醫的幫助,而苗醫通過一系列的儀式進行驅災辟邪,其背后的救治方式多是向祖先的敬獻、與靈魂的交觸。實際上,苗醫是作為活著的人與逝去的祖先之間溝通的橋梁,作為生者與逝者的中間人,具有某種“靈力”的存在。而通過具有“靈力”的苗醫舉行相關的儀式,其人與祖先的距離在“拉近”,從而在祖先的庇佑下使得疾病得以祛除,患病之人得以回歸本位。苗醫的身份在現實和儀式中具有了二元性,在現實生活中被當地人視為是擁有某種“靈力”或者超自然能力的人,在舉行儀式之際,則成為人與神、祖先之間溝通的橋梁,處于一種“閾限”狀態。
(二)“苗醫”的神秘性
苗醫具有“巫醫一體”的色彩,因而也展現出神秘性。苗醫的神秘性展演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當找到苗醫去治療疾病之時,苗醫并不是立馬就答應施醫,做出選擇之前,苗醫會簡單地向家屬了解病情。了解有關病情之后,苗醫會單獨來到自家家屋的香火神龕前,香火神龕主要供奉的是祖先和各路神靈。在香火神龕下,苗醫跪下來使用工具進行占卜,通過特定的儀式來查看今天是否適宜出行治病。其實,在整個占卜過程中,苗醫也是在尋求祖先的指示,占卜只是一種表面的儀式行為,但具體行醫與否還需要得到祖先的明示和庇佑,因此附了神秘色彩。正如許烺光在《祖蔭下》一書中,描述大理喜洲人所進行的日常生產和生活都要經過一定的儀式活動,以求得祖先的庇佑[14]。第二,藥物配制的神秘性,當地苗醫在治療疾病過程中,也會使用到一些中草藥,根據不同的病癥,調制出不同的配方,而這些調制的比例和配方只有苗醫自己知曉,從不輕易語示外人。第三,儀式中操作的神秘性,苗醫在舉行疾病治療儀式時,患病者及家人要準備好儀式中所用到的物品,如香燭、火紙、雞、豬頭肉等。儀式過程中苗醫每到一處會念相關的咒語經文,患者要嚴格按照苗醫的指示行事,整個儀式過程中,任何人也不得以詢問苗醫此種行事的緣由。苗醫在治療疾病過程中,各種儀式操作烙上了神秘色彩,似乎一旦具有苗醫的身份,其治療實踐中便遵循一套身份規則和行醫規則,決不可將儀式中任何巫術性的操作教給別人。作為地方文化濃厚的少數民族地區,苗醫和詳細的治療方式都作為一種不容侵犯的習慣傳統,烙上了神秘的色彩,在苗醫看來,這似乎是不可泄露的“天機”,參與儀式的人們也在治療與被治療中維持著平衡,防止規則的打破,祈求“巫醫一體”的醫與靈。
其實,患者優先選擇苗醫進行醫治,不僅是當地一種由來已久的做法,更是一種對于祖先的敬意和信任,認為通過苗醫的治療儀式會重新得到祖先的庇佑。從當地苗族傳統文化中的孝文化而言,苗醫幫助患者治愈疾病是一種孝文化的表達,這種孝文化的表達有著雙重含義。從顯性表達來看,對于長輩而言,幫助長輩尋求治療方式,被認為是在對長輩盡孝,長輩歷經辛酸將其后人拉扯長大,實屬不易,后人應該在長輩遇到困難時積極伸手幫助;從隱性展演來看,家中有人患病,家屬優先尋求苗醫的幫助,這被認為是對于已逝祖先的孝意,當地人認為苗醫更多地承載了能與祖先交流的身份象征,尋求祖先的幫助說明內心一直把祖先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以此來展示當地祖先崇拜、靈魂崇拜的疾病信仰。
五、結語
從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對黔江當地苗族的疾病治療體系進行探究,終而得出幾點認識:其一,作為疾病治療主體的“苗醫”在黔江當地苗族社會中依舊占據一定地位,當地人患病首要尋求苗醫的診治,傳統的苗醫治療方式至今未被湮沒;其二,巫醫并行,苗醫集藥物治療與巫術治療于一身,同時施行于患者,扮演多重身份;其三,苗族的祖先崇拜、神靈崇拜原始信仰在黔江苗族鄉村中仍在延續。傳統的苗族醫學是與其民間原始信仰結合在一起,黔江苗族鄉村社會中的苗醫集“巫醫一體”,在神圣與世俗的二元共生治療儀式的這個場域內依舊發揮著作用。藥物治療與儀式控制仍然被當地人認為是一種合理和可被接受的治療方式。
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曾說過:“治療術的本質在于使某一既定的局面首先從情感方面變得能夠被想象,使肉體難以忍受的痛苦變得可以被思想所接受”[19]。其實這是一種從情感、思想接受的心理效應。黔江苗族疾病中所施行的“巫醫一體”治療儀式,其實不僅僅是一種對于身體生理上的治療,更是一種地方族群的社會文化治療,有利于維持地方族群社會的平衡與發展。不論儀式治療是否具備生物學意義上的醫學功效,在地方性知識系統內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1] 許烺光.驅逐搗蛋者[M].臺北:南天書局,1997.
[2] 徐義強.哈尼族治療儀式的醫學人類學解讀[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84-88.
[3] 潘天舒,張樂.流行病瘟疫與集體生存意識:關于海寧地區應對禽流感威脅的文化人類學考察[J].社會,2007(4):34-40.
[4] 趙巧艷.侗族靈魂信仰與收驚療法——一項關于B村的醫學人類學考察[J].思想戰線,2014(4):70-75.
[5] 巴莫阿依.涼山彝族的疾病信仰與儀式醫療:上[J].宗教學研究,2003(1):37-40.
[6] 嘉日姆幾.試析涼山彝族臨終關懷行為實踐[J].社會科學,2007(9):124-127.
[7] 看本加,林開強.信仰、符號與疾病治療——絲路文化視野中的藏族護身符[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1):67-70.
[8] 楊躍熊.游魂、空間與蕁麻疹——大理白族“姑悲惹”治療儀式的醫學人類學解讀[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43-45.
[9] 羅鈺坊.儀式療法:土家族過關儀式的醫學人類學闡釋——以鄂西興安村為個案[J].貴州民族研究,2018(1):89-92.
[10] 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編篆委員會,編.黔江縣志[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
[11] 何澤祿.黔江地區志[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28.
[12] 向青松.黔江苗族婚俗儀式與親屬實踐[J].凱里學院學報,2020(4):58.
[13] 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4] 許烺光.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M].臺北:南天書局,2001.
[15] George Lakoff,Mark Johnsen.Metaphors We Live By[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6] 劉倩.身體的邊界性與“去邊界化”——基于醫學人類學的研究和反思[J].醫學與哲學,2017(21):35-38.
[17] 張文義.社會與生物的連接點:醫學人類學國際研究動態[J].醫學與哲學,2017(19):39-42.
[18] 和少英,姚偉.中醫人類學視野下的具身性與多重世界[J].思想戰線,2020(2).
[19] 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M].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09.
Disease Belief and Treatment Ceremony: A Med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Diseases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jiang
XIANG Qingsong1, SUN Yang2
( 1. Research Center of Border Regions and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2.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
In the early Miao medical treatment,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the witch doctor family, the two medicines", Miao doctor was given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wizard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 and thu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ao culture and the Miao society since ancient times. Miao medicine in Qianjiang of Miao nationality, located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witchcraft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sease belief and treatment ceremony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jiang, deeply analyzes the identity symbol and mystery of Miao medicine as the main body of disease treatment, and finally forms the cognition of local national culture,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heterogeneity.
Miao, treatment ceremony, primitive belief, medical anthropology
C955
A
1673-9639 (2020) 05-0114-08
2020-04-26
向青松(1996-),男,苗族,重慶黔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學,亞太民族研究。
孫 陽(1995-),男,河南安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代史。
(責任編輯 車越川)(責任校對 黎 帥)(英文編輯 田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