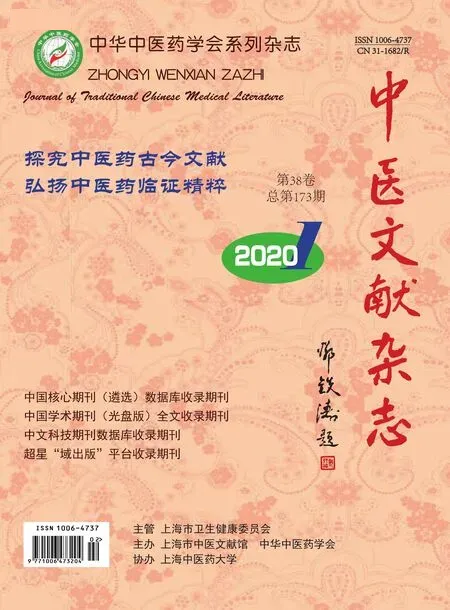《血證論》血下泄證論治規律研究
河北省兒童醫院(石家莊,05003)
《血證論》作者為清代著名醫家唐宗海,該書為中醫血病專著,在歷代醫籍中獨樹一幟。《血證論》全書共八卷,強調了水、火、氣、血的相互作用與轉化在血證病因病機和發展轉歸過程中的重要意義。本文旨在通過對《血證論》中便血、便膿、尿血、崩帶、產血等“血下泄證”內容進行深入系統研究,體會唐氏對于血證的論治思想與用藥心法。
下部出血,從肺論治
唐宗海在血下泄諸證(便血、便膿、尿血、經血、崩帶、產血)的診療中,突出了“從肺論治”的思想,值得關注和深思。在遣方用藥時,注重宣、潤、清三法,密切配合,協同發力,確有殊功。
1.宣肺善用“風藥”,喜遣荊防
“風藥”一詞首見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的著作中,特指具有生發、疏散作用的藥物,具有宣肺、疏利、升陽、祛風等作用[1]。唐氏在諸多“風藥”中,較為青睞荊芥與防風。在篇幅并不長的《血證論·血下泄證》(卷四)中,荊防共出現三次,分別發揮“疏理其氣”“治太陽、陽明傳入之風”“瀉濕清熱”之功。荊芥以散為功,以辛為用;防風氣味俱升,性溫而潤。荊芥入血分,散營陰郁熱,引邪外透;防風走氣分,散風勝濕止癢,二藥相合,氣血同調,風祛而濕清,氣順而血和。
2.潤肺頗愛花粉,多配柴胡
在血下泄證的論述中,天花粉共出現四次,值得關注,可視為唐氏滋陰潤肺的首選藥之一,且每每都與含有柴胡的名方相伍用,即花粉與逍遙散、柴胡湯、小柴胡湯、大柴胡湯相配。天花粉稟天地清陰之氣以生,最善潤枯燥而行津液,《景岳全書》贊其“有升有降,陰中有陽,最涼心肺”。柴胡疏肝,升發陽氣[2],與花粉相配氣陰雙補、體用皆養、滋陰生津、“升發清降”、“兩得其治”。且花粉滋陰力強,能在較大程度上彌補柴胡“截肝陰”之弊,以得萬全。
3.清肺恒賴“瀉白”,常伍人參
在血下泄證諸篇中,唐氏退肺熱的方劑出現次數最多的就是人參清肺湯和人參瀉肺湯。仔細觀察藥物組成即可發現兩點共性,一是均有桑白皮和地骨皮組合,二是均含有人參。“二皮”同用,乃遵宋代錢乙瀉白散的要旨[3],清熱而不傷陰,瀉肺而不損正,使肺清氣肅、肺恙可除。既言“清肺”“瀉肺”之名,人參在此看似“不合時宜”,實則匠心巧妙。血證日久,失血甚多,必有傷津耗液,氣隨津泄之變,人參大補元氣,契合古語“血脫者益氣”之義。血不自生,須得生陽氣之藥乃生,陽生則陰長,血乃旺也。且人參亦別名“土精”,最善補脾胃,在上述兩方中用之,有“培土生金”之妙[4]。
化裁名方,匠心獨運
唐氏治血,多取仲景及金元明清諸家之精華[5],博采眾長、兼收并蓄,但絕不生搬硬套,而是深研其中義理,密切結合自身診療實踐,多有進一步地闡釋和發揮,讀來不落窠臼、耳目一新。
1.拓展赤豆當歸散和槐角丸之精髓,升降同調
在《血證論·便血》篇中,唐氏在論治“臟毒下血”時,首先提到了《金匱要略》名方赤豆當歸散,并“引而伸之”,進一步明確了“臟毒”的兩個重要證型及代表方藥:對于“大腫大痛,大便不通”者,宜“解毒湯”;對于“大便不結,腫痛不甚”者,宜“四物湯加荊芥、地榆、丹皮、槐角、土茯苓、黃芩、苡仁、地膚子、檳榔治之”。在兩方中,唐氏分別用防風、枳殼組合和荊芥、地榆、丹皮、槐角、土茯苓、黃芩、苡仁、地膚子、檳榔組合代替了赤小豆,又分別用大黃、赤芍組合和四物湯組合代替了當歸。防風辛溫發散、氣味俱升;枳殼雖以苦降為主,但亦能用于臟器下垂,二藥相配,體現了“升”的深意;大黃苦寒清瀉,炒炭后可涼血止血,赤芍專于入肝,涼血散瘀止痛,二藥相合,表現出“降”的思路。四藥同用,辛散苦瀉,升降同調[6],邪祛郁解,氣順血和。荊芥質輕上行,疏風透疹,川芎辛散溫通,善至高巔且活血行氣,祛風止痛。荊芥與川芎伍用,再次突出了“升”的用意;黃芩苦寒,清熱燥濕,炒炭止血,丹皮清營涼血,祛瘀解毒,黃芩和丹皮相配,再次彰顯了“降”的特色,且寓升于降,降中有升,氣血同治,左右逢源。
同樣在《血證論·便血》篇,唐氏在探討“腸風下血”時,推崇明代醫家龔廷賢[7]《壽世保元》中的槐角丸,但在其后的討論中,拓展性地提出使用“葛根黃連黃芩湯加荊芥、當歸、柴胡、白芍、槐花、桔梗、地榆治之”。細觀此方,柴胡、葛根升發清陽,疏郁生津;芩連槐地苦降下行,清熱涼血止血;桔梗、柴胡使作“舟楫”,溝聯上下,又一派升降調和之象;當歸、白芍養血活血,補中寓疏,諸藥同用,始成清熱祛風,生津養血之功。
2.發揚黃土湯和石蓮湯之神韻,清補并行
在“遠血”的論治中,唐氏開門見山地明確了黃土湯在“陰結下血”中的獨特地位,并重點剖析了方中黃芩和附子的精妙之處。他指出,佐以附子的原因是“陽氣下陷,非此不能舉之”,使以黃芩的理由是“以血虛則生火,故以此清之”。隨后,唐氏將“黃芩之義”推而廣之,選用了兩個以“清”為主的方劑,分別為人參清肺湯、歸脾湯加梔子、麥冬、阿膠、五味子或丹梔逍遙散加阿膠、桑寄生、地榆;將“附子之義”推而廣之,力薦了三個以“補”為主的方劑,分別為人參養榮湯、膠艾四物湯加巴戟天、甘草和斷紅丸。
在“噤口痢”的論治中,唐氏首先提到了朱丹溪的石蓮湯,但很快強調了“洗胃變津、開胃進食”的重要性,并主張以竹葉石膏湯、人參白虎湯、大柴胡湯加石膏、花粉、人參加以治療。觀此三方,亦能體現“清補并用”之義:均以石膏辛甘大寒以清熱除煩,且煅后又可止血;分別配以麥冬、知母、花粉養陰生津,極盡增陰補液之能,切中“火熱濁攻、胃氣被傷”的病機,必收“攻逆生津、開胃進食”之效。
偏愛種仁,水火氣血同理
唐氏《血證論》的最大學術成就即為“水火氣血論”,強調血證與水火氣血、臟腑功能的密切聯系[8],治療血證時將調氣、降火、治水、止血有機結合,循序漸進,環環相扣。對《血證論·血下泄證》諸篇中的方藥深入統計、總結后發現,唐氏對種仁類中藥[9]的使用頗多,應引起高度的重視。在《血證論·血下泄證》中,唐氏共使用了18味種仁類中藥,將治水、治火、治氣、治血的思想貫穿和細化其中,且往往一藥多能,綜合論治,凸顯出獨特的韻味和精妙之處。
1.治水之種仁藥
檳榔、苡仁、車前子、地膚子、五味子。《血證論·陰陽水火氣血論》所言:“設水停不化,外則太陽之氣不達,而汗不得出,內則津液不生,痰飲交動。”為此,檳榔、苡仁、車前子、地膚子均可利水滲濕,利尿退腫[10]。唐氏又認為如若水陰不足,又會津液枯竭,上則痿咳,下則閉結,外則蒸熱,提出“凡此之證,皆以生水為治法”,于是力遣五味子,極盡其“生津止渴”之功,體現“消水”與“補水”的動態平衡。更值得一提的是,苡仁善清肺腸之熱,車前子善除肝與膀胱之熱,體現出與“治火”諸法的交叉;檳榔以消積導滯為能事,體現出與“治氣”諸法的融合;五味子可療陰血虧虛,心神失養,又體現了“治(養)血”諸法的協同。
2.治火之種仁藥
吳茱萸、梔子、菟絲子。唐氏在《血證論》中突出強調了“邪火”在血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治火就是治血,瀉火就是止血的治療思路[11],在用藥上梔子的頻繁出現就是最好的佐證。但又強調了命門之火的重要性,指出腎陽不足者,則水泛為痰,凌心射肺,發為水腫、奔豚、下利、亡陽等證。由此即可參悟唐氏遣用吳茱萸和菟絲子的用意。吳茱萸暖肝胃,菟絲子溫腎陽,且寒熱之偏不甚,可發揮綿長而持久的功力,收“少火生氣”之效。與此同時,吳茱萸還主疏肝氣之郁滯,契合“治氣”之理;梔子苦寒,又善利尿通淋,符合“治水”之義;菟絲子亦可益精養血而明目,又與“止血”之論甚為和調。
3.治氣之種仁藥
砂仁、杏仁、卜子、枳殼、烏梅、罌粟殼、訶子。《血證論》各篇中反復強調,“治血必治氣”,認為調氣是治療血證的關鍵。由本組種仁藥可推知,斂氣和降氣最是唐氏青睞之法。《血證論·陰陽氣血水火論》指出,肺得潤養,則“其葉下垂,津液又隨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臟戴澤,莫不順利,而濁陰全消,亢陽不作”,所以能治節五臟矣。因此在用藥時,用砂仁、卜子、杏仁、枳殼降脾肺之氣,又以烏梅、罌粟殼、訶子斂肺安肺,達到“肺氣斂則腸氣自固”之效。且本組藥物中,杏仁味苦降泄,善治風熱、燥熱、肺熱之咳,兼可“治火”;烏梅至酸性平,生津止渴,兼能“治水”;罌粟殼醋炒后有止血止痛之功,又可“治血”。
4.治血之種仁藥
桃仁、棗仁、蓮子。唐氏在《血證論》中獨創止血、消瘀、寧血、補血四大原則治法[12],作為“通治血證之大綱”,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本組三味種仁藥,亦是四法的具體體現。對于桃仁,唐氏在《血證論》的“消瘀”部分多次提及。棗仁向為補血佳品,但在唐氏看來,亦有寧血之能,正如其所言“審系肝經風氣鼓動而血不寧者,再加桑寄生、棗仁、玉竹、牡蠣……”蓮子亦被用于“斂戢”虛火,還可養血益腎,澀精止血。且桃仁味苦,常與清熱解毒藥伍用治療熱癰毒盛,可為“治火”之用。大棗甘溫,補脾益氣,自有“治氣”之能。蓮子收澀,止瀉止帶,堪當“治水”之功。
唐宗海在便血、便膿、尿血、經血、崩帶、產血等血下泄證的論治中,遵仲景及金元諸家之理,參合心悟、融匯新知,多有耳目一新之論,值得后學進一步深研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