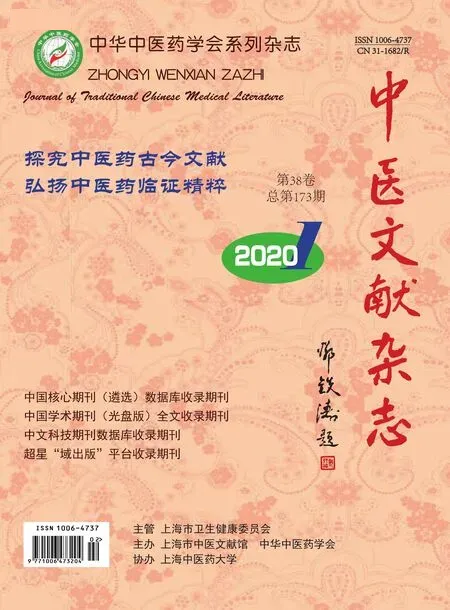滬上川籍醫家劉民叔虛實觀及其臨床運用*
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201203)
劉民叔,名復,字民叔,四川成都華陽縣人。1926年開始續至上海定居,凡業醫四十余年。自清朝以來,江南醫家根據江南的地域特點、人文特點,治病多以溫病學為主,用藥輕靈,如銀翹荊豉之屬。劉氏自四川而來,四川醫家多重視《傷寒》方,且多用重劑。劉氏也喜用經方,常用麻桂姜附等辛溫劑,當時在滬上被稱為“川派”,與祝味菊并稱“火神”。劉氏早年學術以《內經》為主,五十歲之后開始重視漢魏湯液經方。
一般的虛實是虛假和真實的意思,而在醫學上有不同含義。《素問·寶命全形論》載:“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吳昆注:“虛實,人之陰陽消長也。”[1]65《素問·通評虛實論》載:“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1]73實是以邪氣的盛衰來定,即邪氣盛則實,不盛則不實,但不能認為虛,這不是非此即彼的定義。虛是以精氣奪否,精氣多少來定,即精氣奪而余不足則虛,精氣足則不虛。由此可以認為虛實是并列的、對獨立的概念。
劉氏的虛實觀
劉氏認為,邪氣盛者為實,正氣即體力衰弱者為虛。劉氏的虛實觀體現在他的辨證論治理論體系中。劉氏精研《傷寒論》,總結辨證論治法,以虛實為綱,分為六法。六法即汗、吐、下、利、溫中、養陰。汗、吐、下、利治療實的方面,溫中、養陰治療虛的方面。劉氏在《腫脹九例十三方》中說:“原夫任圣伊尹撰用神農所創之《本草經》以為湯液,立六經曰太陽、曰陽明、曰少陽,曰太陰,曰少陰,曰厥陰;立三綱,曰風,曰寒,曰溫;立八目曰表曰里,曰虛曰實,曰寒曰熱,曰氣曰血。其用六經以統百病也,即三綱以論百病之性,其用六法以治百病也,即八目以論六法之宜。”[2]22且劉氏認為治實重在攻邪,補虛重在養陽,陽化氣,陽氣足則有正氣為驅邪之根本。劉氏辨別虛實之后,定出虛實的大致比例,用藥補虛瀉實都有先后側重,而補虛又重在扶陽,常用辛溫的附片等。反映了劉氏重視陽氣的川派“火神”特點。
劉氏治法與用藥特點
1.實證類治法與用藥
根據邪氣的排除途徑分為在表的汗法,在里下法,在半表半里的利法、吐法。劉氏特別強調,因古字“和”“利”相似,認為是后人誤把“利法”當成“和法”,從而產生少陽主和法之論。他說:“對實癥之在表者(初期惡寒發熱)可用汗法,在半表半里者吐法(在上)與利法,在里者可用下法,主要作用就是發散和排泄、驅除病邪。”[2]16劉氏以《本經》為基礎,以《傷寒》為法度,順勢而為,務使藥物與邪氣性質及正邪交爭的趨勢環環相扣,隨證用藥。同一治法下又區分不同情況之所宜藥物,按緩、重、峻三種層次分類,既是將藥分類,也是將病證分類,可謂細致入微。具體來說,汗法的三層代表藥分別是緩藥蔥白、重藥生姜、峻藥麻黃。代表方分別是緩方香豉湯發溫病汗,重方桂枝湯發中風汗,峻方麻黃湯發傷寒汗。下法的三層代表藥是緩藥大黃、重藥甘遂、峻藥巴豆。代表方是承氣湯、十棗湯、自擬原巴豆湯(腫脹九例十三方)。當然這三種藥主治的邪氣有所不同,大黃主治熱結,巴豆主寒積,甘遂主水結,具體來看有寒熱水的差異,但就其勢能來分,可以比較出緩重峻的區別。涌吐法常用緩藥瓜蒂、重藥常山、峻藥藜蘆。三種藥所主邪氣不同,具體來看瓜蒂主心下停水,常山主痰結,藜蘆主風涎。利法即利尿法也分三層,茯苓淡滲緩利,芍藥破血痹以利尿,滑石療積聚以利尿。這里下法與利法中有寒熱氣血之別,即前論劉氏體系中八目的“曰氣”“曰血”“曰寒”“曰熱”。
2.虛證類治法與用藥
虛證類治法分為溫陽與養陰,即滋補精血津液、興奮陽氣為主。溫陽也分出三種層次,代表藥是附子、干姜、吳茱萸,附子如風最急,干姜為熱偏守,吳茱萸苦溫更守,具體到脈象上分屬脈沉微之附子證,脈不沉之干姜證,脈反浮之吳茱萸證。脈浮主邪氣在表,用藥偏于攻邪,故以吳茱萸來溫破。養陰分為養津、養液、養血,這是根據津液的稠薄程度來分的。代表藥如生津之麥門冬、滋液之干地黃、養血之阿膠。
像這樣的用藥方法劉氏還有不少論述。又如“治眩暈一癥,有合于高血壓者,中國古醫名之為氣血厥逆,后世稱為肝陽化風。其輕而緩者可用菊花來清它,其重而急者可用羚羊角來平它,其更重更急的可用大黃來下它。”[2]16他的依據是《神農本草經》所載“上品菊花味苦平,主久服利血氣,中品羚羊角味咸寒,主惡血,下品大黃味苦寒,主下瘀血”[2]16。他將本經的上中下三品以緩急別之,即緩藥居上、重藥居中、峻藥居下而有三級不同效能。
劉氏對于虛實兩證,常分清標本緩急,對于實證力主攻邪。如《腫脹九例十三方》中,從汗法蔥白九莖湯始到下法一物葶藶子湯(方十)止,都是攻邪之劑,其中原巴豆加大黃湯,巴豆、甘遂、大黃并用,可謂攻下之猛。對于虛證首先重視補元氣。例如治療僧惠宗[2]721胃癌吐血一案,因其元氣大虛,危在旦夕,他力辟西醫輸血,認為血為陰物,需要元氣才能推動,處以黃土湯重用姜附扶陽,并與云南白藥止血救標,最后轉危為安。
除上述特點外,劉氏常喜用《本經》所載藥物,善用冷僻藥,如云母、癟竹、珊瑚、瑪瑙、石鐘乳、金蟬花、孔公孽、鬼臼、狼毒、象皮、葫蘆瓢、人參葉、蟹爪、山楂核、柳枝、杏枝、桃枝、李枝,鼠婦,蜣螂等。善用峻猛藥,如甘遂、巴豆、商陸、千金子、牽牛子、大戟、水蛭、虻蟲、大黃等。可以說冷僻藥和峻猛藥是劉氏用藥一大特色,但劉氏用藥也有常規平淡的時候。如楊梅芳[2]737子宮癌一案,雖病如此之重,劉氏卻舉重若輕,僅以歸脾湯加減治之。
劉氏用藥或平常,或出奇,或平和,或峻猛,方無定方,藥無定藥,似乎不可琢磨,但其基本的理法有規律可尋。即分清虛實,順應機體自然排邪反應,按汗、吐、下、利、溫陽、養陰六法互用,把藥物性能按三分法分類,以期與病癥絲絲貼合。這種藥物的三層分法,也對應于病的三層分法,這似乎與《傷寒論》三陰三陽的三分法類似,劉氏可能受這種三分法思維的影響而對辨證用藥也進行了三分類。《傷寒論》的三陽病是著眼于實證而設,其中陽明邪氣最重,正邪交爭最劇烈,所以常用峻藥如芒硝、大黃等。少陽邪氣最輕,正邪交爭較緩,所以常用緩藥如柴胡黃芩等。而太陽居于其中,所以常用重藥如麻黃、桂枝等。三陰病則著眼于虛證而設,陽虛方面少陰最虛,故用偏走而峻猛的附子,以挽垂絕之陽。厥陰陰結最甚,故以吳茱萸之辛溫以破陰結。太陰介于其中,故以干姜之溫而偏守以起寒濕之下利。劉氏在這種三分法的啟發下,更進一步把藥細分,把每種治法下面的藥也分出三層,擴大了《傷寒論》的治法范圍,并豐富了臨床用藥。
集成學習的兩個主要工作一般可以劃分到訓練和檢驗兩個階段。訓練階段是訓練形成集成模型,主要針對訓練樣本數據集,劃分多個弱分類器按照一定的融合集成規則形成一個強分類器;檢驗階段是驗證調整集成模型,主要針對測試樣本數據集,對多個弱分類器的預測結果按照一定的集成整合規則形成集成預測結果。其中,多分類器融合的集成模型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醫案舉例
茲以劉氏治療3例高血壓中風為例,以窺劉氏虛實補瀉的用藥特點。
1.莫長發腦溢血案[2]767
莫長發,男,58歲,1949年12月4日突然驚呼而厥,昏倒不省人事,延醫急救,診斷為腦溢血,施治無效,認為絕望。至翌日十點延劉氏出診。癥見煩躁氣促、搐弱抽掣,攣急如角弓。
劉氏診為厥顛疾。處方:荊芥穗一兩,白菊花一兩,僵蠶二錢,蟬蛻二錢,蚯蚓三錢,全蝎二錢,蠐螬三錢,蜂房一錢五分,楝實三錢,柳枝一兩。
二診,抽搐勢緩,人未蘇。處方:荊芥穗一兩,白菊花一兩,僵蠶二錢,蛇蛻二錢,蚯蚓二錢,水蛭二錢,氓蟲三錢,蜂房二錢,楝實三錢,柳枝一兩。
三診,抽搐漸平,略能識人,反發驚呼如狂。處方:云母一兩,磁石一兩,僵蠶三錢,蛇蛻二錢,蚯蚓二錢,水蛭二錢,氓蟲二錢,蜂房二錢,龍膽草二錢,礞石滾痰丸一兩,柳枝一兩。
四診,驚呼平,神志清,搐弱抽掣全止,不復攣急,但又四肢垂曳不能動。處方:云母一兩,磁石一兩,龜板一兩,鼠婦二錢,水蛭二錢,氓蟲二錢,蜂房二錢,全蝎二錢,龍膽草二錢,礞石滾痰丸一兩。
分析:本案初診二診用荊芥、菊花、柳枝達一兩之重,為全方特點之處。菊花、荊芥、柳在《神農本草經》分別居上品、中品、下品。《本經》論荊芥曰:“味辛,溫。主治寒熱,鼠瘺,瘰疬,生瘡,結聚氣破散之,下瘀血,除濕痹。”[3]67可以得知荊芥辛溫,疏風發表,活血破瘀,可用于治療中風抽搐之癥。《本草思辨錄》也說:“考古治頭項風強,一切偏風中風口噤,及吐血衄血下血,多重任荊芥,是其所司,總不離血中之風。”[4]所以劉氏重用荊芥是有所本。《神農本草經》論菊花曰:“味苦,平。主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痹。”[3]13菊花味苦能瀉火堅陰,氣味芳香又有疏散之性,故能疏風止頭眩,為疏風清熱之品,善治中風而表實郁熱者。《神農本草經》沒有載柳枝,僅論柳華:“味苦寒。主風水黃疸,面熱黑。一名柳絮。”[3]96可以看出柳枝的作用也是疏風清熱,大體與菊花同功,而有緩急強弱之差異。柳樹皮含有水楊苷(甙),從遠古時代起,柳樹皮就被用來治療疼痛、發熱等癥。
綜合此三藥可以看出,劉氏處方用意在于疏風透熱,用以治療在表之實風,所以用藥皆疏散。倘若以精氣不足而生虛風的病機為主要矛盾是不可以用疏散法的。本案本虛標實,故二診即增入云母、磁石以收斂熄風。迨四診驚呼平,神志清,搐弱抽掣全止,不復攣急,但又四肢垂曳不能動時,方去柳枝之散,更加龜板以補精氣、潛陽息風。如此隨癥增損,以歸芍地膠活血養血至十三診病愈,后以知柏地黃丸善后。由此觀之,劉氏用藥分實風、虛風,實風重用疏風散熱藥,虛風重用平肝潛陽藥,后加入滋陰之品,而活血破瘀貫穿始終,可謂與本案虛實夾雜,瘀濁內盛,陰血內虛,實風虛風兩相煽動的病機特點絲絲入扣。實風不可直息,虛風不可妄疏,甚者從之,微者逆之。虛實之間,至微至妙,成敗在于一線。且劉氏步步為營,先后不亂,故能起此疑難危癥。
2.李賢才高血壓至二百二十度案[2]772
李賢才,男,55歲,經南市南洋醫院診治,血壓高到二百二十度,治療無效,遂就診于劉氏。
初診:脈至如湍,頭痛失眠,氣血有升無降,上實下虛,防其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處方:云母一兩,代赭石一兩,菊花一兩,天麻一錢,桑葉二錢,蟬蛻二錢,蚯蚓二錢,膽南星一錢,龍膽草一錢。
二診:頗能眠,頭痛眩脹均已減輕,口仍苦,鼻仍糜。處方:云母一兩,代赭石一兩,菊花一兩,桑葉二錢,蟬蛻二錢,蚯蚓二錢,蜂房二錢。
三診:減菊花增入陳鐵落。
四診:頭腦清寧,睡眠安。
分析:此案初診即上實下虛,虛多實少,故起手就重用代赭石、云母等平肝潛陽,僅用菊花佐桑葉疏風散熱,而菊花、桑葉之疏散力較荊芥更緩,是仍慮荊芥疏散太過,而只選桑菊之緩者。《神農本草經》曰云母“味甘平。主身皮死肌,中風寒熱,如在車船上,除邪氣,安五臟,益子精,明目,久服輕身延年”[3]8。《名醫別錄》曰云母“下氣堅肌,續絕補中,療五勞七傷,虛損少氣,止痢”[5]。綜合看來云母有下氣收斂、補中氣、益精氣的功效。代赭石,《神農本草經》載:“味苦,寒。主治鬼疰,賊風,蠱毒,殺精物惡鬼,腹中毒邪氣,女子赤沃漏下。”[3]78《本草發揮》載其“怯則氣浮,重劑所以鎮之。代赭之重,以鎮虛逆”[6]。《本草備要》載:“代赭石,重,鎮虛逆,養陰血。”[7]縱觀歷代本草論述,可以看出云母、代赭石為金石一類藥物,具備金石的特點,即金主收斂下潛,治療虛風浮動,尤為合拍,以風屬木,虛風則畏金克之故。三診減菊花為五錢,增入陳鐵落一兩,亦是加重潛陽息風之功。《神農本草經》載鐵落“主風熱,惡瘡,瘍疽瘡痂疥氣在皮膚中”[3]77。而《素問》載有生鐵落飲,直接用生鐵落治陽氣厥逆之病。
3.濮秋丞卒中風案[2]774
濮秋丞,男,83歲。1952年6月17日初診。卒中風,口禁不能言,奄奄忽忽,神情悶亂,身體緩縱,四肢垂曳,皮肉痛癢不自知。處方:荊芥四錢,菊花四錢,防風三錢,秦艽三錢,威靈仙三錢,鉤藤三錢,川芎一錢,細辛七分,麻黃六分,桂枝一錢,云母石一兩。
二診:得微汗,慶來蘇,身體漸能收持。處方:同初診方。
三診,眠食安,肢體遂,神情舒適,知感恢復。處方:荊芥四錢,菊花四錢,秦艽三錢,威靈仙三錢,鉤藤三錢,天麻二錢,刺蒺藜三錢,伸筋草二錢,生白芍二錢,云母石一兩。
如此隨證加減至七診完工。
分析:此案初診處方即一派疏風溫散之劑,雖麻黃、桂枝、細辛亦不避,僅云母一味為收斂之用,頗有續命湯之風格。然畢竟患者八十高齡,精氣已虛,故用疏散之藥也是如履薄冰,觀劉氏用麻黃細辛僅幾分,荊芥防風亦只以錢記,與前兩案之重用至一兩有別,反映劉氏用思精微、膽大心細的特點。二診得微汗而取效,三診始加入白芍收斂養血,四診增磁石,六診增天冬、黃精等補虛收斂之品。
4.討論
關于中風病,古代的“中風”是一個廣義的疾病概念,與現在定義的腦卒中概念有所不同。中風學說最見于《黃帝內經》,《內經》所記載“中風”為病因,是中于“風”的一類外感疾病,并不包括現今所指的偏癱、失語等癥狀。當然如“偏枯”“風痱”“薄厥”等疾病癥狀的記載與現在中風表現有相同之處。《傷寒》所論中風是外感病一種證型,也不專指肢體偏瘓、失語之類疾病。而《金匱要略》對于風之為病已經有“半身不遂”等癥候的論述。其中續命湯、三黃湯針對實多虛少證而設,故用藥多麻桂之辛溫發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針對虛多實少而設,故用藥多金石地黃等潛陽息風;侯氏黑散針對中風病虛實并重而設,故用藥以菊花為君,重劑使用,發散而兼收斂。后世醫家,或善于補,或工于瀉,或攻補兩用,要皆不出此范圍。劉民叔治療高血壓中風,分清虛實標本,分別與潛陽活血、疏風清熱、散寒除濕、滋陰養血為治療方案,靈活運用補虛瀉實。這與時下習慣一見高血壓不問虛實即用金石之類平肝潛陽,更不敢以麻桂發散,不可同日而語。劉氏學衷《湯液》,于《傷寒》《金匱》著意尤深。而《湯液》經方與《本經》一脈相承,故劉氏亦深研《本經》,臨證處方多用《本經》所載之藥。從上三案可以窺見劉氏誠為善學善用《本草》《湯液》者,值得我們效仿學習。
劉氏作為川籍中醫,而行醫于滬上,仍沿襲四川常見處方風格,善用重劑驅邪,辛溫扶陽,確有獨樹一幟的特點,可見雖然有地域差異的影響,但治法卻是不變的,全在于醫者善用諸藥。劉氏處方用藥遵《本經》《傷寒》法度,打破地域界限,寒溫界限,明辨虛實,補瀉先后,條理井然,頗有大醫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