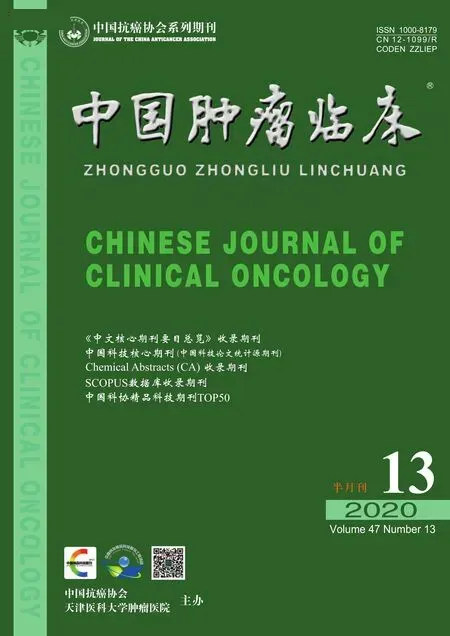促纖維增生性小圓細胞腫瘤靶向治療的研究現狀和展望
佘明金 綜述 陳振東 審校
纖維增生性小圓細胞腫瘤(desmoplastic small round cell tumor,DSRCT)于1989年被首次報道,截至2015年,文獻報道約850 例患者,發病主要在男性兒童和青少年,典型表現為多發性腹腔內腫瘤和獨特的纖維增生間質[1]。該腫瘤缺乏特異性臨床表現,常見癥狀包括腹痛、腹脹及腹部包塊,伴隨癥狀包括頑固性腹水、肝腫大等,確診困難,大多數患者確診時已發生轉移[2]。由于初始化療敏感,化療是多數DSRCT患者的首選治療方法。推薦使用治療尤文氏肉瘤的化療方案,其中P6 方案為長春新堿+多柔比星+環磷酰胺方案(VAC)和異環磷酰胺+依托泊苷(IE)交替方案[3]。DSRCT 的經典化療方案。DSRCT預后差,多數患者中位生存期為17~25 個月[4]。為改變DSRCT 的治療現狀,迫切需要新的治療方法。本文就DSRCT新的治療靶點和治療方向進行綜述。
1 DSRCT的生物學特點
1.1 DSRCT的分子特性
DSRCT 是一種罕見的軟組織肉瘤,t(11;22)(p13;q12)易位是DSRCT 穩定存在的遺傳學特點[5]。確切的組織起源尚不清楚,迄今為止已鑒定出的藥物靶點較少[6-7]。研究發現,90%以上的DSRCT患者存在特異性的染色體異位t(11;22)(p13;q12),使位于22q12 上的EWSR1 基因與位于11p13 上的WT1 基因融合。EWSR1-WT1 融合基因可經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和熒光原位雜交(fluorescencein si?tuhybridization,FISH)檢測,上述檢測方法均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對確診DSRCT 具有重要意義[8]。在多數DSRCT 中,EWSR1-WT1 融合基因為EWS 的1~7 或1~8 外顯子與WT1 基因的8~10 外顯子融合。由于選擇性剪接,導致融合蛋白存在不同的亞型,在鋅指3 和4 之間插入和不插入3 個額外的氨基酸,如賴氨酸、蘇氨酸和絲氨酸(KTS),從而發揮不同的生物學功能[9]。Ferreira 等[10]通過全外顯子組測序對1 例DRSCT 患者體細胞和種系變異情況進行研究,結果確定導致蛋白質改變的遺傳變異,包括12個體細胞和14個種系分子事件(其中11個為種系復合雜合子突變和3 個罕見的純合子多態性),主要影響參與間充質細胞分化的基因。同時發現5 號和18 號染色體的擴增與11p、13q 和22q 染色體的丟失相關,11p和22q染色體的缺失也表明DRSCT存在典型的易位t(11;22)(p13;q12)。DSRCT 特異性分子標記物是EWSR1-WT1 融合蛋白。t(11;22)(p13;q12)染色體易位使EWS 的N-末端結構域和WT1C-末端的DNA結合域融合,導致異常轉錄因子的表達,目前認為EWSR1-WT1 融合蛋白的存在可能是DSRCT細胞增殖的本質所在。DSRCT至今尚無標準治療方案,治療策略主要為手術、放療和大劑量化療[11]。盡管臨床上對DSRCT 進行了積極地治療,但因易復發,迫切需要有針對性的靶向和免疫治療。
1.2 DSRCT與尤文氏肉瘤
在認識到DSRCT 為一個獨特的臨床疾病之前,DSRCT通常被錯誤地分類為睪丸、卵巢、腸系膜或胃腸道的低分化非典型癌。尤文氏肉瘤(Ewings sarcoma,ES)也涉及EWS的基因融合,并且激活與EWS-WT1相似的致癌途徑[12-13]。由于這種相似性,多數DSRCT患者接受ES的治療方案如VAC方案和(或)IE方案作為一線化療方案。由此可見,多數DSRCT的治療策略和治療方案是從ES治療中衍生的[14]。然而,DSRCT患者的生存率明顯低于ES患者,可見DSRCT與ES有著不同的生物學背景[15]。由于DSRCT臨床較為罕見,DSRCT患者通常被納入其他肉瘤患者的臨床研究,而并非基于DSRCT 的特定分子特征進行臨床研究。因此,確定DSRCT的特異性生物標記物和腫瘤相關的藥物靶點至關重要,以通過靶向治療改善DSRCT的不良預后[16]。
2 DSRCT的潛在治療靶點
2.1 靶向EWRS1-WT1下游通路基因
野生型WT1 基因編碼一種鋅指蛋白,是一種轉錄抑制因子。在EWSR1-WT1融合基因中,WT1鋅指區的缺失導致至少35個靶基因的轉錄激活[13]。激活的蛋白包括生長因子及其受體,如PDGFα、IGF1-R、EGFR、IL-2/15Rβ,轉錄調節因子(c-myc、n-myc、PAX2-2、WT-1 和ENT4),以及編碼細胞外蛋白的基因(e-Syndecan-1、e-cadherin 和TALLA-1)。上述蛋白可能與腫瘤生長和治療耐藥相關,從而可能為DSRCT提供新的治療靶點。然而尚未明確上述分子異常通過何種方式促進DSRCT 的發生發展,因此將其作為治療靶點亟需進一步探索。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受體(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receptor,IGF1-R)是一種酪氨酸激酶受體,研究表明IGF1-R 在DSRCT中廣泛表達,與腫瘤的發生密切相關,其抑制劑可以通過IGF1-R、RAS/MAPK和JAK/STAT等多條通路抑制腫瘤的生長,誘導腫瘤細胞凋亡[17]。Tap等[18]在一項Ⅱ期臨床試驗中應用抗IGF1-R 抗體ga?nitumab 治療16例DSRCT 患者,結果顯示1例部分緩解、10 例病情穩定(其中3 例疾病穩定時間超過24周)、4 例疾病進展,臨床獲益率為25%,中位無進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mPFS)為19個月。ganitumab主要不良反應為疲勞和惡心。
2.2 免疫相關治療
細胞表面蛋白為免疫治療提供了潛在的靶點。CD276 又稱新抗原B7H3,在約96%DSRCT 細胞中表達。研究發現其對T細胞具有抑制作用,有助于腫瘤細胞免疫逃逸,在腫瘤生長和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Modak 等[19]研究發現,在DSRCT 患者中腹腔注射放射免疫結合物131I-8H9(8H9為以B7H3為靶點的小鼠單克隆抗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在使用131I-8H9進行治療前,腹腔給予2 mCi124I-8H9示蹤劑,以獲取PET 圖像和生物分布數據,結果提示腹腔注射131I-8H9 安全性良好,未見明顯劑量限制性毒性。在一項Ⅰ期臨床試驗中,應用131I-8H9 治療34 例DSRCT 患者,13 例患者的初步數據表明治療耐受性好,對重要器官的輻射吸收劑量遠低于正常范圍,7例在減瘤術后接受治療的患者中有6 例在治療后11個月仍處于緩解狀態[6]。基于上述研究結果,一項結合8H9 介導的放射免疫療法和外照射放射治療的Ⅱ期臨床試驗已于2016年開始,結果值得期待。
其他細胞表面蛋白主要被認為是免疫抑制劑的靶點,藥物可以通過特異性的單抗與放射性核素交聯形成偶聯物。其中包括富含15-亮氨酸的重復膜蛋白(leucine-rich repeat-containing protein 15,LR?RC15),一種針對LRRC15 的抗體偶聯藥物ABBV-085 在多種實體瘤包括肉瘤的臨床前實驗中已顯示出良好的療效,其在腫瘤進展中的作用尚未明確[20]。脊髓灰質炎病毒受體(PVR,CD155)和PVR相關蛋白2(PVRL2,CD112)也是免疫治療的潛在靶點,兩者均為NK 細胞配體[13],但由于表達水平差異較大,需要對患者進行詳細的分層。靶向CTLA-4 和PD-1(CD279)的免疫檢查點抑制被認為是治療DSRCT 新策略。Burgess 等[21]分析了超過150個肉瘤亞型的腫瘤細胞和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中PD-1表達情況,結果發現高達65%肉瘤細胞表達PD-L1,同時伴有PD-1 TILs 陽性,并且與較差的總生存率和腫瘤的侵襲性相關,但在DSRCT病例中并無上述情況。
2.3 抗血管生成治療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依賴性血管生成在DSRCT發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Bétrian 等[22]評估了9 例進展期DSRCT患者抗血管生成治療的療效,其中6例接受舒尼替尼、2 例接受索拉非尼、1 例接受貝伐珠單抗,平均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ve-free survival,PFS)分別為3.1、3.8、2.0個月,研究發現盡管療效有限,但經過多線治療后,應用靶向治療能夠改變治療決策從而提高療效。Shi 等[23]應用阿帕替尼(500 mg/d)治療1例DSRCT,治療2 個月后發現腫塊退縮明顯,腹水減少,腫瘤標記物降至正常。George等[24]應用舒尼替尼治療1例DSRCT,獲得疾病穩定達56周,該研究建議有必要進一步評估舒尼替尼在DSRCT等非胃腸間質瘤亞型中的療效。Menegaz 等[15]應用帕唑帕尼單藥治療29 例DSRCT,發現疾病穩定者占55%,1 例部分緩解(3%),1 例完全緩解(3%),11 例疾病進展(38%)。mPFS 為5.63 個月(95%CI:3.23~7.47),中位總生存期為15.7個月(95%CI:10.3~32.4),提示帕唑帕尼具有良好的耐受性,為晚期DSRCT 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療選擇。申鋒等[25]報道應用瑞戈非尼治療1例DSRCT,至研究截止時PFS已延長15個月。
安羅替尼作為一種多靶點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可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FGFR)、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R)、c-Kit 和Met。Chen 等[26]應用安羅替尼治療1例復發難治性腹部DSRCT,在治療4個周期后淋巴結顯著減小,截至研究發表時PFS 接近4 個月,患者繼續使用安羅替尼作為維持治療,情況良好。安羅替尼的不良反應主要為高甘油三酯和疲勞,但是可控且可耐受的。安羅替尼為腹部轉移性DSRCT的治療提供了新的選擇。
2.4 DNA損傷修復途徑
近期的突變分析[27]揭示了DSRCT 中與免疫反應、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和DNA 損傷反應(DNA damage response,DDR)相關的基因表達下調。6個DSRCT樣本的全外顯子組測序共鑒定出137個獨特的體細胞突變,其中133 個突變基因是病例特異性的,2 個基因在不同病例中發生了不同位置的突變。上述研究結果突出了DSRCT 基因組的異質性(除融合基因外)。在135 個突變基因中,其中27%與EMT/間充質上皮逆轉(mes?enchymal-epithelial reverse transition,MErT)以 及DNA 損傷修復(DNA damage response,DDR)通路有關。這些蛋白質包括在細胞周期中具有關鍵功能的蛋白質,如共濟失調毛細血管擴張和Rad3 相關蛋白(ataxia telangiectasia and Rad3-related protein,ATR)和核糖核苷二磷酸還原酶亞基M2(ribonucleoside-di?phosphate reductase subunit M2,RRM2)。Mellado-La?garde 等[28]證明了在患者來源的異種移植模型中DSRCT 對PARP 抑制劑聯合治療的有效性。這一策略也被證明在ES 中有效,PARP 抑制劑與標準治療(伊立替康和替莫唑胺)聯合治療的完全緩解率>80%,而標準治療組死亡率為100%。可能原因為在ES和DSRCT中,EWS融合基因對野生型EWS的干擾可導致復制應激和DDR系統缺陷。van Erp等[29]發現PARP1和SLFN11在DSRCT臨床前模型中高表達,并且在奧拉帕尼和替莫唑胺(temozolomide,TMZ)聯合治療后腫瘤退縮。結果研究表明奧拉帕尼和TMZ聯合治療可能是DSRCT的一種潛在治療選擇。
2.5 PI3K/Akt/mTOR信號通路
Subbiah 等[30]對DSRCT 進行了形態蛋白組學分析,結果提示DSRCT 細胞存在P13K/Akt/mTOR 信號通路持續活化。Tirado 等[31]研究發現,mTOR 抑制劑雷帕霉素可以在體外誘導JN-DSRCT-1 細胞(EWSWT1 基因融合DSRCT 模型)凋亡。通過增加雷帕霉素的濃度,可以繼續上調促凋亡蛋白Bax和下調抗凋亡蛋白Bcl-xL,從而誘導細胞凋亡。該研究還發現[31],雷帕霉素阻止mTOR 激酶靶點的磷酸化,從而下調EWS/WT1 融合蛋白的表達。Thijs 等[32]通過每周靜脈注射25 mg的mTOR抑制劑temsirolimus治療1例轉移性DSRCT 患者,結果發現患者生存質量顯著改善,PFS達40周。Naing等[33]應用temsirolimus聯合IGF-1R單抗cixutumumab治療3例DSRCT患者,其中2 例疾病穩定的持續時間超過5 個月,提示該治療方案對于DSRCT治療初步有效且不良反應可耐受。
2.6 其他靶向位點
Fine等[34]報道,應用雄激素阻斷療法治療雄激素受體(androgen receptor,AR)表達陽性的DSRCT,6 例患者中3例臨床治療反應良好,特別是在基線睪酮水平正常的患者中。Xiu 等[35]運用分子探針對35 例DSRCT 患者進行檢測,并與ES 進行比較,結果發現AR表達明顯提高(59%vs.3%)。
神經節苷脂2(ganglioside 2,GD2)是一種在包括DSRCT在內的多種實體瘤中表達的鞘糖脂。其功能尚未明確,但被認為在腫瘤細胞黏附到細胞外基質蛋白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GD2被用作為黑色素瘤、神經母細胞瘤和骨肉瘤的免疫治療和放射免疫治療靶點,然而,在一項20例DSRCT樣本研究中僅2例呈GD2 陽性。GD3 是GD2 生物合成上游的神經節苷脂,在分析的20 例樣品中有14 例表達GD3。GD3 與黑色素瘤細胞的增殖、黏附和侵襲性有關,可能成為DSRCT靶向治療研究的方向[36]。
結締組織生長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CCN2)的表達水平在DSRCT中明顯提高,與大量細胞外基質的產生相關,提示CCN2可能參與腫瘤細胞生長、基質形成和血管生成的自分泌和旁分泌調節,CCN2可能成為DSRCT新的治療靶點[37]。
3 結語
目前,多項靶向治療DSRCT 的研究均為個案報道或小樣本研究,安全性和有效性亟需進一步證實。許多靶向化合物近期已被納入DSRCT的臨床試驗,但多數治療方案是從其他類型的腫瘤中演變而來,有限的患者例數對臨床試驗的開展構成挑戰。
目前,對于驅動DSRCT 的潛在分子機制知之甚少,尚需更多的基礎研究為臨床治療建立堅實的理論基礎。為了支持基礎研究的開展,同樣需要開發更多的模型來更好地描述腫瘤的異質性和腫瘤與基質細胞之間相互作用的復雜性。由于異種移植物難以在體外培養,到目前為止僅已建立一個DSRCT 細胞系。靶向豐富的間質干細胞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在其他類型腫瘤中已成功應用的基礎上。此外,使用液體活檢特別是循環腫瘤DNA(包括腫瘤特異性EWRS1-WT1 融合基因)檢測腫瘤微小殘留、疾病復發以及評估療效可能具有臨床意義[38]。利用EWRS1-WT1 融合基因特異性基因組斷裂點可以設計一種個性化的生物標記物,用于患者隨訪期間評估血漿中的循環腫瘤DNA,該生物標記物有望成為DSRCT診斷、治療和預后判斷的標志物[10]。
綜上所述,根據目前在DSRCT中的分子機制研究,有希望的治療靶點主要與免疫應答、DDR網絡或上皮-間質轉化/間質-上皮轉化有關。DSRCT腫瘤異質性高,確診時多數處于晚期,反復治療后易產生耐藥性,聯合治療可以顯著改善治療效果。化療與靶向或免疫治療聯合應用,將可能是未來的治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