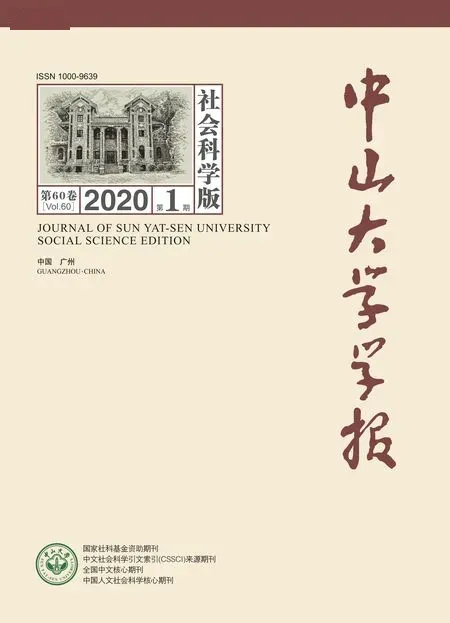基于意圖的說(shuō)話(huà)者意義*
——兼論非自然意義理論與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的關(guān)系
榮 立 武
一、問(wèn)題的引出:意圖對(duì)于解釋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是否必要
Grice在1957年“Meaning”中給出了非自然意義的定義,在1975年“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給出了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定義,其中前者被視為是理解后者的理論鋪墊(1)參見(jiàn)Huang Yan:《Pragmatics》,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ⅸ頁(yè)。。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用統(tǒng)一的語(yǔ)境來(lái)展現(xiàn)這兩個(gè)定義。當(dāng)你向我詢(xún)問(wèn)去哪個(gè)飯店就餐時(shí),我拍了拍肚皮。在該語(yǔ)境下,說(shuō)話(huà)者(我)向聽(tīng)話(huà)者(你)言說(shuō)U“我拍了拍肚皮”非自然地意味著現(xiàn)在我不想去任何飯店就餐,當(dāng)且僅當(dāng),對(duì)你而言,通過(guò)言說(shuō)U,我意圖:(ⅰ)你產(chǎn)生一個(gè)特定的信念——現(xiàn)在我不想去任何飯店就餐;(ⅱ)你知道或者承認(rèn)我有讓你做出上述信念的意圖;(ⅲ)事實(shí)上,你是因?yàn)樽R(shí)別出我的意圖而產(chǎn)生出(ⅰ)中的信念,即事實(shí)上你是通過(guò)(ⅱ)產(chǎn)生出(ⅰ)(2)參見(jiàn)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92。。與此對(duì)應(yīng)地,Grice在1975年討論了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定義。你向我詢(xún)問(wèn)去哪個(gè)飯店就餐,我回答說(shuō)“我現(xiàn)在還不餓”。言說(shuō)U“我現(xiàn)在還不餓”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現(xiàn)在我不想去飯店就餐,當(dāng)且僅當(dāng),(ⅰ’)假定我遵守會(huì)話(huà)準(zhǔn)則,或者至少遵守合作原則:在你向我進(jìn)行詢(xún)問(wèn)的時(shí)候,我的回答應(yīng)當(dāng)實(shí)際地回應(yīng)你關(guān)心的問(wèn)題,即到哪里吃飯;(ⅱ’)為了讓我的言說(shuō)遵守合作原則,我認(rèn)識(shí)到我不想去任何飯店就餐這一假設(shè)是被要求的;(ⅲ’)我認(rèn)為(并且也期待你認(rèn)為我認(rèn)為)你有能力計(jì)算出或者能夠直覺(jué)地把握到(ⅱ’)中所做的假設(shè)——我不想去任何飯店就餐——是被要求的(3)參見(jiàn)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0-31。。
這兩個(gè)定義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由于非自然意義的產(chǎn)生訴諸說(shuō)話(huà)者意圖的表達(dá)、聽(tīng)話(huà)者對(duì)該意圖的識(shí)別以及意圖在交際過(guò)程中為雙方相互識(shí)別,故而非自然意義理論不需要預(yù)設(shè)言說(shuō)在語(yǔ)言學(xué)上的常規(guī)意義,因?yàn)橐鈭D的表達(dá)不一定要以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為中介。例如,上例中拍肚子也可以傳達(dá)意圖。另一方面,由于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產(chǎn)生訴諸具體語(yǔ)境下交際雙方通過(guò)遵守合作原則而進(jìn)行的語(yǔ)用學(xué)推導(dǎo),故而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推導(dǎo)必須以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為中介。聽(tīng)者只有先理解了“我現(xiàn)在還不餓”這句話(huà)的常規(guī)意義是什么,才能根據(jù)語(yǔ)境做進(jìn)一步的推導(dǎo)。無(wú)論如何,兩個(gè)理論的主要差別體現(xiàn)在:(1)說(shuō)話(huà)者意圖的表達(dá)被替換成假定說(shuō)話(huà)者遵守合作原則時(shí)所產(chǎn)生的要求;(2)聽(tīng)話(huà)者對(duì)說(shuō)話(huà)者意圖的識(shí)別被替換成特定語(yǔ)境下聽(tīng)話(huà)者從言說(shuō)U的常規(guī)意義到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邏輯推導(dǎo)(假定說(shuō)話(huà)者遵守合作原則);(3)交際雙方對(duì)說(shuō)話(huà)者意圖的相互識(shí)別被替換成交際雙方相互知道對(duì)方有能力進(jìn)行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邏輯推導(dǎo)。盡管如此,言說(shuō)的非自然意義和會(huì)話(huà)蘊(yùn)含這兩者仍然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一點(diǎn)不僅可以從定義結(jié)構(gòu)的相似性看出來(lái),也可以從二者在交際中所承擔(dān)的作用表現(xiàn)出來(lái)——它們都是為了刻畫(huà)說(shuō)話(huà)者意義。
下面,我們僅以Searle對(duì)非自然意義理論的批評(píng)以及Grice的回應(yīng)來(lái)說(shuō)明這兩種理論在刻畫(huà)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時(shí)各自起到的作用。在二戰(zhàn)期間,一個(gè)被意大利士兵逮捕的美國(guó)軍官吟誦了他在高中時(shí)期學(xué)習(xí)的德語(yǔ)詩(shī)句“KennstdudasLand,wodieZitronenblühen”,其常規(guī)意義是:“你知道檸檬樹(shù)開(kāi)花的地方嗎?”他自己和抓他的士兵都不懂德文,美國(guó)軍官意圖讓意大利士兵把這句德語(yǔ)發(fā)音的問(wèn)句理解為“你不知道我是德國(guó)軍官嗎?”,意大利士兵猜測(cè)到了他的意圖,并且也因此相信他是德國(guó)軍官。在這種情形下,美國(guó)軍官通過(guò)吟詠德文詩(shī)句表達(dá)了一個(gè)說(shuō)話(huà)者意義,而且它也符合非自然意義的定義,但是我們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結(jié)論說(shuō)這句德語(yǔ)詩(shī)的意義就是“我是德國(guó)軍官”呢?任何一個(gè)常規(guī)的意義理論都不愿意承認(rèn)這個(gè)結(jié)果。畢竟,這個(gè)美國(guó)軍官可以通過(guò)言說(shuō)任何一個(gè)德語(yǔ)發(fā)音的疑問(wèn)句來(lái)實(shí)現(xiàn)這一交際效應(yīng)。通過(guò)這個(gè)例子,Searle批評(píng)非自然意義理論:“意義不僅僅是關(guān)乎意圖的問(wèn)題,它也是一個(gè)關(guān)乎慣例的問(wèn)題。”(5)Searle, John, “What is a Speech Act?”, In Philosophy in America.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5,p.230.Grice概括Searle的反駁如下:“[對(duì)說(shuō)話(huà)者U和聽(tīng)話(huà)者A而言] U通過(guò)x意味著某事,指的是(1)U意圖通過(guò)使A意識(shí)到U想要以產(chǎn)生某種效果的方式而使得A產(chǎn)生了這種效果,即U意圖使A識(shí)別出他的意圖使得A產(chǎn)生某種效果,并且(2)(如果言說(shuō)x是言說(shuō)一個(gè)句子)U意圖通過(guò)使A意識(shí)到這個(gè)言說(shuō)的句子通常或按照慣例都用于產(chǎn)生這一效果,并最終以這種通常或慣例的方式來(lái)讓A識(shí)別出U的意圖或讓A產(chǎn)生出這種效果。”(6)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0.
Grice已經(jīng)意識(shí)到(1)與(2)之間的可能背離:通過(guò)言說(shuō)一個(gè)語(yǔ)句,站在聽(tīng)者的角度該語(yǔ)句依據(jù)語(yǔ)言學(xué)的慣例或常規(guī)而讓聽(tīng)者持有的信念,與說(shuō)話(huà)者意圖讓聽(tīng)者持有的信念,兩者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非自然意義理論主要是聽(tīng)者向說(shuō)話(huà)者的“適應(yīng)”,如果聽(tīng)者沒(méi)有如說(shuō)話(huà)者所意圖地產(chǎn)生信念,則交際意圖未獲得傳遞,因而也沒(méi)有什么非自然意義產(chǎn)生。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更多是體現(xiàn)了說(shuō)話(huà)者向聽(tīng)者的“適應(yīng)”,此時(shí)聽(tīng)者所代表的是語(yǔ)言共同體中有能力的說(shuō)話(huà)者,代表的是語(yǔ)言使用的慣例或常規(guī)。不論說(shuō)話(huà)者所意圖表達(dá)的是什么,聽(tīng)者都可以根據(jù)語(yǔ)境信息基于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推導(dǎo)出言說(shuō)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假若此會(huì)話(huà)蘊(yùn)含不是說(shuō)話(huà)者所意圖表達(dá)的,那么說(shuō)話(huà)者也會(huì)承認(rèn)他的意圖沒(méi)能實(shí)現(xiàn)。
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中,Grice劃分言說(shuō)所說(shuō)的和所蘊(yùn)含的,其目的在于強(qiáng)調(diào)脫離語(yǔ)境時(shí)語(yǔ)言使用的常規(guī)性和具體語(yǔ)境中語(yǔ)言使用的靈活性。對(duì)此Saul指出:“對(duì)Grice而言,說(shuō)話(huà)者所說(shuō)的和它所蘊(yùn)含的并不簡(jiǎn)單就是說(shuō)話(huà)者所意圖的。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每一種情形中,始終存在有一些限制使得他們不能隨便地說(shuō)出或蘊(yùn)含任意的東西……說(shuō)話(huà)者使用語(yǔ)句S來(lái)說(shuō)出P,對(duì)于這種情形而言,僅僅依靠說(shuō)話(huà)者意味著P是不夠的,另外的條件是S是一個(gè)句子并且它通常用來(lái)意味著P。我們將論證類(lèi)似的限制也適用于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在此理解下,如果說(shuō)話(huà)者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某些東西,她必須讓這個(gè)蘊(yùn)含對(duì)聽(tīng)者來(lái)說(shuō)是可理解的。說(shuō)話(huà)者并不總是能夠做到這一點(diǎn),無(wú)論他的意圖究竟是什么。”(7)Saul, J. M., “Speaker Meaning,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Nos, 36(2),2002,p.229.不難看出,盡管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可以讓說(shuō)話(huà)者表達(dá)超出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之外的意義,但是這種靈活性比起非自然意義來(lái)說(shuō)還是會(huì)有更多的限制,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必須在具體語(yǔ)境中對(duì)聽(tīng)者是可理解、可計(jì)算、可邏輯推導(dǎo)的。
總而言之,為了刻畫(huà)說(shuō)話(huà)者意義,Grice構(gòu)造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前者訴諸意圖的傳遞,而后者則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了語(yǔ)言學(xué)的慣例在靈活表達(dá)言外之意時(shí)的作用。Levinson曾經(jīng)指出:“非自然意義劃出了一個(gè)交際理論應(yīng)該解釋的交際效應(yīng)的外界。”(8)Levinson, S. C.,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0,p.13.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和非自然意義理論都是一種交際理論。我們討論的核心問(wèn)題是,相對(duì)于廣泛被接受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非自然意義理論到底具有什么價(jià)值?它只是一個(gè)輔助性的理論,用來(lái)容納所有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所解釋不了的說(shuō)話(huà)者意義嗎?通過(guò)文本分析,我們將展示:對(duì)于意義問(wèn)題而言,Grice不僅認(rèn)為非自然意義理論具有獨(dú)立價(jià)值,而且具有更基礎(chǔ)的價(jià)值。
Grice承認(rèn)語(yǔ)言的慣例在解釋意義時(shí)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時(shí)堅(jiān)持意義也可以不依照慣例而產(chǎn)生:“當(dāng)意義的載體是一個(gè)句子(或言說(shuō))時(shí),通常情況下說(shuō)話(huà)者的意圖得到承認(rèn)是由于[交際雙方]知道這個(gè)句子的常規(guī)用法(的確我對(duì)非常規(guī)性蘊(yùn)含的解釋依賴(lài)于這一觀念)。但是,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我傾向于(如果可能的話(huà))把通過(guò)言說(shuō)一個(gè)句子來(lái)意味某事,當(dāng)作通過(guò)言說(shuō)(廣義上的言說(shuō))來(lái)意味某事的一個(gè)特例。與此同時(shí),把句子與特有反應(yīng)間的常規(guī)聯(lián)系[即按照語(yǔ)言的慣例來(lái)產(chǎn)生信念]當(dāng)作言說(shuō)與各種反應(yīng)之間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可能方式之一。”(9)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1.在這里廣義上的言說(shuō),既包括言說(shuō)一個(gè)句子,也包括其他方式的言說(shuō),例如拍拍肚子、畫(huà)一幅畫(huà)等等。Grice認(rèn)為,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只是非自然意義理論的一種特殊情況:(1)非自然意義理論解釋的是廣義上的言說(shuō)與意義之間的關(guān)系,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解釋的是言說(shuō)語(yǔ)句時(shí)語(yǔ)句的常規(guī)意義與可計(jì)算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后者是前者的一種特殊情況;(2)非自然意義理論不預(yù)設(shè)語(yǔ)句與特有反應(yīng)之間的常規(guī)聯(lián)系,即交際雙方不一定要通過(guò)句子的常規(guī)意義來(lái)產(chǎn)生出說(shuō)話(huà)者意義,這一點(diǎn)可以通過(guò)Searle的反例明顯看出來(lái)。最終,Grice認(rèn)為Searle的例子不構(gòu)成非自然意義理論的反例,因?yàn)槭敲绹?guó)軍官說(shuō)出德文詩(shī)句時(shí)的聲調(diào)、語(yǔ)氣和手勢(shì)等這一廣義的言說(shuō)行為非自然地意味著“我是一名德國(guó)軍官”。這一非自然意義不是德文詩(shī)句的常規(guī)意義,也不是根據(jù)其常規(guī)意義在語(yǔ)境中推導(dǎo)出的言外之意。
Grice把言說(shuō)的非自然意義稱(chēng)為“說(shuō)話(huà)者的場(chǎng)合意義”,而把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稱(chēng)為“言說(shuō)類(lèi)型的無(wú)時(shí)間意義”或“言說(shuō)類(lèi)型的應(yīng)用無(wú)時(shí)間意義”,他認(rèn)為“無(wú)時(shí)間意義和應(yīng)用無(wú)時(shí)間意義最終可以通過(guò)說(shuō)話(huà)者場(chǎng)合意義這一概念(再加上一些其他概念)加以解釋和澄清,最終通過(guò)意圖這一概念加以說(shuō)明”(10)②③④ 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91,298,303,44.。換言之,言說(shuō)的語(yǔ)句所具有的常規(guī)意義不是被初始假定的。Grice自己并沒(méi)有著手去探討上述的還原是如何可能的。Grice對(duì)這些工作并不感興趣,他指出:“因?yàn)槲也徽J(rèn)為意義在本質(zhì)上與常規(guī)有關(guān)聯(lián)。”②
提升增值稅專(zhuān)用發(fā)票管理水平,包括以下幾個(gè)方面:首先應(yīng)及時(shí)取得增值稅專(zhuān)用發(fā)票。在確保交易真實(shí)的條件下,供應(yīng)商提供的材料、土方運(yùn)輸及租賃費(fèi),可由國(guó)家稅務(wù)機(jī)關(guān)代開(kāi)發(fā)票;其次要加強(qiáng)對(duì)發(fā)票的認(rèn)證管理,及時(shí)對(duì)發(fā)票上的項(xiàng)目進(jìn)行歸檔處理。避免使用過(guò)與未使用的發(fā)票發(fā)生混合,相互抵扣的。此外在發(fā)票認(rèn)證之前,檢查發(fā)票、合同、單位是否真實(shí)、匹配。若存在供應(yīng)商故意弄虛作假的行為,同時(shí)因建立誠(chéng)信機(jī)制,建立黑名單,對(duì)于進(jìn)入黑名單的供應(yīng)商一律拒絕;最后加強(qiáng)對(duì)增值稅資金源頭的管理,做到確定對(duì)方已經(jīng)付款后,才可開(kāi)具發(fā)票。
Grice在1976年“Meaning Revisited”一文的最后說(shuō)明了這兩種理論的相互關(guān)系,“在某種程度上,拒絕無(wú)窮倒退的意圖或某些鬼祟的意圖這種做法所起到的作用是……為我們?cè)谥罢撐闹兴鶎?shí)施的方案[即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提供一個(gè)理由,以至于我們可以在摒棄意圖概念的情況下完整地給出說(shuō)話(huà)者意義。這可能是正確的,但是這一方案的缺陷在于沒(méi)有說(shuō)明為什么它在解釋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時(shí)總是恰到好處。我認(rèn)為,如果大家接受我所描述的框架[用非自然意義理論和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共同解釋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我們的建議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那種任意性或特設(shè)性就會(huì)被移除,或者至少得到緩解”③。Grice在這里表明了三個(gè)意思:第一,不借助于意圖來(lái)刻畫(huà)說(shuō)話(huà)者意義可能是正確的,即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也可以正確地描述某些說(shuō)話(huà)者意義的生成;第二,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本質(zhì)上是與意圖的表達(dá)和識(shí)別相關(guān)的,否則Grice不會(huì)認(rèn)為利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來(lái)刻畫(huà)說(shuō)話(huà)者意義這一方案是有缺陷的;第三,只有結(jié)合非自然意義理論和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才能對(duì)說(shuō)話(huà)者意義進(jìn)行充分的刻畫(huà)。
我們堅(jiān)持Grice的這一立場(chǎng),下文將從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測(cè)試標(biāo)準(zhǔn)入手,考察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對(duì)于澄清說(shuō)話(huà)者意義的局限性,并以此辯護(hù)意圖在刻畫(huà)說(shuō)話(huà)者意義中的核心地位。
二、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可廢止原則與挑戰(zhàn)
Grice認(rèn)為,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準(zhǔn)是明顯廢止原則EC和語(yǔ)境廢止原則CC:“你要記住,一個(gè)潛在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p被明顯地廢止了,如果一定語(yǔ)言形式的言說(shuō)假定地蘊(yùn)含了p,可是但不是p或我并沒(méi)有意思去蘊(yùn)含p這樣的表達(dá)是被允許附加的;蘊(yùn)含p被語(yǔ)境廢止,如果能夠發(fā)現(xiàn)一些情境,在這些情境下言說(shuō)一定形式的語(yǔ)詞將直接不會(huì)帶來(lái)那個(gè)蘊(yùn)含。”④Blome-Tillmann指出:“Grice認(rèn)為,由于這兩個(gè)原則中的每一個(gè)都是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出現(xiàn)的必要條件,故而它們?yōu)槲覀兲峁┝艘粋€(gè)有用的測(cè)試以確定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在何時(shí)不出現(xiàn):Grice指出,如果這兩個(gè)原則中間至少有一個(gè)不被滿(mǎn)足,那么我們就能確定自己不是在處理會(huì)話(huà)蘊(yùn)含。”(11)Blome-Tillmann,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the Cancellability Test”, Analysis, 68, 2008,p.157.
現(xiàn)在,我們主要來(lái)考察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EC原則。如前所述,在你詢(xún)問(wèn)我的就餐意見(jiàn)時(shí),我回答說(shuō)“我現(xiàn)在還不餓”將會(huì)蘊(yùn)含著“我現(xiàn)在不想去任何飯店就餐”,因?yàn)榧俣ㄕf(shuō)話(huà)者“我”遵守合作原則,那么在聽(tīng)者“你”看來(lái)——如果我回答了你關(guān)切的問(wèn)題則該蘊(yùn)含是被要求的。事實(shí)上,按照Broome的分析,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推導(dǎo)不是被要求的而是被允許的:聽(tīng)者從相信說(shuō)話(huà)者現(xiàn)在還不餓,推出相信說(shuō)話(huà)者現(xiàn)在還不想去飯店就餐,這是被允許的(12)Broome, John, Rationality Through Reasoning, Oxford: WILEY Blackwell,2013,pp.189-191.。無(wú)論如何,站在聽(tīng)者的角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一個(gè)被允許進(jìn)行的計(jì)算和推導(dǎo)。與此相對(duì)應(yīng)的一個(gè)事實(shí)是,說(shuō)話(huà)者可以通過(guò)附加說(shuō)明來(lái)直接撤銷(xiāo)或明顯廢止這個(gè)推導(dǎo)過(guò)程。Walczak指出:“一個(gè)人可以通過(guò)添加一個(gè)注銷(xiāo)條款以廢止蘊(yùn)含,這時(shí)明顯的廢止就做出了。然而,注銷(xiāo)條款的添加必須是被‘允許的’,并且也不能導(dǎo)致‘邏輯上的荒謬’或‘語(yǔ)言學(xué)上的冒失’。換言之,注銷(xiāo)條款不能導(dǎo)致真值論上的矛盾關(guān)系。這就是為什么[以注銷(xiāo)條款的方式來(lái)]廢止常規(guī)性蘊(yùn)含(13)Huang Yan指出:“常規(guī)性的蘊(yùn)含是一種非真值條件的推理,它不是根據(jù)言說(shuō)所說(shuō)的、以某種一般而又自然的方式所做的演繹推理,而是根據(jù)附著于特定語(yǔ)詞或語(yǔ)言形式的約定性特征而產(chǎn)生的推理。” (Huang Yan:《Pragmatics》,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54頁(yè))例如,從言說(shuō)“約翰很窮但是他很誠(chéng)實(shí)”可以推理得到“約翰很窮并且他很誠(chéng)實(shí)”,這是基于該言說(shuō)的真值條件而進(jìn)行的衍推;但是從該言說(shuō)推導(dǎo)得出“約翰的貧窮和他的誠(chéng)實(shí)是對(duì)比鮮明的”或者推導(dǎo)出“貧窮的人一般都不誠(chéng)實(shí)”就是根據(jù)特定語(yǔ)詞“但是”的常規(guī)性意義而進(jìn)行的衍推。是不恰當(dāng)?shù)模源藦U止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則是恰當(dāng)?shù)摹!?14)Walczak,G.,“On Explicatures, Cancellability, and Cancellation”, SpringerPlus, 5:1115,2016, pp.1-2.
無(wú)論如何,EC和CC原則,一直被認(rèn)為是識(shí)別和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基石,是最好的測(cè)試(15)參見(jiàn)Portner, P.H., What is Meaning: Fundamentals of Formal Semantic, Oxford: Blackwell, 2005, p.205。。但是,Weiner在2006年對(duì)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EC提出了挑戰(zhàn)。Alice和Sarah正在乘坐一輛擁擠的列車(chē),Alice看上去體格強(qiáng)壯卻橫躺著占了兩個(gè)位置,Sarah站在旁邊。這時(shí),Sarah對(duì)Alice說(shuō),[P]“我十分好奇這一點(diǎn),你讓個(gè)位置給其他人來(lái)坐這一點(diǎn)在物理上是否可能”。此時(shí),該言說(shuō)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當(dāng)然是[Q]“Alice應(yīng)當(dāng)讓出一個(gè)位置”。假定現(xiàn)在Sarah加上一句話(huà)說(shuō),[but not Q]“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說(shuō)你應(yīng)當(dāng)讓出一個(gè)位置,我只是好奇你讓出一個(gè)位置在物理上是否可能”。Weiner指出:“這個(gè)例子完全符合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被明顯廢止的形式。但是,這時(shí)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并沒(méi)有被明顯廢止。附加說(shuō)明后,人們通常認(rèn)為Sarah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甚至是以更加粗魯?shù)姆绞綇?qiáng)調(diào)Alice應(yīng)該讓座。”(16)Weiner, M., “Are All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Cancellable?”, Analysis, 66, 2006, p.128.在這個(gè)反例中,Sarah所附加的說(shuō)明更應(yīng)該被恰當(dāng)?shù)乩斫鉃榉粗S,因而是加強(qiáng)了蘊(yùn)含q(即Alice應(yīng)當(dāng)讓出一個(gè)位置),而不是將其廢止。該反例對(duì)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測(cè)試標(biāo)準(zhǔn)所帶來(lái)的巨大挑戰(zhàn)在于,無(wú)論如何細(xì)致地描述附加說(shuō)明——例如“我的意思真的是如此”,“我絕對(duì)沒(méi)有諷刺你的意思”如此等等,在此語(yǔ)境中所有的附加說(shuō)明始終會(huì)表達(dá)反諷從而加強(qiáng)蘊(yùn)含,而不是按照該說(shuō)明的常規(guī)意義廢止蘊(yùn)含。
在聽(tīng)到言說(shuō)P的時(shí)候,Alice面臨一個(gè)抉擇:到底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是按照該言說(shuō)P的常規(guī)意義去理解,還是她要表達(dá)某種言外之意呢?毋庸諱言,Alice知道自己是以一種健康的狀態(tài)呈現(xiàn)在Sarah面前,Sarah也明白Alice了解這一點(diǎn)。因此,Alice在此語(yǔ)境下會(huì)做出類(lèi)似這樣的推導(dǎo):Sarah不會(huì)關(guān)心我的健康狀態(tài)——挪個(gè)位置出來(lái)在物理上是否可能,考慮到當(dāng)下的情況,她一定是建議我應(yīng)當(dāng)讓座。這是一個(gè)典型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推導(dǎo)的過(guò)程。為了測(cè)試該語(yǔ)境下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否出現(xiàn),根據(jù)Grice的建議,我們可以引入一個(gè)注銷(xiāo)條款來(lái)直接廢止該蘊(yùn)含:如果該測(cè)試通過(guò),那么此時(shí)此地我們可以確定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出現(xiàn)了,否則這就不是一個(gè)關(guān)于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推導(dǎo)。然而,當(dāng)Sarah附加說(shuō)明[but not Q]時(shí),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被期待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明顯被廢止并沒(méi)有出現(xiàn)。Alice不會(huì)從常規(guī)意義去理解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相反她會(huì)認(rèn)為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是一種反諷,其本質(zhì)是另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
Alice的推導(dǎo)可能是以下面的方式進(jìn)行的:Sarah明明可以看出我身體健康,因而她就是要我讓出位置,但是她卻故意說(shuō)出一個(gè)與自己真實(shí)想法相違背的說(shuō)明——“我的意思并不是說(shuō)你應(yīng)當(dāng)讓出一個(gè)位置”,這顯然是表達(dá)一個(gè)反諷(17)參見(jiàn)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4。。Sarah意圖通過(guò)附加說(shuō)明想要表達(dá)何種意義呢?也許Sarah就是想表達(dá)一個(gè)反諷,也許Sarah是覺(jué)得之前的言說(shuō)P過(guò)于唐突因而想廢止原言說(shuō)P的蘊(yùn)含q。但是,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面向聽(tīng)者的語(yǔ)用推導(dǎo),Alice沒(méi)有義務(wù)去識(shí)別Sarah的真實(shí)意圖,在當(dāng)下語(yǔ)境中Alice沒(méi)有理由不認(rèn)為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不是在表達(dá)反諷。無(wú)論如何,在Alice看來(lái),該附加說(shuō)明都是在加強(qiáng)原有的蘊(yùn)含而不是廢止它。
一個(gè)讓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尷尬的處境出現(xiàn)了:當(dāng)我們?cè)跍y(cè)試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時(shí)候(即言說(shuō)P是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q),我們又不得不面對(duì)另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即附加說(shuō)明[but not Q]是否以反諷的方式加強(qiáng)了蘊(yùn)含q)。如果我們想讓第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通過(guò)明顯廢止原則EC的測(cè)試,我們就必須表明后面的附加說(shuō)明不是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換言之,附加說(shuō)明依據(jù)其常規(guī)意義廢止了原言說(shuō)P的蘊(yùn)含。不幸的是,如果不借助于Sarah和Alice對(duì)意圖的相互識(shí)別,我們沒(méi)有任何方式來(lái)判定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不是一個(gè)表達(dá)反諷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根據(jù)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測(cè)試?yán)碚摚胍卸⊿arah的附加說(shuō)明到底是不是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我們只能繼續(xù)使用明顯廢止原則EC,然而即便Sarah又一次地附加說(shuō)明也終究于事無(wú)補(bǔ),因?yàn)槟侵粫?huì)讓我們?cè)侔焉鲜龅恼撟C過(guò)程重復(fù)一次。于是,在火車(chē)乘坐反例中,為了測(cè)試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否出現(xiàn),我們就會(huì)陷入對(duì)其他會(huì)話(huà)蘊(yùn)含進(jìn)行測(cè)試的無(wú)窮倒退之中,這才是火車(chē)乘坐反例對(duì)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及其測(cè)試原則給出的巨大挑戰(zhàn)。
如前所述,一個(gè)言說(shuō)的非自然意義與該言說(shuō)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可能是相互背離的,甚至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根據(jù)非自然意義理論,Alice可能識(shí)別出Sarah的意圖——通過(guò)言說(shuō)[but not Q]廢止之前言說(shuō)P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進(jìn)而會(huì)話(huà)雙方達(dá)成了一個(gè)成功的交際效應(yīng)。另一方面,根據(jù)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Alice沒(méi)有義務(wù)去識(shí)別出Sarah的真實(shí)意圖,因而她會(huì)繼續(xù)將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理解為反諷,進(jìn)而加強(qiáng)了原來(lái)的蘊(yùn)含q。
Grice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及其測(cè)試原則在此處所面對(duì)的困難主要有兩個(gè):第一,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言說(shuō)的非自然意義與它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之間存在著間隙,這使得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只能處理部分類(lèi)型的說(shuō)話(huà)者意義。假若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確實(shí)想要撤回之前的蘊(yùn)含,那么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將會(huì)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認(rèn)為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不是在表達(dá)反諷呢?我們不能認(rèn)為這些反例是不恰當(dāng)?shù)模鴷?huì)認(rèn)為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自身是不完善的。無(wú)論如何,我們現(xiàn)在更能理解Grice為什么堅(jiān)持用非自然意義理論和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共同來(lái)解釋說(shuō)話(huà)者意義了,“這一方案[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的缺陷在于沒(méi)有說(shuō)明為什么它在解釋說(shuō)話(huà)者意義時(shí)總是恰到好處”(18)Grice, Paul,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03.。第二,僅僅限定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中,言說(shuō)P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這一點(diǎn)是無(wú)法通過(guò)明顯廢止原則EC來(lái)進(jìn)行測(cè)試的。我們不能蒙著自己的眼睛說(shuō),火車(chē)乘坐案例中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測(cè)試是一個(gè)失敗的例子,盡管看上去它符合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推導(dǎo)的一切條件。由于它通不過(guò)EC測(cè)試,所以它就不是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挽救這一局面的一種可能方案是,借助于Sarah言說(shuō)[but not Q]時(shí)她的意圖以及Alice對(duì)該意圖的識(shí)別,Alice終結(jié)了她原本進(jìn)行的推導(dǎo)(即認(rèn)為附加說(shuō)明是在表達(dá)反諷),進(jìn)而廢止了言說(shuō)P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于是,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明顯廢止原則EC還是被妥善地保留下來(lái)了。我們通過(guò)意圖的相互識(shí)別把Alice從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測(cè)試的無(wú)窮倒退中拽了出來(lái)。
也許我們的這個(gè)結(jié)論來(lái)得太輕松了,有人會(huì)認(rèn)為火車(chē)乘坐反例只是表明聽(tīng)者在理解附加說(shuō)明的時(shí)候違背了說(shuō)話(huà)者的本來(lái)意圖,這并不表示在做出附加說(shuō)明之前聽(tīng)者不能按照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所描述的那樣來(lái)進(jìn)行蘊(yùn)含的推導(dǎo)。只要聽(tīng)者能夠根據(jù)相關(guān)的語(yǔ)境給出蘊(yùn)含的推導(dǎo),而且我們能夠設(shè)想出該蘊(yùn)含被廢止的情形,這就足夠了。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明顯廢止原則只需要蘊(yùn)含的廢止是原則上可行的,我們并不需要強(qiáng)調(diào)蘊(yùn)含的廢止一定是現(xiàn)實(shí)的。
三、對(duì)EC原則的挽救
Tillmann認(rèn)為,火車(chē)乘坐反例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有力,它不會(huì)從原則上動(dòng)搖Grice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測(cè)試原則EC和CC。Tillmann指出,火車(chē)乘坐反例中,言說(shuō)P所帶來(lái)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既可以被語(yǔ)境廢止,也可以被明顯廢止。很明顯,存在有一些語(yǔ)境使得Sarah說(shuō)出P的目的就是想知道Alice挪一下位置這一點(diǎn)在物理上是否可能,而不是意味著Alice應(yīng)該讓座,例如當(dāng)Sarah作為一個(gè)大夫在給Alice看病時(shí)。當(dāng)然,也存在有一些語(yǔ)境使得Sarah說(shuō)出P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q,但是q是可以通過(guò)注銷(xiāo)條款而被明顯廢止的,例如Sarah在觀察到Alice受傷的腰后再說(shuō)出[but not Q]并且Alice也確認(rèn)Sarah之前沒(méi)有觀察到這一點(diǎn)。火車(chē)乘坐案例真正挑戰(zhàn)的只是:在類(lèi)似于火車(chē)乘坐的特定語(yǔ)境中,言說(shuō)P的確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q,并且通過(guò)附加說(shuō)明直接廢止q似乎是不可能的。對(duì)此,Tillmann建議是將Grice的明顯廢止原則(EC)弱化為EC*以容納上述反例(19)Blome-Tillmann,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the Cancellability Test”, Analysis, 68, 2008, pp.159-160.:
EC:在一個(gè)語(yǔ)境C中,如果言說(shuō)P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那么言說(shuō)[P且非Q]或是[P但我并不意味著Q]在語(yǔ)境C中是被允許的,并且說(shuō)話(huà)者對(duì)q的承諾將據(jù)此被廢止。
EC*:在一個(gè)語(yǔ)境C中,如果言說(shuō)P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那么存在有語(yǔ)句Q和一個(gè)語(yǔ)境C’使得:
[1]在語(yǔ)境C’中,言說(shuō)P能夠傳達(dá)q;
[2]在語(yǔ)境C’中,言說(shuō)[not Q]能夠傳達(dá)(q;
[3]在語(yǔ)境C’中,言說(shuō)[I don’t mean to imply thatQ]能夠傳達(dá)說(shuō)話(huà)者不在語(yǔ)境C’中蘊(yùn)含q;
[4]言說(shuō)[not Q]或[I don’t mean to imply thatQ]在語(yǔ)境C’中是被允許的,并且說(shuō)話(huà)者不再承諾q。
Tillmann認(rèn)為,盡管在語(yǔ)境C中注銷(xiāo)條款[not Q]并不能廢止言說(shuō)P的蘊(yùn)含q,但是只要存在有語(yǔ)境C’使得該注銷(xiāo)條款可以廢止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那么我們?nèi)匀豢梢哉J(rèn)為語(yǔ)境C中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滿(mǎn)足弱化版的明顯廢止原則EC*,即使它不滿(mǎn)足Grice的原初版本EC。Tillmann認(rèn)為Grice的明顯廢止標(biāo)準(zhǔn)依然可以作為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測(cè)試標(biāo)準(zhǔn),只不過(guò)它是以一種弱化的形式出現(xiàn)的。Tillmann的建議初看下去是特設(shè)性的假定(ad hoc),但是它確實(shí)能夠容納EC失效的例子。一個(gè)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被推導(dǎo),只要它原則上是可被廢止的。至于特殊語(yǔ)境中,它在事實(shí)上被廢止與否并不重要。
Tillmann的方案似乎是可信的:按照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一般慣例(convention),言說(shuō)P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是可以通過(guò)EC被測(cè)試的,盡管不排除例外情況。具體到火車(chē)乘坐反例中,依據(jù)慣例我們通常會(huì)認(rèn)為言說(shuō)P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q,因?yàn)樵摃?huì)話(huà)蘊(yùn)含在原則上是可以被廢止的,盡管在此語(yǔ)境中Sarah的附加說(shuō)明并不能事實(shí)上廢止它。于是我們的討論似乎又回到了原點(diǎn)。請(qǐng)回憶Saul的觀點(diǎn)——不僅言說(shuō)S的常規(guī)意義是一種慣例或常規(guī),而且言說(shuō)S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也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慣例或常規(guī),即以聽(tīng)者可理解、可計(jì)算、可推導(dǎo)的方式得出。不過(guò),這種觀點(diǎn)太模糊了,我們有必要對(duì)此展開(kāi)進(jìn)一步的討論。
談及慣例,Lewis指出:“一個(gè)群體P使用一種語(yǔ)言L的慣例是指一個(gè)L中關(guān)于誠(chéng)實(shí)(truthfulness)與信任(trust)的慣例。在L中是誠(chéng)實(shí)的就是以如下的方式來(lái)行動(dòng):絕不試圖使用在L中不為真的任何語(yǔ)句。除非人們相信某個(gè)語(yǔ)句在L中為真,否則就要避免使用它。L中的信任就是以如下的方式形成信念:把L中的誠(chéng)實(shí)賦予其他人,當(dāng)其他人說(shuō)出L中的某個(gè)語(yǔ)句時(shí),這個(gè)人就逐漸相信被說(shuō)出的語(yǔ)句在L中為真并以這個(gè)態(tài)度對(duì)他人的言說(shuō)行為進(jìn)行響應(yīng)。”(20)Lewis, David, “Languages and Language”,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40-511.Lewis刻畫(huà)了按照慣例來(lái)使用語(yǔ)言L的六個(gè)特征:(1)在使用L時(shí),有一個(gè)關(guān)于誠(chéng)實(shí)和信任的規(guī)則廣泛流傳于P中:說(shuō)話(huà)者一般只說(shuō)那些他相信在L中為真的語(yǔ)句——這是誠(chéng)實(shí)地使用L;通過(guò)分享說(shuō)話(huà)者的信念并據(jù)此調(diào)整自己的其他信念,聽(tīng)話(huà)者(或讀者)對(duì)說(shuō)話(huà)者及其言說(shuō)進(jìn)行響應(yīng)——這是信任地使用L。(2)群體中的成員都相信以上規(guī)則普遍流行于這個(gè)群體之中。(3)成員普遍遵從這一規(guī)則并對(duì)此有所期待,正是這種期待通常給每個(gè)成員他自身也應(yīng)該如此遵從的可靠理由。(4)P中的成員都遵從L中有關(guān)誠(chéng)實(shí)與信任的規(guī)則,這是一種普遍的偏好和選擇。(5)L中有關(guān)誠(chéng)實(shí)與信任的規(guī)則R是有替代選項(xiàng)的。這一特征主要用來(lái)描述慣例的任意性和可變更性,因?yàn)橥耆赡苡辛硪环N關(guān)于誠(chéng)實(shí)和信任的規(guī)則R’使得上述(3)和(4)兩個(gè)條件都成立。此時(shí),規(guī)則R’就構(gòu)成了規(guī)則R的替代選擇。(6)所有這些規(guī)則R是全體成員的共同知識(shí),即沒(méi)有人相信另有人懷疑它們,也沒(méi)有人相信另有人相信另有人懷疑它們。
Lewis把慣例視為群體P為了維持彼此交流的旨趣而達(dá)到的博弈均衡,從而語(yǔ)句就可以依據(jù)其常規(guī)意義來(lái)表達(dá)并傳遞有能力說(shuō)話(huà)者的真實(shí)信念。一個(gè)誘人的想法是,把這種語(yǔ)句依據(jù)慣例而具有意義的想法擴(kuò)展到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討論中來(lái)。說(shuō)語(yǔ)言L中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依據(jù)慣例而被推導(dǎo)的,當(dāng)且僅當(dāng),群體P中盛行著一個(gè)關(guān)于L中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被推導(dǎo)的誠(chéng)實(shí)和信任的慣例:只有當(dāng)說(shuō)話(huà)者確實(shí)意圖用言說(shuō)P來(lái)蘊(yùn)含q時(shí),說(shuō)話(huà)者才會(huì)言說(shuō)P,否則他就會(huì)避免這么做;聽(tīng)話(huà)者把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這種誠(chéng)實(shí)使用賦予說(shuō)話(huà)者,并且相信當(dāng)說(shuō)話(huà)者言說(shuō)P時(shí)他確實(shí)會(huì)話(huà)蘊(yùn)含著q;以上依據(jù)慣例而進(jìn)行的蘊(yùn)含推導(dǎo)是群體P的共同知識(shí)。
然而,這樣的說(shuō)法顯然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言說(shuō)P的常規(guī)意義是語(yǔ)言共同體內(nèi)所有成員唯一的、現(xiàn)實(shí)的選擇,與此不同的是言說(shuō)P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卻是多種多樣的,這一點(diǎn)可以從雙關(guān)、隱喻等語(yǔ)言現(xiàn)象中輕易地發(fā)現(xiàn)。在火車(chē)乘坐反例中,Sarah既可以按照附加說(shuō)明的常規(guī)意義來(lái)取消蘊(yùn)含,也可以按照反諷的方式來(lái)加強(qiáng)蘊(yùn)含,相關(guān)的語(yǔ)境信息并不足以讓聽(tīng)者判斷哪一種方式真實(shí)地反映了說(shuō)話(huà)者的意圖。因而,檢測(cè)說(shuō)話(huà)者是否按照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來(lái)表達(dá)信念是可行的,因?yàn)槲覀兛梢酝ㄟ^(guò)一些語(yǔ)用學(xué)上的事實(shí)去判斷他是否真實(shí)地持有這一信念,但是僅僅通過(guò)語(yǔ)用學(xué)事實(shí)來(lái)確定說(shuō)話(huà)者真實(shí)想要表達(dá)的意義卻是很難實(shí)現(xiàn)的,畢竟說(shuō)話(huà)者有太多的方式通過(guò)同一個(gè)言說(shuō)來(lái)表達(dá)各種不同的意義,甚至是彼此對(duì)立的意義。修改后的明顯廢止原則EC*只是表明言說(shuō)P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q原則上可被廢止,即存在有廢止該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語(yǔ)境,但是它并沒(méi)有解釋在火車(chē)乘坐反例中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如何事實(shí)上被廢止了。火車(chē)乘坐反例不是用以挑戰(zhàn)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的一個(gè)壞例子,我們必須在不借助交際意圖這一概念的前提下,把Alice從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測(cè)試的無(wú)窮倒退中挽救出來(lái)。僅僅依靠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理論顯然做不到這一點(diǎn)。
結(jié) 論
言說(shuō)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和它的常規(guī)意義在規(guī)范性程度上是不一樣的。在Lewis那里,群體P在使用語(yǔ)言L時(shí)所遵從的慣例是唯一的、現(xiàn)實(shí)的選擇,即語(yǔ)句的常規(guī)意義是唯一確定的。正因?yàn)槿绱耍珿rice才認(rèn)為,言說(shuō)的常規(guī)意義加上一些語(yǔ)境的信息(以明確指示詞、索引詞的指稱(chēng))可以唯一地決定言說(shuō)的真值條件。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說(shuō)話(huà)者的言外之意,它是不進(jìn)入言說(shuō)的真值條件的,因此言說(shuō)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是可以被廢止的,并且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廢止并不會(huì)和言說(shuō)的真值條件構(gòu)成矛盾。由于Grice堅(jiān)持區(qū)分言說(shuō)的蘊(yùn)含和言說(shuō)所說(shuō)出的內(nèi)容,因此是否可被廢止就成為辨別二者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準(zhǔn)。言說(shuō)所說(shuō)的內(nèi)容是不能撤銷(xiāo)的,因?yàn)椴荒茏龀銮昂蟛灰恢碌难哉f(shuō);常規(guī)性蘊(yùn)含是依據(jù)特定語(yǔ)詞和語(yǔ)言形式的特征被帶入的蘊(yùn)含,它的撤銷(xiāo)會(huì)違背語(yǔ)言的常規(guī)用法,從而導(dǎo)致語(yǔ)言學(xué)上的“冒失”;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無(wú)疑是可撤銷(xiāo)的,只要我們恰當(dāng)?shù)亟o出一個(gè)語(yǔ)境條件(語(yǔ)境廢止)或直接表明說(shuō)話(huà)者并無(wú)此意(明顯廢止)。總而言之,在Grice看來(lái),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可被撤銷(xiāo)是揭示會(huì)話(huà)蘊(yùn)含本質(zhì)的一個(gè)最重要的標(biāo)準(zhǔn),也是測(cè)試會(huì)話(huà)蘊(yùn)含的基石。
如同一開(kāi)始時(shí)所談及的,言說(shuō)的非自然意義主要是聽(tīng)者向說(shuō)話(huà)者的“適應(yīng)”——聽(tīng)者知道說(shuō)話(huà)者有讓他產(chǎn)生特定信念的意圖,并且他也據(jù)此產(chǎn)生了相關(guān)信念;另一方面,言說(shuō)的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則主要是說(shuō)話(huà)者向聽(tīng)者的“適應(yīng)”——說(shuō)話(huà)者知道為了表明其遵守合作原則,通過(guò)言說(shuō)P意味q是被要求的,并且說(shuō)話(huà)者也知道聽(tīng)者明白這一點(diǎn)。正因?yàn)檫m應(yīng)方向的不同,總是存在有說(shuō)話(huà)者所意圖表達(dá)的和實(shí)際上該言說(shuō)所蘊(yùn)含的這兩者之間的間隙。在火車(chē)乘坐反例中,我們能夠想象Sarah想要通過(guò)言說(shuō)[but not Q]以撤回蘊(yùn)含q時(shí)的無(wú)可奈何:她被假定是遵守合作原則的;她知道只要她被假定遵守合作原則,言說(shuō)[but not Q]就會(huì)被Alice理解為反諷,因而加強(qiáng)了q而不是廢止它;Sarah知道(并且她也沒(méi)理由反對(duì)Alice認(rèn)為她知道)Alice肯定會(huì)將[but not Q]理解為反諷。但是,她除了說(shuō)出“我并無(wú)意叫你讓座”之外,她還能通過(guò)什么方式來(lái)撤銷(xiāo)原本的蘊(yùn)含呢?她唯一的期待可能是:Alice,丟開(kāi)會(huì)話(huà)蘊(yùn)含吧,請(qǐng)看看我真誠(chéng)的雙眼,領(lǐng)會(huì)我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