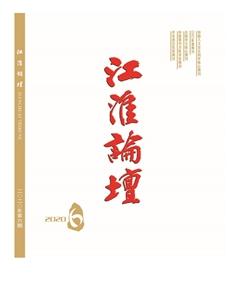論后現代小說與媒介書寫
張東芹 史巖林
摘要:媒介時代帶來了文學書寫的視覺化轉向,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文學與媒介之間的多重互動中,媒介已經超越了文學跨時空傳播的物質載體,而日漸由外在表現形式轉化為文學探討的對象與內容。庫普蘭德、德里羅和品欽等人的后現代小說從媒介與文化、政治及歷史三者的關系入手,探討了媒介話語的運作邏輯,揭示了現代媒介與后現代社會錯綜復雜的關系。對后現代小說媒介書寫的探討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內涵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后現代小說;媒介書寫;文化;政治;歷史
中圖分類號:I207.4?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0)06-0186-007
后現代社會浸染著市場化邏輯,以欲望生產和消費文化為典型特征,作為文化產業的大眾傳媒不斷與大眾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后現代主義的烙印。一方面,現代傳媒活動竭力迎合大眾消費文化,以最大限度搶占市場份額,謀取經濟利益,使得集團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消長;另一方面,大眾文化為現代傳媒的散播開拓了多種渠道,保證了傳媒活動的有效進行,促進消費社會的蔓延和消費符號的全球化復制。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為大眾傳媒的高速發展注入活力。然而,傳媒技術的進步和突破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將帶來思想意識上的束縛。傳媒成了現實生活的延伸,人們不自覺地生活其中,被以文字、聲音、圖像等符號表達權利的媒介話語所牽引,形成了傳媒無意識。在媒體話語的引導下,公眾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逐漸趨同,形成具有一致公共價值的群體,繼而鞏固媒體對人群的操控,易于形成大眾受媒介話語操縱的怪圈。
道格拉斯·庫普蘭德、唐·德里羅和托馬斯·品欽等人的小說從媒介與文化、政治及歷史三者的關系入手,以后現代反諷形式生動再現了媒介話語的運作邏輯:后現代傳媒產業帶來的視覺盛宴不斷沖擊著人們的眼球,把消費者帶入一個充滿仿真和超現實視像的世界;媒介文化與政治話語合謀,政治簡約為形象、展覽和故事,政治意義通過表面無害的消遣方式展現給廣大觀眾;媒介制造的超真實影視和影像代替了歷史,以娛樂的方式篡改甚至抹去歷史。
一、媒介與文化
以現代數碼技術為依托的電影、電視、攝影、互聯網等媒介用機械性復制手段完成商品化生產,正在營造著一個視像時代“讀圖”的氛圍,并促成當代社會審美文化消費的蓬勃發展。現代媒介憑借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飛速發展,為大眾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沖擊,人們的目光被電視電影、報紙雜志、巨幅廣告招貼畫和海報欄上一個又一個轉瞬即逝的圖像所吸引。鋪天蓋地的廣播、電視、報刊、廣告宣傳悄無聲息地將人們塑造成沒有思想、沒有判斷力,甚至喪失個體感官經驗的消費者。在這個圖像充斥、信息橫流的時代,大眾并非依據客觀的現實存在對外界作出反應,而是被動接受大眾媒介以技術手段對現實世界的擬態投射,這些經過刻意加工的圖像形態成了人們競相模仿的對象。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將這種通過現代媒介向千家萬戶復制傳播的視覺影像稱為擬像,大家就生活在這種擬像化的文化境遇中。
現代媒介技術的發達帶來一個模糊了現實和幻想的界限而讓人無從分辨虛實的時代,人們體驗到的不是過去那種可怕的孤獨和焦慮,而是一種浮于表面的非真實感。可以說,后現代社會是一個媒介和擬像建構的超真實的世界。超真實的領域比真實更真實,虛擬體驗比真實生活更具誘惑力。庫普蘭德的《X一代》中,克萊爾興奮地告訴安迪“紐約除了有更好的發型和紀念品以外,就像是一個迪斯尼主題樂園”。[1]178由此可見,在人們心中迪斯尼樂園成了現實生活的范例,不是迪斯尼樂園在模仿真實生活,而是真實生活在模仿迪斯尼樂園,并最終超過迪斯尼樂園。正如鮑德里亞所說:“迪斯尼樂園的存在就是為了隱藏這一事實:‘真實的國家,‘真實的美國才是迪斯尼樂園……迪斯尼樂園被呈現為想象世界,為的是使我們相信其余世界是真實的。”[2]迪斯尼樂園是仿真序列里最完美的樣板。它是一個微縮的世界,通過各種模擬造就了人們想象中的景觀,體現著美國安定和平的價值觀。那些非真實的人造景觀影響著真實的美國,成為人們改造現實世界的藍本。這種仿真起到了掩蓋美國價值缺場的作用,并恰恰通過這種掩蓋來證明美國價值觀念。實際上,迪斯尼樂園這個公開的文化工業掩飾了美國這個模仿文化工業的國家的真實面貌。主題公園可以代替旅行、探索真實文化或是了解他人的需要。主題公園作為一種心理技術,與媒介時代相聯系,含蓄地隔離甚至明確地抹去虛假與真實的界限,逐漸導致大眾的去社會化和疏離感。在這一點上,庫普蘭德在《香波星球》中借泰勒之口諷刺性地用“法定”(legislated)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對迪斯尼的印象,用“迪斯尼樂園的法定記憶”[3]5來展示主題公園的強制性作用,強調了媒介時代中擬像世界強加給人們的歷史記憶。當泰勒表示要去歐洲旅行的時候,他的朋友哈默尼很是吃驚:“歐洲?我不明白……我們已經在佛羅里達艾波卡特中心(epcot)主題公園建立了一個很完美的歐洲啊。是不夠好嗎?還是其他什么原因?”[3]96迪斯尼樂園提供了空間游戲世界的一個虛幻之旅。它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適當凈化和神化后,聚集在了這個包含多重空間秩序的純粹幻覺的地方,藉此消除真實旅行的麻煩。它僅僅以一種純粹的、凈化的和非歷史化的形式使商品文化和專業技巧的拜物教永久化。在這里,模型再一次超過了真實世界:在迪斯尼樂園的烏托邦世界里已經包含了幾乎所有東西,為什么還要去見證歐洲衰敗呢?迪斯尼不是以那里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嗎?哈默尼的態度生動地表現了后現代媒介社會的文化惰性,相信迪斯尼樂園的絕對表征,相信歷史和地緣政治可以被包裝和再生產,而拒絕探索真實歷史的行動;認為歷史是用來消費的,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滿足任何苛刻的消費者。他對迪斯尼的偏愛展示了后現代社會生活的刻板,真實的生活被視為想象的、非物質的、令人不滿意的,媒介傳播中虛擬的幻想才是真實可信的。人們對媒介技術及擬像世界的信任和依賴暗示了后現代世界是一個符號和形式加速增長的虛無世界,存在著一種不斷加速的內爆和惰性,一切都是可見、明晰、透明的,但又是高度不穩定的。
伴隨著消費主義全球化的浪潮,遍及全球的超市成為以美國化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文化使者,在全球范圍內傳遞著西方現代性的理念和美國文化價值觀,成為大眾文化的代表性符碼。連鎖超市的廣告和宣傳噱頭宣揚的是美國價值觀、家庭親情和享樂主義,把消費者帶入了一個神話般的超現實世界,仿真的邏輯決定了個體看待自身、他者和世界的方式。這類超市已成為美國價值的典范,比美國社會更能體現出美國人的價值觀。消費者在購物的過程中也在消費其“符號價值”,即對其所表征的文化的認可,獲得了西方現代性的消費體驗及社會歸屬感。換句話說,消費者被帶入一個充滿仿真和超現實視像的世界,同時依靠購物場所構建了個人的文化身份。在德里羅的《白噪音》中,看電視和超市購物成了主人公杰克一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個周末,全家人都會聚在一起觀看電視,欣賞插播的商業廣告和突發新聞。大家對“飛機失事”和“自然災害”這樣的新聞事件充滿興趣,因為對他們而言,鏡頭傳遞著短暫的暴力美學和絕妙的想象空間,可以壓抑內心的死亡恐懼。[4]14他們也從電視廣告中獲取最新的商品信息,依據廣告宣傳的美好畫面規劃自己的生活,換句話說,杰克一家的超市購物清單完全依賴于電視廣告的宣傳。與具有持久誘惑力的災難新聞一樣,電視商業廣告也已悄無聲息地嵌入觀眾的深層意識,不斷生根發芽。杰克一家人甚至在說夢話時都會蹦出商業廣告中頻繁出現的品牌名:豐田卡羅拉(Toyota Corolla)、豐田得利卡(Toyota Celica)、豐田克雷西達(Toyota Cressida)、松下電器(Panasonic),這些宛若計算機自動發出的跨民族的名字,幾乎全世界人都會發音。[4]155這表明,媒介文化最終將觀眾轉化為數字化鏈條上的一個節點,成為媒介網絡傳輸的一部分,促使欲望驅使的個體產生某種虛假的自我超越感。杰克一家在遭遇毒霧事件后倍感孤單和無助,想到自己無望的未來更是無奈與沮喪。令人吃驚的是,這種孤獨和無助感在進入超市時一掃而光,超市就如同一面鏡子一樣確定了杰克一家人在消費社會中的地位,使他們瞬間找到屬于某一群體的歸屬感和安全感,讓他們在靈魂深處“達到一種存在的圓滿”。[4]19-20如此巨大、干凈而現代化的超市,伴隨著櫥窗、廣告、包裝和生產商標發出的刺眼光芒,似乎為困于荒野的杰克一家指出了未來的出路,成為某種神明的啟示。[4]38在杰克看來,超市象征著荒原中的文明和安全感,是矗立著自由雕像的舒適的大眾聚會場所,可以瞬間填補內心的空虛,甚至可以代替他所拋棄的親情、友情和愛情。超市這一文化符號,幫杰克緩解了焦慮,購得自我意識和自尊身份,使他體會到自己屬于便利社會一份子的自豪感和認同感。但是,這個形式巨大、設計人性化的超市只能為身體和精神提供垃圾食品,其內容上的空虛和微不足道令杰克一家的安全感和舒適感迅速消失。為了滿足個體的欲望,他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光顧,重復同樣的購買行為。事實上,表面琳瑯滿目的超市可供選擇的產品種類卻不斷減少,暗示了多元文化的衰落。跨國公司日益控制著全球的產品生產,決定了人們有什么商品可以選擇,信從什么價值體系,而全球連鎖大型超市的激增則徹底扼殺了個性,使得公眾消費、思考和行為都出奇地一致,就像店里流水線上統一加工復制的商品一樣。大眾逐漸順從和適應這種環境,其購買行為看似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實際上個人的自主和自由選擇最終成了追求便利的犧牲品。杰克自以為占有主動權和選擇權,可以依個人喜好選擇商品,依靠廣告和商品形象建構一個自以為完美的個體,最終卻被媒介主導的消費文化所左右。
顯然,這種以消費主義為基礎的媒介文化帶有強烈的“宿命論”和“歷史虛無感”。人們認為生活在便利的無歷史的世界很幸運,可以維持文化進步和穩定性,卻無力改變生活,只有被動地接受,用媒介包裝的升級換代的產品安慰自己,掩飾虛假的社會進步和面對自我墮落的無力感。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充滿形象的媒介社會,一個仿真的“超真實”時代。現代媒介和擬像構建的世界是圍繞著仿真以及形象與符號的運用組織起來的,在這個現實缺乏的社會,人們逐漸失去個性而趨同,周圍環境出奇類似,克隆式的連鎖機構遍布全球。這種商店特許權侵蝕了個體與物質來源和歷史的關系,成為了滋生單一文化的空間。在這樣的后現代空間,人們追求越現代越好,越方便越好,卻忘卻了過去,只關注虛無縹緲的未來,使個體深陷于一個充滿仿真和超現實視像的世界。
二、媒介與政治
后現代小說家對意識形態形塑的探討揭開了后現代媒介文化與政治話語的合謀關系,切入了晚期資本主義媒介政治的實質。隨著傳統媒介向數字化媒介的轉變,政治操控手段也變得更加隱蔽。廣告和電視等現代媒介不再圍繞著一般意義上的告知或宣傳的觀念來建構,而是日益適合于通過各種形象來操縱各種欲望和思想,在潛移默化中灌輸某種權威意識。媒介文化制造的表征旨在誘使人們同意某些政治立場,使社會的成員將特定的意識形態看作是事物的現狀,認可霸權性的政治立場,進而重新界定公共意識。[5]換句話說,媒介文化與政治話語一樣,可將政治形態簡約為形象、展覽和故事,將大眾意識禁錮在電視、電影、音樂等娛樂活動中,以達到操控公民意識的目的。
在美國小說家唐·德里羅的創作譜系中,《墜樓人》和《指向終點》描繪了政治權力通過現代媒介在美國社會確立主導性社會話語,進而將這種社會話語轉變為對外干預的政治話語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墜樓人》是《指向終點》的前奏,關注布什政府如何通過媒介文化構建主導性社會話語。《墜樓人》以美國“9·11事件”為故事背景,描述了襲擊事件后紐約城的生活狀態,展現了“9·11事件”給人們的精神和肉體帶來無法愈合的創傷經歷。其中,大眾媒介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指出,以電視為代表的傳播媒介全天候播出將這一事件變成讓人身臨其境的活劇,那些飛機先后撞向雙子樓,雙子樓先后坍塌和行人四散奔逃的場景成為讓全世界觀眾永生難忘的畫面,隨后幸存者從瓦礫堆里被拖出、救助和搜索過程中感人至深的故事以及美國民眾應對災難的過程都在觀眾心目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以至于許多事件親歷者都受到夢魘和心理危機的困擾。[6]與此同時,布什政府在當天就將此次事件定性為恐怖主義對高舉自由和理想的美國的攻擊,所以必須聯合盟國堅決消滅恐怖分子。他的這番講話不僅迅速凝聚民意,而且為隨后媒體的大規模宣傳報道預先設定框架和議程。美國媒體不斷再現恐怖襲擊的悲慘畫面,竭力渲染美國公民的悲痛和絕望以及此事件對全球經濟的損失,刻意凸顯二元對立的文明沖突模式。沒有媒體愿意為民眾梳理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展開批判性的辯論。事實上,這些反復播放的畫面讓我們記住了具有特殊效果的不真實的影像資料和媒體中混雜的情緒與感情,而媒體的精心安排和故意放大又刺激了我們的情感反應,讓人們誤以為得到真實的歷史事件本身,恰恰揭示了我們感覺的分裂。[7]通過精心選擇的新聞事實,美國媒體不僅使公眾的情緒得到集體宣泄,而且增強了美國的凝聚力和愛國心,挽救了支持率不斷下滑的布什政府。在事后一周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布什又特意強調恐怖分子并非整個伊斯蘭世界。布什政府為了掩人耳目,避免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世界直接聯系在一起而僅以伊斯蘭世界為敵的印象,布什總統在他的國情咨文中將伊朗、伊拉克、朝鮮、古巴、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列為“邪惡軸心國”,指責他們贊助恐怖主義的政權,危害世界和平。[8]在諸如“美國有線電視網”《今日美國報》《華盛頓時報》和《紐約時報》等美國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美國政府因捍衛自由平等而遭受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形象深入人心,成為美國社會的主導性思維邏輯。隨著美國國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這種受害者心理迅速轉變為固有的偏見和狂熱的復仇言論,支持布什政府發動報復行動的呼聲不斷。布什總統的支持率不僅升高,而且將美國推向了道德制高點,使得美國在全球謀求霸權師出有名。
如果說《X一代》中安迪的歷史記憶始于越戰碎片,品欽《葡萄園》中索依德·威勒的記憶則始于里根時代的右翼保守政治。在1980年大選中羅納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戰勝前任總統卡特,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出身于好萊塢職業演員的總統。里根集政治領袖和職業演員于一身,開創了名人政治的先河。他精彩的政治臺詞和絕佳的公共形象都通過媒體完整地呈現給公眾,仿佛是在按照好萊塢電影劇本扮演著美國總統的角色。媒體與政治的緊密聯系清楚地表明美國總統要想獲得成功,首先要成為媒體上的名人。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媒體成為總統選舉和執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決定了其政治生命的成敗。換句話說,媒體文化的符碼決定了總統政治的形式、風格和外觀,因此好萊塢能培養出美國總統并非歷史的巧合。在由傳統媒體向數字化媒體轉變的影像時代,媒介技術的泛濫使個體沉迷于影像的世界,而豐富的頻道選擇造成政治自由選擇的假象,使觀眾能夠隨時跳過不悅的畫面,由媒介控制新聞和歷史的表述形式最終使大眾逐步遠離歷史。在里根時代,風起云涌的60年代被定義為荒謬、混亂和動蕩的時期,只能作為映襯80年代偉大進步的歷史影像得以再現。對于當時的右翼保守勢力而言,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反戰示威、反文化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及環境保護運動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噩夢,必須予以堅決地制止和鎮壓。這種傳媒政治所滲透和塑造的文化記憶又不斷影響著80年代美國民眾的反抗意識和對待社會運動的態度。例如,在60年代曾叱咤風云的嬉皮士搖滾樂手索依德,在80年代只能以精神失常的形象示人來獲取政府的撫恤金,而在60年代臭名昭著的檢察官布洛克·馮德在80年代卻成為媒體的寵兒,成為“反大麻運動”的領軍人物。通過對歷史事實的篡改和歪曲,60年代用追求社會政治變革的叛逆形象轉化為80年代頹廢墮落的代名詞,60年代瘋狂鎮壓學生運動、搞“政治改造計劃”集中營的極權形象則轉化為80年代正義的化身。這些60年代殘存下來的文化遺跡恰恰表明,里根時代的政治與媒介聯手重寫了60年代,篡改了人們過去的歷史記憶。當索伊德憶起60年代婚禮時的美好情景,海克特和弗瑞尼茜在賭城“哈瓦那夜總會”喝的“巴蒂斯塔復仇”酒、DL和同志在去救弗瑞尼茜的路上看到的反卡斯特羅塑像提醒人們,這一切不過是索伊德的幻覺罷了。索伊德對美國政府過去行為的有意忽略反襯出80年代媒體政治對公眾意識的成功塑造。80年代的美國民眾在這樣一個被媒體和政治共同營造的歷史語境中成長起來,政治和媒介合力剝奪了他們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就像“類死人”一樣沉溺于消費的瞬間快感和不斷膨脹的個體欲望,拒絕對社會和歷史承擔任何責任。當1984年里根獲得連任,也就是《葡萄園》講述的“現在”,反共尚武的右翼保守思想開始主導美國的官方政策。里根政府一方面利用大眾文化和傳媒(如電視和電影)營造個人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氛圍,調動人們的情緒和情感,為越戰敗北帶來的恥辱感提供補償;另一方面,通過圖像、場面、話語和敘述等媒體文化再現善惡對立的兩元敘事話語,誘使公眾支持官方意識形態,用侵略性的軍事行動解決國際政治爭端,如入侵格里納達、轟炸利比亞等。正是這種媒介與政治的權力運作機制使得里根政府可以輕而易舉地麻痹大眾的思想與意識,在潛移默化中實現了對公眾和個體的規制,讓他們永遠禁錮在娛樂文化與總統迷人的微笑相融合的電視節目中,規規矩矩禁錮在官方經濟體系中。[11]
后現代小說家借助主人公的瑣碎記憶回望歷史,以諷刺口吻勾畫了一個歷史愈來越少,真實性愈來愈低的媒介社會,揭開了與政治力量合謀的媒介技術甚至將真實歷史轉變成娛樂工業來迷惑大眾的真實面目,批判傳統官方歷史敘事的虛偽性。他們的小說展現了媒體社會的本質和人類的真實生存狀態,警醒大眾意識到美國社會日益極權化的殘酷現實,同時引領讀者回眸過去以實現對歷史真實性的把握,顛覆了現代媒體和官方歷史攜手共建的敘事話語。
四、結 語
自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12]這一觀念以來,整個世界似乎變得更加自覺自愿地接受著媒體的影響,文學也不例外。媒介時代帶來了文學書寫的視覺化與圖像化轉向,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文學與媒介之間的多重互動中,媒介已經超越了文學跨時空傳播的物質載體,而日漸由外在表現形式轉化為文學探討的對象與現實意義。以庫普蘭德、德里羅和品欽為代表的后現代小說家不斷以媒介話語為切入點真實展現了媒介與文化、政治及歷史錯綜復雜的關系,揭示晚期資本主義內在的文化邏輯,媒介書寫為后現代小說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對后現代小說媒介書寫的探討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內涵和現實意義,值得文學評論界的關注。
參考文獻:
[1]Douglas Coupland.Generation X: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M].London:Abacus,1996.
[2]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Trans.Paul Foss,Paul Patton,and Philip Beitchman[M].New York:Semiotext(e),1983:25.
[3]Douglas Coupland.Shampoo Planet[M].London:Simon &Schuster,1993.
[4]Don DeLillo.White Noise[M].London:Penguin Books,1986.
[5]道格拉斯·凱爾納.媒介文化:介于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文化研究、認同性與政治[M].丁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02.
[6]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當代美國社會文化透視[M].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14.
[7]Fredric Jameson.The Dialectics of Disaster[J].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Spring 2002,101( 2):287.
[8]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218.
[9]Don DeLillo.Point Omega[M].New York:Scribner Press,2010:23.
[10]Jean Baudrillard.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C]//The Anti-esthei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Trans,J.Johnson,in H.Foster (ed.) Port Townsend.WA:Bay Press,1985:130.
[11]托馬斯·品欽.葡萄園[M].張文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236.
[12]聶艷梅.媒介變遷中女性廣告形象的呈現形態與社會意義[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97.
(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