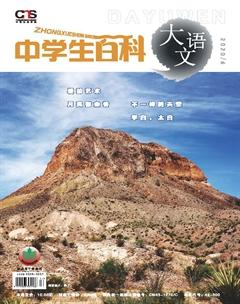誰又不是阿圖羅呢!
李蘭
這是一個發(fā)生在小人物身上的小故事。西班牙先鋒作家塞爾吉·巴米艾斯似乎特別喜歡寫小人物的故事,哪怕他把人物放置在一個相對魔幻的情境中,他也會抓住主人公在生活片段里的心理做細致深入的刻畫,讓你覺得既真實又典型。如果說一般的先鋒作家喜歡用極端化的情境和戲劇化的人格來藝術地展現世界,巴米艾斯則喜歡用戲劇化的情境和通俗化的人格來展現。他在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手法中,加入了現代派文學的視角,他塑造的人物很真實,但不是像《水滸傳》里的林沖或是《紅與黑》里的于連那種類型的真實。他的主人公沒有那樣立體和復雜。他傾向于把普通人身上某一種人格特質進行突出和強化,而后把這個人物放到戲劇化的或是相對復雜的社會情境中間來進行表演。
如果說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就像是從河里直接舀一杯水來給你觀看河水的面貌,那么現代主義文學則是把河水用復雜的工序提純蒸餾后給你看。而巴米艾斯很有趣,他是對河水進行了半提純處理——要么對人物進行提純,對社會則保留大部分真實,透過他的這杯水,我們能看到某種人格特質的命運走向,也能直觀感受到社會環(huán)境特別真實的矛盾和豐富;要么就集中筆力寫出某一生活情境中人物內心活動的豐富復雜,然后對環(huán)境進行提純,簡化環(huán)境的設置,模糊環(huán)境的影像。從這個角度來說,《實驗》可以視為巴米艾斯的代表作。
小說主人公阿圖羅的人格特質非常突出,他是一個特別按部就班、循規(guī)蹈矩的人:周一看電視,周二看電影,周三去超市,周四看電視,周五滑冰,周六探望父母,周日做彌撒。但在節(jié)奏日益變快,且求新求變的現代社會中,凡事都講究程序化的他慢慢被人看成一個怪胎。周圍的人都開始無法理解他——孩子取笑他,妻子抱怨他,經理也開始慢慢忽視他。
其實,在小說中,阿圖羅并非從一開始就被視為怪胎,這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情,要知道“經理不久前還夸獎他的才干和謹慎”。小說開篇寫道:“阿圖羅總是在固定時間起床。他從來不改變上班路線,并且認為為了世界的正常運轉,日常習慣的系統(tǒng)化是不可或缺的。”接著又說:“然而,最近幾個月,他發(fā)現周圍的人不能理解自己這種對規(guī)則的遵守。”也就是說,阿圖羅一直都是這樣,他從來沒有變,變的是環(huán)境,是他外面的這個世界。
堅守不變的人物和開始變化的環(huán)境,這就構成了一對矛盾。小說的整個故事也就起源于這個矛盾。
主人公感覺自己原來一直奉行的價值觀不吃香了,人們不再尊崇條理性,而是轉而崇尚不考慮明天的“隨心所欲”,“輕易改變看法和感情上的朝三暮四也常常受到贊美”。也就是說,“心血來潮”和“反復無常”成了一種時尚,而“堅守”和“不變”則代表了落伍。
需要注意的是,在整個故事中,作者并沒有表現出特別明顯的價值立場和情感傾向,我們看不太出來作者到底是支持主人公,還是反對他。如果說是支持他——“在與這種大肆鼓吹反復無常習氣作斗爭時,阿圖羅努力不生氣:生氣相當于在對手面前示弱。越來越少有人意識到事物的不可預見性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這種情況讓阿圖羅很吃驚。”這段話可以有兩個理解方向:一方面我們看到了整個社會過于求新求變,以至于“大肆鼓吹反復無常”,這就有點扭曲和走極端了,會讓人們忽視“無常”中隱藏的風險;另一方面,“阿圖羅努力不生氣:生氣相當于在對手面前示弱”,又讓我們感覺到了一點類似于堂吉訶德的滑稽。阿圖羅心里面的那個“對手”是誰?是整個劇烈變化的社會。他“努力不生氣”,是為了讓自己不“示弱”,可這種心理活動本身就暴露出自己的“弱”了。其實,客觀來說,“事物的不可預見性”不一定都是有害的,“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這種極端的判斷則顯示出了阿圖羅本身的拘泥。而阿圖羅的“吃驚”,又讓我們讀出了他無法適應快速變化的現實的那種窘迫。
雖然阿圖羅不愿意“示弱”,可在現實的壓力下,阿圖羅還是決定做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簡單來說,就是改變他一直以來循規(guī)蹈矩的形象,讓自己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以檢驗自己秉持的價值觀是否正確。“這個決定不是為了求證,而是為了再次肯定自己的態(tài)度;也不是源于沖動,而是出于理智。”也就是說,這次實驗是阿圖羅經過深思熟慮的,并非為了探尋答案,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系統(tǒng)化、程式化的生活方式的正確性。阿圖羅的實驗方式比較奇特,他并沒有去做一些驚險刺激的事情,而是采用了遲到20分鐘、改變衣著風格、打破生活固定流程等小舉措,作者說“為了不驚動周圍的人,他做得很謹慎”。然而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現了,他的“微調”還是引起了地震式的反應,沒有人對他的改變感到驚喜,而是紛紛表示受到了驚嚇。在這個實驗中,原來勸說阿圖羅“改變”的人,都特別不理解他的行為。阿圖羅的妻子對他改變時間表提出去泰式餐館吃晚飯的建議先是“一聲回應都沒有”,繼而又明確反對他在本該看電影的那一天留在家吃飯。當阿圖羅用妻子曾經勸說過自己的言辭,反過來勸說妻子接受建議做出改變的時候,妻子表現出了明顯的不耐煩和憤怒。最后阿圖羅為了引入“創(chuàng)造性的變化”,心血來潮,大半夜地趁妻子睡著了去外邊晃了一圈,回來的時候,“妻兒都在門口等著他。他們沖他大吼大叫,指責他既沒有事先通知也沒有留張便條”。
他的實驗徹底失敗了,可他從始至終都沒有一絲沮喪,因為他認為自己所有別出心裁的行為只是一場實驗,而實驗的失敗則恰恰證明了自己一直奉行的價值觀是正確的。可以用一個失敗的實驗來證明自己,他感到心滿意足、怡然自得,他感覺一切都如他所料。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實驗又是成功的。而且,他認為這個實驗說停止就能停止,接下來他依舊能夠輕松掌控自己的生活。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事態(tài)的發(fā)展已然失控:“大家都不聽他解釋。妻子開始嗚咽,斷斷續(xù)續(xù)地發(fā)出刺耳的聲音,孩子們則仿佛面對墮落分子似的看著他。”他甚至被趕出了公司和家庭。
這個“實驗”的過程充滿了喜劇化色彩,因為主人公是抱著興致盎然、興高采烈的心情來做實驗的。但“實驗”的結局卻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悲劇——他最終成了一個被放逐的人。有人說巴米艾斯喜歡寫苦樂參半的人生,《實驗》這個故事似乎恰恰印證了這個評價。
故事的“樂”來自作者寫出了現實生活的戲劇化和荒誕感——當今社會,似乎大家都喜歡和期待充滿了未知挑戰(zhàn)的“變化”的生活。但是這種喜歡很有點“葉公好龍”的味道,是表面上的趨之若鶩和骨子里的口是心非。真相是,習慣的力量無比強大,改變日積月累的習慣往往帶來的是不適應、恐慌甚至憤怒。作者把人們的這種內外矛盾巧妙地裸呈出來,從而展現了一種別有意趣的荒唐。
故事的“苦”來自主人公從始至終不被人理解的孤獨,來自主人公誤以為能夠用證明自我的方式來堅持自我,進而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卻沒想到環(huán)境的力量會如此強大,完全不以自己的意志和設計為轉移。自己只能被現實裹挾著前行,任何處心積慮的質疑和反抗不只是徒勞,還可能導致惡劣的后果。
當然,客觀來說阿圖羅對改變和創(chuàng)新其實是存在誤解的。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的變化”不該被理解為簡單粗暴地偏離既定的生活軌道,做一些不被他人接受的出格的事。“創(chuàng)造性的變化”其核心不只是“變化”,還應該包括“創(chuàng)造”,也就是說,這種變化應該是具有建設性的、可以改善現狀的變化,而不是無視他人的感受、消解自身的責任、隨心所欲,甚至挑戰(zhàn)社會規(guī)則的膚淺幼稚的變化。
作者讓我們看到了小人物可笑的局限,但作者又似乎并不想過多地苛責這個小人物。整篇小說都以阿圖羅作為主要的敘述視角,引導讀者用阿圖羅的價值觀念來審視這個世界,引導讀者去體貼阿圖羅細膩的內心活動。所以,我們這些讀者反而會比他的家人更加理解阿圖羅在“實驗”中的言行,理解他的思想和情感。這種理解恰恰是因為作者特別的敘述視角而產生的。從表面上看,作者躲藏在整個講述背后,他的情感很隱秘,似乎是不加任何判斷地把事實本身展現給我們看。但事實上,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對阿圖羅的同情,以及對社會中所有類似的無法在劇烈變化的社會中安放好自己的小人物的悲憫。
我們都是普通人,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固然無趣,卻會給我們帶來安全感,讓我們每天按部就班地過好日子。但我們的心底卻又不甘于這樣一眼看得到頭的無趣,我們強烈地盼望著變化,就像阿圖羅一樣:“最初幾周,他多少有些急切地盼望。后來,是平靜地盼望。隨著時間流逝和不斷堅持,他把這種盼望變成了一種習慣。”
小說的結尾意味深長。
此刻,讀完結尾的你內心是不是有了些許觸動?在“始終如一的踏實感”和“心血來潮的刺激感”之間左右搖擺的我們,就像阿圖羅或者說“實驗”里的每一個人那樣,活得辛苦又卑微,矛盾又掙扎。
是的,我們誰又不是阿圖羅呢?
最后給大家推薦巴米艾斯的另一篇文章——
休閑旅行車
[西班牙]塞爾吉?巴米艾斯
你對住在201室的鄰居毫無好感。他沒有對你做過什么,不過經驗告訴你討厭一個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自從那個鄰居搬到這座樓,你就遠遠地觀察過他,只是為了證明那種不好的第一印象。或許這是一種不夠成熟的表現,但是直覺告訴你,如果在看待周圍環(huán)境時都不能任性一點的話,你的生活會變得更加不易。如果你在口味上有連你自己都不明白的偏好,比如假設你喜好吃兵豆勝過菠菜的話,為什么對待鄰居們就不能同樣地憑心意而為呢?
他和妻子一起登門做自我介紹時,你就開始嫌惡他。你沒有請他們進門,對于對方的例行問候,你只是客套地略表歡迎。接下來,你就在心目中把這個鄰居(他的妻子除外)列入討厭之人的行列。在一段時間里,你承認這種毫無根據的討厭令你感到不安。而現在,相反,你覺得這和其他人那種一視同仁的親切一樣合理合法。
在停車場,你發(fā)現那位鄰居的車位恰好在你車位的正前方。如果你們碰巧遇上,你只是淡淡地打個招呼,而他則是借著聊聊天氣延長時間。一天下午,你們恰好同時從各自的車里出來,你沒法視而不見地揚長而去。他借此機會問你是否對你的休閑旅行車非常滿意。你沒有發(fā)現這個問題有任何其他企圖,于是回答說是的。你甚至向他展示了側拉門的優(yōu)勢——在狹窄的地方方便上下車。
過了兩天,他來敲你家的門。在轉彎抹角地對突然造訪解釋了一番后,他問你是否可以聊一聊。作為一種懲罰,你讓他坐在廚房的小凳子上,借口說妻子正在客廳的沙發(fā)上睡覺,你不想打擾她(當時你妻子已經離你而去,睡在沙發(fā)上的人是你,因為一個人睡的話,臥室那張床實在是太寬大了。但是你沒對他說,因為你認為鄰居對自己的了解越少越好)。
你們聊了聊休閑旅行車,鄰居向你坦言他正在研究買一輛這種車的可能性。盡管這消息令你感到難過,你卻掩飾著。你對你的這輛車非常滿意,他從你們上次談話中了解到了這一點。同時,你知道自己不喜歡在停車場的同一排看到和你同款的車,看起來就像是車行展銷似的。除了你對自己的車非常滿意這一點之外,你還得意于周圍沒有人和你有一樣的車,無論是同事、飯友、親人,還是鄰居。
你思忖著如果你夸大這種車的缺點,鄰居可能會猜到你想勸阻他。你斟酌著自己的言辭,選擇刻意的夸贊,因為你認為直接的貶低不如讓他產生懷疑來得有效。你對他說那輛車有很多優(yōu)點,當然也有些許缺點。你不停地列舉著,直到發(fā)現他感到不舒服了:他沒料到你會講那么久。最后,你用一種銷售商般的確定口吻總結道:“假如我是你,就一定會買的。”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你看到他的車位上停著一輛嶄新的敞篷跑車。你湊近去看:真皮座椅,做工精細,不失優(yōu)雅。你正贊嘆著,鄰居的妻子出現了,她笑瞇瞇地問你:“喜歡嗎?”你努力想用一個矜持的“是”來回答她,但是事實上你為這輛車著迷。她補充說道:“我知道你曾向我們推薦過你那款休閑旅行車,但是最后我們選擇了這一輛。這是301室的鄰居向我們推薦的。”她打開車門,一鍵啟動后,駕車離開了停車場。空空的車位上,還回響著引擎轟鳴的動聽聲音。
你不敢看那輛休閑旅行車。電梯的鏡子里映出一個落拓的男人形象。到家后,你癱倒在沙發(fā)里。你大睜著眼睛,盯著天花板,試著想象樓上鄰居家的家具是如何布局的,墻是什么顏色,墻上掛的畫是什么風格。漸漸地,你意識到最讓你痛苦的,不是鄰居買了那輛超級棒的車,而是他更愿意聽取301室鄰居的意見,盡管這正是你原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