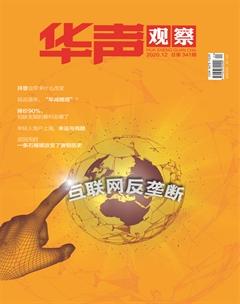降價90%,冠脈支架的暴利去哪了
周小鈴

從這次國內(nèi)外廠商不約而同給的降價幅度來看,砍掉的90%價格正來自流通和市場推廣環(huán)節(jié)。
11月5日上午10點,冠脈支架全國集采結(jié)果在天津市陳塘區(qū)科技商務(wù)區(qū)服務(wù)中心一間會議室內(nèi)公布。冠脈支架從均價1.3萬元下降至中位價700元左右,平均降幅94.6%。
在國內(nèi),不管是藥品還是耗材,以往的銷售模式都必須借助代理分銷,通過返利和回扣來爭奪醫(yī)院市場。而在中國以公立醫(yī)院為主體的醫(yī)療體制下,醫(yī)生的勞動價值得不到完全市場化體現(xiàn),形成了“以藥養(yǎng)醫(yī)”“以耗養(yǎng)醫(yī)”的畸形補償機制。
全國耗材帶量采購,自2019年5月開始推動,徹底改變了這條穩(wěn)固的價格暗鏈。
超級買家出手
冠狀動脈支架,是一種被用于心臟介入手術(shù)的常用醫(yī)療耗材,起到疏通動脈血管的作用。業(yè)內(nèi),這一介入手術(shù)被稱為經(jīng)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手術(shù)中常用到的高值耗材還有導(dǎo)管、球囊等。
相對低值耗材,高值耗材是國家組織“團購”的重點領(lǐng)域。主要指介入人體、臨床使用量大、價格較為高昂的消耗性醫(yī)療器械,包括心臟血管介入、非血管介入、骨科植入、神經(jīng)外科、電生理類、起搏器類、體外循環(huán)及血液凈化、眼科、口腔科等幾大類。
醫(yī)保基金是高值耗材最大的出資方。以往,對單獨收費的一次性醫(yī)用高值耗材都有價格和醫(yī)保支付比例的要求。以冠脈支架為例,浙江省最高限額3萬元,省內(nèi)平均自理比例從5%到20%不等。江蘇省南京市每人限額12000元,限額內(nèi)20%由個人自理。
中國醫(yī)學(xué)裝備協(xié)會技術(shù)部主任楊健龍在研究中提供了一組數(shù)據(jù):2018年,我國PCI手術(shù)量已超91萬例,冠脈支架的醫(yī)保年支付額約為375億元。高值耗材的醫(yī)保年支付額應(yīng)在千億元以上。根據(jù)2018年國家醫(yī)保局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全國基本醫(yī)保基金總支出為1.78萬億元。僅冠脈支架就占醫(yī)保總支出的2%。
打不掉的高價,從2018年開始有了轉(zhuǎn)折。那年3月,國家醫(yī)保局成立,它將人社部的城鎮(zhèn)居民基本醫(yī)療保險和生育保險、衛(wèi)計委的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職責(zé)、民政部的醫(yī)療救助職責(zé)和國家發(fā)改委的藥品與醫(yī)療服務(wù)價格管理職責(zé)“四權(quán)合一”。這意味著,花錢的人能參與定價。
成立八個月后,“超級買家”開始出手,在藥品領(lǐng)域推行帶量采購,成效穩(wěn)固后,2019年中旬開始推行耗材帶量采購。
帶量采購的核心,是中標(biāo)者可以以量換價、“贏者通吃”,這會讓廠商們相互搏殺,直到殺出底價。
“帶血”廝殺
冠脈支架,因為單價高、用量大,成了國家耗材帶量采購第一個“動刀”的地方。2020年10月16日,國家組織高值醫(yī)用耗材聯(lián)合采購辦公室發(fā)布的《國家組織冠脈支架集中帶量采購文件》規(guī)定,冠狀動脈藥物洗脫支架系統(tǒng),材質(zhì)可以是鈷鉻合金或鉑鉻合金,載藥種類為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首年意向采購107萬個。本次集采共有11家企業(yè)參與投標(biāo),帶來在境內(nèi)注冊上市的26個冠脈支架產(chǎn)品。
對有志于競標(biāo)的耗材廠商而言,最低價尤其重要,考驗每家廠商的競標(biāo)決心和承受能力。
在11月5日公布的冠脈支架中標(biāo)名單中,藍帆醫(yī)療旗下的山東吉威報出支架產(chǎn)品的最低價469元,中標(biāo)價的中位數(shù)為750元,十個產(chǎn)品均低于千元,十款產(chǎn)品價格的平均降幅達93%。
在一家外資耗材企業(yè)工作的彭立透露,吉威中標(biāo)后,心臟介入器械將采用直銷模式,徹底砍掉中間渠道環(huán)節(jié),給出的報價只能滿足企業(yè)自己的經(jīng)營需求。
相較國產(chǎn)廠商,外資耗材廠商由于前期的研發(fā)投入和關(guān)稅成本,降價壓力更大。然而,這次投標(biāo)名單中,不乏外資身影。外資巨頭中,美敦力、波士頓科學(xué)、雅培都帶著產(chǎn)品參與了競標(biāo)。
拆掉利益鏈
在過去很多年中,像冠脈支架這樣的高值耗材改革是“難啃的骨頭”,原因在于醫(yī)療行業(yè)的行政管理、業(yè)務(wù)機構(gòu)與耗材廠商之間有千絲萬縷的利益往來。
上海一位從業(yè)十余年的心外科醫(yī)生告訴記者,以往醫(yī)療機構(gòu)的購銷模式較易產(chǎn)生尋租空間。一個耗材產(chǎn)品的購買路線是這樣的:首先要進當(dāng)?shù)蒯t(yī)保目錄,然后經(jīng)過科室主任申請,行政部門耗材科或者保障科、醫(yī)保辦等部門審批,分管院長乃至院長審批,通過后才能進入醫(yī)院,臨床方可使用,臨床科室的帶組主任有權(quán)決定“用誰不用誰”。
廠商在跟醫(yī)院采購科室談判時,需要給到明確的折扣,比如廠商給醫(yī)院七折,一個億的產(chǎn)品,醫(yī)院可以留下三千萬利潤,用以彌補醫(yī)院里其他不盈利的科室。
支架,曾經(jīng)是醫(yī)生的盈利項目。這位醫(yī)生解釋,正常情況下,支架最多不超過兩個,需放第三個支架時,需要醫(yī)生提出申請并寫明原因。“以前由于利益驅(qū)使,又缺乏監(jiān)管,大家能放支架就放支架。”
從這次國內(nèi)外廠商不約而同給的降價幅度來看,砍掉的90%價格正來自以上流通和市場推廣環(huán)節(jié)。
彭立拆解了冠脈支架的各環(huán)節(jié)利潤點,在這90%中,醫(yī)生拿小頭,代理經(jīng)銷商拿大頭。他解釋,通常會給醫(yī)生掛網(wǎng)價的兩成,大概是兩三千元。剩余部分給中間層層代理經(jīng)銷商,每一層經(jīng)銷商都要在拿貨價上加碼,經(jīng)銷商會對比廠商給出的商業(yè)政策,選擇最優(yōu)惠的折扣拿貨。
國家集采后,耗材廠商亮出了產(chǎn)品的“地板價”,原先能給代理商和醫(yī)生的利潤蕩然無存。彭立判斷,對醫(yī)生來說,來自耗材廠商的灰色收入勢必減少,而他身邊的代理商朋友,一聽到集采價格,也紛紛表示要退出。
醫(yī)生勞動誰來補
實際上,以往耗材廠商給醫(yī)生的“回扣”,一些業(yè)內(nèi)人看來,是對醫(yī)生勞動價值的一種“補償”。
北京安貞醫(yī)院心內(nèi)科的一名主任醫(yī)生透露,心內(nèi)科醫(yī)生在一臺介入手術(shù)中需要穿著厚重的鉛衣去為病人打開血管,冒著輻射的風(fēng)險,一站幾個小時。有時,碰上復(fù)雜病變,醫(yī)生要比往常付出更大的精力。“到頭來,醫(yī)生的勞動價值還不如一位修腳匠人。”
從單臺手術(shù)收費標(biāo)準(zhǔn)來看,醫(yī)生的手術(shù)費大約在1500元,一臺手術(shù)大致有5個人共同完成。這相當(dāng)于,一臺CPI手術(shù),分到每個人頭上只有幾百元。
上海的一名心外科醫(yī)生相信,耗材集采后,短期內(nèi)醫(yī)生對開展心臟介入手術(shù)的動力可能有所下降。但患者需求卻沒有發(fā)生變化。少了耗材的補償,想請醫(yī)生做手術(shù),補貼醫(yī)生的費用自然就轉(zhuǎn)嫁給了患者。
彭立畢業(yè)于臨床醫(yī)學(xué)專業(yè),身邊有好幾個同學(xué)最近剛拿下心內(nèi)科主刀的資格證,耗材帶量采購下來后,朋友們都表示想轉(zhuǎn)行了。彭立也在思考自己轉(zhuǎn)行的方向,如果被“優(yōu)化”,他會考慮去診斷、醫(yī)美設(shè)備等領(lǐng)域。
摘編自《南方周末》202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