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那些老先生們
張明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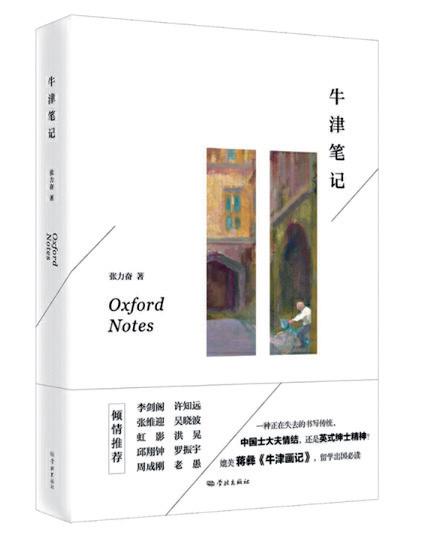
20世紀初,牛津一個學院餐廳里直徑兩米、長達45米的橫梁被蛀空,一時找不到如此巨大的橡木。一位年輕院士提議,學院擁有很多土地,沒準也種了橡樹。于是院方找來學院分管林業的管家,管家平靜地表示,他們等待這個召喚已經等了幾百年。自1379年學院初建時就種了一批橡樹,據說歷代管家交接時都會重復一句話:“這批橡樹不能砍,以后學院餐廳大梁要用。”
在《牛津筆記》一書里,張力奮又將這個段子講了一遍,他還為此在牛津考證了一番,結論是“尚無可靠證據”。
這些年,去國外訪學然后寫下一本書蔚為風潮。這些書水平不一,但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缺憾,就是基本都是一種書齋式寫作。作者往往大量引用資料,但卻缺乏對當地社會的一手深入觀察。
而《牛津筆記》幾乎是對以上這種“寫作傳統”的一種徹底顛覆。縱觀全書,你很少看到作者大段討論英國的保守主義和制度沿革,更多是看到了他與當地人的各種溫情互動。
特別是書中寫到的那些“牛津老先生”,作者或許沒有刻意寫他們的風骨,但卻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讓人感覺他們才是英國文明甚至人類文明的“托命之人”。他們的身上見不到時下盛行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只有溫情、專業、友善、豁達與人類的共同情感。老先生就是牛津,就是大學,就是傳統。
書中寫到了一位牛津古典學教授羅賓。他還是一位明星園丁,經常穿著西裝給學院的花園澆花,“手上有泥,精通古希臘文明”。最驚人的是,羅賓可能是全世界持續寫作最久的專欄作家。他從1970年起為《金融時報》的專欄寫稿,整整47年,一人單挑半世紀的專欄,沒落下過一期,并且,專欄是關于園藝,而不是他的本行古典學。
以人情厚重見文明,于生活細節見制度。正如本書的特約編輯陳季冰先生所說:“英國保守主義的精髓不是某種意識形態,而是日常生活中對人類精神和文明的堅守和傳承。”
關于牛津的傳統與保守,張力奮特別提到了牛津草坪的“規矩”。據說一些學院規定,只有導師才可以踏入草坪,學生只有在畢業儀式上才可以象征性地走一次。年輕學子們自然多不喜牛津的圍墻與清規戒律,專欄作家凱拉韋就曾感嘆,她在牛津讀書時也很討厭牛津城堡式的封閉,但二十多年后應邀回校演講時,突然醒悟自己如此幸運,“曾在被陽光烤成金蜜色的圍墻里,享受思想的芬芳”。
我想,這就是英式的保守之美、牛津的傳統之美吧。
摘編自《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