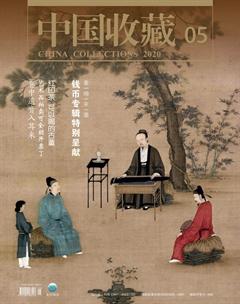文人琴 文人造
閔俊嶸
琴作為禮樂的一部分,在歷代不斷發展演變。目前能見到清代中和韶樂、丹陛大樂所用琴的實物,其形制有統一的規范,制作工藝和演奏方式與文人琴基本相同,但整體氣韻略顯呆板,使用頻率也很低,只有在元旦、大婚等重要慶典時才用。所以古琴文化傳播的主體是作為修身工具的文人琴,文人用琴文人造,或許雖不必親自動手,實則每每參與其中。
在具體的斫琴實踐中,除文人參與以外,皇室貴胄參與斫琴的成效似乎更為顯著。比如宋徽宗,集天下名琴成“萬琴堂”,并且御制宣和式琴“松石間意”。再如清乾隆帝,將收集的名琴登記造冊,繪制御制琴譜。還有明代的弘治帝、崇禎帝,以及益王、衡王、寧王、潞王等皇親國戚,都參與了制琴。他們與普通文人相比雖然位高權重,但從學識與藝術情操來講,不能說一生寫四萬余首詩的弘歷不是文人,也不能說編寫了《古音正宗》的潞王朱常澇不是文人。

宋人摹顧愷之《斫琴圖》故宮博物院藏
各有分工
斫琴包括木工和髹飾工藝兩部分,其中“斫”字的釋義是砍和削,主要指挖斫槽腹結構,安裝岳尾等配件;髹飾指的是制作琴體表面的灰漆層,髹漆的本意是刷漆。這類工藝美術活動一般由工匠完成,但是斫琴有別于一般的造物活動。當琴的使用從祭祀和禮樂轉移到音樂審美以后,就與文人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是出土發掘的器物,還是歷代傳世名琴;無論是宮廷官造琴,還是民間“野斫”,琴的制作與使用都與文人密切相關。他們或創制、或監制,或親自參與制作。
斫琴技藝包括復雜的流程,一人很難將各個工序出色完成,最直觀的就是宋摹本顧愷之的《斫琴圖》。圖中人物分為六組,共繪14人,左側年輕力盛者在砍削琴面弧度,地上散落著木屑;左下方一年齡稍長者在挖斫槽腹,此二人屬于基礎木工組。右側下方兩人席地而坐,一人擼起袖子用筆在木塊上標識切割的鋸口位置,另一人執筆若有所思,似乎是在聽右側長者所言,等待長者指出槽腹內需要如何修正。琴胎旁邊放有斧頭、手鋸、木銼和刨子等工具,這一組在作比較細致的槽腹木工微調和配件安裝。兩位執筆者所坐的墊子分別是獅和虎的整張皮,與旁邊長者所坐的雙層織繡墊子形成很大反差,反映出他們不同的身份特征。右側的長者顯然是屬于比較儒雅的文人。畫面右上方描繪—人在制作琴弦,在木制弦弓上繩絲為弦。
畫面中部是另一位深諳音律的文人在調弦審音,此時的琴體已經髹涂完漆液,色澤較深。其右側坐著一位督造者,兩人所用墊子也有所不同,督造者使用的同樣是比較樸素的織物墊子,之所以能成為督造者,推測是由于他在樂律造詣和審美經驗方面高出一籌。
斫琴與督造過程中,一位手持憑杖的主人出現在畫面左側,他是這個斫琴團隊的核心人物,負責把控進度與整體方向。此外還有五位童子,或隨從、或佇立,還有一位背著包袱做奔跑狀,或許是背著一包鹿角霜,正在趕往髹漆的作坊。畫面中人物形象鮮明,所使用的工具,以及著裝配飾體現出他們不同的身份特征。整個工藝流程說明斫琴在當時是一件復雜的事情,文人在其中發揮著統領作用。
感性記述
琴的常見樣式有幾十種,如伏羲氏、神農氏、仲尼式、連珠式、蕉葉式、中和式等。這些樣式靠琴體的外部輪廓特征來區分,但不論哪一種樣式,都遵循著一套槽腹規律,即琴體木胎結構比例關系。槽腹制度根本上決定了琴音色的風格與品質。
唐代李勉在《琴記》中載:“其身用桐,岳至上池厚八分,上池以下厚六分,至尾厚四分。”從琴體岳山至尾的厚薄尺寸記錄很清楚,但前提是用桐木這種材料,如果換成其他木質,尺寸就會有相應變動。琴面與底的配比要達到和諧,否則會出現韻短、聲焦等問題。北宋石汝歷在《碧落子斫琴法》中對琴面底匹配關系作了詳細描述:“凡面薄底厚,木虛泛清,利于小弦,不利大弦。面底皆薄,木泛俱虛,其聲疾出,聲韻飄蕩。”
琴體槽腹、髹漆,以及琴弦和放置琴的琴桌,甚至彈琴所處環境的溫度與相對濕度,都是除演奏者以外,會對音質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但是從斫琴角度來看,槽腹結構是最核心因素,它是材料學、力學、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琴材的新與舊、陰與陽、疏與密等具體性能,琴體各個部位所用不同材料與尺寸之間都存在著辯證關系。
今天我們能把斫琴技藝分解開去做各種分析研究,而古人更多的是感性經驗的總結,并通過文人用委婉的語言來描述。如《琴苑要錄》中所述:“誰識倚山路,江深海亦深,洞中多曲岸,此處值千金。”其中“山路”“江海”“曲岸”等名稱是對古琴納音、龍池等部位的指代,“誰識”“亦深”“多曲岸”是指其中的奧妙無法用語言表達。
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張“九霄環佩”琴,龍池結構正如秘訣中所講,隆起的納音有一道深淺不一的“山路”,崎嶇不平,或許是天然形成的蛀洞,或許是斫琴過程中的人為。北宋蘇軾在《琴書雜事》中記述雷琴獨有余韻,為了探究其中奧秘,將琴破腹打開,發現龍池與鳳沼處的納音微隆如韭葉,音韻被攔截在池沼內使其徘徊往返,余音裊裊。這些經驗需要在斫琴過程中不斷實踐,在操縵過程中細細體味每一種組合關系產生的音質變化,經過無數次的調整,最終總結出規律,用文字的形式記錄傳播,這也是文人參與斫琴的意義所在。
重于漆藝
《斫琴圖》里沒有描繪琴體髹漆的場景,或許是因為畫幅不夠長,也可能因為髹漆動作不易表現,但琴體髹漆對于一張琴來說是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
漆器髹飾工藝的歷史要久于古琴,但關于髹飾工藝的記述文字卻沒有像古琴一樣,有那么多的琴譜流傳下來。其主要原因是單純的髹漆工藝被視為形而下的體力勞動,文人士大夫很少參與其中,也不愿在其過程中留下自己的名字。而髹漆的工匠大多沒有文字記錄和著述能力,五代的《漆經》已經失傳,剩下唯一的是明代漆工藝專著《髹飾錄》。

從斫琴角度來看,槽腹結構是最核心因素,它是材料學、力學、聲學等多學科的交叉。

《斫琴圖》里沒有描繪琴體髹漆的場景,可能因為髹漆動作不易表現,但琴體髹漆對于一張琴來說至關重要。
《髹飾錄》分為乾集和坤集,詳細記錄了漆器髹飾工藝中所用到的材料、工具、各類裝飾工藝,以及造物的法則和禁忌。其中坤集糙漆之第三次煎糙載:“右三糙者,古法,而髹琴必用之。今造器皿者,一次用生漆糙,二次用曜糙而止。”一般的器物第一遍糙生漆,第二遍糙調制的熟漆即可完成,而琴的糙漆按照古法必須糙三遍。由此可見,琴在古代造物中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器物。琴譜中有大量關于琴體髹漆的記錄,如《琴苑要錄》中記載的合琴光法:“煎成,光一斤,雞子清二個,鋁粉一錢,研清生漆六兩。”這些由琴人記錄的髹琴技法反過來又豐富了漆工藝的內涵。
無論是對于帝王將相,還是文人士大夫,以及眾多習琴、愛琴之人,琴聲出于天籟、成于人心,借助器樂可以宣情、修身。如《琴訣》中所講:“攝心魄,辨喜怒,悅情思,靜思慮。”人們對生命情感價值的探索,常常源自于生活中喜怒哀樂的形成與表達。古琴可以幫助文人從現實生活中走出來,去關注詩意和遠方,達到心平德和,琴就從器走向了藝,進而走向對德與道的探尋,無疑這是從古至今文人參與斫琴的原動力。
(注:本文作者系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