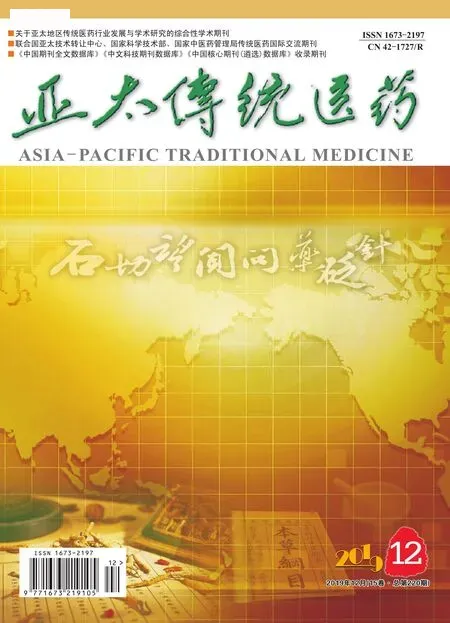近五年中醫外治法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研究進展
張春燕,趙淑華,李 利,李文龍
(1.天津中醫藥大學,天津 300193;2.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天津 300150)
慢性疲勞綜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是以疲勞為主要癥狀的癥候群。其臨床癥狀表現為不明原因的持續或反復發作的嚴重疲勞,經充分休息后不能緩解,持續時間在6個月以上,有的還伴有低熱、頭痛、咽喉痛、肌肉疼痛、關節痛、失眠健忘、注意力不集中等癥狀,或伴有頸部、腋窩淋巴結輕度腫痛[1]。
西醫認為其發病機理與病毒感染、內分泌系統、免疫系統及神經系統紊亂等有關。現代醫學對CFS還未發現特別有效的治療手段,常用類固醇和抗抑郁藥物治療,其中類固醇藥物需小劑量服用,大劑量服用會抑制腎上腺功能,且其只能短期改善CFS患者的臨床癥狀,藥停后療效消失;抗抑郁藥物僅對CFS的并發癥產生療效且副作用多,停藥后可能出現嚴重的情緒不穩定等不良反應[2]。西醫治療也用免疫療法對其進行治療,但研究表明采用 IgG免疫療法效果不佳,同時還伴有副作用的產生[3]。
現代醫學對CFS治療不足的地方給中醫診治提供了寶貴的空間。臨床發現中醫治療在改善 CFS患者的疼痛、疲勞、睡眠和抑郁等癥狀方面有較好的療效,尤其是中醫外治法在治療本病上有獨特的優勢,采用針灸、拔罐、推拿等聯合療法治療該病均有良好的療效。現將近五年中醫外治法治療CFS的概況綜述如下。
1 針刺治療
針刺具有舒經通絡、運行氣血、調和陰陽之功效,可改善由氣血運行失常、經脈不通、陰陽不調等導致的慢性疲勞等癥狀。
1.1 毫針針刺
陳金狄[4]采用以中醫神志學說為基礎的“通督調神針刺法”治療本病,治療組取穴四神聰、神庭、印堂、百會、神門、內關、三陰交、足三里、太沖穴;對照組Ⅰ取百會、肝俞、脾俞、腎俞、合谷、太沖、三陰交、足三里穴;對照組Ⅱ取穴以腹針中的引氣歸元法為主,以中脘、下脘、關元、氣海四穴為主穴,以三陰交、太沖、足三里為配穴,1次/2天,共治療4周。三組治療前后各量表評分比較差異顯著,治療后軀體疲勞評分方面,治療組與對照組I療效相當,但優于對照組Ⅱ。各量表評分及總有效率方面,治療組均優于兩組對照組。
李榮臻[5]采用“針刺調神方”治療CFS,主穴取神庭、四神聰、印堂、內關、三陰交;配穴用病程區分,小于1年者配四關穴,大于1年者配天樞雙、中脘、關元穴。對照組不予以治療,以基線干預為主。治療后兩組患者FAI、FS-14總分及各維度評分、SAS、SDS評分均較治療前顯著改善(P<0.01);觀察組總有效率為83.33%,優于對照組的62.50%(P<0.05)。
黃潤楷[6]治療90例CFS患者,將其分為治療組(鄧氏平衡針組——主穴取脊中、脾俞雙、筋縮、懸樞、三焦俞雙、督俞雙、身柱、百會、大椎、靈臺)、對照1組(常規針刺組主穴取百會、印堂、神門雙、太溪雙、太沖雙、三陰交雙、足三里雙)和對照2組(口服谷維素、維生素B)。治療組、對照1組治療后的FAT、FS-14、SAS及SDS評分較治療前均明顯降低(P<0.01)。治療組有效率為93.33%,對照1組為76.67%,對照2組總有效率為60.00%,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7<0.01)。
韋斌麗等[7]將92例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46例,觀察組施以樞經滯針療法(經穴選手足少陽經和手足少陰經4經上的原穴和絡穴;配以足三里、關元、百會。操作:得氣后,單方向捻轉針柄≥2周,造成滯針狀態,留針30 min,起針時將針柄回旋,快速出針),對照組施以常規針刺療法,均治療14天。觀察組總有效率為93.48%,對照組為82.61%,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治療后FS-14評分均較治療前下降,且觀察組優于對照組(P<0.05)。
1.2 電針
李金霞等[8]研究經皮穴位電刺激治療CFS的臨床療效,觀察組(46例)采用任督脈經穴TEAS治療,大椎與命門配對、神闕與關元配對;肝郁、心氣虛、脾虛、肺氣虛、腎虛分別配以肝俞、心俞、脾俞、肺俞、腎俞穴;操作:于背俞穴處貼電極片,疏密波2 Hz/100 Hz,強度設置為(14±2)mA,30 min/次,1次/天,5次/周,觀察4周。對照組(43例采用任督經穴模擬TEAS治療,其中TEAS強度設置為1 mA,其余均同觀察組。治療后觀察組FSS及SPHERE評分較對照組下降明顯,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
1.3 耳針
鐘偉泉等[9]采用耳穴貼壓(黏有王不留行籽的耳穴貼)治療CFS患者25例,耳穴取交感、皮質下、內分泌、腎上腺、心、肝、腎、脾,共治療4個療程。治療后總有效率為84.0%,與治療前比較整體癥狀評分下降(P<0.05),免疫球蛋白IgG含量有所提高(P<0.05)。
1.4 穴位埋線
周蕾等[10]治療150例CFS患者,治療組采用穴位埋線治療,取關元、腎俞、血海、足三里、陽陵泉穴;對照組采用杞菊地黃丸治療,治療后治療組總有效率顯著優于對照組(P<0.01)。
1.5 穴位注射
聶霞[11]治療陰虛型CFS患者135例,分為穴位注射治療組和針刺對照組,治療組以生脈注射液于以下兩組穴位交替注射治療:①足三里、三陰交、尺澤、陰郄、太沖、太溪及中脘;②心俞、肺俞、肝俞、腎俞及胃俞。均取雙側,1次/天,每次1組穴位,5次為1個療程,共治療6個療程;對照組取穴同治療組但以常規針刺治療。治療后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3.30%,顯著高于對照組的83.34%。
2 灸法治療
灸法具有溫經、通脈、散寒、激發人體正氣、增強免疫力等功效,配合辨證取穴等手段可治療經脈痹阻、寒凝血滯、正虛等引起的病癥。
2.1 灸法
王玲[12]采用扶陽火艾灸法治療脾腎陽虛型CFS,于患者腰背部的督脈和膀胱經上行扶陽火艾灸法治療,3次/周,12次/療程,治療后總有效率為92%,FAI及脾腎陽虛證癥狀積分改善明顯。梁蔚莉等[13]研究背俞穴隔藥餅灸治療CFS的臨床療效,對照組予以維生素B1、谷維素、維生素B6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加用背俞穴隔藥餅灸治療,將附子、白術、生地黃、丹參按照1∶1∶1∶1的比例制作成藥餅,將藥餅放置在膀胱經第一側線上的背俞穴,由上往下,每次取雙側6個穴位,將艾柱放于藥餅上并點燃,每穴灸5壯,6次/周,共治療4周。結果觀察組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治療后FS-14及PSQI評分下降較對照組更明顯,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 溫針灸
鐘偉泉等[14]將80例CFS患者隨機分成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組于中脘、下脘、關元、氣海及雙側足三里、陰陵泉、三陰交、肺俞、心俞、脾俞、腎俞、肝俞穴處施以溫針灸;對照組于上述穴位處施以電針,10次/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結果治療組治療前后臨床癥狀積分差值大于對照組(P<0.01);治療組治療后免疫球蛋白各項指標改善情況優于對照組(P<0.05);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2.5%,顯著高于對照組的85.0%。
2.3 穴位敷貼
李歡等[15]采用穴位熱敷法治療CFS,于觀察組40例患者的關元、氣海、大椎穴處敷以加熱后的敷料(艾梗、花椒、丁香、小茴香),每天1次;治療組40例患者予以口服地黃丸治療,1丸/次,2次/日,均治療2個月。治療后觀察組總有效率為92.5%,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2.5%。
3 拔罐療法
拔罐的適用范圍廣泛,具有舒經活絡、行氣活血、緩解疲勞等功效。陳翔[16]將56例患者隨機分為走罐組和閃罐組,兩組施術部位均為背部督脈和足太陽膀胱經背部第1、2側線,走罐組以患者背部感到皮膚顏色變化或發熱時駐罐5 min后起罐;閃罐組至罐體微熱或皮膚潮紅后駐罐并于5 min后起罐,均1次/1周,共治療6次。治療后,走罐組總有效率為96.5%,閃罐組為81.8%;治療后FS-4,FAI量表評分結果顯示,走罐組優于閃罐組(P<0.05)。
4 推拿
推拿即通過推拿手法作用于人體的特定部位和穴位,可發揮舒經通絡、行氣活血、調整臟腑、提高機體抗病力等作用。
梁峰等[17]將40例CFS患者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組采用通督推拿法,手法以推法、揉法、捏脊法、擦法為主,治療部位以督脈和太陽經為主,1次/日;對照組予以黛力新治療,1片/天,兩組均治療4周。治療后,兩組患者FS-14評分較治療前均有下降(P<0.05),且治療組下降更顯著(P<0.05)。
陳飛騰[18]將72例CFS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采用通經調臟手法,推拿以彈撥法、點按法、按揉法、擦法、推法、拍打法為主,主要選取肝經及其循行路線所過部位,取穴為五臟俞和膈腧穴,隨證配穴,1次/日;對照組口服維生素B1和谷維素治療,兩組均連續治療4周。治療后治療組患者FS-14積分降低程度較對照組明顯(P<0.05);在耐力MF及肌力RMS變化程度方面,治療組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
5 聯合療法


田薇[21]將CFS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30例,治療組采用溫針灸聯合拔罐治療,于足三里雙、神門雙、氣海雙、三陰交雙穴處行溫針灸治療,1次/天,5次/周,于背部膀胱經處行閃罐治療并于脾俞穴和腎俞穴上留罐15~20 min,3次/周,治療4周;對照組口服氫化可的松片治療,常規治療30天。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3.3%,顯著高于對照組的76.7%。
6 結語
慢性疲勞綜合征從病因和臨床表現來看可歸屬于中醫學中“虛勞”“郁證”等范疇,其病機主要為先天不足、情志失調、飲食失衡、過度勞累等導致陰陽失衡、臟腑氣血失調等正虛,亦有外邪、血瘀、氣滯、痰飲等邪實,病位主要涉及肝、心、脾、腎及腦。古籍將CFS的臨床表現描述為四肢勞倦、懈惰、四肢不用、健忘、咽痛、不寐等,如《素問·示從容論》中云:“四肢懈惰,此脾精之不行也”;《東垣十書·四肢不收》中云:“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靈樞·本神》中云:“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中醫外治法中,針刺具有疏通經絡、調和陰陽、祛邪扶正等作用;艾灸具有溫經通絡、祛寒除濕、消腫散結、升陽舉陷、行氣活血、回陽救逆等作用;推拿具有疏通經絡、推行氣血、扶傷止痛、祛邪扶正、調和陰陽等作用。
綜上所述,針刺、艾灸、推拿、穴位注射、艾灸、穴位埋線、耳針等中醫外治法治療CFS是通過刺激經絡腧穴以調節臟腑功能及氣血運行,亦由于其主要直接作用于皮膚等淺表組織,激發神經體液等系統的自主協調功能發揮抗疲勞、抗應激等作用,其療效肯定,不良反應少,無毒副作用。但尚有以下不足:①對于慢性疲勞綜合征和他病所致的疲勞癥,現今尚缺乏統一的診斷標準和鑒別診斷標準;②中醫的辨證分型標準和其對應的療效評價標準不統一,論證性不強,需要制定統一的療效評價和辨證分型標準;③各醫家外治選用的穴位及治療部位多依靠經驗,隨意性比較強,沒有達成一致的治療原則,亦缺少規范的治療方法;④各項臨床研究處于初級階段,樣本量少,難以進行大規模的重復試驗,缺乏嚴格的對照設計和遠期隨訪,缺乏循證醫學的可靠依據;⑤衡量研究結果的量表選擇不統一;⑥對其發病的機制仍有較少的認識,外治法治療慢性疲勞綜合征的作用機制近年來雖有研究但不多,致使中醫外治法在臨床上的推廣應用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