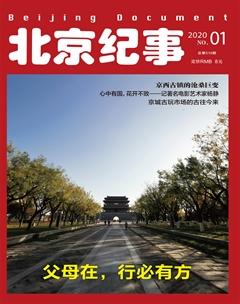面面俱到的全能型藝人
趙浩博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穩重、可靠。和大多數演員穿著隨意不同,我兩次見到趙浩博,他均身著襯衫西褲,以至于第一次向我介紹這位演員時我都愣了一下。事實上,趙浩博身兼團里演員隊副隊長的職務,我去《王致和》劇組采訪那回,他還是《王致和》的制作人。所以在介紹之前,我看到趙浩博的形象,感覺他就是一位管理者,劇組的負責人。在《王致和》彩排現場采訪男女主演的時候,可能是怕我等得太久(其實看劇組彩排很有意思),趙浩博總是等演員排練完一下場休息就幫我安排采訪,其作為制作人協調演員的執行力之高可見一斑。
我還在趙浩博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張他在書店讀書的照片。那家書店我經常光顧,所以一眼就認得是哪家。那里每天都聚集了不少書蟲,大伙兒在書店的茶飲區看書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有句話說得好:“演員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底蘊。”我相信,有趙浩博這樣踏實、肯追求的曲劇青年演員在,北京曲劇的未來一定大有可期。

聲樂生的曲劇路
2008年,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上學的趙浩博正在積極備考,打算考進中國音樂學院繼續進修聲樂。這時他的老師向他們介紹,北京市曲劇團現在來咱們學校招生,曲劇團是北京的事業單位(當時還沒轉企),畢業了包分配還能解決戶口問題,你們有興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老師說得很實在,也引起了趙浩博的好奇心。“你報這個是要去學唱戲嗎?”一個同學問趙浩博。“我也不知道,所以先去看看曲劇究竟是什么再說。”趙浩博抱著探索的心態第一次接觸北京曲劇。他和其他有興趣的同學一道,進劇場看了曲劇團的經典劇目《北京人》。令趙浩博感到驚喜的是,北京曲劇一聽就懂,不像傳統戲曲的戲詞兒那樣難以理解。而且《北京人》的表演和臺詞很像話劇,對像他那樣的年輕人充滿了吸引的魅力。
心有所動的趙浩博回來后和老師商量,老師給他的建議是,學習聲樂的人才非常之多,而且未來投入的精神和物質成本也高得多,與其走獨木橋不如另辟蹊徑,去承襲咱們傳統藝術。
老師一番客觀的建議擦亮了趙浩博清醒的眼睛。于是,他報考了中國戲曲學院北京曲劇代培班。備考時他聽曲劇音頻資料,學著唱。但老師說他唱出來老有唱歌的味兒。“北京曲劇的唱腔和發聲方法和聲樂有很大區別,這個一上來很難適應。”趙浩博介紹。另一大困難是臺詞和表演的備考,作為一個聲樂學生,這方面他接觸得不多,只能專門找老師臨陣磨槍。雖是臨陣磨槍,但趙浩博磨得認真、磨得用心。而且入學考試,老師主要看一個孩子的天賦條件怎么樣,適不適合演曲劇。這些方面趙浩博都入了考官的眼,因此他能在100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成為20多個中榜者之一。
雖說進了曲劇班,但所有學生第一節課學的并不是曲劇,而是北京岔曲兒。因為北京曲劇生發于北京岔曲兒,所以學習曲劇須追本溯源,從北京味兒更濃的岔曲兒開蒙。趙浩博之前學習聲樂的方式是不管唱什么,先看譜子。可他唱起北京岔曲兒,感覺譜子和唱腔的許多地方差之甚遠。因此時有發生唱得不對的地方,老師就告訴他你不能完全按照譜子唱。趙浩博頭上畫出一個大問號,說:“這個不按譜子唱按什么唱啊?”
老師說:“譜子是給你一個大概的方向,具體到每個細節,你得靠聽。”學唱不看譜子,靠聽。這對于從小學聲樂的趙浩博來說很不可思議,他有時聽了好幾個晚上,唱出來依然很別扭。可他觀察同班原先學京劇的同學,他們甚至不識譜子,可真的聽幾遍音頻,就能學得有模有樣。最終,趙浩博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漸漸熟悉了北京岔曲兒的發音方式,它行腔走板的規律。“就是像老師說的,只能靠多聽,‘熏長了味道自然就出來了。”
口音問題在趙浩博以往學習聲樂時并不突出。可學了曲劇后,得有臺詞、得有北京味兒,口音上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你演的是北京曲劇,講的是北京故事。說臺詞最起碼是標準普通話,在普通話的基礎上,你們再尋找北京味兒。”老師上臺詞課時給他們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趙浩博生在東北,從小說的是東北話,即便在舞臺上改說普通話,仍會冷不防夾雜上東北話的味道。因為這不像南方話改說普通話,仿佛換了一個發音系統,是從“一張白紙”學起。東北話和普通話都屬于北方語言系統,語音、語調大部分差不多,只在細微之處有差異,這反而讓人防不勝防。
“這個母音是非常難改的,你說臺詞的時候即便有強烈的意識,也會一不小心帶出母音來。你甚至都沒意識到自己說的臺詞里還有東北話的口氣。可別人一聽,卻能敏感地察覺出你臺詞里還有東北味兒。”趙浩博如是說,可筆者采訪時的直觀感受是,如果他不說自己的家鄉是哪里,我從他的口音中一點都聽不出來。想一想,東北口音往往很容易就能聽出來,可見他在學說普通話這方面下了很深的苦功。
表演——也是擋在趙浩博學藝路上的又一座大山。以前學聲樂,表演只是簡單地做一些手勢就行了。現在學曲劇,演的是人物。所以趙浩博不無感慨地說:“以前的老師告訴我們,沒有表演的表演是最好的表演。其實不是這樣的,學了曲劇以后,顧威導演告訴我們,沒有表演痕跡的表演才是最好的表演。在舞臺上,任何一個表演自然的動作,都是經過臺下苦心孤詣地設計和千錘百煉地打磨,最終呈現在舞臺之上。表演并不是生活的照搬,它永遠要高于生活。”
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雖然趙浩博心里也明白表演的奧義,也把團里藝術前輩的表演看在眼里,可真到自己表演的時候,卻怎么也做不出來。而且老師說了一遍,自己還做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不好,心里就郁積了深深的挫敗感。“這個時候你會很痛苦,每個表演者都會遇到自己表演的困惑期,但往往就是這個時期是自己漲功的重要階段。”趙浩博深有體會地說,“我在學曲劇時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演繹那些和自己反差極大的角色。假如你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卻要你在舞臺上演繹非常狂放、特別外向的角色。這不光是對你演技的挑戰,更多是來自內心的考驗。特別是當你覺得自己演得很到位了,但別人覺得你演得還沒到家,這內心的考驗就會變得更大。當然,如果你頂住壓力,突破了這個角色,將來你再駕馭其他角色時,就會明顯從容許多。”
從駕馭小角色到挑戰反差類角色
2012年,趙浩博從中國戲曲學院順利畢業后直接進了曲劇團。和大多數年輕演員一樣,趙浩博先是從龍套演起。“其實年輕演員,你跑龍套的時間越長,對你今后的表演越有幫助。因為北京曲劇沒有絕對的龍套,只有小的角色。北京曲劇的龍套不是站在后面沒有表情地打旗,充當千軍萬馬。曲劇里的龍套都會根據劇情的發展有自己的表情和形體動作,年輕演員如果能把一個個的小角色演活了,就能把底子打穩,將來演大角色才能駕馭得了。所以年輕人跑幾年龍套是大有裨益的。”趙浩博滔滔不絕地談龍套。
在跑了許多龍套之后,趙浩博演了非常多的小人物,類似于京劇中喜劇色彩很濃的小花臉。“這可能是團里的領導和老師給我的定位,回過頭來看,我發現自己演的角色有很多都帶著幽默的成分。”

《十不閑傳奇》趙浩博飾二祖爺《林則徐在北京》趙浩博飾龔自珍《龍須溝》趙浩博飾劉巡長
此后,趙浩博接觸的角色越來越多。他是《四世同堂》中血氣方剛的祁瑞全;是《方珍珠》中貪得無厭的丁副官;是《龍須溝》中熱心腸的劉巡長;是《林則徐在北京》中浩然正氣的龔自珍……除此之外,他還在《煙壺》中飾演九爺、《駱駝祥子》中飾演小順子、《茶館》中飾演老林、《黃葉紅樓》中飾演敦誠、《正紅旗下》飾演多大爺、《十不閑傳奇》中飾演二祖爺、《花落花又開》中飾演李根生,話劇《懷清臺》中飾演葛湯、《北極光》中飾演蘇榮達……在舞臺上駕馭不同角色,表演技巧區別很大。趙浩博會根據歷史背景、角色的個性、學識涵養等作多種處理,包括表演的肢體動作、速率、節奏、語氣、聲調、眼神等方方面面的變化。
接觸的角色越多,趙浩博演技上的成長越快。不過在眾多的劇目、角色中,讓他成長最多的要屬《煙壺》中的九爺。這個角色趙浩博大三時就曾有所接觸,九爺與趙浩博的性格相去甚遠,因此趙浩博一直認為九爺是他演繹之路上的一座高山。他為九爺這個角色付出了很多努力。先是像對待其他角色一樣熟讀劇本,了解人物在劇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接著去和前輩老先生溝通,和導演不斷交流去打磨這個角色。“當我第一回登臺表演九爺的時候,不能說緊張,應該是一種表演前的興奮。當我說一句臺詞或者抖一個包袱后,臺下觀眾有強烈的反應時,這種興奮又變成一種滿滿的幸福感,就覺得你的努力獲得了觀眾的肯定。”趙浩博的話語洋溢著自己對曲劇表演的熱愛。
“《煙壺》只有八九個角色,就能把整部戲撐起來,這因為每一個角色仿佛都是一種活生生的再現。除了九爺,我還演過里面的烏世寶和李貴。”趙浩博談起《煙壺》難掩喜愛之情,“《煙壺》是北京曲劇的轉折點,也是老一輩藝術家留給我們年輕演員的一份寶貴資產,可以說常演常青。像這類老戲,我們每次演都會有收獲,這種收獲可能是第二次演才能感悟出來的,也可能是演對手戲的人帶給你的。特別是跟老一輩藝術家同臺演老戲,你受到的觸動會更大,常常感慨原來人物還可以這么演。感覺老先生們不是在表演,是登上舞臺的一剎那,劇里的那些人物活了。看不到老先生任何的表演技術程式,哪怕他們咳嗽一聲,都讓人覺得這是劇中人在咳嗽。”
副隊長、制作人、演話劇,他是全能多面手
2018年,趙浩博在中國殘聯、北京殘聯以及國家話劇院聯合出品的話劇《北極光》中飾演蘇榮達。此劇旨在關注正常人的心理缺陷與殘疾人的身體缺陷等問題。讓趙浩博感觸頗深的是與國家話劇院的許多老演員的接觸。例如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丁義珍市長的扮演者許文廣老師。“許老師進組的時間較晚一些,但他進組一和我們對臺詞,那種人物的感覺馬上就能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所以跟他對戲,你會很緊張,也會很享受。他說的每一句臺詞都能讓你有所啟發,讓人感覺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2019年,趙浩博成為曲劇團年度好戲《王致和》的制作人。在此之前,趙浩博作為演員隊副隊長就負責團里演員隊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演員打交道。目前團里的演員隊有將近70人,常常三大任務同時展開——這邊彩排《王致和》,那邊還有話劇需要完成,日常的綜藝演出任務也不能少。如何調配這70位演員,讓大家擰成一股繩,發揮各自的特長,是趙浩博和演員隊隊長的主要工作。
演員隊副隊長的工作經驗也讓趙浩博做制作人時應對裕如。“制作人就是一部戲的大管家,從這出劇最開始的籌備、創作,到人員的管理、統籌,再到彩排的協調。其實對我來說,責任大于挑戰。一部戲代表了一個劇團的品質,作為制作人,我始終提醒自己要平衡各個方面的關系,從臺前到幕后,從演員到樂隊,每個人都有最佳的表現,才能讓一部劇立起來。”趙浩博采訪到最后興致勃勃地說,“2019年,不論是年初的《太平年》《林則徐在北京》還是《王致和》,我感覺北京曲劇正在一點點重燃它的魅力。因為北京曲劇的魅力,或者說特長就在于講北京的故事。它的配器、唱腔,都有深深的北京烙印。所以像我們最近推出的《王致和》,就是發生在北京的故事,這樣我們才能揚長避短,走出屬于我們自己的道路。”
(編輯·韓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