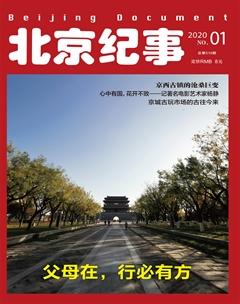不再要镚兒的镚兒廳
九兒
前兩天,阿姨說家附近有一個兒童游樂城,我和孩兒他媽想著孩子在家愛哭愛鬧,不如把蓬勃的精力發泄在兒童游樂城里。這樣孩子玩得開心,我們陪他也感覺輕松些。不過等到我們去了后,才發現所謂的兒童游樂城只能算小半個。大半個區域擺放的都是電子游戲機,沒辦法,想必電子游戲機一定是比蹦床、滑梯、人造玩沙區掙錢快得多。孩兒他媽就非常排斥這些電子游戲機,游戲機的屏幕亮光毀眼,各種游戲機的聲音轟轟隆隆混在一起,像噪音一樣。總之她一句話定性:這些都是聲光電污染。

游戲廳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的
我很理解孩兒他媽的心情,畢竟在電子游戲廳或者我們“80后”俗稱的镚兒廳最風光、最紅火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镚兒廳里是沒有小女孩兒的。有的也是零星一兩個,已經上了初中,早熟、早戀,跟著男朋友來看看的女生。所以孩兒他媽對镚兒廳沒印象、沒感覺很正常。我卻恰恰相反,每每在商場不經意走進電子游戲場所,總是能夠勾起兒時在镚兒廳里玩耍的歡樂畫面。
上世紀90年代初,也就是“80后”這一代剛上小學或初中時,電子游戲廳突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風靡。那時的家用游戲機是任天堂的紅白機,插橙黃的游戲卡玩游戲。紅白機的聲音、畫面都無法與游戲廳新出現的電子游戲機(也稱街機)相提并論。況且孩子在家玩紅白機,總有父母教誨的叨擾,但游戲廳就不一樣了,里面全是孩子,現在看來簡直是孩子們自己在開Party。
電子游戲廳一出現,理所當然受到孩子們的追捧。那會兒剛出現的游戲廳面積不算大,通常二三十平米的平房,屋里靠墻圍一圈擺著十來臺游戲機。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游戲廳的規模發展越來越大,有了兩層樓上百臺游戲機的游戲廳。這種大型游戲廳,在方圓數公里的孩子圈里,常常無孩不曉。那會兒游戲廳里的游戲機是最原始的一類,不像現在重體驗的游戲機。那會兒的游戲機是一個立著一人多高的大盒子,盒子被涂鴉得五顏六色,還畫一些與游戲相關的動漫人物。盒子上端鑲嵌著游戲機的屏幕。中端伸出一個平臺,有兩套控制鍵。每套控制鍵包括一個搖桿,6個按鈕,按鈕通常分成紅黃兩種顏色。搖桿控制游戲中人物的行動方向;按鈕控制人物的動作,像多數動作類游戲,按鈕就是輕拳、輕腿、重拳、重腿。方向鍵與鍵位的不同組合,能夠讓游戲角色發出不同的、威力更強的招數。例如搖桿搖下上之后,緊接著按拳或腿鍵,人物就能發出氣功波或掃堂腿。當然,還有更復雜的鍵位組合發出更炫酷的招式。想一想,那會兒沒有百度,沒有游戲攻略。游戲怎么玩,怎么操作發招,全靠孩子們自己摸索,然后口口相傳。所以镚兒廳里會玩的孩子總是特別引人矚目,他玩的時候,周圍有一圈孩子圍觀。這情景恐怕是如今流行的游戲主播,直播玩游戲上千人在線圍觀的最早雛形了。當時那些游戲玩得好的人是無名英雄,現在知道他們叫什么了——“高玩”“大神”——可見社會發展了,行行都能有飯吃,據說知名游戲主播、職業玩家年收入幾百上千萬元……
話休扯遠,再回過頭來說游戲機,機身的下端有個帶鎖的小門,門上還有一個投游戲幣的端口。平時孩子們玩游戲,就從這里投幣。投得多了,老板就把小門打開,把幣從游戲機里取出來接著賣。
對于孩子來說,镚兒廳的精髓全在這镚兒上,因為沒有镚兒您玩不了啊。我現在買東西,人家找我零錢,偶爾給個鋼镚兒,攥在手里,還能憶起小時候的感覺。怎么講?那會兒的游戲幣五毛錢一個,可真不便宜,所以镚兒廳里看的孩子多,玩的孩子少。我們那會兒兜里也就揣個三五塊零花錢,我通常花兩塊錢買四個镚兒。買了舍不得投,先看別人玩,镚兒揣在兜里攥得手心都出汗了,所以現在手里一攥鋼镚兒還有那種小期待的興奮感。
我們買了镚兒,先看別人玩,一是過眼癮,二是看別人在游戲里,哪掉了血,哪Game Over了,這都是前車之簽。說起來,那會兒玩的游戲都挺暴力,以現在的標準估計應該是14+或16+了。我印象中還有成人麻將,據說是脫衣麻將,那肯定得18+了,不過麻將小孩子都不感興趣,這類游戲機通常放在游戲廳犄角旮旯背人的地方,偶爾有人玩一玩,感覺都是大人。
我們玩的游戲呢?按現在的分類,大都屬于動作類電子游戲。分成兩種類型,也是動作類游戲最基礎的兩類——雙人對打型和雙人闖關型。雙人對打型游戲顧名思義,好比拳擊運動,兩個玩家控制各自的游戲角色對打,誰被打趴下誰輸,一般是三局兩勝制。只有一個人玩時就和電腦打。主要的游戲包括:“街霸”“鐵拳”“拳皇”“侍魂”等。

如今“80后”的游戲廳已經進化成VR模式了
闖關類的游戲是兩個玩家通過配合或一個玩家自己打電腦,隨著游戲角色的移動,場景不停變換,總有敵人出來阻撓你前進。每個場景到最后,有個關底,現在叫Boss——是這一關最厲害的角色,Boss血厚,還帶各種厲害的技能包,常常把玩家打得很狼狽。闖關類的游戲有“恐龍世紀”“圓桌騎士”“合金彈頭”“吞食天地”(以三國為題材)系列等。除了動作類游戲,游戲廳還有一些小飛機的射擊類游戲,大型游戲廳還有像“泡泡龍”這樣的益智類游戲。
這些游戲都很經典,有的游戲例如“街霸”“鐵拳”等,至今還在PS3、Xbox等游戲機終端更新版本。20多年下來,積累了很多的粉絲。有些游戲角色,深入人心。例如“街霸”里的春麗,我們人稱“北京小妞兒”,成龍就在自己的電影里Cos了一把。還有以三國題材設計的“吞食天地”,當年林志穎、徐若瑄、張震岳主演的電影《旋風小子》也有模仿這款游戲的橋段。可見镚兒廳的游戲對當時流行文化的影響是很大的。
在一旁看的時間長了,自己也要投镚兒玩一玩。現在回憶,我在游戲廳里的叛逆都和這镚兒有關系。沒辦法,誰讓能玩的镚兒這么少呢?首先游戲廳的游戲機有吃镚兒的情況,就是你投了镚兒,但游戲機沒反應。因此我和我的小伙伴有兩三回,打到關底的Boss,差一點點過關,卻功虧一簣。我們兜里沒有镚兒了,但還是理直氣壯地大喊一聲:“老板吃镚兒了!”老板聽了就拿一個镚兒,慢悠悠走過來。我們則表現出一副又氣憤又著急忙慌的表情。氣憤是假,著急倒是真的。因為投镚兒續命有時限,過了時限,得從第一關開始打,之前的就白打了。我們當時覺得自己表演得很像。現在想想,孩子再怎么表演大人能看不出來?可老板為什么還要送我們一個镚兒?這叫“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一個镚兒只能接一個人的關,另外一個人想玩還得花錢買镚兒。結果是,我和我的小伙伴連回家坐公交車的錢都買了镚兒,最后只能腿兒著回去。
還有一次,我無意中兜里揣了一個镚兒回了家,我就拿家里5毛錢的鋼镚兒和游戲幣放在手里比分量,感覺差不多沉。我想如果把五毛錢直接當游戲幣投了應該也能玩,但一個镚兒本身就5毛錢,這有什么意義?我又拿出一個一毛的鋼镚兒,明顯分量輕很多。當時我正在寫作業,桌上有一瓶涂改液,我很自然地用涂改液把一毛錢涂了厚厚的一層。再用手掂了掂,感覺雖然比游戲幣輕一些,但差距不大了。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待會兒寫完作業可以用自己做的一毛錢“游戲幣”試試能不能用,如果能用我就一毛錢一個镚兒玩游戲了。

如今的镚兒廳變成了親子樂園
但我當時還不到10歲,玩的時候一興奮把試驗這事給忘了。等我打完了游戲從游戲廳出門,一摸兜才發現游戲幣和那一枚我涂了涂改液的一毛錢都沒了。這說明我給用了,而且管用。但我后來也沒再涂過,大概是嫌一枚一枚地涂太麻煩,而且心底深處也覺得這么做不大光明。
其實我們還干過比這更刺激的事。有一次我們幾個孩子在一個大型游戲廳玩。這時經理拿著兜子過來回收游戲幣。他走了之后,我們發現他竟然忘了鎖游戲機底下的小門。我們中間有一個大一點的孩子,已經上了初中,他打開小門,看懂了投幣的機關,手伸到里面撥出99個镚兒來(游戲機屏幕最高顯示99個镚兒)。這下我們可是樂壞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們幾個人換著玩,誰輸誰下,竟然玩了一下午。可我們終究是小孩子,抓著一只羊可勁兒薅羊毛,等經理第二次來回收游戲幣的時候,我們還故作鎮定,他已經發現屏幕里顯示好幾十個镚兒,可游戲機里一個镚兒都沒有。他是明白自己沒鎖小門,非常生氣,可又不能直接向我們幾個孩子撒火。他就把小門鎖上后,又猛踹了幾腳。我們知道他的警告是沖著我們來的,就沒敢再把剩下的镚兒玩完,其實我們一下午也玩夠了。現在想想,那時一下午我玩的是什么游戲,已經沒了印象,但這種逾矩帶來的刺激體驗,我記憶猶新。
任何物件都有它的宿命,有壯年就有暮年。不過镚兒廳的暮年實在短暫,短到我連它消失的印象都沒有。它就像孩子玩過的舊玩具,說扔就扔了。那孩子的新玩具是什么,就是90年代末,慢慢走進千家萬戶的電腦。那會兒北京的大街小巷,陸陸續續開起了網吧。電腦不管是畫質、音效,還是游戲的多樣性,對镚兒廳的游戲機來說都是碾壓式的。而且電腦可以多人互聯游戲,還能看電影、上網聊天。所以大伙對镚兒廳的離去沒有半點戀戀不舍的意思。
但镚兒廳并沒有就此一蹶不振,沉寂多年之后,它以體驗式的方式重新回到人們的眼前,找到屬于自己的一條獨特之路。不論是在跳舞機前來一段舞蹈,或手握方向盤開一圈賽車,抑或手拿激光槍打一串僵尸,還有投籃游戲、打鼓游戲、滑雪游戲……更加真實的體驗是電腦游戲不能取代的。只可惜現在的游戲廳只需辦卡刷卡就能開始游戲,沒有了買上幾個镚兒,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覺,也沒有投镚兒緊攥著咣啷一聲后一瞬間的興奮感。這不禁讓我這個曾經在镚兒上動過心思的“80后”感慨:人的童年總是有許多無法再次復制的美好啦。
(編輯·韓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