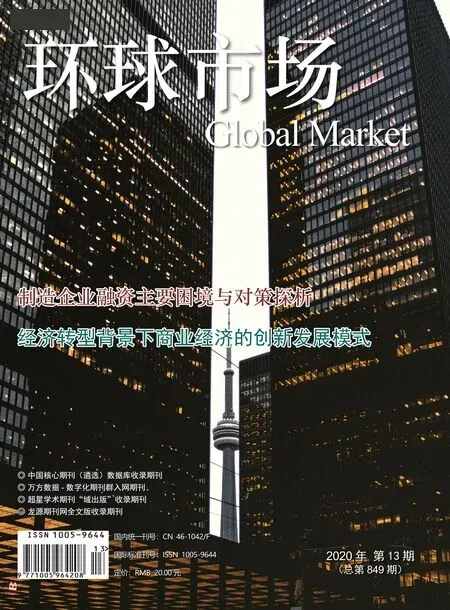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下“網絡暴力”的法律規制
魏珍 李世偉 江西師范大學
一、何為“網絡暴力”?
(一)網絡暴力現象
“教師體罰學生致吐血反轉案”中網友們對涉事教師和學生家長的激烈言論;當紅流量明星的粉絲為了“愛豆”對一切批評的聲音進行抵制,甚至惡意中傷不相關的人,諸如此類的事件中網友的行為由該如何定性?是正常行使權利,還是濫用權利滋生的“網絡暴力”?這值得我們思考。
(二)網絡暴力的概念
在理論研究中,有的學者將網絡暴力定義為:一定規模的有組織或者臨時組合的網民,在“道德、正義”等“正當性”的支撐下,利用網絡平臺向特定對象發起的群體性的、非理性的、大規模的、持續性的輿論攻擊,以造成對被攻擊對象人身、名譽、財產等權益損害的行為。有的學者則認為網絡暴力是一種網絡失范行為。筆者認為,對于網絡暴力的定義應當從主體、特征、行為、后果等方面綜合考慮,網絡暴力是不特定的網民利用網絡平臺針對特定對象所為的具有匿名性、非理性、低成本性,從而對受侵害對象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現實和廣泛影響的非理性行為。
二、網絡暴力出現的原因
(一)網絡技術的發展
截止2019 年6 月,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62.1%,互聯網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網絡技術猶如一張無邊際的網,建構起一個與現實社會平行又相互交融的空間,在這個獨立的空間里,多樣的網絡平臺供人們選擇,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傳播。網絡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可能性中蘊含著危險的因素。如網絡信息的快速傳播,加重了不實信息帶來的影響。網絡技術的發展為網絡暴力提供了客觀條件。
(二)網民群體結構的變化
CNNIC 統計報告顯示,根據學歷結構劃分網民群體,初中學歷占絕大多數為 38.1%,而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的僅占9.7%。學歷和職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人的素養和見識,網民自身的價值觀和素養是當今社會出現網絡暴力的因素之一。
(三)網絡主體的匿名性
匿名性是網絡交流的重要特征,在發揮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如同一把傷人的利劍,侵害著他人的權利。匿名使網民濫用權利變得更加容易,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空間里,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不滿、發泄情緒而無視后果,權利的極度放大讓人們忽視了義務的存在。網絡暴力就這樣在網民們濫用權利的過程中發生。
三、“網絡暴力”的影響
從2006 年的“銅須門”事件,到近期的“教師體罰學生致吐血事件”,在事實尚未調查清楚之前,網民們習慣性地以樸素的正義觀評判對錯。但行使權利應當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權利為界限。網民們激烈的語言、“人肉搜索”等行為,對當事人名譽權、人身權和隱私權造成侵害。不僅使當事人心理受到創傷,也給他們的現實生活帶來影響。但最終制裁他的應該是法律和國家公權力,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暴力。網絡暴力具有群體性,群體的觀點對于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巨大,如果任憑網絡暴力發展,不對其加以規范,網絡終將成為無序混亂的代名詞。
四、網絡暴力的法律規制
(一)專門制定“反網絡暴力法”
我國法律體系中存在許多法律專門針對某一社會現象或犯罪。一部專門針對反網絡暴力的法律的出現,既能起到法律教育的目的或者是懲罰施暴者的目的,又有益于治理網絡暴力。通過立法手段實現對網絡暴力言論的分級管理,嚴格事后追懲制度,實現依法治理的目標。
(二)發揮網絡平臺的作用
網絡平臺作為網絡服務的提供者,在網絡行為的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網絡平臺自身具有提供和傳播網絡信息的功能,也是最先接觸到網絡信息的主體。網絡平臺應當及時擔負起社會責任,對網上所有信息全方位進行監控,及時通過技術手段刪除侵犯個人隱私、危害國家、社會的帖子;推行互聯網實名制分析疑問,降低網絡暴力發生的概率。
(三)推行互聯網實名制
正如上文所說,匿名性是網絡暴力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推行互聯網實名制能夠使網絡暴力的施暴者在施暴前考慮到行為的后果,從而達到約束網民行為的目的。
(四)引導網民防備網絡暴力,增強法律意識
面對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網民要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保持理性,將網絡暴力消失在萌芽中。同時,網民還應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把握好言論自由和網絡暴力的界限,在行使權利時不損害他人合法權利。同時保持健康的心態,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不傷害他人,共同構建和諧文明的網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