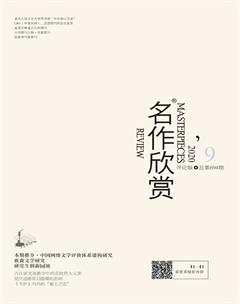法律與文學的對視
摘 要: 法律和文學的交叉地包括“法律與文學”和“文學與法律”兩個方面。“法律與文學”研究有“文學中的法律”、“作為法律的文學”“通過法律的文學”、“關于法律的文學”等四個分支,但“文學與法律”研究成果較少。本文以法律和文學兩個站點出發,相互對視,分別研究“法律與文學”和“文學與法律”,試圖對這兩個學科的交叉地全面探索。
關鍵詞:“法律與文學” “文學與法律” 跨學科
法律的傲慢和文學的偏見,導致兩個學科的研究相對封閉。直到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法學界的“法律與文學”運動掀起了這個交叉領域的研究熱潮。本文試以文學和法律兩個站點,分別從法律和文學兩個站點出發,相互對視,以“法律與文學”和“文學與法律”兩個方面為依托,對這個交叉領域進行全面的分析。
一、法律與文學的相遇
法律和文學研究相對封閉。法律是指由國家專門機關創制的,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并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的調整行為關系的規范,它是意志與規律的結合,它是階級統治和社會管理的主要手段 。a文學是以語言為手段塑造形象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藝術形式,它是人類情感的記錄。法律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具有同質性,可以成為幸福的伴侶。法律作為社會調整或控制的技術,是人類對自身社會的性質、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社會關系及其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的結晶 。b它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法律傳統和價值觀念,包涵著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公序良俗等跨時代、跨國家、跨歷史的人類永恒的文明成果。而文學作品也是人類對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等人類美好理想的另一種體現。因此,法律和文學終極目標趨同,本質相同,這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同。德國歷史學家和文學家雅可布·格林在其1816年發表的論文《論法之詩》的開篇中所說:“法與詩相互誕生于同一張溫床。詩中蘊涵有法的因素,法中也蘊涵有詩的因素。”c蘇曉宏認為:“文學與法遵從的都是美和正義的傳統,它們之間在本質上不存在勢不兩立的利害沖突,在最高意義上,二者應是友好互動,相互信任的關系。”柯蘭也認為:“法律并非文學的天敵,而是法學與文學具有某種不同尋常的同構性。這種同構性不是它們使用詞匯和思維方式的同構,而是終極關懷的同構——尋求人的具體尊嚴和人類的具體作用。”d法律和文學都體現了人們對自由、公平、正義的追求,體現了人類對真、善、美的期望。只是兩者采取的路徑和手段不同而已。法律用國家警察、監獄等國家暴力手段來約束個人行為以達到穩定社會,從而使個人權益合理地、現實地、有效地實現;而文學作品是依靠增強豐富的情感和飽滿的故事,增加作品感染力,直接表達人們對自由理想的追求。總而言之,法律與文學具有同質性,在終極目標是趨同的。
二、從法律到文學
(一)美國“法律與文學”運動 在法律與文學的交叉地成為美國學者研究者的“新大陸”。早在1920年,著名的英國法律史學家威廉.S.霍爾茲沃思發表了《作為法律史學家的狄更斯》一書,首先駛入了這塊領域,但他只是偶然的“闖入”,并非系統研究。真正意義的法律與文學研究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法律與文學”運動。197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詹姆斯·懷特出版了《法律的想象:法律與思想與表達的性質研究》一書,掀起了“法律與文學”的運動的帷幕。(法律與文學)真正成為一門顯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 。美國學者理查德.A.波斯納先后出版了《超越法律》《法律與文學——一場誤會》等經典著作。1989年,期刊《卡多佐法律與文學研究》在紐約卡多佐法學院創刊,從而把這場運動推上了高潮。21世紀,法律與文學運動已經在美國法學院站穩了腳跟。 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朱蘇力翻譯波斯納的《超越法律》,把“法律與文學”介紹到中國,隨后他也出版了專著——《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1999年,香港學者馮象出版了《木腿的正義》,隨后臺灣的張麗卿、林東茂、韓政道開展了法律與文學研究實踐。
波斯納把法律和文學分為“文學中的法律”,即法律中(in)的文學,作為(as)文學的法律,通過(through)文學的法律以及有關(of)文學的法律 四個研究領域。其中,第一個是“文學中(in)的法律”, 是指以文學文本,探究其中內涵的法律問題、法律文化、法律思想。近年來,該領域研究范圍逐漸擴大到電影、電視、大眾傳媒等現代媒體。同時,我國的學者提倡“載體”本土化,即以中國文學作品為對象,例如《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的司法文化》《法學與文學之間》。第二是,“作為(as)文學的法律”這一方向是用文學批評方法研究法律文本的修辭等。英美法系國家注重“敘述法學”,把“敘述故事”方法運用到法律研究中。中國內地法學學者注重 “解釋法學”,即借用文學中的語言分析、修辭等方法解釋法律條文的內涵和外延。第三是通過(through)文學的法律,即“運用各種文學解釋理論來啟發長期存在的、關于解釋制定法和憲法之妥善的爭論” 。換而言之,這個分支是以文學的形式來表達法學思想,類似成果有馮象的《政法筆記》、劉星的《西窗法雨》。第四個“有關(of)文學的法律”,是用法律保護文學作品,即用知識產權來維護作者權利,處理與著作權有關的法律問題。
這四個分支的發展也不同。其中“作為文學的法律”,因西方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從“法律與文學”轉向“解釋學”,這個重心的轉移使該分支背棄了其初衷。“通過文學的法律”則完全被排斥在法學主流話語之外,始終處于被遺忘的位置。“通過(through)文學的法律”則被認為是民商法的傳統內容——知識產權。在實際中被知識產權研究消解。唯一活躍的只有“法律中的文學”。就像朱蘇力的評價那樣:“美國法律與文學運動的雙股劍還沒出手,在中國只剩下的一柄是‘文學中的法律。”
三、從文學到法律
“文學與法律”是以文學為站點,運用法律知識進行文學研究。我國首先關注這方面研究的是余其宗,他提出了從文學視角審視和解釋法律理論系統的文學法律學。他提出“法律與文學”研究 的“十大領域”是以法律為參照體系的法律研究,是文學家以文學為知識儲備加入的法學研究隊伍,進行法學研究。其后繼者鄭周明,試圖建立文藝學法學。吳笛教授在《哈代新論》中用了一個章的篇幅研究苔絲失身案。
美國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 指出了文學作為一種活動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讀者等四個要素組成的。 換而言之,“文學與法律”的研究內容包括法律與文學作品、法律與作家、法律與文學世界、法律與文學作品的讀者等四個分支。
第一,法律與作品。內容與形式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對范疇,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構成了作品的全部。因此,文學研究者可以研究作品中的法律主題、人物形象、情節、環境等。例如法律主題、作品中律師、法官、罪犯、警察、證人等形象;審判、殺人、合約、追捕等涉及法律的情節;還可以從研究文學作品的法律思維出發,研究文學作品的法律思維結構和敘事方式。此外,文學作品中常會出現題目與內容不對稱的情況。可從法律的角度來進行作品類型的鑒定。例如《公平和不公平的》,從題目來看,屬于法律小說,但深究內容,則屬于成長小說。
第二,法律與作家。作家研究主要研究作家的創作思想、創作經歷、創作風格、創作靈感。作家的法律知識基礎或者法律經歷會對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狄更斯與法律的糾纏,使他成為批判法律的斗士,這影響了他的創作思想,使他的作品大都對法律進行批評。同時,文學作品對法律評價與專業法律評價存在一定的差異,而研究這些差異背后的原因,對理解作家的創作思想至關重要。
第三,法律與環境。時代環境的變革對文學也會產生重大影響,例如英國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的英國司法改革,使文學界對法律產生了持久的偏見。同時,文學作品對法律變革也產生反作用,美國法律以種族歧視為特點,而《湯姆叔叔的小屋》不僅引起了南北戰爭,也迫使美國政府修訂了法律。法律豐富了文學的創作類型。法制文學是法律事實與文學方法結合而成的,這方面包括了法制小說、法制文藝、法制故事、法制隨筆以及法制文學理論。同時隨著時代的進步,也包括了法制電影、法制電視、法制訪談等聲光電結合媒體新形式。
第四,法律與讀者。現代文學評論已將讀者研究納入其中。文學只有進入了讀者視野才算是作品,作品只有被讀者接受后,才算是有生命的作品。讀者的態度、經歷、基本常識對作品的正確理解至關重要。然而文學作品中包括了大量涉及法律的內容,這些內容專業性強、深奧晦澀,不具有法律知識的讀者很難理解。同時,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差異較大,不同歷史階段的法律差異較大,不同國家地區的法律傳統差異更大。因此,普通讀者,必然很難理解作品中的法律事件和其中的內涵。于是,從法律角度解讀作品,對于厘清誤讀,這對于正確理解作品有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法律與文學是一場巧妙的相遇,他們一個傲慢,一個懷有偏見,但如果相互了解,定能成為一對幸福的伴侶。但要注意的是“法律與文學”與“文學與法律”是法律和文學這兩個學科交叉領域研究的不同的兩個方面,是一塊硬幣的兩面。這兩方面相互補充,不可偏廢。
參考文獻:
[1] 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 蘇曉宏.法律與文學在中國的出路[J].東方法學,2011(4).
[3] 柯嵐. “法律與文學”中的局外人[J].北大法律評論,2011(2).
[4] 理查德·波斯納.法律與文學[M].李國慶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5] 理查德·卡倫伯格.毀約:哈佛法學院親歷記[M].胡正勇,林正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6] 朱蘇力,法律與文學[M].李國慶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基金項目: 本文系杭州市哲學與社會科學課題《法律與文學視野下的維多利亞時期小說研究》(M17JC15)研究成果
作 者: 薛青,文學碩士,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法律與文學。
編 輯: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