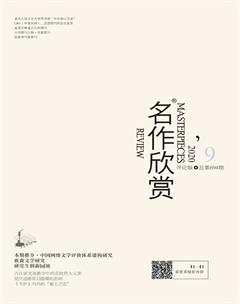《韋護》內外的“瞿王之戀”
摘 要: 丁玲的中篇小說《韋護》是以好友瞿秋白與王劍虹戀愛本事為原型的,但雖有現實人物的對應,其在創作時依然對諸多情節做了變動。丁玲或改寫,或縮寫,或保留都有其背后的原因與動力。在當時“革命加戀愛”文學創作模式的規范下,丁玲試圖從文學書寫的規范中逃脫,加入更多自己的情感與態度,保留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通過現實與小說的對讀,也從側面展現了丁玲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生活經歷與創作觀念。
關鍵詞:《韋護》 丁玲 瞿秋白 王劍虹
《韋護》是丁玲創作于1929年末的中篇小說,1930年1月至5月在《小說月報》上連載,這篇小說系以摯友瞿秋白和王劍虹為原型,小說發表后,瞿秋白于1930年末曾托胡也頻捎信給丁玲,信末署名便是“韋護”,可見也得到了瞿秋白本人的認可。不過即便其中的情節與人物十分真實,對于現實的還原度較高,我們也不能把其當傳記坐實了來看。事實上,在丁玲寫完初稿拿給胡也頻看時,二人意見曾產生分歧,胡也頻堅決要求丁玲重寫,在《我的自白》中,丁玲回憶道:“他說:太不行了,必須重寫!我們為此大吵特吵起來。結果,我又重寫一遍。”a丁玲自己也承認她是對現實事實本身做了修改后才寫進《韋護》中的,“有的朋友很不滿意,說我把《韋護》赤裸裸地印上紙面了,但我以為與本來面目大不相同;但一點影子都沒有,這也難說。”b因此,通過丁玲本人的敘述可以看出,即便《韋護》有原型,其中依然存在許多對現實改寫后的情節。
一 、從瞿秋白到韋護
小說中,作為革命者與大學教員的韋護在和麗嘉陷入甜蜜而熾熱的戀愛之后,幾乎是完全放下,甚至拋棄了自己的工作,整日沉溺于二人世界的一方天地中,甚至一有空閑時間,連小小居室的門都不愿踏出一步,以至于連曾經最喜愛的詩歌創作都丟下了,對于工作,他更是敷衍,身邊同事都對他抱有看法甚至敵意。書中對于二人間甜蜜愛情的描寫十分細膩,有多處情節展示了韋護在這段戀愛中不斷迷失自我的過程:
很快的一個星期過去了,他們兩人變成一對小鳥兒似的,他們忘記了一切,連時光也忘記了。他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棲在這小房子里……他們的眼光從沒有離開過,而嘴便更少有停止了。c
“韋護,你還作詩嗎?”
“不做了,我的生活已經全盤是詩了,還需要很笨的去做嗎?而且我沒有心去寫了,心都在你的身上。” d
從這些描寫中,丁玲為讀者展現了一對完全沉浸在愛情中的戀人形象,結合后的二人如膠似漆,一刻也不愿分開,比起精神上的交流與陪伴,二人的感情在丁玲的筆下更帶有些情欲的味道。在戀愛中,韋護拋棄愛好,丟下工作,失去自我,但并不以為意,他的心里全然只有麗嘉一人。讀者不禁要問:這樣的韋護真的是一個革命者形象嗎。如果單獨摘出這些描寫來看,相信讀者只會聯想到: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些詞匯,絕不會將韋護與革命隊伍的戰士聯系到一起。然而現實中的瞿秋白真的如此嗎?通過閱讀丁玲回憶瞿秋白的散文《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筆者認為,現實中的瞿秋白并沒有如書中的韋護那樣夸張:
(秋白)開學以后,也常眷戀著家……他每天寫詩,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給劍虹的情詩……劍虹也天天寫詩,一本又一本。他們還一起讀詩,中國歷代的各家詩詞,都愛不釋手。
秋白在學校的工作不少,后來又加上翻譯工作……我見他安排得很好……他這時顯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來仍然興致很好,同劍虹談詩、寫詩。有時為了趕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點上支煙,劍虹陪著他。他一夜能翻譯一萬字,我看過他寫的稿紙,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氣氣的字,幾乎連一個字也沒有改動。e
可以看出,丁玲回憶中的瞿秋白與小說中塑造的韋護有不小差距,一個將愛情與工作協調安排得井井有條,并從愛情中獲得積極向上的動力;一個則陷入愛情與工作的矛盾中,任何一邊都無法顧及周全。丁玲在將瞿秋白作為原型書寫時,也夸大了他身上的矛盾。當沉溺于戀愛中的韋護幡然醒悟,這才發覺已離曾經的自己十分遙遠,而此時,韋護并沒有采取任何折中調和的方法,嘗試去平衡麗嘉與工作的矛盾,而是選擇了遠去廣東,將痛苦狠心地全丟給麗嘉。丁玲筆下呈現的韋護是一個對待愛情與生活頗為幼稚、遇到問題只想逃避、心智不成熟且有些自私的成年人形象。事實上,比起小說中愛情的戛然而止,瞿秋白曾為這段愛情的平衡與挽回做過自己的努力。王劍虹于1924年1月23日曾寫給瞿秋白一封信:
你問我“容許你‘社會的生命和‘戀愛的生命相‘調和不?”我想了又想,歸于“茫然”,不知怎樣答你!“社會的生命”,“戀愛的生命”,“調和”,“不”,——不,我實在不會答復你。我還不懂什么是……你要回上海便回上海,你不能回上海便不回上海……你且莫問我什么“調和”……我不懂……那社會的生命和戀愛的生命調和便怎樣?不調和又怎樣?……我看著你的影兒好笑!我對你講:你原意怎樣,要怎樣才覺得心里好過,那便是我容許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謂我“命令”你的。這個答復滿意嗎?f
從這封王劍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對于二人的感情是有顧慮的,并且希望以折中調和的方式來讓感情順利地維持下去,以修補感情與革命的矛盾。而在小說中,丁玲筆下的韋護對于同麗嘉關系中的不和諧因素一直避而不談,試圖以表面上更加濃烈而熾熱的愛來解決矛盾,當麗嘉善意提醒韋護已將工作丟下太長時間時,韋護也并未采取委婉的方式,想辦法耐心地去解決工作的問題,而是以急轉直下的姿態去逃避。因而才會給讀者一種革命強制介入愛情中書寫的突兀感,認為小說中丁玲對于愛情描寫的篇幅與細膩程度遠遠勝于革命,革命反而成了空洞乏味且缺少說服力的事物,最后結局的邏輯缺乏支撐,陷入了模式化的僵局。g
通過上述兩則現實與小說的對比可見丁玲在塑造韋護這個形象時,對于現實的瞿秋白是有變動的。那么丁玲為什么要刪掉與改寫其中的部分內容,將其中的邏輯略去,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丁玲知曉“瞿王之戀”中早有不和諧因素,但出于對摯友劍虹的維護,因而略去瞿秋白的平衡與調和,使讀者將感情失敗的原因重點關注在韋護方面。張志忠曾提供一條線索,認為早在1928年發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瞿秋白與王劍虹戀愛的不和諧就已初露端倪。丁玲在該小說中對瞿秋白進行了間接指責:“唉!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后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為什么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經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遮飾不住的虛情……”h作者在小說中的描寫使人不自覺地進行遐想與猜測,聯系丁玲于1931年5月在《我的自白》中講到好友瞿秋白時轉引了后者的自述:
他曾說,他愛她并不如他誠懇的那樣,他只以為那女人十分的愛他,而他故意寫詩,特意寫的那樣纏綿。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愛她。每日與朋友都是熱烈地討論一切問題,回家時,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關于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他很希望得到一個心目中所要來的一個愛人。他曾老老實實地對我這樣說過。我很希望我能執筆把它完全筆之于書。i
其中“故意”“特意”二詞值得重點關注,丁玲對“瞿王之戀”中的不和諧是知情的,在瞿秋白與王劍虹的戀愛中,兩人的感情投入并不對等。在瞿秋白后來察覺到自己無法平衡愛情與工作時,仍然采取了隱瞞甚至欺騙的做法,并且為了敷衍王劍虹,故意寫一些情感纏綿而并不以為然的情詩,使劍虹仍沉浸在二人世界中并對感情抱有極大信心。作為劍虹的摯友,丁玲對于瞿秋白的這種做法顯然肯定是有怨的。
因而在韋護身上隱去瞿秋白主動調和與王劍虹的戀愛,筆者認為首先是因為丁玲認為將調和的內容寫在書中實際已無必要,她知道瞿秋白曾嘗試的平衡并非真心出于對王劍虹不可分離的愛,瞿秋白真正想要的是與后來既是愛人也是黨內同志的楊之華相戀愛那樣的“融合”——瞿秋白于1929年3月15日曾致信楊之華,信中寫道:“好愛愛,親愛愛,我倆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倆的工作也要融合在一起。” j可見調和不過是“瞿秋白對王劍虹戀情中的虛與委蛇”k,并無誠心想兼顧王劍虹與革命工作的想法。當然只根據丁玲的一家之言,我們無法確證與指責瞿秋白的虛偽與薄情,筆者在這里想討論的只是丁玲在選擇材料進入文本時的考量。其次,是出于丁玲對王劍虹——麗嘉形象的保護,韋護在面對麗嘉做出艱難的選擇之前,其實并沒有實際投入革命的工作,他只是在心里不斷放大麗嘉與工作間的矛盾,因而最后的出走也帶有強烈的逃避色彩,將瞿秋白的主動調和隱去,使讀者在理解這段戀愛失敗的原因時重點放在韋護心中的內在矛盾,而非麗嘉一方。
第二,丁玲本身在創作小說時就并未想把韋護寫成革命戰士,因而在展現韋護的心路歷程時,并非從英雄的維度對其革命思想進行刻畫,而是更多展現了韋護作為“人”的個體其內在的心靈斗爭及懦弱的一面。
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文壇上掀起了“革命加戀愛”模式題材小說的創作,從五四而來的追求人的個性解放逐漸為社會解放的需求所替代,個人的個性主義啟蒙已不再適應主流意識形態需求。正如茅盾所言:“那時中國文壇上要求著比《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深刻更有社會意義的創作。中國的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正在勃發。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長久站在這空氣之外……丁玲女士開始以流行的‘革命與戀愛的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就是那《韋護》。”l但事實上,革命并不在丁玲最初的創作意圖中,丁玲在《我的創作生活》中曾說:“好些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來作為普羅文學批評,我真覺得冤枉。因為我沒有想把韋護寫成英雄,也沒有想寫革命,只想寫出在五卅前的幾個人物……到《小說月報》登載,自己重讀的時候,才很厲害地苦惱著,因為自己發現這只是不滿足于寫作‘一個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戀愛與革命沖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3如果按照尋常革命加戀愛題材小說的模式,丁玲應當創造一個堅定的韋護,對革命抱有著絕不動搖的意志,任何誘惑都阻擋不了韋護獻身事業的熱情,在全書筆墨的分配上也應當更側重于革命,但正相反,丁玲并沒有這樣進行創作,她保留甚至夸大了韋護作為一個尋常人的情感,將其沉醉于戀愛的狀態以及后來的矛盾暴露得十分完全。
從南京到上海,瞿秋白對丁玲的思想有著很大影響,二人相識于1923年8月,當丁玲還沉溺于個人主義的生活時,是瞿秋白引其走上了革命道路,因而丁玲對瞿秋白也有著同情心的理解。“我想,一個人總會有所偏,也總會有所失。在我們這樣變化急劇的時代里,個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 4,因而強硬地將瞿秋白改寫為一個革命志向堅定的戰士違背了丁玲珍愛作為個體的自我堅持的信念。其原本的意圖是在紀念性的創作中發覺瞿秋白的個性矛盾,用錢理群先生的話說,是想要“從個人感情生活的角度反映個人在走向社會過程中的矛盾與抉擇”! 5,而非深究革命與戀愛的高低關系。寫出其間矛盾,并非因為丁玲否認瞿秋白的革命精神,相反,從各個時期丁玲記敘瞿秋白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始終都對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比起丁玲后來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所塑造的更標準的革命者形象若泉與望微,韋護顯然并不符合當時文學創作的規范,但一個革命者首先是一個人,有著自然的需要,其次才是一個革命者。《韋護》并非丁玲響應“革命與戀愛”流行模式的創作,她想要寫的是革命在發生轉向時一些新的事與新的人以及這個轉型過程給個體帶來的影響,丁玲追求的是對個體生命的展示,而非弘揚革命至上的觀念。所以在對韋護形象的塑造上,便保留了這些后來革命文學往往不會寫的內容。
二 、從王劍虹到麗嘉
(一)對麗嘉性格的塑造 根據丁玲回憶,瞿、王二人在相處交往的過程中雖然對彼此暗生情愫,但卻始終沒有什么明確而主動的表示,只得都在暗戀的相互猜測中一邊甜蜜一邊痛苦著。“施存統問我:‘你不覺得秋白有些變化嗎?我搖搖頭。他又說:‘我問過他,他說他確實墮入戀愛里邊了。問他愛誰,他怎么也不說,只說你猜猜。”! 6丁玲在施存統那里得知瞿秋白陷入了戀愛中,回去將此事告訴了王劍虹,但王劍虹的反應卻超乎尋常的冷淡,甚至說過幾天要回四川去,丁玲不解地詢問王劍虹,而“她只苦苦一笑:‘一個人的思想總會有變化的,請你原諒我。她甩開我就走了。”! 7丁玲感到十分不解,直到后來在王劍虹墊被下發現了她寫給瞿秋白的情詩,這才知曉其中的秘密。丁玲再三思考后,還是決定把劍虹的心意告訴秋白,于是去了瞿秋白的住處,將王劍虹的詩稿慎重地交給了他,并表示了自己對于二人感情真摯的祝福,這才解開了瞿王二人的心結,順理成章地結合在了一起。可以說,丁玲算是二人感情的媒人,按照二人的性格,如果沒有丁玲的促成,二人間的互相暗戀與折磨需要很久才能被捅破。在丁玲的記敘中,對于王劍虹的性格有如下的表述:
她是一個深刻的人,她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她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在心里,窒死她,她不會顯露出來讓人議論或訕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氣了,我只為她難受。我把這詩揣在懷里,完全為著想幫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間里踱著。! 8
可以看出,王劍虹雖然內心十分渴望真摯的愛情,但在表面上依然以一副冷若冰霜的態度來應對,這與她的原生家庭有一定關系。王劍虹從小就失去了母親,因而善于隱藏自己的感情,不會輕易將不安與悲傷示人。讀者在丁玲回憶中看到的劍虹是一個自尊心很強但同時自信不足又有些怯懦、習慣掩飾情緒的人。對于瞿秋白的朦朧感情,即使是和自己情同親人的丁玲,劍虹也是諱莫如深的。但在小說《韋護》中,丁玲一改王劍虹的這一性格,麗嘉活得張揚,愛得肆意,充滿著原始的感染力和生命的活力。
麗嘉出場滿帶著自信,與韋護的第一次見面便帶著鋒芒,“她坐在桌子對面,緊緊的瞅著韋護,兩個圓圓的大眼,大張著,發著光,顯得逼人似的。”! 9這里的麗嘉完全洋溢著青春的力量,有著獨屬于年輕女性的活力,那雙“嫵媚,又微微逼人的眼睛”滿寫著追求個性與崇尚自由。在與好友珊珊閑聊中,麗嘉并不掩飾自己對于韋護的關注與好感:“‘你說韋護如何?珊珊想不出應怎樣答應。這是第一次,她不愿將韋護太夸獎了,在麗嘉面前。她只說:‘這人很聰明。‘是的,我還沒有遇見一個人能如他這樣的人。珊珊,你說呢?”@ 0在與韋護第一次見面后,麗嘉和珊珊聊天時便將話題引到了他身上,十分坦蕩而直接地與好友交流自己的感受。而在丁玲的回憶中,王劍虹對瞿秋白的好感是隱藏得很深的,從不與自己交談過多,即便因誤會以為瞿秋白愛上了別人,也仍然在極度掩飾自己的失落。而書中,在愛情來臨時,麗嘉雖然也帶有獨屬暗戀與曖昧的迷茫,但感受到了韋護對自己可能有的愛意,她還是勇敢而積極地主動迎了上去:
可是麗嘉卻隨著他走去,他快走,她便跳著跑著;他一慢,她就悄聲的咕咕的笑起來了。韋護不懂她意思,以為她特意跑來逗他玩,他忍不住掉頭望了她一下。只見她靜靜的臉上布著一層和善的微笑,沒有一點淺薄的倨傲和輕率的嘲諷,只是一派天真而且溫柔。……“我是來找你玩的。這幾天我太寂寞了,我有許多說不出苦惱,只希望你來談談,你卻不來。今天我跑到這里等你,足足站了半個多鐘頭;你又不理我,借口說有事,我很失望;但我跟著你跑來了。我相信你不至真的就不再同我說一句話了。韋護,我們一向都很好的,為什么對我這么冷淡?”她躥到他身旁,一邊走,一邊說,又一邊不住的拿眼睛來觀察他……她稍稍跑到前面半步,反轉臉來望著他說:“韋護,我只相信你!”@ 1
丁玲在書中讓麗嘉做了愛情中主動的一方,面對著對自己有些冷淡的韋護,不但沒有逃避,反而積極用熾熱的愛去融化韋護心中的堅冰,使韋護之前堅定下的決心不值一提。筆者認為,丁玲在此處的改寫沿襲了五四以來追求個性解放、崇尚自由戀愛的觀念。面對愛情坦然而主動的麗嘉會使讀者聯想到丁玲早期作品中莎菲的氣質,麗嘉所體現的生命力帶有著原始感染力的號召,在她身邊的人也因此從她身上獲得了生命的活力,從而聚集在她周圍。而正是麗嘉明朗活潑的外貌與朝陽般的青春吸引了韋護,正如韋護所說:“這熱情的,有魔力的女人,只用一只眼便將他已死去的那部分又喊醒了,并發展得可怕。”@ 2對愛情的自由追求正是五四時代人們用巨大力量才爭取的,而這也是丁玲所珍視與不愿放棄的,這種思想由莎菲的身上沿襲到了麗嘉。雖然在“革命加戀愛”模式文學創作的背景下,丁玲在這一時期的創作已與莎菲時期不同,但對于“莎菲之氣”,丁玲在創作中仍有不自覺的堅持。可以說,丁玲對麗嘉形象的創造,是以王劍虹為原型,但同時又帶有莎菲的痕跡。
不過,麗嘉對于愛情的理解雖仍然帶有莎菲式沖動的影子,但卻又不同于后者。“只是太崇拜了自由,又厭惡男性的自私和淺薄,所以他們處處就帶了輕視”@ 3,麗嘉經常去戲謔嘲笑如柯君那樣平庸而又自作多情的男生,而革命者韋護的出現讓麗嘉眼前一亮,他不卑不亢,從容自信,穩重得體,對于生活、藝術和革命都有著獨特的見解,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革命者”。可見,麗嘉對于韋護的愛是有選擇的,所愛之人的形象也不同于《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葦弟與凌吉士,而是在靈魂契合下的有欲望的戀愛。
(二)對劍虹結局的改寫 在王劍虹與瞿秋白墮入甜蜜的戀愛不久,丁玲就離開二人北上,雖然因為孤獨對劍虹有些許的“埋怨”,但更多的仍是對二人感情順利的祝福。可是,不幸總是突如其來地打破寧靜。“一天,我收到劍虹的來信,說她病了。這不出我的意料,因為她早就說她有時感到不適,她自己并不重視,也沒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 4半個月后,丁玲收到王劍虹堂妹從上海的來電:“虹姊病危,盼速來滬!”等丁玲匆匆回到上海,卻連劍虹的最后一面也沒有見到。丁玲和王劍虹,情同親人的摯友,就這樣陰陽兩隔。而在小說《韋護》中,丁玲隱去了王劍虹去世的結局,一改物是人非的凄涼氛圍,讓麗嘉從強烈但也短暫的悲傷中很快地重新振作了起來,和珊珊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可是這時天已在發亮了。市聲轟起,她仿佛明晰的看見那海中遠去的船,而韋護正以蒼白的臉色,向著海的這方。于是她又哭起來。她遞過一雙手去給抱著她的珊珊,無力的說:“唉,什么愛情!一切都過去了!好,我現在一切都聽憑你。我們好好做點事業出來吧,只是我要慢慢的來撐持呵!唉!我這顆迷亂的心!” @ 5
丁玲在回憶散文《韋護》中談到如何結局時說:“我要寫劍虹,寫劍虹對他的摯愛。但怎樣結局呢?真的事實是無法寫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結局時,我寫她振作起來,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戰斗下去。因為她沒有失戀,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楊之華同志戀愛的,這是無可非議的。”@ 6經過丁玲改寫后,麗嘉的振作雖然來得及時,但在讀者看來卻缺少必要的邏輯,一個陷入戀愛至深的女人為何可以仿佛脫胎換骨般如此快速地從陰影之中走出來,這或許是小說很大的瑕疵,但本文所重點關注的是丁玲為何寧愿舍棄其中的邏輯,也要對麗嘉的結局進行改寫,筆者認為有兩層原因:
第一是作者“不忍”去寫。丁玲對于瞿、王二人的感情經歷是有著深刻體悟的,在這段戀情伊始階段,丁玲滿懷希望地祝福二人:“你們將是一對最好的愛人,我愿意你們幸福。”@ 7后來,當丁玲看著劍虹在愛情旋渦中越陷越深,“完全只是秋白的愛人”時,她的內心是惶恐而不安的,但作為局外人,除了擔心卻也無法插手。在丁玲的回憶中,劍虹本是“一個比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學”@ 8,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后,她也成了參與學生會工作的積極分子,以尖銳而辟透的口才激起同學們的熱情。這像烈火與利劍的尖兵在遇到瞿秋白之后反而沉醉在個人世界的戀愛中,甚至失去了生命。其實,麗嘉對于韋護的事業是堅定支持的,在麗嘉的心里,是希望自己與工作在韋護的心中共存的,不必非要做出選擇,當韋護最終丟下麗嘉,丁玲讓麗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實際也是換了另一種方式讓韋護依然陪伴在麗嘉的身邊——戀人雖然離去了,但留下的革命種子卻在麗嘉的心里生根發芽。丁玲知道劍虹對秋白的深愛,對于有著親人般感情的劍虹,丁玲不忍寫真實的結局,既然劍虹的生命已不會再回來,不如將劍虹無法再完整的青春在小說中得以呈現,讓她恢復當年的青春與張揚,從而將這段愛情對其的傷害降到最低。所以出于“不忍之心”,丁玲在結尾處做了處理與改寫。
第二,包含了丁玲對于女性應走之路的看法。在《我的自白》中,丁玲說道:“那時,我每天沉思默想:假如我是書中的女人時,應怎樣對付?”@ 9面對愛人的離去,麗嘉選擇了與珊珊彼此扶持,多少流露出了作者認為女性應自強自立,不應當依附于男性的觀念。對劍虹結局的改寫也包含了丁玲作品轉型的軌跡:從莎菲到麗嘉,丁玲不僅看到了“五四”女性個性解放的亢奮與失落,也用麗嘉的選擇向讀者展示了社會革命轉型時期女性走向成熟的內心世界。時代已不再容許“莎菲們”還沉溺于追求戀愛的個人世界中,階級解放與社會革命成了主旋律。于是“莎菲們”變成了走向革命的“麗嘉們”。在丁玲筆下,女性的世界應當是廣闊的,她珍愛作為女性自我的意識,并將其放到時代的革命語境中進行思考,這也是五四之聲的延續,展現了丁玲對知識女性尋求自我出路的期許。表面上看,愛情與革命不可兼得,但其實正是愛情賦予了革命深入人心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愛情與革命通過麗嘉的結局呈現出了巧妙的對話。
實際上,麗嘉走上革命之路的結局也投射了丁玲與胡也頻戀情的影子。1929年和1930年,胡也頻分別創作了小說《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們前面》,皆是以革命加戀愛的模式,分別描寫了身為政治要人的少婦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女主人公,受到戀人的啟蒙加入到革命的實踐中。當時正在戀愛中的丁玲和胡也頻就馬克思主義以及《韋護》寫作的問題進行過許多交流,胡也頻對丁玲寫作此書的鼓勵和影響是很大的。左聯成立后,胡也頻“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 0。隨著胡也頻的迅速左傾,丁玲也深受其影響——于1930年5月參加了左聯。愛人遠走之后,決心收斂個性,好好做出事業的麗嘉恰恰對丁玲日后的道路做了一次隱喻和預言。
可見,麗嘉雖然以王劍虹為原型,但同時也是丁玲筆下的人物,也是作者進行自我申張、自我投射的窗口,與丁玲本人的人生經歷有著緊密的聯系。丁玲在《韋護》中對于“革命加戀愛”模式有所背離,但同時亦有更進一步的突破:傳統“革命加戀愛”模式中男性拋棄了女性走上了革命之路,而丁玲將被男性拋棄后女性的出路也寫了出來。丁玲比起莎菲時期對于愛情有了更辯證的思索,在書中也表達了她對愛情與革命的雙重訴求。《韋護》之后,丁玲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作為麗嘉的某種呼應補充塑造了更加主動投入革命陣營、有追求有覺悟的美琳,這代表丁玲在麗嘉之后,進一步探索女性在社會變革時期,在時代革命浪潮下的地位與處境,面對個人情愛與集體命運應當何去何從的思考。而丁玲在《韋護》中對劍虹結局的改寫,一方面營造了具有時代特色的革命敘事氛圍,一方面也給出了自己對于這一問題初步但也鮮明的答案。
三、結語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文學創作方向轉換的年代,“不僅人的思考中心發生轉移,思維方式也發生相應變化:對人的個人價值、人生意義的思考轉向對社會性質、出路、發展趨勢的探求”# 1 。 文學呈現出的內容以及傳遞的思想也因此逐漸從“五四”之風變為另一種形態——戀愛不再等同于革命,革命必須放棄戀愛,即便“寫戀愛時也是從禮教與戀愛的沖突到革命與戀愛的沖突了”# 2。作者身處時代旋渦中,不可能脫離其規范與影響,身上自然也帶著這種轉變的痕跡,從“莎菲”而來的丁玲,其創作也因與時代聯系的日益緊密而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韋護》中,即便“革命加戀愛”模式非為作者創作的初衷,小說里對革命事業的描寫也缺乏一定的邏輯,但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可以看到丁玲由個體女性經驗的書寫轉向了革命敘事。
不過在《韋護》中,丁玲對于創作仍有著自我的堅持,在規范下嘗試“戴著鐐銬起舞”。她沒有“照相式地”反映瞿王二人的生活及感情經歷,也沒有如當時革命文學規范所要求的,完全套進“革命加戀愛”的模式中。對于曾經的人和事,丁玲有所突出,有所回避;有的地方濃墨重彩,有的地方淡而化之。對于瞿秋白,她沒有如革命文學規范的那樣,寫一個堅定不移的革命斗士,而是展現了其為“人”的獨特生命體驗;對于麗嘉,她改寫了劍虹的性格與去世的結局,寫出了女性也應有自己獨立的一片天空;對韋護與麗嘉的塑造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作者對革命與愛情關系的困惑糾結與冷靜思考,丁玲以改寫的方式在小說中討論了個體的權利、自我的完滿在時代與社會的要求下其位置如何的問題。在人物塑造上,丁玲試圖從當時文學書寫的規范中逃脫,加入更多自己的情感與態度,也保留了歷史的豐富性與真實性。
對瞿王二人戀愛的書寫,既是如丁玲本人所說,出于對他們的懷念,其實也是丁玲自我說明與自我伸張的需要,特別是其中被改動的部分。文學是社會話語與個人話語的實踐,任何作家的寫作都是向讀者展示自己人生觀、價值體系與創作選擇的過程,而通過了解丁玲如何改寫,探究背后內在的原因與動力,也可以觀照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壇創作的風向以及丁玲的心路歷程及思想變化,更加豐富了《韋護》的可解讀性,這便是筆者本文的目的及意義所在。
abi@ 9丁玲:《我的自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頁,第300頁,第299頁,第299頁。
cd! 9 @ 0 @ 1 @ 2 @ 3 @ 5丁玲:《韋護》,《丁玲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頁,第109頁,第43頁,第47頁,第88頁,第89頁,第64頁,第123頁。
enpq! 8 @ 4 @ 6 @ 7 @ 8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頁,第103頁,第88頁,第89頁,第90頁,第96頁,第102頁,第91頁,第82頁。
f 王劍虹:《王劍虹致瞿秋白(1924.1.23)》,轉引李曉云:《瞿秋白書信一束》,載于《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2期,第8頁。
g 參見任雨菲:《〈韋護〉——披著革命外衣的愛情故事》,載于《哲學文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81頁;參見常彬:《虛寫革命,實寫愛情——左聯初期丁玲對“革命加戀愛”模式的不自覺背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1期,第181頁。
h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
j 瞿秋白:《致楊之華(1929.3.15)》,轉引自李曉云:《瞿秋白書信一束》,載于《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2期,第6頁。
k 張志忠:《強化史料意識,穿越史料迷宮——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的幾點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2期,第159頁。
l 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選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頁。
m 丁玲:《我的創作生活》,《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頁。
o# 1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頁,第208頁。
# 0 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文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頁。
# 2 茅盾:《關于“差不多”》,《茅盾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頁。
作 者: 李佳銘,武漢大學文學院2018級在讀碩士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